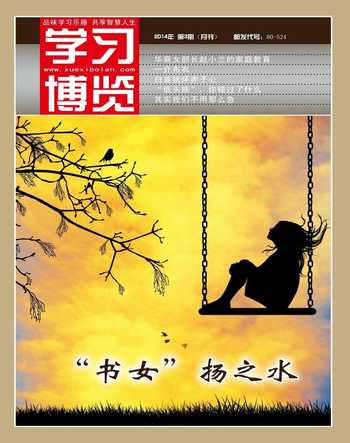观点
中国的年轻一代有胆量关心政治吗?
亚历克·阿什
在中国,二十几岁的这一群体被共同称为80后、90后。表面上看,这些年轻人对政治普遍冷漠,就连国家领导人换届选举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我们无关”。这种冷漠的背后有四个理由:
第一,政治无聊。媒体总是单调乏味地报道政治的结果,而非其过程。每个学龄儿童都要接受大量的思想政治必修课教育,枯燥乏味的课程内容让学生一辈子都不想碰政治。
第二,政治很危险。在一个由专制权力来决定是非对错的体系里,人会自然发展出一种内在的晴雨表,以告诉自己什么可说可做,什么不能说不能做。当然,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这一代的父母经历过政治风雨,他们会设法教导孩子——最好远离政治。
第三,政治没有优先性。有太多的竞争——学校,工作和配偶。有太多的经济压力——买房,买车,赡养父母。还有太多的分心之事——性爱,娱乐,毒品,以及魔兽世界。
最后,政治无望。既然知道自己无可奈何,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你不是无意于此,也不是没有胆量——你只是正视现实罢了。
但是个体却与政治息息相关。年轻人的权利意识更强,期望更高,承担的风险也更少了,因此他们有更大地勇气去伸张。
(亚历克·阿什,自由作家,居住北京,《洛杉矶时报书评》记者。译言网)
社会的“心态紧张”消磨中国的改革能力
郭于华
80年代改革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相伴。那时候有比较开阔的胸襟,开放的心态,开明的思想,使社会活力充分释放出来。一次改革,实际上要释放社会的活力,带动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改变,带来一种生机,一种发展。但是这次改革大家感受不到这些,神经比较紧绷。
80年代改革开放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各个阶层普遍都有奔头,觉得只要努力,只要付出了,就有相应的收获,可能会改变处境,改善生活,提升社会地位。
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经济结构变了,而且走得很快,但是政治结构跟不上,已经有点尾大不掉了。
重建社会或许是唯一出路。社会建设至少应包括或可始于以下基本面向:首先需要制约权力,法律至上,真正落实依法治国,权力不能比法律大。
建设社会,首先是把社会领域内的事办好,如大力发展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改善社会管理和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等。作为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主体,社会建设即培育一个独立、自主、自治、自律的主体性社会。另外政府要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信任,信任了才有信心,不至于有绝望、无安全感、猜谜等心态。完善利益表达,承认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公民需要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常规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必不可少。一个健全的体制应该容纳各种合法的表达方式,包括信访、上访和通过各类媒体的意见、质疑和批评的发表,也包括集会、游行、请愿、对话等法律框架内的抗争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地严防死守、草木皆兵,压制社会诉求。
(《南风窗》)
校长脱“官帽”为何难推行?
线教平
苏州推行校长职级制,成为教育圈一大热门话题。此前已有上海、广东中山、山东潍坊、安徽马鞍山等多地先后为中小学校长摘了“官帽”。然而该项制度并未在全国推行。
校长职级制落实往往涉及三个问题:门槛,评价,评价后的职级待遇。实现真正的去行政化,评价的主体要十分清晰——到底谁说了算?校长是为公共教育服务的公职人员,其选拔或考核的主动权理应交给学生、家长与公众。但目前,校长的选拔、培养、使用、评价等环节,仍牢牢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中。
理顺政校关系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放权;二是监管,建立科学、高效、全面的评价体系。新加坡实施校长评价由校长的直属上司“校群领导”负责,以“360度”评估法中的自我评价为核心,评价者是与校长亲密接触的人员,如上司、同行、学生及其家长、社区负责人、职员、教师(中层干部)等;而美国校长评价由县教育行政长官组织教育中介或行业协会进行,如权威的校长评价机构全美校长联合会。
陶行知先生在《整个的校长》一文中谈到:“国家把整个的学校交给你,要你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校长职级制”并非以等级看其优劣,根本上还是以此力量鞭策、鼓励校长更好地治校和前行,倘若“四级六等”级别异化为新的行政职级的追逐,很可能背离制度改革的初衷。
(人民网教育频道)
污染与治理:发达国家前车之鉴
梅雪芹
环境污染发生质的变化并演变成一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始于18世纪末兴起的工业革命。首先是英国,而后是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及日本,伴随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出现了烟雾腾腾的城镇,河流等水体也严重受害。此后,随着汽车工业和石油与有机化工的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消耗大量资源和原料,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废弃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气之中,最终造成环境污染的大爆发,环境污染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成为西方国家重大社会问题。
西方国家在环境污染发生初期,采取过一些限制性措施,治理污染源,减少排污量,给工厂企业补助资金,建立净化设施,征收排污费或者“谁污染,谁治理”,并颁布了一些环境保护法规。但是,仅这些被動措施未能阻止环境污染蔓延的势头。
污染公害事件对于经济和人身健康的影响,使公众从痛苦中觉醒。在学者们和广大公众的强烈要求下,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力图从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西方国家相继成立环境保护专门机构,开始了对环境的认真治理,工作重点是制定经济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长期政策。这样,到8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
1992年,183个国家的首脑、各界人士和环境工作者聚集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这是人类环境价值观由不科学到科学的转变。
(《社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