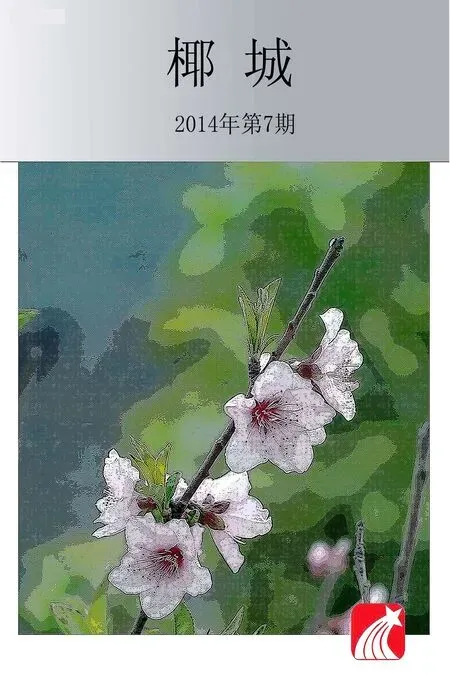很想倾诉
■萧烟
很想倾诉
■萧烟

小敏,真不认识非叔了?瞧你这一脸茫然。
人的成长,也许真就是一种悲哀。那年非叔临走,你流着长鼻涕直追着我哭哦、闹哦,你妈无法把泥在地上的你拉直来。非叔当时差不多咬破了嘴唇,就为不使自已回头再看上一眼。非叔走了,一晃就是五年,算来你也刚好满十岁了吧。可小敏你咋了,难道非叔真就激不起你的星点记忆,看你那懵愣两眼吧。
那晚,你黑心肝的老爸又揍你妈了,你哭嚷着过来叫非叔,非叔冲了上去也连带被你爸扇了两巴掌。那次非叔真豁出去了,羸瘦的身子拼命护住你妈,像护着一只绵羊,两手叉腰。后来,你爸泄气了,勾着头带走了那一身浊重的酒气。你妈黯然盯着我:何苦呢?非娃。当时你多可爱,凑上前一个劲地抚摸着非叔这被打痛了的脸。
你妈很美,也很柔弱。你爸曾经疼得她发疯,后来又恨得她发疯,亏他还是个文人,那阵儿竟嗜赌如命,手气一不顺,就拿你妈泄气,一顿拳脚过后,又总是勾着头絮絮不断地悔过,喃喃念叨:我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你妈最后总会像抚弄一只羊羔般抚弄着他,脸上漾起一种凄笑。你恨透了你爸,常跑过非叔这边,发泄对那人的嫌恶,说你长大了要离开这个家。可那时你才五岁,五岁的你让非叔给你吹大红气球,气球大了“嘣”地窜上了天。你说,你就是这轻轻的气球……最后,你爸又隔着院墙向你恶喊。
后来,你爸像中了哪股子魔,对你妈揍得特别紧,也特别狠。听说他在写一部小说,主题是探讨女人的存在悲哀。似乎为体验生活,那晚,他几乎把全城不三不四的女人全网罗着带回了家,肆无忌惮地唱啊,闹啊,一个个像大黑牢里逃出的恶囚,浑身来劲。你妈那晚冷漠得有点超然,照旧倒茶递烟,那晚她的美真达到了极致。
在那群人兴尽力竭时,你妈叫住你爸:阿华,冷静看看自己吧,你咋会变成这样?看你现在多颓丧多消沉,以前你有才气,有理想,你就听任这样自暴自弃,一蹶不振……你爸当时的确像被蜇了一下,脸随即变得青紫,像个魔鬼,倏而扭转头对那群女人吼道:滚——烂婊子,骚娘们,全给我滚!砰——砰——两只酒瓶就被你爸砸碎在地上,酒浆横流。那群女人“哇”地一阵尖叫,一溜烟工夫跑了个精光。
你爸嘿嘿笑两声,扭过头来:你称心了?臭娘们,这一下你称心了?忽而他歪着头像只颈毛竖立的公鸡,向你妈歇斯底里地喊叫:就这样讨厌我了?朝三暮四的尤物!见我落魄,你就烦我了?烦你的去吧,可恶的女人。他回转身子,灌着烈酒趔趄着走出院门,一边拉开嗓门朗声念着:悲哉!女人,曾叫我痴迷,又无尽折磨我;悲哉!女人,你温情的陷阱,我何时才彻底挣脱……
小敏,那晚你把非叔叫去看你妈,你妈当时就一头扑在我怀中,语无伦次地说道:过不下去了,这日子我咋也过不下去了……
我就像一根枯木被她抱紧,被她摇撼,不知怎样才能把她安定下来,只觉得浓重的夜岚特别悚人;骤然,夜岚中浮出你爸那张扭曲的脸,当时见到那张脸我一个寒颤,本能地推开你妈。你妈吓呆了。
就这一刻,你爸真成了一头野兽……撕心裂肺的哀喊声中,你妈浑身便有了紫斑。那时我已昏了头,红着双眼冲进厨房,操起菜刀冲上前去,你妈当时一声厉叫:你要干什么?!我被惊醒,吵闹的场面有了片刻沉寂。
后来,我颓然放下菜刀,一步一步走到你爸面前,你爸本能地后退两步。我忽然将胸脯拍得擂鼓一般,叽哩呱啦,指手划脚,在慌乱中一阵乱号……终于,大家都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已铁定了心。
我走!
五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支撑我活下去的信念,是心中容装着一个美丽女人。五年的光阴蹒跚过去,当你妈上吊的噩耗,像一个闷雷在我头上滚过,我千里迢迢赶回来,就为实现一个夙愿,能走到你妈坟前,去伴她长眠。
可是,坟前已塔起一间草舍,里面呆着你那已经木然的老爸。他说,在他的余生里,他要重新认识这个女人——你妈临死前曾念叨,她将用死来招回一个迷失的灵魂。归来的我,仍旧无家可归,因为心中的女人一直就是别人的女人,到最终我也没有伴她厮守的资格。
可是小敏啊,在你的混沌童年,难道非叔真就是一个闪逝物象,怎么也闯不进你的记忆?苦命的非叔,在他内心深处曾强烈地企盼,盼望能在你妈身边做一个忠实的奴仆,侍候她终生,她的美在我眼中是那般圣洁。可怜的非叔也曾企盼你小敏一辈子不长大,让非叔像呵护一朵小花般永远照料你,你是那般纯真无邪。可是,谁又知道我的全部苦衷,以及我的所有悲衰,因为……
谁叫我是一个哑巴啊!不会用言语交流,彻头彻尾的一个——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