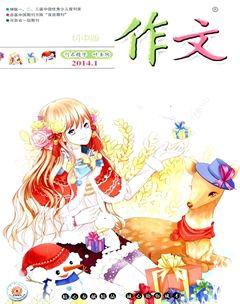父与子
柴静
“对不起,24万!生命!在那场灾难中离去。对不起,我,今天才知道。”这是博客里的留言。
不,不意外。
这次在唐山,我见到了钱钢的儿子。
小钱24岁,是学物理的男生,喜欢轮滑和漂亮女生。
“我是一俗中之俗人。”他老得意洋洋地这么说,以强调他和老爹一代的区别。
听到他和他爸谈起地震就那么一次——
在车上,他问:“地震之前,猫啊狗的,真的会知道吗?”
他爸也像跟娃娃说话一样的口气说:“一看你就没好好看我的书。”——那书里,记录了全部灾前的动物预警。
小钱后来跟我说,他在上大学前从来不知道唐山大地震的事,也没看过他爸的书,“哪有时间,我忙完中考忙高考,这个事儿考试又不考。”
现在嘛,要忙着研究生毕业,找一份挣钱多点儿的管理工作。
钱钢说:“我没有要求过他非了解什么,顺其自然。”——他连香港政府把他关于地震的文章列入教学,也很有惶恐之意,生怕历史成为考试,成为负累。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遗传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会去寻找过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强求。
包括小钱这次跟着他爸去唐山,也是小钱自己的想法。
“我就是尽一个儿子的义务。”他嘴硬得很。
看上去一副不上心的样子,背着手,东晃西逛。他爸跟30年前的故人聊天,他在旁边看一下,一言不发,过一会儿就转身到邻居家去看小狗。
只有一次,在医院的灵堂里,我看他拿出个数码相机拍。
我问他拍什么。
他含含糊糊敷衍一句:“看看那个盒子上的雕刻。”
混熟之后,我跟他说要采访他一下。
他不习惯得很,“别谈那些正经的事儿。”
“你到底拍什么了?”我看他的相机。
拍的是一个小孩的骨灰盒上,刻了一只凤凰。
“为什么拍这个?”我问他。
他说:“我觉得刻的人可能希望他重生吧?”
吆……
我看见他桌上的纸,才知道他这两天正赶着交毕业论文的点儿,白天跟着去各个地方,回来恐怕得连夜写,困得滴里嗒拉。
“那你到底来干什么?”
“说了,陪我爸。”
“还有呢?”
“来看看亲戚。”他狡黠地笑一下。
“还有呢?”
他往后倒了一下,做一个“服你了”的表情。
我等着他说。
“我想找点东西。”
“什么?”
“像我这样的人最缺的东西,”他还补充了一下,“迷茫的人。”
“是什么?”
他有点不好出口,但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信仰”。
这个词,让我愣了一下。
“在哪儿找?”
“从他们(幸存者)眼神里看到一点儿。”
“什么呢?”
“就是……好好活着。”
“活着,并不简单,”他的父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因为我们曾经经历不尊重生命的年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