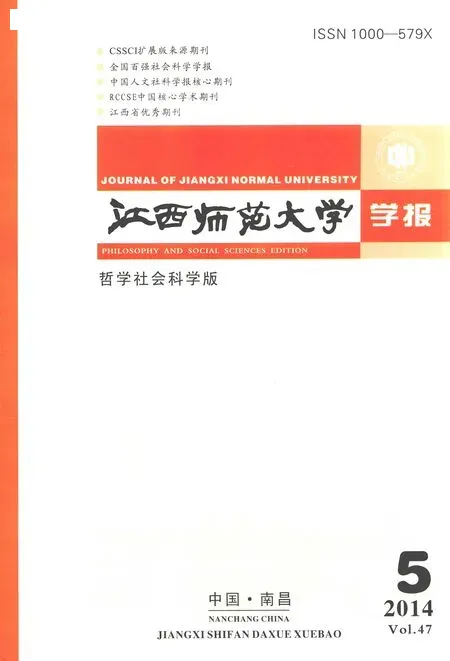群体性事件底层群体的政府信任再造与传统媒体引导研究
李春雷,曹 珊
(江西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群体性事件底层群体的政府信任再造与传统媒体引导研究
李春雷,曹 珊
(江西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伴随社会转型中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增,各类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建设的突出问题。而底层群体对基层政府信任的缺失,是导致大规模矛盾冲突并走向极端从而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而社会的媒介化框架又将其演化成媒介化事件,故作为权威和主流的传统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传播、舆论引导显得尤其重要。本文以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分析底层群体对基层政府信任认知的偏差化,以及传统媒体的“不当介入”催生政府信任危机并产生社会负面影响。由此,本研究拟通过倡导树立传统媒体公共传播理念,扩展深化群体性事件中传媒的功能,以期能够实现底层群体政府信任的再造。
政府信任;传统媒体;群体性事件;底层群体
引言
社会转型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p38)随着政治与经济等利益格局不断变化调整,转型期不仅带来了社会进步发展,也“使我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底层群体”。[2]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次和规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底层群体对越级上访、网络泄愤等非正常表达渠道的大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对政府的满意度不高,群体性事件中底层群体的非制度化参与更是进一步表明其对政府信任的缺失。而齐美尔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3](p178-179)所以信任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信任,它“是公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心理判断,主观意识上反映公众对于政府满足其利益需要的心理趋向”。[4]基于此,本文所论述的基层政府信任,是指群体性事件中绝大多数的底层群体对基层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等的一种心理判断和评价态度。
就当下的群体性事件而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合力推进媒介化事件的到来,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政府与底层群体的媒介需求,同时也使得“底层社会的传播生态发生着巨大变迁”。[5]然而,传统媒体在政府的工具理性与公众的信息诉求之间难以平衡,极易催生政府信任危机。本文是以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信任再造为导向,分析事件爆发前底层群体所形成的对政府信任的认知,以及事件爆发后传统媒体的“陨落式介入”对政治信任危机的催生机制,并借以提出传统媒体疏解的可行路径。
一、群体性事件频发下底层群体对基层政府信任的认知
“个体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是被动的对社会环境做出反应”,[6]而是试图通过主动的选择来操纵对外界环境的认知。长期以来底层群体所形成的对政府信任的认知往往是通过传媒、自身经历等形成的先验意识,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等的刺激和控制形成的一种群体感知。随着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以及媒介使用的深入,底层群体对基层政府信任逐渐出现刻板印象固化的内在认知。
(一)期待落差下的选择认知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尤其是计划经济时代,绝大多数的底层群体都拥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的思想。随着电视媒体技术的普及,观看《新闻联播》等新闻节目逐渐成为底层群体获取政府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些信息往往给民众塑造一种“心系民生、关注基层”的全能政府形象,而这一形象的感知会使其对政府在社会众多领域中产生过高的期待。但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建设中,政府逐渐将自身职能范围的事情推向市场。为实现GDP大增长,在政策的制定上偏向于资本的力量,形成贫富差距鸿沟,而这与底层群体的先验意识相去甚远。过高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引发底层群体对政府认知的心理落差。
个体在涉及相关利益抉择的时候,“不仅容易出现非理性,而且还会出现理性选择向非理性选择的转化” 。[7]在这种落差心理和利益非理性的驱动下,底层群体对传媒所传递的政府相关信息亦会进行“选择”,从而对先前所形成的政府全能形象进行“对抗式解码”。除了通过传媒间接形成对政府的认知之外,底层群体也常以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的方式,直接获取政府当局相关信息并进行选择认知,而这与其先前形成的观念更是相去甚远,进而引发底层群体对政府的认知失调。
(二)群际情绪下的形象偏见
以农业为主的底层熟人社会中,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历史记忆,能将客观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主观上的体验,从而极易形成利益共同性的大集体。随着媒介嵌入的逐渐加深,媒体报道中凸显的“暴力行为、权贵身份、老弱病残孕与女性性别这三类信息”,能激发底层群体的自身感受,“并促使其形成主动参与的动机与群体意识的心像”,[8]这种或隐或显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无形之中会加剧底层群体“弱势群像”的形塑。
史密斯的“群际情绪”理论指出,人们为寻求群体间的心理认同,会对内群体、外群体进行划分来完成自身的身份定位,并固定情绪体验。“这些群际情绪如同标签,被所认知或交往的特定群体唤起,成为群体的社会支配取向。”[9]在基层政府“强制性权力”面前,底层群体通过群际划分形成弱势效应,不满情绪随之扩散,有意无意之间在底层群体中达成对政府相关利益部门的形象偏见。
(三)相对剥夺下的刻板印象固化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的生活和工作满意感并非依赖绝对、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周围的人为参照群体进行评价,比较的结果若是自己处于比较低的地位,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9]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基层政府在自身公共服务职能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权衡,公共事业领域建设中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对公众的利益诉求置若罔闻,尤其是底层群体的利益。而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发展是建立在一方利益受损的基础上,“一旦个体感知到相对剥夺,就会因此而引发一系列情绪及行为反应”。[9]
丹尼斯·库恩认为刻板印象是“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过于简单的印象”。[10](p781)在公共事件的报道中,传媒为增加“可看点”,通过“受难”式的情节叙述将官民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加以放大,这样一种“传播的观念对受众有着内在的、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受众的刻板印象”,[11]会给公众尤其是底层群体造成一种夸张性的误导,形成官民冲突普遍存在的底层群体误判“幻像”,进而进一步加剧底层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基层政府的负面形象逐渐被固化。
二、陨落式介入:传统媒体对基层政府信任危机的催生机制
根据底层群体对政府行为的心理反应强弱,政府信任评价指标可分为“公众满意度、政府公信力和政治信任感三个衡量标准”。[12]然而在群体性事件中,由传统媒体所建构的“媒介景观”是政府信任危机形成的条件、重要机制。基于群体性事件爆发前底层群体对政府信任所形成的负面认知的前提,本部分以传统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作为研究视角,并通过政府信任的三个衡量标准来分析底层群体政府信任危机的生成机制。
(一)集体失语:信息传播真空深化认知偏差
在底层社会的管治中,长期以来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基层政府部门的施政行为通常是单向的、强硬的,享有话语权优势的他们习惯于对底层群体进行自上而下“命令式表达”。在群体性事件爆发后的初期,事件中的各种偶然性都会使人们的信息需求骤增,但由于信息可信度及技术掌握条件等相关因素,底层群体首先会去选择传统媒体。然而一些地方官员则认为底层群体在获取相关信息后的利益诉求表达会对政府权威性产生挑战,要进行压制。故出于刚性维稳的需要,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限制传统媒体报道的自由,甚至屏蔽、封锁相关信息。传统媒体因受到体制的规约,集体失语、集体沉默已成一种常态。
基层政府和传统媒体的沉默失语会形成底层群体对信息需求与信息提供之间的矛盾,造成官民之间沟通隔阂。在这样一种信息真空的环境下,“当民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一切”,[13](p82)“就有可能放弃理性思考而在感情机制的作用下作出选择”。[14]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下的底层群体极易选择相信网络中的谣言并散播开来,一些人甚至会认为正是由于相关政府部门处于理亏的境地才会采取信息封锁屏蔽等极端做法,此则进一步深化了先前所形成的偏差化认知,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同时,也表明由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真空所引致的官民沟通隔阂会使底层群体对于政府的心理感受满意程度下降,影响其对政府管理与服务感知体验程度。
(二)被动跟进:叙事框架失衡助推情绪升级
随着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展,新媒体逐渐占据着舆论的制高点,基层政府在舆情民意压力下,开始借助于传统媒体公开信息、澄清质疑。而“喉舌”功能取向的传统媒体,为缓和底层群体的情绪及维持群体性事件的稳定,更多的只是充当政府的“传声筒”,宣传政府的观点和主张,表现出被动跟进的一面。如果我们借助于传统媒体叙事框架中的形式框架和内容框架来进行分析,会发现就形式框架而言,主要采用主题式的叙事框架,综合利用数据、案例、综述等形式按照官方维稳的主题来组织新闻报道;而内容框架方面,则是采用危机处理的叙事框架,消息来源上更多地是依赖于官方,其选择与引用暗含着媒体对事件态度立场的官方化;语言的选择使用上,受传统报道观念的影响,习惯性地使用一些语义模糊的政治性词语或专业术语,底层群体往往被冠以“被煽动的越轨者”,相关政府部门则被称作“依法执法者”等,对群体性事件进行过度政治化解读。
新媒体所传递的简单刺激性的信息,使底层群体对传统媒体所发布出来的官方解释持质疑的态度,并通过相关认知经验的转移嫁接,对当事人的遭遇形成感同身受的效果,产生强烈的共鸣。传统媒体失衡化的叙事框架,不仅没有对底层群体不满情绪起到疏导和抚慰的作用,反而使得底层群体深感自身话语权缺失的弱势地位以及传统媒体与政府的联姻。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15]那么传统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被动跟进的不当表现,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底层群体对于基层政府的负面评价。最终,个体的和集体的负面情绪会随着失衡化信息的传播,通过感染或传染形成强大的集群焦虑情绪。
(三)压抑后狂欢:归因导向偏颇诱发信任危机
在群体性事件的消解期,随着上级政府的介入,基层政府、传统媒体、底层群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呈现出自上而下的调整,传统媒体开始全面地介入到事件中去,进行调查报道及舆论引导。由前期的“压抑”到后来的“狂欢”,传统媒体为迎合受众的情绪意见,追捧平民化立场及话语体系,将相关责任部门推向风口浪尖。在舆论的建构引导中,传统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归因往往运用基层官员“公权力滥用”、“制度缺失”等污名化脚本。而这样一种归因偏颇正与处于质疑、焦虑等负面情绪下的底层群体叠加共振,群体极化下利益相关者的理性逐渐被异化失去理智,一旦有相关敏感因素触动,极易引发二次群体性事件。
“传统媒体在长期的新闻生产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叙事逻辑,生产着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认同的符号,影响公众的认知模式和归因方式。”[16]传媒推动社会制度的建设无可厚非,但报道中的归因导向偏颇,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底层群体对政府制度的正确评估。由对某个具体事件的质疑发展到对基层官员的不满,在基层政府刻板印象和焦虑情绪的操纵下甚至会使底层群体形成非制度化抗争的行为基础,从而进一步降低其政府信任感,这种长期累积的民怨会引发底层群体对于公共政策、政府官员乃至政治制度信任的缺失,催生政府信任危机。
三、救赎式建构:公共传播理念对基层政府信任再造的引导路径
“公共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理念,是媒介所进行的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公共信息的公开传播活动”,“有效的公共传播能形成平等、参与、信任、协作的公共精神,最终达到良好的社会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17]如上文所述,正是由于传统媒体的不当表现间接或直接影响底层群体,并使其对政府形成认知偏差、负面情绪,信任危机转化为现实行动也成为可能。因此本部分所界定的公共传播是指传统媒体以建立对话机制为核心要素对底层群体公共利益的建构和维护,包括“平等共享”、“平等参与”两个阶段,[18]从而实现底层群体“理性选择信息和客观传递信息,让信息的传播进入可控轨道”,[19]重塑底层群体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最终降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维护社会稳定。
公共传播的核心要素是一种公开的对话机制。对话是行为主体之间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起点,也是达成共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传统媒体作为公共利益的主要诉求机构,需从宣传角色转变为对话角色,借助于民生化的语言、平衡的叙事框架、体验式的报道等建构一个面向底层社会的对话机制,创造官民平等共享、自由讨论的话语空间。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底层群体与政府之间可以借助于这样一个对话机制,以互为主体的状态进行信息的交换和观点的碰撞,加强双方在思想、感情、信息上的联系,并在沟通协商中使政府的决策行为得到理解与接受,从而缓解二者之间因利益关系产生的冲突和对抗,促进个体之间、团体之间有效的合作与合理的发展。
共享是公共传播实现的初级层次,指自由获取多样化的信息,为对话各方提供信息准备。“信任来自主体与客体间的反复交往,公众对政府了解得越多才可能对政府付出更多的信任。”[20]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要改变原有的思维惯性,联合政府成立专门的应对小组,及时介入事件现场收集相关核心信息,并做好决策咨询工作,争取在第一时间内满足底层群体的信息需求,抢占舆论的制高点。有效的公共传播首先要保证底层群体对事件的知情权,增强政府公共服务的公开透明性,传统媒体亦需遵循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性的原则,让真实、完整、多元的信息成为底层群体认知、判断、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平等共享”可以通过不断地提升政府公共信息的效能,促进底层群体在认识与理解中重塑政府形象,从而形成对政府更加客观、公正、理性的认知。
参与是公共传播实现的高级层次,指广泛的信息传播权,也是对话行为的展开。传统媒体是公民行使权利、处理公共事务的重要载体,理应成为社会各群体利益表达与聚合的公共平台,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底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过于闭塞。传播成为一种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开启对话以分析和解决问题策略的工具,最终目标是利用传播作为一种赋权工具,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21]公共传播是公众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所以在当前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环境下,传统媒体应赋予底层群体更多的话语权,携手政府共同构建社会公共议题,在合法的框架下经过讨论形成公共舆论,再通过公共传播将观点传至社会各阶层,从而实现政府决策中底层群体利益最大化。“平等参与”可以通过传媒传播权力的下放,实现底层群体的“私人认知体系”朝向“公共认知体系”转变,缓解和疏导现行官民冲突的负面情绪,引导群体意见趋于理性归因,从而提升底层群体对政府的信任。
结语
中国正在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社会结构同时呈现碎片化和两极化的形态,正在加速“断裂”与“失衡”。[22](p28)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征地拆迁愈演愈烈、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无一不动摇着底层群体对政府的信任,而公众的信任是政府有效运行的基础和保障。[20]就现阶段而言,如果说官民利益冲突是群体性事件的显性特征,那么政府信任危机才是其背后的隐性风险。故政府和传统媒体应倡导信任沟通意识,帮助底层群体重建政府印象,回归理性认知。然而,仅仅依靠传统媒体实现政府信任再造乃是杯水车薪,唯有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媒体等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才能为信任的再造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从而降低由信任危机而引致群体事件发生的概率。
[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李春雷,张剑波.政治弱势心理的泛化与传媒对底层社会的引导策略研究——基于“东明事件”的实证分析[J].现代传播,2012,(6).
[3]G.Simmel 1978.The Philosophy of Monery [M].London:routledge,178-179.
[4]刘 浩.群体性事件政府信任建构路径研究[D].苏州大学,2010.
[5]李春雷,易小军.草根情结的异化:底层社会传播生态的另一种解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6]赵晓秋.本土文化背景下印象管理对上下级信任的影响[D].浙江工商大学,2008.
[7]何大安.个体和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07,(2).
[8]周 瑾.论群体事件中的信息传播与群体心理[J].科技创业月刊,2011,(10).
[9]王二平.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学分析[A].科学发展: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复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论文集(上卷)[C].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09.
[10]〔美〕丹尼斯·库恩.心理学导论——思想与行为的认识之路[M].郑 钢,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11]李春雷,刘颖洁.刻板印象与消费主义文化下的媒介女性形象——基于京、沪、赣等地问卷调查分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12]王 强.民主行政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及其构建研究[D].吉林大学,2007.
[13]〔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M].郑若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4]何大安.个体和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07,(2).
[15]刘 浩.群体性事件政府信任建构路径研究[D].苏州大学,2010.
[16]金 凤.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媒介真实建构[D].南京师范大学,2011.
[17]石长顺,石永军.论新兴媒体时代的公共传播[J].现代传播双月刊,2007,(4).
[18]石永军.论新兴媒体的公共传播[D].华中科技大学,2009.
[19]李春雷,凌国卿.风险再造:新媒体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框架分析[J].新闻界,2013,(16).
[20]李春雷,马俐.政府信任构建与大众传媒对拆迁心理的引导机制研究——基于唐福珍自焚事件的实证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3,(5).
[21]韩 鸿.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
[22]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余小江)
ResearchingtheConfidence-rebuildingofUnderlyingMassesinGroupEventsinGovernmentandtheGuidanceofTraditionalMedia
LI Chunlei,CAO Sha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With the surge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various group events have become prominent problems affect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construction.Underlying masses’ lack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resulting in large-scale conflict,going to extremes,eventually evolving into group events.The social media framework in turn makes them evolve into media -oriented events.Accordingly,the traditional media as the authoritative and mainstream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f group events.Taking the developing venation of group events as the main line,the paper analyzes underlying masses’ cognition deviation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t the grass-roots level,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nd social negative influence caused by “improper interven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edia,and tries to extend and deepen media functions in group events by advocating setting up the tradition media public dissemination idea,so as to realize the confidence-rebuilding of underlying masses in government.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traditional media;group events;underlying masses
2014-04-20
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困难群体心理疏导与传媒引导机制研究”(编号:12CXW016)
李春雷(1976-),男,博士,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新闻心理。 曹 珊(1992-),女,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
G206
A
1000-579(2014)05-005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