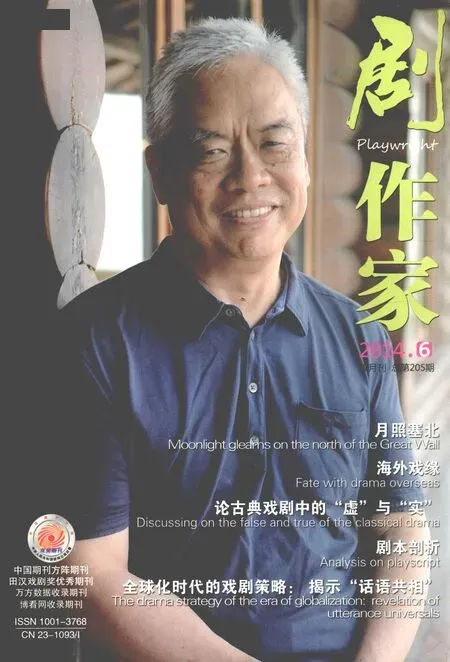全球化时代的戏剧策略:揭示“话语共相”
濮 波
全球化时代的戏剧策略:揭示“话语共相”
濮 波
全球化时代的戏剧倾向:舞台认知的国际化
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显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以及时间和空间跨越、重组的问题。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时空分延,正是这个时代的镜像和标志性意象特征。后起的剧作家、作家、诗人也敏感地把握到了这种多元混杂和“古玩店”般错层陈列的文化特征。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在全球化的人员大迁徙中还发现了诸如“离散”和“混杂”等特征。
戏剧的发生语境与社会语境是呈现对应关系的。相对于全球化的混杂、离散、时空分延等特征,戏剧领域,总体上由于这个时代赋予的情感结构和审美形态的更迭,导致了戏剧模式和主题、题材的对应流变。在差异性呈现的同时,也提供给观众一种可以在眼花缭乱的世界舞台上找到识别模式和定位系统的认知能力。之所以观众可以在当代培养出一种超越国界的新舞台认知,是因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戏剧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一种相似性。伦敦西区、纽约百老汇、东京、首尔的演剧区的戏剧,在形式上都呈现了具有多元特征的“共相”,也指向一种前所未有的戏剧舞台——文化和语言的融通。这种新的认知(观众可以轻易识别的舞台国际化语言),被人类表演学理论家Janelle G. Reinelt命名为“国际性表演认知”(internatinal performance literacy)。[1]这个认知背后的语境包括:在全球人员流动增强的背景下,国际性的大都市剧场都流行多国表演(polynational performance),即在一个剧目中演员的多国籍合作。它的流行,还与戏剧理论家、表演学家谢克纳、Patrice Pavis等对表演趋势的预测相关。比如戏剧表演理论家Patrice Pavis在1982年提出了当代人“应该具有一种全新的认知结构能力”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当代人需要能对舞台语言进行认知。所谓舞台语言的认知,就是能够读懂舞台中发生的“视觉意象、身体活动、文化记忆和本土的流行文化等社会交往语言”。[2]这种通融国籍、跨越国界的“共相”既反映了全球化、国际化导致人们观念交流的机会增多的事实,也是对人们日渐增长的一种“表演性认知能力”塑形。这种新认知,可以归结为一种行为、意象、结构、主题的整体性认知能力,借助对修辞、身体的识别能力。包括对直觉、触摸、交往、身体、文化、历史、地理、象征、隐语、反讽等等与现阶段发生在舞台上的审美和现象息息相关的一种识别能力。如目前剧场里,观众对于剧中的“双语”、“多种语言混合”、Devised Theatre (合作生成戏剧的英文专有名词,如《东方三部曲》The Orientations Trilogy就是典型的合作生成戏剧[3])等都不再陌生化。这就是在新的语境中,对于观众观看像《马拉/萨德》《戏谑》《上层女子》《生日晚会》式的戏剧,或者更为先锋的后现代戏剧时所具有的剧场认知——的审美认同前提。多国籍演员组合演出的戏剧越来越普遍,无论彼得·布鲁克《西服》中国版[4]、蒋维国导演的《太阳不是我们的》、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上导演的京剧版《麦克白》还是澳洲Marvellous Melbourne的作品,都体现了这种趋势;与此同时,戏剧的话语和修辞的混用现象也层出不穷。多国语言、修辞混合,合作生成某种程度上走向了目前舞台表演的共性之一。
这些表演的“共相”在东西方舞台上的频繁出现,如被称之为Devised Theatre的品种更是跨越几大洲,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同时兴起。其背后是与全球化时代的戏剧舞台的新认知相挂钩,这些新认知也指向一种新的剧场美学:跨文化、身体性、物质性、多元、不可通约性。
舞台形态的趋同化,令人想起两百年前的哲学家维科所谓的永恒“诗性”的回归或者“想象的共相”(imaginative universals)的概念。后者假设人类具有“共同的心灵词典”(a common mental dictionary)。[5]揭示出“尽管一个民族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其成员所讲之语言和文化,但文化并不止步于该社会单元的疆界。所谓同情,即源于对他者的认同,是团结之基础。既然我们能够学会某一种语言(即我们的母语),我们原则上也能通过类似的方式学习其他语言和文化,哪怕它们与我们最熟悉的语言和文化相隔千山万水。文化这一概念的潜台词是,文化的多元宇宙永远不会大门紧锁,不相往来。任何人都必须走出其文化所预设的先在结构(prestructuring)”的真理。[6]可以说,维科发明的“共相”,正是目前戏剧舞台上提倡新的表演性认知、一种东西方思维再次邂逅的写照。那么,这种共相所表征的又是什么领域呢?
戴维·马梅特《奥莉安娜》传达出的话语“共相”
《奥莉安娜》这个戏剧是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导演之一戴维·马梅特(David Mamet)1990年代重要的作品,剧情的设置简洁到了极致,体现了马梅特的政治学——在极度简洁中抵达时代主题:话语的呈现。第一幕,教授约翰和女学生卡罗儿面对面坐在桌子边。这一幕展开了女学生落入困境的全部背景和男性教授的优势:女学生为了混张文凭,在学业上有求于教授;教授在怜香惜玉和恃强凌弱的双重心理下用身体触碰了女学生;第二幕,所有的舞台设计都类似镜像:教授和女学生依然坐在桌子边(我观看的英国约克剧院的演出版本,导演设置是第二幕两人坐的位置刚好互换,暗示着权力关系的变更,暗示剧情中权力关系与第一幕颠倒)。女学生状告了教授,委员会已经立案调查。教授为此可能丢掉饭碗,优势顿失。两人的关系形成第一幕的颠倒。这会儿女学生坐了教授原先的位置——舞台设计跟随了情节。通过女学生的控告,我们还知道了,教授之前还做出了过分亲密的身体接触,可能是一个拥抱之类的动作。第三幕,争论在继续(约克版的导演设计是这样的:他们俩却都没有坐到原来的位置上,教授坐到了四边形桌子的另一个没有坐过的角落。女学生换位,依然在教授的对面——暗示着权力关系的角斗延续)。我注意到有一个剧情加强了这个冲突。教授的妻子打电话来,教授称其为“亲爱的”,就是这称呼,激怒了被性骚扰的学生。她当场就对教授说“别用这个肉麻的称呼”。教授被激怒了,失去了控制,从而对女学生进行了刚好她所缺少的证据:殴打女学生。戏剧就在这里戛然而止。
《奥利安娜》表面的剧情是性骚扰纠纷,深层的所指却是人类语言:包括貌似深奥的学术词汇和专业词汇,比如“性骚扰”、“控告”、“裁决”等;表面上,是一个学生和教授之间由于关于性骚扰的一次揭穿与抵赖、控告与反制约。深层的涵义则是多元的、模糊的、暧昧的。我们再来详细分析第一幕的场景,其中,卡罗儿来到约翰教授的办公室,她有求于教授。他们之间有关于学习的对话。但是由于性别和地位不同,他们很难达成共识,卡罗儿在与教授的对话中感觉糟透了。她这样回击——
卡罗儿不,你是对的,‘哦 天啊’我搞砸了。扫地出门,这是垃圾。我所做的每件事,‘在这篇文章里包涵的观点代表了作者的感觉’。对极了。对极了,我知道我很笨,我知道我是什么。(停顿),我知道我是什么,教授,你不必再告诉我了。(停顿)这挺可怜的,是不是?[7]
卡罗儿埋怨学术话语的模糊性,她不知道,她进入的其实是学院逻各斯和男人(双重)中心主义的话语场。在这个语境里,卡罗儿明显感受到了被无处不在的话语霸权置于边缘的境遇。她可以感觉到这些,但是她说不出来这究竟是什么。这就是类似“在这篇文章里包涵的观点代表了作者的感觉”这样的话语。这是一个强权世界里的话语规则,这个规则的逻辑是自我涉指的,也就是“A等于A”这样的专制逻辑和思维范式。
拿罗兰· 巴尔特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同语反复”[8]。导致语言的封闭性趋于极端,且不容你争辩,在命名与判断之间不再有任何耽搁[9]。卡罗儿显然在这个陷入资本主义里的专制方式[10]里接近失语了。比如当卡罗儿诉苦说“我有问题”(具体个案)时,教授说“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普遍性)。作为异性的女孩子,显然觉得在男性主导的学术这个话语场里自己的弱势。卡罗儿感叹“太多的语言……语言是一个问题”,教授则说“不必在乎这个”。卡罗儿不能快捷地记笔记,教授说“笔记也是多余的”。
因此,这个戏剧揭示学院里存在的普遍的现象:话语权的争夺和语言滥用。
“话语”的争夺,在这个戏剧里提升到了主题的层面。一开始,教授在话语上占有绝对的强势。他能巧妙和自然地运用语言的修辞术和诡辩术,利用语言意义的暧昧和歧义。比如,上述“笔记也是多余的”这句话,经由教授的口吻说出,就充满了话语的霸权。这句话可以放在不同的语境里解释:第一,“所有的课堂知识都是瞎扯”;第二,“因为我喜欢你,你不用认真,我肯定会让你过线的”。第一幕结尾处,卡罗儿由于一味求真而不得,困惑继而导致了愤怒。话语的失衡在这一幕非常明显,占据话语优势的人:教授,掌控了语言之于意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暴力功能。第二幕,愤怒的卡罗儿向校方投诉,约翰大梦初醒。然而,在对话中显示出:约翰尽量想表达“自己不明白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一幕里,他似乎成了受害者,情境刚好与第一幕颠倒。卡罗儿成为性骚扰的控诉人,约翰主动约请卡罗儿谈判。当然,这回有了黄牌在手的卡罗儿占据了话语的优势。她用约翰之道弹劾和制约约翰。这一幕,话语权呈现了逆转,卡罗儿巧妙地使用技巧,掌握了主动性,她用的武器是第一幕约翰使用过的“程序的暴力”或“程式的无意识”。即她不仅用罗兰·巴尔特所点题的“同语反覆”,即程式就是程式,我们谁也不能决定结论,要看程序。话语背后的逻辑是:既然她已经向校方投诉,那就暗示得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而不必走捷径了。约翰败下阵来,他常常用的思维范式:“A等于A”,在这一幕卡罗儿拿它对他进行了嘲讽。按照范式,约翰可能会失去教职,也可能失去在第一幕他与妻子甜言蜜语在私聊的“一处高档房产”,甚至失去一切。第三幕,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循环往复,没有结果。约翰为了说服卡罗儿,想方设法使得她能够回撤销指控,而卡罗儿依然在运用“法律范式”。 关于“留”还是“不留”上,两个人绕口令般争来争去。卡罗儿亮出了女性主义色彩的复仇言辞,“关键之处不是我的感觉,而是普天之下女人的感受”。 这里,卡罗儿也让语言走向了普遍性。(记得第一幕里,卡罗儿要约翰照顾她这么个特殊案例的时候约翰的普遍性话语:“每一个人都有问题。”)这个话语技术是约翰在第一幕里所灵活运用的。最后,约翰恼羞成怒,众目睽睽之下打了卡罗儿。
《奥莉安娜》的结局指向一种开放性:既可以指向话语——由于人类极不负责的语言习惯和那种理性:不仅喜欢概括、总结、归纳,而且喜欢用谚语、成语、新词汇的这些特点,让语言生不逢时,遭遇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可以指向两性、权力关系的永恒悖谬。上海话剧中心在2003年上演的汉语版《奥丽安娜》[11]中,结局处是剧场工作人员面对观众作了一次教授和女学生“错在哪一边”的投票,将观演关系推向了一种互动。在这些开放性中,《奥莉安娜》提出了诘问:人类的话语空间,因为统治了西方二千年的二元逻辑和辩证,是否在这个领域里,已经不再能够起作用?言下之意,这个空间是暧昧不清的,属于爱德华·索佳的第三空间,这个空间本应消除边界,所有的对立的思维都是局限的。
该剧也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交流的困境:一方面双方渴望理解,另一方面语言被误用和滥用,体现出男女争夺话语权的焦虑。同时,对美国现有的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出戏以多以小剧场形式演出,以现实主义风格呈现,诠释这一充满现代思辨的作品,对剧作所蕴含的人性的欲望,男女交流的语境差异、话语权的争夺,现有教育制度的利弊等社会问题进行深度的剖析。由于这样的开放性,对《奥莉安娜》主题的解读就应该——建立在作者构建的语境基础之上,而不应只着眼于其表层意义——人类的语言危机。语言,这个由人类主观性、文化强加于自己的符号,在后现代的语境里,已经出现了疲态。它不再万能,在中世纪或者现代时期可以制定法律、条约、编撰词典等等科学性的媒介,在当下遭遇了危机。《奥莉安娜》借用隐喻式的话语权争夺,其实本身也指向人类生存意义的虚无和话语本身的任意性,揭示出:人类充满了语言的困惑,也充满了话语的歧义和由于“话语”互相抵牾的事实。
法国符号学家于贝斯菲尔德在《戏剧符号学》中断言:“现代戏剧写作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种相对话语内容本身的移位。在最新的戏剧里,重点很少放在情感和思想的冲突或所说内容之上,而更多地放在语言冲突、话语的特有战略、人物言语的功能之上,以及放在它每一个时刻对言语情景和主要角色关系的‘重新处理’和‘重铸模式’的方式上。”[12]这个戏不仅符合于贝斯菲尔德所说的话语特有战略、言语功能、“言语情景”的重新处理以及“主要角色关系”的重铸之范式,更在于通过对诸如“性骚扰”、“捍卫权利”、“控告”等话语的反思,揭示了戏剧中共存的话语主题倾向。
话语“共相”中的中西融通
正如维科所发现的人类想象是具有宇宙共相的,而并不仅仅是国家的一样。“共相”这个词汇本身,也指向一种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异质同构”。如果说,《奥莉安娜》(Oleanna)揭示了一种话语主题的倾向和趋势,那么也就道出了在不同国家和地域之话语探寻中存在着一种揭示戏剧话语共相的真谛。这种被揭示的“共相”,折射的潜台词是这样的:在不同国家和文化的社会、心灵、舞台三者之间,具有可以参照、融通的戏剧认知结构和模式。下面的例子,说明中西在一种抵达戏剧主题上的融通性,它们因为超越边界而具有出现了国别和风格的混合性质。
1、京剧《成败萧何》(2010年)的“话语”主题
中国戏剧的当代尝试中充满了“话语”,上海京剧院出品的新编京剧《成败萧何》是其中一个。它是新创京剧,该剧被评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作为难得的当代戏剧的经典,它最大的特色是“结局开放性”。传统京剧剧目的主题大多是明晰的,或惩恶,或扬善,均一目了然。而新编历史剧《成败萧何》并没有明确的主题,它具有本人尝试性的概念“第三空间戏剧”[13]这样的涵义。即它的主题涵指辽阔,所表演的内容即成语的来由(关于一个成语的产生的元戏剧)。编剧李莉希望站在历史的高度,抛开非此即彼的创作模式,写出历史人物的真实处境。剧本在取信历史的前提下,很好地涉及到关于诚信、道德、国家和个体的关系等丰富的现实内涵,并非将是非对错简单地区分;它的旨趣超越于单纯的政治批判和道德评价,而是将观众引向深层的历史文化反思,对历史作重新诠释。萧何与韩信的故事流传千百年,周信芳先生主演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是麒派的经典名作,家喻户晓。新编历史剧《成败萧何》,则揭示出封建政权确立之后,君臣之间关系的变化,把着力点放在“败也萧何”上,最后发出“成败岂能由萧何”的悲叹。
与传统戏剧不同的是,此剧中的主要人物,皆被移植进当代的语境中,被塑造成了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为当代人理解的现代人形象。与其说他们在创造历史,不如说他们都处于历史大势的无奈中。在戏剧里,刘邦一改传统的形象道:不要再打仗了,希望做一个太平皇帝;吕雉说:请丞相为我母子安定乾坤;萧何说:从今往后,再不要杀伐了;韩信说:羞为自身起战祸;就连萧静云也对父亲说:若再打仗,百姓们承受不起了。虽然,每一个人物的初衷不同,却有意无意地站到了同一个基点上——经过两百多年战祸纷争煎熬的生命集体,企盼生存,企盼和合,企盼安宁。这是历史的大潮流,人心的大趋势。个体生命在这大潮流大趋势中,必定会有相应的大局限,谁也无法自觉超越。[14]
因此,戏剧性在这台戏里变成了人性、国家意识、个体和集体四者之间相互粘联、撞击、撕裂和绞杀。该剧以全景或者并置的现代手法,在“滚滚滔滔的历史混沌中,揭示出丑陋、高贵、阴暗、灿烂之人性”。 由于戏剧性重点的转移,该剧主要表现人际之间的巨大痛苦和话语的困境:不仅可以是“事君王,保知己”难以“周全”的萧何痛苦万分,韩信也如此;甚至,宽泛一点,这个悲剧的重点可以是揭露“封建王朝话语”的普遍性悲剧。因为在话语的层面,我们知道君臣之间的不对等,才是悲剧的源泉。话语权力的不对等,导致话语的失衡和关系的扭曲。《成败萧何》正是话语悲剧的典型。话语导致文化符号、符码的附加值增加。一个拥有王位的符码的人和阶级,其总可以欺凌弱者。体制也一样,一旦它不可逾越,便造成“暴力”。如,有时候它借助这个符号来约束社会,有时候又成为反对自己的一个极好托辞,以此拉拢臣民。朝廷上的封建伦理、话语、符号,所指广阔(在这样的隐喻下,我未尝不可以将之隐射到伊拉克问题中“千错万错总是我错”的弱势群体和国家面临的语境里)。皇权专制排斥异己存在的一般规律,在中国的语境里几乎成为“习俗”。京剧《成败萧何》就是在这个历史语境里展开,它以刘邦铲除韩信的具体事件为基础,揭示出“自由必不见容于专制的冲突”,从而“和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深层的关联”[15]。
在话语的层面,我们知道:掌握“话语”的人(例如在《麦克白》悲剧里的三女巫),无疑就是掌握暴力的人。她们在第一幕中说的话“你虽然不是君王,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和在第四幕称麦克白为“伟大的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被理解为话语的任意性暴力。同样的一句占卜之话语,既可以是“理所当然”、“顺天意”的意思,又可以是反向的“理所不当然”、“篡权”的意思。麦克白就在这样的话语任意性暴力里被愚弄了一番,最后人头落地。在人类的历史中,依靠这种话语任意性暴力登堂入室的人不计其数。再深入探究话语的任意性暴力,我们观察到,在任意性之间的意义,却通向“非彼即此”的二元政治(在二元的政治领域里,显然还没有类似爱德华·索佳在《第三空间》中强调的三元体系的消解权力的特征)。原因很简单,西方逻各斯主义和东方的封建话语在本质上是属于相似的话语暴力,而且其思维习惯已经在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里面搭建“现象/本质”的大厦。西方的谚语和箴言,与中国的成语有着同样的话语威力。依靠成语,在中国可以登上话语运用的最高境界——皇帝就是成语符号最灵活自如的运用者。他是语言帝国里的话语大师(在中国,所以汉字都为他所用)。依靠成语程式的灵活性,他可以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成语(习语、谚语)来制造暴力,也可以用“海纳百川”这样的语言程式来制造皇恩浩荡的幻象。生杀予夺大权,全在他一个人手上。正手和反掌,全在霎那间可以转换。《成败萧何》无疑也抵达了这样的意义拷问。此外,《成败萧何》还因为涉及到表现一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怎样被文化产生的这样的涵义,它还是一部元戏剧。同时,《成败萧何》在树立成语辩证意义的同时,也瓦解诸如“皇恩浩荡”、“天之骄子”、“生杀予夺”这种顺民式的思维程式和框架。“话语”流行背后的文化是这样的:真理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或“世上本无真理”。
2、萨拉·凯恩的《摧毁》(Blasted,1995)
萨拉·凯恩的《摧毁》(Blasted)首演于英国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它的剧情如下:病入膏盲的中年记者伊安与弱智的年轻女孩卡丝在英格兰利兹的一家豪华旅店相会,伊安对卡丝施暴。隔夜之后,爱尔兰内战爆发,一位士兵的突然闯入,将犯罪者与受害者的角色翻转,伊安不但被士兵强暴,双眼还被活生生地吸出,吃掉,瞎了眼的伊安在饥饿难耐之下,活剥生吃了卡丝带回来的死婴。[5]
它运用的策略,却是切合时代主题的:通过场景和境遇的突然转换(过渡的直接,类似蒙太奇的硬切)来凸显话语和语言暴力这个主题。场景的转换:从利兹一家高级宾馆,一下子到了战场——对应着话语的转换:语言暴力到政治暴力。而中间无过渡的这种突兀设计,正是主题蕴含的地方:它要揭示“语言暴力即政治暴力”的这个“即”(中国语境中具有万物对应的意蕴)。背后的隐喻是这样的,家庭的语言暴力,等于战争暴力。这样的戏剧空间我认为等于通过空间的并置来说明内部结构的相似性,它们之间或许缺乏逻辑关系,但是,空间的并置本身却共同臣服于一个母题:内部暴力等于战争暴力。在 “高级旅馆-战场”两个势不两立的空间之间的跳转和置换,权力和话语存在内在镜像关系之主题呈现了清晰的维度。
在英国皇家宫廷剧院的官网网站上,对于这个戏剧主题关于国内暴力(domestic violence)和战争相关暴力( war-related violence)之并置策略和观众反应,做了客观描述:“该剧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首演后,成为剧界三十多年来最受争议的作品。然而世界著名的戏剧家品特(Harold Pinter)及邦德(Edward Bond)却高度评价她的作品。自莎士比亚的《泰特斯·安德鲁尼克》以来,尚无一部剧作能运用这般锐利的幽默及深刻的心理洞察如此深入地刻画了人性的堕落与残忍。”[16]用中国的习语、成语去概括《摧毁》的语境,则我们可以找出:“天有报应”、“两两相对”、“上天有眼”等反应对应关系的成语。中西戏剧,不仅主题相似,其揭示话语的“共相”也说明一种超越思维固有界限和结构的存在。
“话语共相”戏剧的适用性和逻辑结构
在上面的关注人类生存于不同地域却有着同样话语困惑主题的戏剧案例中,我们发现,其共同点是均生产在20世纪的80年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十年。因此可以看出,“话语”问题或者话语暴力已经成了全球化时代的戏剧主题。话语戏剧关注人类存在的深层困惑,它超越国界,与人类表演学倡导的“多国表演”的趋势平行。在这个模式里,剧作家不再为某一特定的群落而写。“话语共相”戏剧消弭了国界,它通向国际性表演性舞台认知能力(internatinal performance literacy)”的剧场新认知。具体话语上,《东方三部曲》(英国)、Walk Together Children(美国)、《房间》(英国)、《送菜升降机》(英国)、《无人之境》(英国)、《背叛》(英国)[17]、《杜甫》(中国大陆)、《鹿鼎记》(中国)、《奥利安娜》(美国)、《部落》(英国)、《摧毁》(英国)、《怀疑》(美国)《wireless》(匈牙利)、流行在欧美的Devised Theatre(例如蒋维国导演的《太阳不是我们的》)等均可以称为揭示话语共相的戏剧。
在《奥利安娜》《成败萧何》《摧毁》等戏剧中,我们看到,顺应全球化时代的语言融通,这些揭示“话语共相”的戏剧还具有一种“台词脱域”的特征。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在《什么是少数文学?》这篇论文中,以德语世界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卡夫卡的例子,说明了“少数文学”的写作特征,它们具有如下特在:(1)语言解域;(2)文学中的一切都是政治的[18];(3)在这种文学中,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即语言的解域化,个体与政治直观性的关联,以及表述的集体组合;[19]这样,像类似卡夫卡在德语世界里操练自己不太熟悉的文字,其写作就具有这些由于文字的陌生化导致的语言不繁缛然而话语却被强调了特征。
这也是全球化戏剧写作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在这些话语戏剧里,台词都不约而同走向了简单化。比如卡夫卡的写作,不属于纯粹的资本社会现代主义时代的写作,按照德勒兹的说法,他是“从资本主义的纯粹写作中脱域出来”的写作。而品特,则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的极度简约的戏剧台词中也几乎是拒绝“可辨认的国家和地域特色”的。从哈罗德·品特、大卫·马梅特等人的剧本中,我们发现了一种通行于新舞台的趋势——极简化的国际舞台语言的未来趋势,这也是“去文化”的倾向(即在这些戏剧中,当地文化的丰富性。去文化的台词等于承认了多国表演或者国际性舞台认知能力的前提:即任何文化都没有优先权)。
揭示“话语共相”的戏剧一般拒绝二元对立,或者说,对这种造成全球化交流困境思维障碍的消除,正是戏剧的革新目标。当今社会的不同话语和权力的抵牾,一定程度上是历史上西方对于话语体系的垄断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合力所造成的,这种垄断和专制既包含了西方以技术和宗教控制世界文化霸权的延续,也包含了东方集权的封闭、封建对于民生的涂炭。既包含了西方对东方的征服,也包含了东方对西方的媚俗想象。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发现的那样,传统的东方学具有无意识中对于西方的臣服意识:“东方主义是关于东方的思想、信念、陈语或知识体系,具有‘体系自身统一性、保存着不随社会变化而变化的有关东方’的观念,如东方的怪异、落后、麻木、懒惰及女性洞察力等。”[20]又如霍米·巴巴对于“西方多元性这个透明范式的建立,表面上促进了交往,实际上成为文化‘围堵’的工具”的辩证发现[21]。这些悟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当今世界的不同层面和区域的话语冲突将持续下去。话语冲突的泛滥也表明,当今社会实际依然与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和公共空间建构的设想相去甚远。揭示“话语共相”的戏剧剧场实际上还是一个人类交往的替代空间。揭示“话语共相”的戏剧模式应该是取消形式和内容的对立,也一定程度上瓦解题材和主题的绑架,需要一种为着这个不确定性(认识、话语、哲学、思维、语言)等方方面面的混杂性特征[22]栖居的表演场所。可以说,全球化时代下,提倡揭示“话语共相”的戏剧正逢其时。
除了混杂性、不确定性、不可通约性等这些特征之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倡揭示“话语共相”的戏剧模式还应该表现出一种真正的不为“他者”等观念劫持的跨文化特征;在表现手法上,揭示“话语共相”的戏剧,往往表现主体的漂移、漂泊,没有对固定的、坚定的、游移的信念做出终极性价值判断的武断,虽有落入随遇而安、醉生梦死、看不见未来的虚无主义的可能,但却以拒绝僵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揭示“话语共相”戏剧的维度里,所有在二元范畴里建立的爱憎分明、非彼即此均需要反思和“重访”。
揭示“话语共相”戏剧能量的采得需要策略。在改编或者原创的时候,戏剧剧本和全球化人们的生存境遇达成一种相似的情感结构,即主题的勾连。具有后殖民特色的城市如印度的班加罗尔、中国的上海,在其戏剧的主题上,走向了后现代的一致性。在形式的呈现上,却依然五花八门。如宁财神从金庸原著《鹿鼎记》改编的同名话剧,在原著剧情框架不变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加料和重构。这个戏剧,经过与原著写作时间几十年的跨度,在当下要表达的是一种超越狭隘社群和政治划分的那种机械性给人的窒息,它要表现社会阶层的一种模糊性而不是确定性。这个戏剧的改编者顺着金庸的路子,彻底瓦解了人们关于皇权和民间界限的传统认知,也突破了思维惯性,作为一种话语策略,话剧《鹿鼎记》其实想到达到的是对政治的一种瓦解和救赎,以及我们当代人压抑人生的一种痛快的宣泄。它这样的策略,带起的情感结构是被观众认同的。因此,刘剑梅这样评价:“在这个戏剧里,韦小宝是好人还是坏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身便是一个杂体,而他又能轻易地平衡社会上的所有杂体。这杂体不仅对所谓的男性‘理想人格’提出质疑,也对任何固定的本质化的写作立场提出质疑。”[23]
还有一种戏剧方法上的揭示“话语共相”。即戏剧形构的并置特征和营销的无国界特征上的“共相”。前者,可以从张广天《杜甫》等剧场十分“盈满”[24]的戏剧实验中获得对于当今戏剧潮流反叙述的理解;后者,如美国的百老汇、中国上海的戏剧大道、德国柏林的戏剧剧院营销均采用的戏剧俱乐部式的操作。中国的戏逍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会员制、与德国的观剧俱乐部相仿。而且,它们有一点十分相似,即观剧俱乐部一般都是独立的非赢利性机构,它们最经常的工作是买票、分票,为每个成员选择合适的日期和座位。除此之外,他们还编辑分发免费的戏剧文化杂志,组织成员参观剧场、排练、与戏剧家讨论等活动,帮助剧院进行民意调查,帮助政府进行文化政策方面的咨询。这样的趋势,也说明揭示“话语共相”戏剧外延可以不断拓展的事实。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揭示“话语共相”戏剧的跨国界传播,也提供这样的“后现代景象”:至今,人类生活在一个大众传媒、远古甲骨文化石考古发现、经文、宗教教义、口头语、书面语等媒介一起混杂使用的时代,人类的语言在象征、借用、比喻、反复的世界里,不仅模仿文学、电影和戏剧,也创造让戏剧模仿的语言。文本、表演、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正在打破;在网络时代,戏剧性的引发因子,看似被“后现代”(利奥塔尔)和“虚无主义”(尼采)、“无政府主义”(如德勒兹)和“新历史主义”(福柯)削减了,实际上这样的虚无和式微并没有发生。原因之一便是网络化时代携带虚拟性和数字性特征,这些特征对于人类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提供史无前例的便利,也在扼杀人类的创造性;它提供虚拟的、泛滥的视觉堆积,也屏蔽了面对面交往的冲动。由于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二元藩篱依然绑架着思维,以及一种匿名世界性(anonymity of worldliness)的越界观念的匮乏[25]。人类关系依然走向狭窄的敌意的可能性。话语和性别冲突在本质上没有消除的可能。所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更应该掌握一种舞台的国际性认知,我们称之为知识的“共相”。
正因为揭示“话语共相”戏剧揭示出当代人的存在困惑,因此,它也是朝向开放可能性的、一种带有元戏剧倾向的当代戏剧趋势。它的第二步应该是:超越“揭示”的阶段,在舞台上实践如何解决话语冲突这一人类境遇的“共相”。
注释:
[1]Janelle G. Reinelt , Is Performance Studies Imperialist? Part 2, TDR: The Drama Review(Volume 51, Number 3 (T 195), Fall 2007.pp. 7-16.
[2]同上。
[3]The Orientations Trilogy, 由英国Border Crossings公司出品,该剧剧本见书籍:Border Crossings, The Orientations Trilogy Theatre and Gender: Asia and Europe, by Border Crossings Ltd, 2010.
[4]彼得·布鲁克《西服》(Suit )中国版,上海戏剧学院上戏剧院2012年12月20、21日演出,此剧演出时采用了中国、英国等不同国籍的演员。
[5]维科的观点与海德格尔有差异。后者关于人类存在和栖居的概念,前者倾向于人类具有大同的思维形构这样的文化观念。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本真状态唯有与世隔绝的孤独个体方可获得。卡西尔在《符号、神话与文化》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进行了批判。因为,海德格尔提供的人类存在之前提并不能完全通达文化,即人与人之间的某个交往空间之私密性。(德国)海因茨·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评哲学五题》,邓文华翻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页。
[6]卡西尔关于这个问题的阐述,具体见(德国)海因茨·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评哲学五题》,邓文华翻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0页。
[7]见《奥莉安娜》(Oleanna)剧本第一幕(Act 1). David Mamet,Oleanna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Inc. 1998.act 1.
[8]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9]同上。
[10]按照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里的说法,同语反复是典型的专制式的话语方法。
[11]汉语版《奥利安娜》于2003年9月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由吕凉扮演教授,赵思翰扮演演卡罗尔。后又复排,复排中的女演员龚晓还获得了第16届佐临话剧艺术奖最佳女主角奖。
[12](法国)于贝斯菲尔德著,《戏剧符号学》,宫宝荣翻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13]对于“第三空间戏剧”的论述,见本人论文《论第三空间的戏剧模式》,《四川戏剧》,2013年第一期。
[14]于帆,《〈成败萧何〉:引向深层历史文化反思》,《中国文化报》,2011年1月13日。
[15]李伟,《怀疑与自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
[16]http://www.royalcourttheatre.com/whats-on/blasted,登入2013年8月25日。
[17]这个被称之为Cross-racial theatre的案例,在美国的Williamsburg 的1950、60年代上演,演员有非洲裔和美国本土演员的混杂阵容组成,共有8名白人和6名非洲裔或者非洲-美国混合人演员。 见Bruce McConachie, Approaching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Grassoots Theatre, Performing Democracy,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p29.
[18]关于文学写作的泛政治化,也可见布朗肖的《文学政治学》等论文。
[19](法国)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合著《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陈永国翻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20]Edward Said, Orientalism ,Routledge Kegan Paul,1978, p205-206.
[21](美国)爱德华·索佳,《第三空间》,陆扬等翻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22]同上。
[23]刘剑梅,《狂欢的女神》,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266页。
[24](德国)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李亦男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9页,专门提及了后现代剧场的“场景盈满”现象。
[25]匿名世界性由卡西尔提出,是指人类接受特定文化之前的世界性。见(德国)海因茨·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评哲学五题》,邓文华翻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0页。
责任编辑 原旭春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