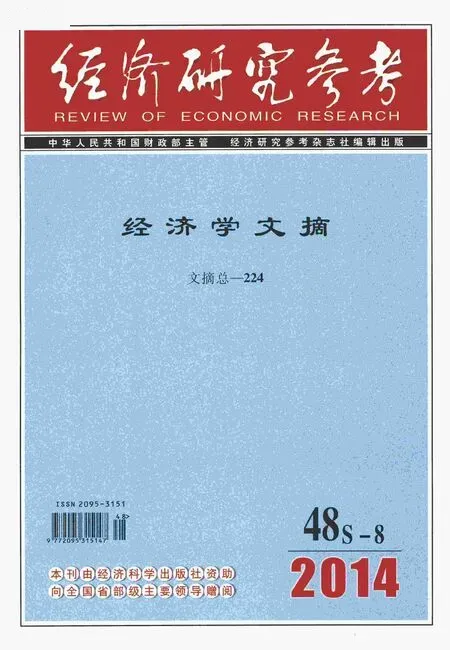中国宏观税负的合理区间
赵春晓 付敏杰
中国宏观税负的合理区间
赵春晓 付敏杰
罗森《财政学》开场白的第一句话是:“人们对于政府应该如何从事其资金运作的看法,深受其政治哲学的影响。”政治哲学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人们对于政府经济活动适当范围的看法,从而也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从而也就有了财政学中所谓的要素禀赋、效用主义和平均主义公平观之间的区别及其各种可加总情况下的复杂混合方式。由不同公平观及其混合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再分配偏好和再分配效率直接决定了“馅饼”的大小。在动态环境中,理性预期的纳税人可以直接将再分配效率内生于偏好之中,所以再分配偏好就成为影响各国宏观税负,当然也是中国宏观税负的首要因素。
已有的研究认为,居民的公平观和再分配偏好受到信仰、收入、职业等个人特征的影响,但是从总体来讲,偏好、职业和收入的差别在宏观层面上要远远小于微观层面,甚至还可以出现中和。对于居民偏好产生系统性冲击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社会哲学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都会深刻影响个人对公共部门、政府作用方式和政治决策进程的看法。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居民再分配偏好的扩张是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最明显的自然历史实验就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德国经历的国家分裂再到国家融合的过程,从而为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所强调的控制实验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历史背景。Alesina and Fuchs-Schuendeln(2007)的实证研究发现,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东德更加偏好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而东西德国之间由于45年(1945~1990)面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居民再分配偏好差距需要20~40年(1~2代人)才能弥合成完全一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已经达到60余年,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收入分配差距小而缺少激励: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长期的社会主义传统,会导致中国居民对于社会公平和再分配的偏好会更加显著的高于其他国家,导致财政政策用于收入分配功能的比重会更高,理应意味着更高的宏观税负。
影响中国宏观税负的第二个因素是计划经济传统所造就的政府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给宏观税负的上升提供了巨大空间。国家能力的核心是政府资源动员能力,而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社会体制为基础。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是以市场价格为基本竞争平台的政府强干预,分税制框架下的政府竞争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非价格补贴措施,竞相压低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利率)成本而实现了以供给面扩张为基本特征的低价格工业化和对全面市场的迅速占领,由此带来了中国奇迹。政府作为一个资源配置主体而具有了拓展市场的企业家职能,是中国生产型政府的典型特征,也是造成中国诸多结构问题的根源。中国政府的强资源动员能力,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平台上,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土地等公有制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形式的税收或租金收入,其作为资源实际控制者的角色使得可以通过扭曲资源价格来增加相应的政府收入,从而会对应更高的宏观税负水平,这无疑与众多发展中国家脆弱的国家能力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个因素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财政政策理应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扩大相伴而生,而控制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是财政的主要功能。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明确,现代政府支出的绝大部分是转移性支出,用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由于中国没有公开的家庭调查数据,根据各种已有数据估算的个人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迫近了0.5的警戒线。由于缺乏财产税等直接税种来减少私人财富的累积速度,建立在私人财富起点上不平等逐步加剧。结合前面我们对于国民分配偏好的分析,社会主义传统会使得中国国民更加注重平等,这样就必须要求高税率的财产税和较高水平的公共支出,以减少私人部门的收入分配差距。
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居民具有更强的再分配偏好和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从而意味着相对而言更高的宏观税负,而中国政府极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又为宏观税负的攀升提供了现实基础,所以在同等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由财政功能所决定的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会明显高于一般国家。
(成林摘自《地方财政研究》2014年第7期《国际宏观税负演进趋势与中国的合理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