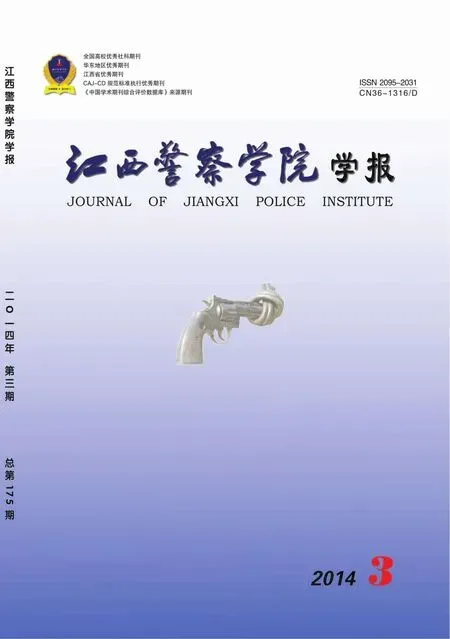论晚清的法治思潮与法政教育的兴起
刘白杨
(江西警察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0)
论晚清的法治思潮与法政教育的兴起
刘白杨
(江西警察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0)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了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艰苦探索。经过西方传教士的传播、留学生的引进、维新派思想家的宣扬、清政府官员的主张,法治思想得到广泛响应,汇成晚清的法治思潮。这股法治思潮为法政教育提供了营养的土壤。在获得对法治思想的高度认知之后,维新派思想家、清政府和社会舆论从培养法政人才——建立法治国家——救亡图存这一逻辑出发,推动了法政教育的进程。
晚清;法治思潮;法政教育
一、研究缘起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法律思想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从此开始了中国传统法律的近代转型历程。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法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而且绵延不绝,形成了自成系统的法律体系。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产生了激烈的碰撞。由此,近代中国鼓荡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法治思潮。在这个过程中,法政教育迅速兴起,并一时臻于兴盛。研究晚清法治思潮与法政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促进我国的法政教育、进一步建设法治国家有重大的意义。
晚清法政教育和法治思潮是近代法律史领域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十分显著,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汤能松以专著的形式对近代法政教育的发展历程、管理机制、课程设置等内容多有探索;[1]王立中论述了近代中国法政留学教育的动因、状况及影响;[2]宋方青分析了近代法律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3]并总结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侯强等人阐释了民初法学教育及其对近代中国法制化的影响;[4]李贵连还开展了法律教育机构及教育家的个案研究。[5]
赵竹芹对近代以来中国“法治”思想所经历的历史转变进行了探讨,[6]认为近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主法治取代专制独裁成为社会的主流。张晋藩从理论和历史的结合上,阐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法学与法治的发展过程与时代特征,并提出法学与法治互补互动的反思。[7]刘家波对近代西方法律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途径展开了探索,认为传教士、商人、留学生、驻外使臣等皆为西方法律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8]
二、晚清的法治思潮
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做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合理诉讼程序的现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法治有内容和形式之分,法治的内容是指根据法治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各法律主体应有的权利义务和实然的权利义务,其形式是指根据法治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各法律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形式和存在形式。
鸦片战争后,传统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儒学治国的大清帝国的治乱循环被完全打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向何处去?在“东渐”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强力冲击下,志在“救国图强”的有识之士开始了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艰苦探索。一时间,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法治思潮就是其中颇成规模的一股。西方传教士的传播、留学生的引进、维新派思想家的宣扬、清政府官员的主张,法治思想通过这些途径得到广泛响应,汇成勃勃涌动的大浪潮。
(一)西方传教士的传播
1887年上海广学会创立,该学会的主要成员是英美传教士,它出版了许多传教士编译的作品,如《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宣传西方的民主法制;1868年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 《万国公报》是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的主要窗口,该报大量刊登介绍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文章,广泛宣传西方的法律文化。它在发行量比较大,在1898年甚至发行了38400份,影响遍及全国。[9]另外,《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等刊,也向中国传播了各类法律知识。西方传教士在翻译西方法学著作方面的贡献更大,中国历史上引入的第一本法学著作《各国律例》就是林则徐让美国传教士翻译的。丁韪良和傅兰雅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翻译了诸如《万国公法》、《法律医学》等著作上百种。他们也参与了近代早期法律教育。传教士对介绍西方法律知识、引入西方法学、启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法律意识作了重要的贡献。[10]
(二)留学生的引进
中国近代的留学生是活跃于近代史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晚清的法治思潮也离不开他们的推介和鼓吹。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回国后一度担任过香港高等审判庭的译员和见习律师,并曾将派森的《契约论》和一部英国法律书籍翻译成中文。[8]1874年赴英留学的伍廷芳则是第一个系统接受英国法律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成为清政府推行西方法律、实行“新政”的重要人物。19世纪最后的那几年,清政府更是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学校了日本的政治、法律等知识,从1896年的数十人发展到1906年的八千人,他们接受新思想后大多变成了民主法制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也成了“新政”的主力军。
(三)维新派思想家的宣扬
早期开明派的代表梁廷枬所著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本系统介绍美国通志的著作,在书中他曾极力赞扬美国的法治。郑观应主张国际间关系以法来维系,王韬、马建忠等人都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大力推介,然而他们的思想还是比较粗浅,缺乏理论阐释和践行。真正将西方法律制度运作到制度层面上的是康、梁等人。康有为特别着重于改革专制制度和制定资本主义法律上,认为它是变法问题的核心与关键。他对三权分之、责任政府、司法独立、宪法至上等学说的认识是当时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最高水平。而梁启超则是近代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他的法治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系统总结,更是他在政治实践中对西方近代法治观念大胆吸收的产物,是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结晶。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在当今仍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清政府官员的主张
清政府官员中的开明人士,如驻外使节、出洋考查人员、出使大臣等,为西方法律思想的输入和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认为西方重法治而中国讲德治,西方国家由于法律制约,君主不能胡作非为,国家政治也不会因为君主的改变而发生混乱。对日本法治有较多介绍的是首任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翻译日本近代法的开路人,还是学习日本新法的第一位实践者。黄遵宪对现代法治理念有了一定的把握,强调了法治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作用,否定了中国传统德治的合法性,认为中国传统统治秋序是不合时宜的,并宣扬了西方法治模式的先进性,这对中国人心目中传统的意义秩序是一个有力的冲击,鼓舞了民众反抗列强、推翻满清统治、争取个人权利的斗志,他的改革思想时后来维新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1]
晚清的法治思潮是在国门被船坚炮利打开后,一些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而掀起的。在积贫积弱的晚清中国,这股法治思潮被社会各界视为解救危亡的法宝,不计其数的法政人士涌入思潮,为建立法治国家努力奋斗。学法律、兴人才、立新政成为晚清挽救危局最直接、最重要的行动。
三、晚清的法治思潮与法政教育的兴起
庚子之战后,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亡,下令实行新政,稍后又下令仿行宪政。新政和立宪推动了法律改革,法律改革又推动了法律教育。1904年,清政府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指出,“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学堂内讲习政法之课程,乃是中西兼考,择善而从。于中国有益者采之,于中国不宜者置之”,“政法一科,惟大学堂有之,高等学堂预备入大学政法科者习之。此乃成材入仕之人,岂可不知政法,果使全国人民皆知有政治、知有法律,决不至荒谬悖诞,拾外国一二字样一二名词以摇撼人心矣。”[12]1905年,京师法律学堂的建立,为各省法政学堂的举办起了先导的作用。到了1909年,全国共有学堂 (指高等教育层次)127所,学生23735人,其中,法政学堂47所,学生12282人,分别占学堂总数的37%和学生总数的52%。[1]法学教育一下成为教育主体的势头,盛极一时。
近代法政教育虽然是立宪运动推动起来的,但不可否认,晚清的法治思潮是为法政教育提供营养的土壤。在西方先进法律文化广泛传播、法治思潮得到高度认知的情况下,清政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法政教育运动。以下从维新派思想家、清政府、社会舆论三方面出发,探究他们对法治思潮和法政教育的有关言说和主张。
(一)维新派思想家
提及维新派思想家对法治的推崇和宣扬,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梁启超。继早期改良派对法治的引进,梁启超是登上法治舞台的第一位主角。他在学习、翻译、宜传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中,形成了自己的法治思想,并对以后的政治秋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是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是近代宣传新学、致力于民主法治启蒙的思想家,它的法治观一时左右着典论,久久影响着学术界,他本人也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积极作用于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局势,断然宣称:“法治主义乃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3]梁启超把“法”说成“天下之公器”,认为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并进一步认为“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可能更微于近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籍曰有之,而不能舍法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14]梁启超高瞻远瞩,认为法治是将来世界之必然,并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法治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历观中国数千年治乱之道,有乱之自君者,如嫡庶争之,母后擅权,暴君无道等是也;有乱之自臣者,如权相篡弑、藩镇跋扈等是也;有乱之自民者,或为暴政所迫,或为饥馑所驱。要之,皆朝廷先乱然后民乱也。若立宪之国,则无虑是……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15]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梁启超认为法治主义是当今中国医治沉疴,振兴国家的苦口良药,而法治的实现又依靠新型法政人才的培育。1896年,梁氏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其中又以讲求法政之学培植法政之才为本。[16]一年之后,梁启超在订定湖南时务学堂功课章程时,设 “公法学”,内含“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旨在培养中国急需的“政才”。[17]
(二)清政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法政与国家富强的紧密关系,日渐为国人所辨识。中国著名政治史家李剑农曾说:“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一个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中日和日俄的两次战争,便是最明白的证据。”[18]正是基于立宪能够救国强国富国的考虑,清末才可能走上筹备立宪之路。
清末法政教育的兴办,最主导的力量乃是朝廷和地方重臣,官立的法政学堂通常由朝中大臣或督抚奏报设立。清政府官员对法治的认识大多一知半解,却从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中认识到法律、新政与救时济世的紧密关系。身为修律大臣的伍廷芳将法律、法制视为“内政外交之枢纽,将欲强国利民,推行无阻,非专设学堂、多出人才不可”。[19]立宪派人物端方主张大力兴办法政教育,广造法政人材。他以为“朝廷注重法治”,并认为“法政为立宪基础,尤近今切要之图”。[20]东北三省总督徐世昌在奏设奉天法政学堂时说:“预备立宪,百务更新,……所有行政官员自应竭力养成,多方勤勉,使之研究法治之原理,以为推行新政之预备。”[21]由此可见,此时的清政府大员是在战败于人的痛心疾首中获得对西方法律文化的认识,是在民族危机中思考法治对救国兴国的意义。濒临灭亡的清政府把法治、新政当成了救命稻草,法政教育在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中产生了,声势浩大、丰富多样,而且迅速臻于鼎盛。
(三)社会舆论
清末新政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新型政治法律制度要求具有相应法律观念和法律知识的专门人才职掌操作。早在 “新政”之初,伍廷芳就指明新政进行对新式法律人才的需求,称:“法律成而无讲求法律之人,施行必多阻阂。”[22]与此同时,舆论界也多有关于新式法律人才需求的言论。《申报》有文指称:“今日者,国事危矣……论者每归咎于国家人才之缺乏。夫国家之人才,果真缺乏哉。所缺乏者,明法政之人才也”,进而认为“国之中有一人明法政,则国之中多一劲旅,有数十人明法政,则多数十劲旅,有千百人明法政,有亿万人明法政,则多千百亿万之劲旅”。[23]《大公报》亦有文曰:“夫既为国民,孰不宜明法律。识时者之言曰:中国欲强也,以法律思想普及为断旨哉”,认为急宜推广法律学堂,使京内外官吏皆成为“法律中人”,以行法律、亲百姓、救国家。还认为应通过法政教育向人民宣扬“非法律不足以立国”的思想,“凡有学堂之处,无论高等中学小学蒙学,分别高级法律初级法律,悉数增入法律学一科”,国民有发达的法治思想,国家才能立宪,国家才能发达。[24]
清末新政时期,伴随着新式法律教育的快速发展,通过译书办报传播西方法文化的速度也明显加快。湖南留日学生1902年编辑出版的《游学译编》,就以翻译西书为主。据统计,1902年《新民丛报》刊行24期,一期中首篇和第二篇的内容属于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就占了23期。其他刊物,如《国民报》、《湖北学界》、《江苏》、《醒狮》、《民报》、《复报》、《河南》、《江西》等,或专门开辟“法政”专栏,或经常刊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和法学的译著文章,无不注重对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介绍。[25]由此,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西方法文化传播热潮。
清政府实行新政之后,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输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出现了明显的飞跃,西法东渐的速度也明显加快,致使法治思想纵论于朝,横论于野,不仅在知识界广为流传,而且在市民乃至工农群众中间也家喻户晓。以至于民国建立的第二年,张东荪就指出的,“中国之当为法治国,已为全国上下所共认”。
四、小结
近代法政教育在短短数年内迅速兴起并走向极盛,这当然是法治思潮下开明之士寻求救国之路的结果,但近代中国的法政教育却没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最终没有形成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严密的法律教育体系。
由于近代法政教育的发展历程并非传统社会的自我演进的结果,而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法律转型之下的单方面行为。这当然与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紧密相关,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旧秩序下的法治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是被国人祈望的一根救国魔棒,法治思想没有渗透到全体国民的心里底层,成为他们的心理需要。所以,它在近代中国的式微也是必然。但这并不否定一代代仁人志士追求法治理想而为法政教育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也并不能否定法政教育曾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法政人”。尤为重要的是,经过教育家们的宣扬和实践,为后人逐渐积累了一种“文化动力”,时刻激励着国人培养法律人才、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
[1] 汤能松.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 [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2]王立中.论近代中国的法政留学教育及影响[J].史学月刊,1993,(3).
[3]宋方青.中国近代法律教育探析[J].中国法学,2001,(5).
[4]侯强,陆建洪.民初法学教育与法制现代化[J].法商研究,2003,(6).
[5]李贵连.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李宁,赵竹芹.试论近代以来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沿革[J].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7]张晋藩.总论百年法学与法治中国[J].中国法学,2005,(5).
[8]刘家波.近代西方法律思想在华传播途径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6.
[9]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61.
[10]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08.
[11]李宁.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与政治秩序的互动——关于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理性思考 [D].陕西师范大学,2002.
[12]张百熙,等.学务纲要[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04-206.
[13]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A];范忠信:梁启超法学文集[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4]梁启超.管子传[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C].北京:中华书局,1989.
[15]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97.
[16]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A];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集[C].昆明:云南出版社,2001.
[17]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07.
[19]伍廷芳.奏请专设法律学堂折[A];丁贤俊,喻作风.伍廷芳集(上册)[C].中华书局,1993:271-273.
[20]端方.法政学堂办法折(宣统元年闰二月)[A].端忠敏公奏稿(卷十三).北京:文海出版社,1967:1615.
[21]徐世昌.东督徐奏奉天法政学堂并考验办法折[N].申报,1908-06-14.
[22]沈家本.法学通论讲义序[A];历代刑法考(四)[C],北京:中华书局,1985.
[23]毛怀新.论研究法政为今日之急务[N].申报,1910-03-27.
[24]论宜推广法律学堂[N].大公报,1906-06-30/07-01.
[25]侯强.论近代中国法律教育人才观的变革[J].大学教育科学,2007,(2).
责任编辑:黄永强
DF09
A
2095-2031(2014)03-0121-04
2014-03-10
刘白杨(1983-),女,江西永新人,江西警察学院思政部讲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