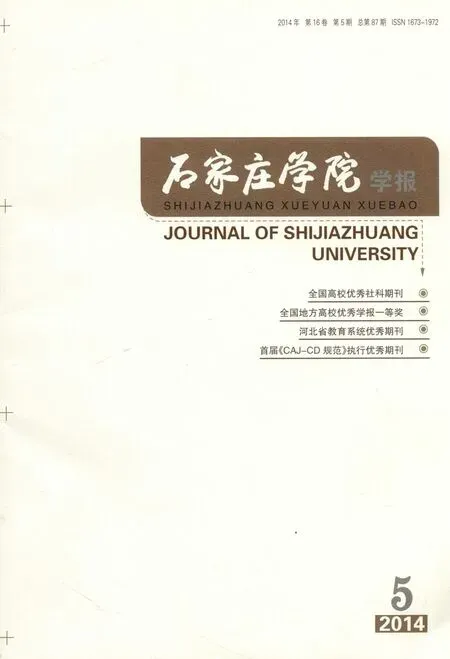诗人已逝 神话犹存
——略论罗曼·雅各布森的神话诗学
江飞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诗人已逝 神话犹存
——略论罗曼·雅各布森的神话诗学
江飞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罗曼·雅各布森不拘一格地将作者、文本与语境统一起来,服务于生平与作品关系的研究,揭示出诗人的诗歌神话即诗歌文本潜在的深层结构所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被形式诗学所抛弃的“作者”和“语境”要素的决定价值,实现了对当时盛行的“庸俗生平主义”研究和“反生平主义”研究的超越。雅各布森的神话诗学既不同于“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文论,也不同于纯粹“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文论,而是综合运用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究诗歌文本意义生成的条件机制。
雅各布森;诗歌神话;作者;文本;语境
作为结构主义神话学研究的先驱,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年)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其对法国结构主义神话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产生了重要影响,更在于他提出了自己独特深刻的神话诗学理论。1930年代,雅各布森相继写下《论消耗了自己诗人的一代》(1931年)、《什么是诗歌? 》(1933-1934年)、《论艾尔本作品中的神话》(1935年)、《普希金诗歌神话中的雕像》(1937年)等一系列文章,细致生动地阐述了自己的神话诗学主张,“作者”“生平”“语境”“神话”一跃成为其语言诗学(linguistic poetics)的关键词。在这些文章中,雅各布森不拘一格地将作者、文本与语境统一起来,服务于生平与作品关系的研究,虽然其结构分析的重心依然在于探求文学文本的语言系统,但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自己早期的纯粹形式主义诗学立场,复活了被形式诗学所抛弃的“作者”和“语境”这两个要素的决定价值,使文本从一种自足封闭的“语言”变为具有个人性、目的性和现实性的“言语”,从而实现了对当时盛行的“庸俗生平主义”研究和“反生平主义”研究的超越。时至今日,这种神话诗学理论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一
在《论艾尔本作品中的神话》一文中,雅各布森明确说道:
神话是首要的,它不能被取自任何东西,也不能被降减为某种东西。它是一个幻影(phantom),因此不可被理性地和寓言地解释。它是客观的,又是强制的。它由内在的、固有的法则单独控制。它有其自身的真正的标准,有其自身的深奥话语。它先于历史,而且是不朽的。神话只充分地提出现实,而不动摇现实;神话只是对难以表达的(inexpressible)东西的一种暗指。[1]381在这里,雅各布森主要强调了这样三层意思:其一,“神话”是一种特殊的、本源的、相对自足自治的世界,是一种具有客观性和强制性的形式结构,具有某种非理性的、超验的,甚至神秘的永恒性,当然,雅各布森并未言明其为何如此的原因。对此,美国宗教学家伊万·斯特伦斯基 (Ivan Strenski)做了很好的应答,他说:“神话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种积极地以非理性方式构成文化形式的典型规范。神话之意义,不假任何自治的逻辑力量而成,全然不似三段论逻辑那样,以演绎而成意。”[2]48由此可见,神话是人类以非理性的原始思维构造的“幻影”,不依赖于理性的逻辑演绎,按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神话就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因此对其进行理性的或寓言的解释是无效的。
其二,“神话”是一种既提出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有秩序的结构,有其自身独有的规则、标准和话语,从而确保其成为先于历史且不被历史轻易改变的本源。它寓居于各种文化形式中,以隐喻手段来表达现实,正如我们总可以在“莫名其妙”的神话故事中,发现当时的某些社会现实,如宗教、风俗、人伦等。比如“女娲造人”的创世神话,反映出史前时代母系氏族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原始先民对人类起源的最初想像。而在不同的社会现实、文化环境中诞生和传播的神话作品,多样性和差异性虽然显而易见,但在其中却总能发现某些同质性的神话创作功能或结构,这已为诸多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所证实,雅各布森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自己的结构音位学研究 (在繁多的音位中寻找极少的、共同的“区别性特征”),以及民间文学尤其是普罗普的功能理论(民间故事的形态学研究)中,[3]16明确意识到这种本原的、恒定的“神话”是存在的。因此,他专注于在某个诗人甚至整个民族的不同作品中,寻找和发现这种神话结构,并且不忘与现实和历史相结合。
其三,“神话”本身并非目的,它只是一种功能,一种特殊的符号代码,其所暗指的“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大而言之,那是人类从古至今试图参悟的社会秩序和宇宙奥秘;小而言之,正是文学艺术(以神话故事为源头)的形而上追求所在。正如清代文论家叶燮所言:“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4]30人人能说的理和事是浅显的、易表达的,而“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才是根本的、难以表达的。按雅各布森的意思来说,诗人之所以能够传达出“幽妙”之理,凭借的正是反复出现的神话“意象”,比如普希金的“雕像”。这意象不是突然诞生于文本语言中的,而是存在于诗人的现实生平中,甚至是内含于其民族的精神传统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语境的不同,也使“神话”具有了多种可能性,既可能是某个诗人的诗歌神话,也可能是某个民族的诗歌神话,本质而言,都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表征”。为揭示此种神话,神话学者必须坚持结构分析法,对神话的衍生文本(总体话语)进行深入的比较、发掘和阐释,以析取出晶体一般的神话结构;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默会”便足矣。
总之,在雅各布森看来,“神话”不仅是值得研究的一种口语传统,而且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要素潜藏在我们的所有行为背后。[1]300换言之,神话作为一种先验的、本源的结构,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为和方式,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元结构”。
二
对诗人生平事实和文本事实之间对应关系的研究,是雅各布森神话诗学的重要方面。其研究结果表明:所谓的真实的事实对诗人来说是不存在的,生活中的每个细节瞬间就转变成一个符号元素,并以这种形式与诗人紧密相连,也就是说,符号现象对他的生活是有效的,并且至少和真实事件一样重要,诗歌神话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就被自然而然地抹去了。当人类学家还在争论神话学思想的特性、范围、应用领域等问题的时候,雅各布森已率先以符号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文学领域中的神话问题了。
在雅各布森看来,诗人的诗歌神话是指“某种组织性的、凝聚性的恒定要素,它们是诗人多样化作品中的统一手段(或‘媒介物’),它们给这些作品打上诗人的个性烙印”[1]318。很显然,这个界定是有意含混且充满歧义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神话是诗歌文本隐在的深层结构,“结构的事实是第一位的”[5]676,存在于诗人想像的、易变的、多种形式的文本符号之下;这一隐在的恒定要素作为手段,把诗人的个人生平(生活)引入到多样化的诗歌主题之中,其目的在于在常规文学之上获得最大化的个性认同,使普希金的诗成为“普希金的”,使马哈的诗成为“马哈的”,使波德莱尔的诗成为“波德莱尔的”,或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神话,寻求它在传统神话学序列中的正当理由,如艾尔本的神话。这种“神话”乍看起来类似于某种标志性的作品“风格”,但很显然,作品风格不仅表现出作家主观的创作个性或装饰思想(意义)的修辞意图,更体现出某一特定时代、民族、阶级等属性,它并非恒定,常常是不断变化的,正如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所言:“风格不是一种形式,它并不属于文学的符号学分析的范围。风格其实是不断遭到形式化威胁的实体。”[6]220而“神话”则是内存于文本中的一种客观不变的深层结构,起着主导作用,控制着具体的文本结构(如韵律安排、行节设计、语义选择等)和功能机制,完成着对意义的直接表达,并对其他变化要素进行限制,同时还确保这些诗歌文本与一般语言的诗歌形式区别开来。
雅各布森之所以对诗人的诗歌神话进行研究,缘于两起接连事件:一是他的挚友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的自杀(1930年),二是他的好友帕斯捷尔纳克 (Pasternak)出版了著名的长篇自传散文《安全通行证》(1931年)。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悲剧和意味深长的死,促使雅各布森开始认真回想诗人的生活,而不是置生活背景于不顾,仅仅专注于诗人诗作的符号和韵律。在形式主义早期,雅各布森一方面为了建立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为了坚决区别于当时盛行的“传记学研究”(如赖帕、谢格洛夫等)、心理学研究等庸俗模式,不得不将“文学性”聚焦于文本本身,作者的生平因而被抛弃掉。而随着结构主义思想的建立,雅各布森又不得不寻回失落的“生平”,再次追问起作家生平与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之间的关系。这与其说是一种倒退,不如说是一种为了更好前进的战略性后撤。
生平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在浪漫主义时代被认为是“诗与真”的问题,即作为作家生活的“铁的事实”与呈现在作家作品中的“美丽的谎言”之间的一种明显的分裂。而19世纪后期的实证主义传统,则坚持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一种机械因果关系,把生平视为一个作家作品的主要原因。这两种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现实与心灵之间的一分为二的假定,而这种区分早在康德的哲学中已经错误地提出。此外,世纪之交的格式塔心理学,以心理—生理学的检测对哲学的客观对象进行了证实,他们认为,人们有意识的知觉(内在心理世界)不仅仅是对客观对象的外在世界的复制,而且与之形成一种同构关系。
相较于浪漫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的主观或机械,雅各布森的方法可说是既实在又辩证的,他通过指出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解决了因与果、现实与心灵的矛盾。他所坚持的是,在诗人的真实生活中,这两个传统上对立的领域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诗人自己的“神话”。也就是说,一方面,生平事实(biographical fact)可被诗人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人感知的方法来解释;另一方面,他自身所创造的诗歌事实(the poetic fact)能在他的生活中获得一种现实地位。比如,赫列勃尼科夫(Khlebnikov)几乎无意识创造的语言实验作品,引起他生理上可感知的种种情绪;而马雅可夫斯基则存在于他的生活情境中,而这生活情境在他的诗歌中被先在地或同步地创造出来;在后来对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的研究中,雅各布森更是揭示出诗人精神分裂症、言语交往障碍的生活与其诗歌的语言学症状 (丧失了人称和语法时态)之间的密切关系。[7]388-446可以说,“神话”是雅各布森在作者生平与文学文本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反馈系统,具有跨界、比照和综合的特性。
由此,这种“神话”观就对读者或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读者在阅读某个诗人作品的过程中,能够直觉地感知到某些神话要素构成了文本动力结构不可取消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读者的这种直觉力是值得信赖的;而研究者的任务就是遵从作为读者的这种直觉力,并通过一种内在的、固有的分析,从诗歌作品中直接提取这些不变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不变量(常量),而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可变组成部分的问题,则要查明在这种辩证的运动中,什么是一贯的和稳定的,从而决定变量的底层结构。雅各布森的这种结构主义分析思路与方法,是从比较语言学研究转化而来的,其意图在于以系统描述为先决条件,在作者生平和作品之间、作者单个作品与其作品系列之间,进行一种富有成效的比较,以确保对符号常量的提取与定位,从而与当时颇为流行的“庸俗生平主义”和“反生平主义”区别开来。
庸俗生平主义(vulgar biographism)是把文学作品当做最初的生活情境的再生产,并从一部作品来推测某种鲜为人知的情境;而反生平主义(antibiographism)则武断地否定作品与情境之间的任何联系。而在雅各布森看来,“把诗歌虚构作为一种现实之上的机械的超结构,以及排斥艺术和它的个性与社会背景之间关系的‘反生平主义’,这些庸俗观念是必须反对的”[3]144。“反生平”的立场与过分简单化的生平研究是等同的,文学批评家不应当也无法在诗人的个人命运与其文学生平之间划定严格的界限,因为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一个作品抽离出一种情境,同时,在分析一个诗歌作品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一种情境与一个作品之间重要的重复性的一致,尤其是一个诗人的几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普遍特性,与一种普遍地点或时间之间的有规律的联系,如果它们是相同的,我们也不应忽视作为它们起源的生平的(传记的)先决条件。正是秉持这种作品与生平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对应与比较研究,雅各布森对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的“超现实神话”进行了细致考察,在作品变量中寻找主题不变量,在符号系统中提炼深层结构。
三
在雅各布森看来,诗歌与神话是两种紧密关联同时又非常矛盾的力量,这两种基本力量之间的冲突在于:诗歌被定位于变化,而神话的目的在于不变。而这种关联和差异由诗歌和神话之间大量的相互关系所连接,也就是说,在种种显而易见的变化之下,潜藏着一个深层的、不变的诗歌神话。
举例来说,普希金的三篇著名的诗歌作品,一为戏剧《石客》(1830年),一为叙事诗《青铜骑士》(1933年),一为童话《金鸡的故事》(1834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不变量,即“致命的雕像”(destrctive statue),它预告和预见了诗人生活中的某些“致命的”事件。一方面,在作品中,雕像既是话语的客体,又是行动的主体,是具有造反精神的悲剧主人公(指挥官、彼得大帝、占星家)的化身,是一个“僵化的人”的形象;另一方面,雕像主题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凯瑟琳沙皇(即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背景也悄悄进入诗人的私人生活中,比如他的婚姻便建立在他祖父铸造的一尊凯瑟琳雕像之上,诗人半开玩笑半可悲地称之为“青铜祖母”;而诗人在故乡波尔金诺的三个秋天,对应于他创作生涯中 “雕像”神话诞生的三个特殊阶段:第一个秋天写《石客》时,诗人渴望妻子,却试图逃避婚姻,他的诗歌和绘画都充满着雕像的意象,他不自觉地回忆起彼得堡皇村的纪念碑和花园中的雕像以及少年记忆,并以雕像为主题写下了一系列诗歌,如《皇村的雕像》《皇村回忆》《在生活的开端》等,甚至还在理论文章《论戏剧》(On Drama)中讨论了雕像问题;第二个秋天写《青铜骑士》时,诗人年轻时的反抗与批判激情,此时遭到压制而被迫顺从,加上经济窘迫,不得不过着大理石般的没有自由的生活,在给妻子冈察诺娃的信中充满了伤感和猜疑,因此,婚姻生活在《青铜骑士》第八章中被略去,在该作初稿中,诗人称青铜彼得是一个偶像,并否定其权威,而在最终版本中却没有丝毫“好战”的踪迹;在第三个秋天写《金鸡的童话》时,一种嘲弄的怪诞风格取代了悲剧的彼得堡传统,一位被阉割的占星家取代了彼得大帝,一只塔尖上的公鸡取代了悬崖上的那个巨大骑士,此时雕像的牺牲者(即诗人)已经变老了,诗人对他妻子轻率的抱怨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而带给他致命的自我毁灭的决斗也随之而来。由此,“诗人的神话完整而有机地与它的不同变量融合在一起,以至于难以将这三部作品标题的主人公从神话中抽离出来,正如难以把他们与三尊真实的雕像混为一谈一样”[3]146。可以说,“雕像神话”成为诗人作品中独立自主的周期性的刺激物,是普希金生平和作品之间共鸣的音叉,三部诗歌作品成为了诗人的“个人神话”(personal mythology),三个雕像形象实质上是一个符号系统中的要素。雅各布森更敏锐地注意到:普希金这三部作品的诗歌类型随着雕像主题的消失也消失了——《石客》是诗人最后以诗歌形式写成的独创的、完整的剧本,《青铜骑士》是其最后的叙事诗,《金鸡的故事》是其最后的童话。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那么,神话诗学似乎只是对作家的作品和生活语境中的主题不变量进行追踪和提炼而已,事实上,对于雅各布森的神话诗学研究来说,这只完成了一半任务,另一半任务在于对这一诗歌意象和诗歌神话的内在结构进行深入探究,而这种探究必须要进入符号学的论域中才可能得以进行。仍以普希金的雕像神话为例,雅各布森继续关注的是,一种艺术作品(雕塑)转换为另一种艺术模式(诗歌)中的符号问题,对此,他明确指出:
一尊雕像,一首诗歌——简言之,每种艺术作品——都是一种特殊符号。关于一尊雕像的诗歌,因此是一个符号的符号,或一个意象的意象。在一首关于雕像的诗歌中,一个符号(signum,能指)变成了一个主题,或一个意指对象(signatum,所指)。[1]352
在诗歌中,符号的内在系统与符号间接指称物之间总有一种张力,这是任何符号世界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的“普遍法则”。而在一首关于雕像的诗歌中,指涉物自身又是符号组成的,即雕像符号成为诗歌符号的主题成分 (能指),成为诗歌语言所意指的对象(所指),因此,诗歌变成了“符号的符号”“意象的意象”,其结构表现为这两种符号之间以及它们与实在的雕像之间的对立与张力。笔者以为,雅各布森选择普希金和“雕像”是非常有眼光和启发性的。一方面,“雕像”是图像符号、索引符号和象征符号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主要的、多样性的图像符号,它的姿势和位置又是指向一个特殊情境的索引符号,而它在西方艺术的社会文化语言中的功能,又在一个特定的差异系统中提供给它一种象征的作用。另一方面,普希金非常喜欢的一种形式手法,就是把一个符号转变为一种主题的成分,由此在一个符号交汇的结构中,表现出一个主题意象自身所包容的冲突和对立。正如我们在上述三部作品中看到的,雕像无生命的、固定的物质形态与雕像所代表的有生命的、运动的生物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这一诗歌神话的内在结构,正如作品标题(“石客”“青铜骑士”“金鸡”)所显示出的根本对立和矛盾。
进而言之,在普希金的诗歌活动中,“雕像神话”是在有雕像介入的全部作品中唯一的恒久形式,这是一个症候;而在普希金的所有作品中,雕像意象又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的整个诗歌神话有机联系的,也就是说,在普希金的符号系统中,二元主义是其个性原则,雕像所具有的能指固定性和所指运动性,同样是其诗歌神话的内在结构,正因如此,在其诗歌中,“流水”“船”等具有动态特性的符号意象被频繁使用,同时,诗人又希望时光在短暂的睡眠中安静下来,把庄重的、平静的休憩与神圣美妙的“美”联系在一起,赞颂“永恒的沉睡”“庄严的安息”。雅各布森还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将“普希金作品中的雕像”按时间(1814-1836年)和文本(诗歌、书信、散文和绘画)制作成表,使得这一长达50页的细致入微的神话分析更加令人叹为观止。总之,雅各布森对普希金诗歌神话的条分缕析,预设了作者意图的一致性而采取了对应(平行)分析法,并效仿语言的结构分析法而创用了一种主题批评法,试图重新建构作品的内在隐喻。他将普希金不同时期创作的所有文本都视为一个整体(如一个句子),经由整体到部分、由变量到不变量的深入阐释,提炼出潜在的具有客观稳定性的深层结构(如某个音位),并发现其最本源的二元对立项(如音位的区别性特征),从而建构起纵横开阔又层层相连的神话诗学体系。
如果将上文当做是雅各布森神话诗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的话,那么,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则是他神话诗学研究的起点,带给他极大的震动。事件发生后,雅各布森闭门数周,思考诗人自杀的真正原因,终写成充满深情、悲愤与洞见的《论消耗了自己诗人的一代》。当时一些苏维埃体制内部的批评家别有用心地把马雅可夫斯基的死亡解释为 “纯粹的个人的悲剧”,雅各布森对此不以为然,他力求揭示出诗人自杀与历史时代之间的密切关系,发掘出植根于文本中的某种神话结构。在他看来,如果把马雅可夫斯基的神话翻译成思辨哲学的语言的话,那就是“我”(I)与“非我”(not-I)的对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造性的“自我”(ego)与他实际存在的“自身”(self)不能共存,后者无法接受前者,从而形成了冲突。这冲突又具体表现为“革命”“爱”“复活”“未来”等重复性的主题,而在此之下,存在着革命与诗人的毁灭、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的不朽与俗世的肉身、对未来的迷恋与对儿童的厌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自我”热切地呼唤来自未来的“一次精神革命”,相信超越死亡、征服时间的复活的胜利,然而,“自身”却堕入权力机制之下渺小的处境,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狭窄的生活和“爱”的折磨,孕育着这一代人无法平衡、无法和解的苦痛:诗人注定是“存在的弃儿”,是乌托邦理想的殉道者,是献祭于即将到来的普遍的、真正的“复活”的牺牲品。因此,当诗人在1930年4月14日饮弹自杀的时候,他那些诗歌中早已反复渲染的“自杀”主题,实实在在地被转换为一种“文学—历史的”事实。正如诗人叶赛宁死后,马雅可夫斯基说,他的死变成了一个“文学的事实”(literary fact),雅各布森也由此认为,“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中曾经想过的自杀主题,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文学手法”[1]373。
进而言之,无论是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还是中国当代诗人海子,他们都非常理解诗歌与生活的联系,并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预见他们的生活进程,而不是相反。这成为他们对“艺术现实主义”的某种界定,显示出他们创造自己命运的神话的预言意义。而仿佛宿命的“自杀”,更是将诗人的生活与文学作品升华至一个无以复加的神话顶峰:诗人已逝,神话犹存,这正是“诗歌神话”或者说“诗人神话”的魅惑所在。
总之,雅各布森的神话诗学既不同于“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文论,也不同于纯粹“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文论。因为其目的不在于求证作者意图或否定作者的主体价值,也不在于真空地提纯文本的内在价值,而在于综合运用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究文本意义生成的条件机制。其结果在于:以一种后撤的和更包容的结构主义立场,熔作者、文本、历史(语境)于一炉,突破了单个文本的局限,修正了自己早期只专注于文本本身的形式主义诗学的偏颇,并由此进入到符号学的崭新视域之中,为后来者如洛特曼建立文化符号诗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当然,其中隐在的问题在于,如果过于专注于从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寻找和抽象出共有的“神话”结构,如同维谢洛夫斯基(Veselovski)的“母题”,那么,将会导致普遍的、相似的共性掩盖特殊的、差异的个性,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每个作品毕竟都是独特的个案,而非仅仅只是神话结构的摹写,即便在摹写的过程中,不同的文本也是以不同的话语形式表现出不同的主观意图、社会指向和审美意蕴,这是不容否认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Jakobson Roman.Language in Literature[M].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美]伊万·斯特伦斯基:二十几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卡西尔、伊利亚德、列维-斯特劳斯与马林诺夫斯基[M].北京:三联书店,2012.
[3]Jakobson Roman,Pomorska Krystyna.Dialogue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4]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法]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裸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法]罗兰·巴尔特.神话修辞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Jakobson Roman.SWⅢ:Poetry of Grammar and Grammar of Poetry[M].The Hague,Paris and New York:Mouton Publishers,1981.
(责任编辑 周亚红)
On Roman Jakobson’s Mythic Poetics
JIANG Fei
(School of Arts,Anqing Normal University,Anqing,Anhui 246133,China)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nd works,Roman Jakobson unified the author,text and context.To some extent,this effort revived the determining value of two factors,namely,“author”and“context”,which were neglected by formal poetics and consequently excelled the researches of “vulgar biographism”and“antibiographism”.This study of poetic mythology,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author-centred”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text-centred”formal literary theory,multiply applies historicism,structuralism and scientific positivism methods to the research on the conditions of the formation of poetic text significance.
Roman Jakobson;poetic mythology;author;text;context
I052
:A
:1673-1972(2014)05-0087-06
2014-06-19
江飞(1981-),男,安徽桐城人,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西比较诗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