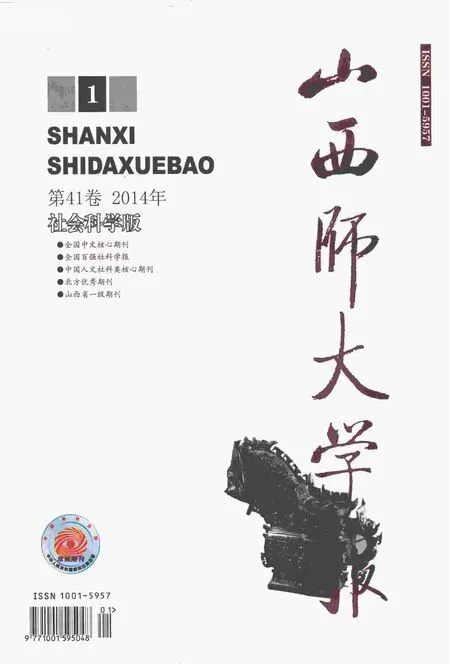对土改小说的认识与思考
吉晓萤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专门描写土地改革的小说,较为集中的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这两个时间段描写的虽然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土改运动,但因为这些作家生活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人生经历和社会体验不同,因而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时代性。当前已有的关于土改小说的研究资料倾向将土改小说分为“正统土改小说”和“非正统土改小说”两大类,以黄勇先生的分类来进行说明:最早进行土改小说写作的是丁玲、周立波等亲身参加过土改的老一辈共产党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仅是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品,更初步奠定了此后近二十年的大陆主流写作模式,黄勇先生将这类土改小说称为“正统土改小说”。张爱玲所写的与正统土改小说针锋相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乔良的《灵旗》,张炜的《古船》,尤凤伟的《诺言》、《合欢》、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洪峰的《模糊年代》等小说呈现出明显区别于“正统土改小说”的艺术风格,故将其命名为“非正统土改小说”。
一、对正统土改小说的认识和思考
在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讲话》的要求,反映土改运动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文学的中心内容之一。周立波、丁玲等一批作家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参加土改运动,将亲身见闻感受记录并抒写出来,在作品中宣传党的土改政策,讴歌土改斗争。代表作品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暴风骤雨》(周立波)、《邪不压正》(赵树理)、《秋千》(孙犁)等等。
“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坛规范文学的三大准绳”。在作品中,作家们大都采用政治化的口吻,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极力描写地主阶级的丑恶面貌,挖掘农民几千年来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人物刻画相对比较单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呈现出绝对性的二元对立。这种完全的阶级对立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参与性,但同时也使得农民在政治参与中产生了过度参与的行为,对待富农和地主没有区别,甚至有些乱打乱杀的行为。对于这些暴力行为,大多数正统土改小说作家在作品中都是简单略过,不做详细描述。
这些老作家们在作品中描画了生动真实的生活面貌,重现了土改对其生活以及心灵的深刻影响,使其作品如史诗般气势宏大。然而他们的缺陷同样很明显,“典型化”的描写使得作家的艺术表现受到局限,政治视角的单一切入,使得当时的历史真相及现象背后的本质无法得以真实的表现。他们笔下的农民,缺乏自主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程式而单一,难以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同时也束缚了作家们原本多元的创作风格,从而降低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
正统土改小说的典范性还体现在它所书写的土改运动的发生与进行,都严格遵守官方的一套完整工作模式或者程序,首先是工作组的进驻宣传,然后是诉苦大会和批斗大会的召开,最后是浮财分配。这种典范模式是涉足土改小说创作所不能绕过的,是土改运动本身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无论是正统土改小说还是非正统土改小说,在这方面是有相同之处的,只不过在非正统土改小说里,作家们或多或少地突破了这一叙述程序,或者说对这一模式框架内容作了改写。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老一辈作家笔下的土改运动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这种紧密的联系性使其作品具有庄严而神圣的内涵。但是历史观念和政治视角的限制使其艺术表现受到影响:作品中所出现的绝对的阶级矛盾,英雄人物与地主恶霸的对比刻画,固定的写作模式等使得客观历史本质和人性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等多个问题被忽略了,而年轻作家则对这一缺陷进行了有力的反拨,这点我们在下文进行详细的论述。
二、非正统土改小说的历史性视角和对人性的描写
虽然土地改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给当时的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许多作家在作品中争相描写土改运动,但随着历史的前行,土改运动渐渐被人们淡忘,尘封于记忆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西方新思潮不断涌入中国,中国出现了多元的文化意识,在不同的文化意识的碰撞中,人们开始尝试重新认识和界定一些历史现象和事件,企图理性而冷静的对这些事件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进行反思。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没有土改经历的作家开始了对这一历史的书写。主要的作品有《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古船》(张炜)、《灵旗》(乔良)、《诺言》(尤凤伟)、《白鹿原》(陈忠实)、《枫杨树故事》(苏童)、《预谋杀人》(池莉)等。
四五十年代的土改小说是权威话语即政治话语对弱势话语遏制与剥夺的结果,而80和90年代的作家们则祛除掉传统意识形态所赋予它的政治内涵,有意识地淡化了历史的政治痕迹,从人性的角度去关照和阐释历史,这种对个体命运的关照,对历史本质的阐释,还原了某些真实的历史现象,使我们看到了正统土改小说神圣内涵背后那被隐藏的另一面。在那些正统的土改小说里,人物的关系呈现出绝对的对立性,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情被淡化,而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则注重对人性的挖掘和塑造,包括扩大斗争范围的“过火”现象,积极分子的流氓劣迹,斗争中的暴力行为等。
正统土改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典型化”的积极分子,但是这些光辉伟岸,品质高尚的英雄人物,在非正统土改小说中却不见了光彩。在非正统土改小说作家的笔下,土改充满了权力的斗争和个人的欲望,甚至是复仇式的泄愤。非正统土改小说对干部流氓化这一现象的揭示,彻底颠覆了传统小说所倚重的、类型化了的任务形象,反映了土改的一些侧面和背后的内容,显示了历史的复杂性。
正统土改小说对斗争中的过火和暴力行为一般都是简单掠过或者回避,惯用暴力的是地主阶级,农民的暴力也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地主阶级的暴力历史只是在农民的控诉中被当做罪恶揭露出来,并没有具体描写出来。但在《故乡天下黄花》《诺言》《古船》这些小说里,作家们并没有回避暴力行为,而是对其进行直接描写。这些对暴力的描写多少受到当时整体创作环境的影响。文学远离了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情况,使得年轻作家不再向老一辈作家那样只能从单一的政治视角表现历史和生活,而是有了多元的选择。
三、两阶段小说的弊端及农民在土改中的政治参与透视
四五十年代的作家由于大多都是土改运动的经历者与参与者,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党的宣传者,其次才是作家,这种身份使得他们的小说难以摆脱政治的影响,创作主题多表现为对土改的宣传和歌颂,人物形象的塑造采取的是二元对立的写作方法,叙事则按照官方的工作程序,从这些方面来看,四五十年代的作家们可以说是政治内涵的代言者。
而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们则在作品中刻意揭露被老一辈作家多忽略的历史阴暗面,还原任何历史变革都会出现的血腥和残暴的一面,更多的从人性的角度探索、还原历史,关注历史中个体的生存和命运,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土改运动,缺乏直观而真实的感受,只能借助虚构和象征去描写土改运动,因而无法揭示这一运动的复杂性,导致他们的作品缺乏历史的厚重感。
在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农民的政治心理具有二元的倾向,兼保守与激进于一体,这种心理和参与的结果都对以后的历史进程起到了深远影响。在土改的推动下,农村原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都出现了根本变更,不仅在经济上,同时也在政治上严重打击了地主和富农,但在积极参与中也产生了过度的偏激行为,阶级成分的错划,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对待地主和富农方面没有区别,出现了乱打乱杀的现象,不必要的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
土地关系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要动员民众,关键就在于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复杂的土地问题,又使得农民在参与土改时呈现出复杂的政治心理。
四、土改小说对现在农村小说的影响以及对目前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借鉴意义
土改运动是20世纪中国乡村最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变动,真实地再现历史,是文学的使命。而土改运动中的许多枝蔓,依然对今天的中国现实存在着影响。当代作家应该冷静审视土改小说,深刻反思其经验和教训,从而使得中国的农村小说能够得到真正的进一步发展。
土改运动促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极大地改动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关系。但是土改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这无疑是当前备受关注的“三农”问题的原因。经过土改后农民真的获得阶级意识了吗?当前的农村社会,虽然在物质文化生活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在某些方面与土改前的农村社会仍然是相似的,城市文化占据主流,农村被边缘化,少数强势群体重新出现,他们的特殊地位和霸道行径,同“正统土改”小说中所刻画的地主恶霸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村的阶级差别和分化也日益加剧。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代表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充分调动其生产积极性,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问题。与以前相比,当下农民的政治参与度和生产积极性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但是大多数农村还存在着基层民主建设不够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淡薄的状况,这不利于实现我党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土地改革对于当前面临着新一轮转型的中国农村社会,仍不失其借鉴作用。我们仍需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汲取土改的历史教训,继承土改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1]陈非.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J].文学研究,2008,(6).
[2]贺仲明.重与轻:历史的两面——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土改题材小说[J].文学评论,2004,(6).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4]张懿红.简评当代小说中的暴力描写.甘肃教育学院院报(科学社会版),2002,(1).
[5]王锦辉.1947—1949年土改中农民政治参与的透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