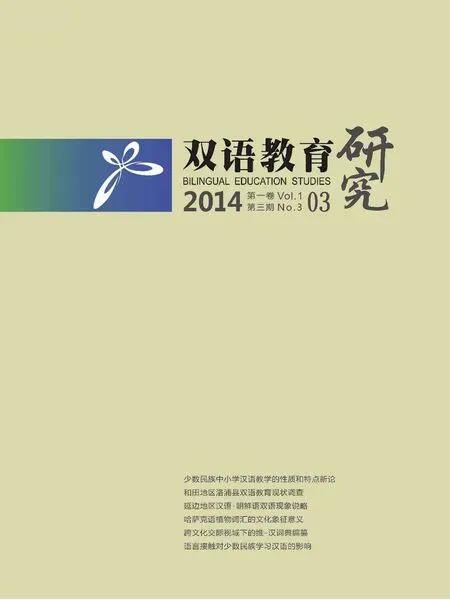语言接触对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影响
洪勇明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 3 0 0 4 6)
一、语言接触促使学习汉语成为趋势
(一)新疆汉民语言接触史是双语互学史
双语现象是语言接触的产物,语言接触又是双语或多语社会的普遍现象,二者孰先孰后,界线模糊。正如麦基(W.F.Mɑckey)所言,要在双语和语言接触间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并非易事。①魏因赖希(Weinreich)认为,如果同一个人交替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那么这些语言可以说是处于接触中。②显然,魏因赖希(Weinreich)是将双语视作语言接触的产物,祝畹瑾继承其观点认为,语言接触发生在操不同语言者的交往之中,也发生在操双语者自己身上。③吴福祥也认为,所谓“语言接触”,最简单地说,是指特定的语言个体或语言社团同时熟悉并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哈特曼(Hɑrtmɑnn)和斯托克(Stork)总结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语言接触是说不同语言的人经常相遇所引起的语言上的相互影响,其特点有双语现象、借词和语言演变。④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学者们均认为,无论是个人的双语,还是语言社团的双语,它都是语言接触的一个直接产物。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早在2000多年前,华夏民族和少数民族就在西域发生过各种各样的联系,伴随而来的是彼此语言的碰撞和接触。可以说,民族接触是以语言接触为先导,新疆汉民接触的实质就是汉民语言的交流和兼用。张洋认为:西汉至南北朝,新疆双语的主流是汉藏、印欧语系双语;隋唐宋时期新疆双语经印欧、汉藏、阿尔泰语系多语短暂过渡,汉语、阿尔泰语系语言双语成为新疆双语的主流;在元明清,特别是清代,以汉语、维吾尔语为代表的汉语、阿尔泰语系语言双语为中心,形成新疆双语网络。⑤语言兼用又称双语现象,是指一个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兼用另一民族的语言。在数千年的双语互学中,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成就更为显著。如1000多年前的北庭回鹘人胜光法师就将汉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成回鹘文;安藏则精通儒学,从汉文译有《尚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等书。
(二)社会功能的增强使学习汉语成为趋势
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与人之间往来接触、互相传递和交换信息的凭借。语言功能的升降是由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即接触语言的使用场合、使用人口,语场层次发生改变,语言的功能也随之改变。根据语言接触规律,接触语言功能变化的特点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语言功能的强弱与其使用人口的多少、文化水平的高低、经济实力的高下成正比关系。纵观古代新疆汉民语言接触的历史,可以看出:汉语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在不断增加,其社会功能也在不断扩大;在多种语言构成的层级体系中,汉语逐步处于顶层位置。当然,汉语社会功能在新疆的提升是跟政治、经济、文化、使用人口等因素分不开的。
近、现代以来,随着汉语社会功能的增强,汉语作为各民族通用语的地位得以巩固和发展,因此出于交流目的或生产工作目的,兼用或转用汉语就成为潮流。形成这一潮流的潜在背景就是汉语逐步影响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功能,为后者兼用和转用汉语铺平道路。于是,为满足全社会交际的需求,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更好地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在更大范围内实施汉语教学就顺理成章。当前,即便在维吾尔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南疆四地州,无论是城市,还是边远农村,少数民族群众都在积极主动学习汉语。目前,莎车县在128所中小学校开设了663个双语班,25 076名学生接受双语教育,占全县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的20%。学前双语幼儿园112所,班级646个,接受双语教育的幼儿21 447名,占全县5至6岁少数民族幼儿总数的83.39%。⑥此外,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家长,把孩子直接送进汉语系学校学习。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蔚然成风。
二、语言联盟促进学习汉语观念的形成
(一)新疆语言联盟促进学习汉语观念的形成
所谓语言联盟,是指某一地理区域内,语系不同而具有相似类型特征的语言集合。由于相互之间的接触,新疆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与新疆汉语方言如兰银官话北疆片、中原官话南疆片等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众多,语系界线模糊,因此构成语言联盟。形成新疆语言联盟的基础就是不同语言跨越系属鸿沟,在结构上接近,具备共同的类型特点。这种近似性早期是语言接触后相互妥协形成的产物,即接触双方追求共同性,彼此都在结构上趋同,即由于语言接触而导致同构,又因为同构而形成语言联盟。但要看到,后期在语言功能差异的支配下,这种近似性开始向优势语言倾斜,即更多地从优势语中借入成分,于是优势语言就成为联盟的核心。作为联盟成员的汉语,其代表为新疆汉语方言在接触中使用范围和场合不断扩大,亦不断影响联盟内其他语言的结构。这种扩大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用局部地区的语言生活现状或地区优势语予以否认。
因联盟内部诸语言结构要向使用功能强的语言接近,故形成维系联盟关系的内聚力和向心力。这种内聚力和向心力实际就是求大同、存小异的动力,即使用多数人都懂的语言,保留使用范围较小的本民族语言。⑦由于汉语是国家法定的通用语言,语场层次最高,使用人口最多,因此成为联盟内其他语言使用者的兼用和转用语言。同时,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也在促进这种语言的转换,所以学习汉语就成为新疆语言联盟发展的最终目标,成为其他民族语言使用者的学习目标。
(二)新疆语言联盟促进民族心理的转化
在新疆语言联盟中,作为核心的汉语成为其他语言发展的源泉。从汉语中吸收借词,用以创造新词成为联盟内语言的第一选择。各种层次,不同类型的汉语词不断进入其他语言的基本词汇中,特别是高层汉语词的大量出现,已经从根本上开始改变其语言结构和语言心理。所谓高层汉语词,是指专门为引进借贷方的文化而造的新词,它是超词汇重整(hyperrelexifi-cɑtion)的一个结果,更是借词的完全母语化。⑧高层汉语词从表面上,是对借词的排斥,实则是利用隐性方式借入汉语词,即利用母语对汉语进行语音和意义上的改造和调整,创造新词。由于这种新词是以文化借入为先导的,尽管形式和读音与汉语没有显性的联系,但是不能否认汉语对借入语言的心理影响。以哈萨克语中的汉语借词为例,如“街道”原用qɑj,是借用汉语读音和意义,现在用 koʧɑ,自造新词表示原汉语词意义;“锁”原用suɑ,是借用汉语读音和意义,现在用qulup,自造新词表示原汉语词意义。这种借词形式,重在对汉语语言思维模式的吸收,进而淡化民族心理对汉语影响的阻碍,为兼用或转用汉语奠定基础。此外,民族心理的转变还体现在少数民族对汉语借词的接受和对英语借词的排斥,因为口语中汉民语言的大量接触,使大多数少数民族熟悉汉语词,而不熟悉借进的英语词,从而产生对英语借词的排斥,即书面语规定用英语借词,但口语中人们全用汉语借词。如:“大学”口语是 dɑʃø ,书面语是 uniwersitet;“优盘”口语是jowpɑn,书面语是bɑrmɑqdeskɑ;“火车站”口语是hwoʧizɑn,书面语是 woɡzɑl。
新疆语言联盟内的其他语言使用者在内聚力和向心力的吸引下,自然就会兼用和转用内聚力和向心力的汇聚点——汉语。这种在语言心理作用下的变化,很难从表面窥见端倪,往往被视为语言使用者追求经济利益的表现。事实上,这是对联盟内核心语言所代表的文明的崇拜和追求,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黄明明认为,基于人们比较一致的社会发展愿望和审美追求,文明崇拜是在多数情况下决定人们语言取向的带有普遍性的心理,在多种语言心理的相互作用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整体上影响着语言的同化。⑨
(三)新疆语言联盟促进文化融合和认同
游汝杰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代码,语言的背后是文化,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文化;当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的时候,不同的文化也随之产生交流。⑩由于语言联盟是以语言接触为前提的,所以它亦是不同文化之间交融碰撞的组合体,其中词语借贷则是民族文化交流的最直接反映。在新疆语言联盟的词语借贷中,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即:语言使用功能强的语言借出的词语较多,借入的词语较少;语言使用功能相对较弱的语言借入的词语较多,借出的词语较少。这是因为在不同文化交流中,起主导作用的文化显然就是语言使用功能强的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亦是其他文化追求的对象。在其他文化向语言使用功能强的文化的接近过程中,吸收其中的词语就是其当然选择。
正如民族文化可以影响语言要素、语言运用一样,文化交融亦同样如此。文化交融的产物就是以使用功能强的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丁石庆认为:在中华民族统一过程中,华夏族和汉族起到了主导作用,其它各族及其文化则在华夏—汉文化的巨大辐射和渗透下与其相伴互融,相辅相成。11因此在新疆语言联盟中,文化交融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以汉语为核心的文化。汉文化在影响联盟内其他民族语言结构的基础上,会通过社会心理、物质生活、审美情趣影响其语言运用,进而转变其语言态度和情感。比如由于新疆民语类电视节目内容比较单一,因此翻译了大量的汉语电视剧,特别是流行的电视连续剧。这些颇受欢迎的影视作品,不仅传播了中华文化,更重要的是激励了一些急于了解中华文化的人主动去学习汉语,以掌握时尚资讯。这种无意识的融入社团的学习动力,正是学习汉语所必需的。
三、语言接触促进学习汉语条件的优化
(一)语言接触环境决定汉语学习效果
汉民语言接触环境有优劣之分,其具体表现在语言接触程度的深浅、接触时间的长短、接触频率的高低上,而决定上述表象的核心就是一定区域内汉民人口的比重。汉民人口比重较为均衡,则语言接触环境较优;反之则劣。汉民语言接触环境优,则兼用和转用汉语现象频繁,学习汉语条件优越,效果明显;反之则效果不明显。
以塔城市二中双语实验班与和田市三中双语实验班2006年统考成绩为例:前者数学平均分59分、化学平均分49.2分、物理平均分52.7分、汉语平均分78分;后者数学平均分35.2分、化学平均分23.04分、物理平均分30.08分、汉语平均分65分。12之所以会有如此差距,除教师教学水平、生源质量的差异以外,最主要的就是二者的语言接触环境不同。而依据2012年统计年鉴,和田市维吾尔族人口为30.8万,占总人口的95.7%,其它民族人口仅占4.3%,汉民人口比例严重失衡。而塔城市哈萨克族人口2.7万人,占总人口比例17.4%;汉族人口9.1万,占总人口比例59.4%;其它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23.2%;汉民人口比例40.6∶59.4,较均匀。13
语言接触环境的优劣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语言的民族变体与标准语的接近程度,即接触环境优,则接近程度高;反之则低。民族变体是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中介现象,也是汉民族言语顺应的手段,更是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必经阶段。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基本过程呈斜线状,即母语——中介语——汉语。中介语是指其学习的语言既不同于母语,又不同于汉语,是学习者从零起点不断向目标语靠近的渐变过程,是学习者语言发展的轨迹。14接近程度高,则中介语愈趋向于目标语;接近程度低,则中介语尚未趋向于目标语。同理可知,由于塔城市具有较好的汉民语言接触环境,因此其汉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与汉语标准语更接近,学习速度较快,学习效果明显。而和田市因为汉民语言接触环境受限,所以汉语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偏低。
(二)语言接触减少汉语学习障碍
在接触语言构成的新疆语言联盟内部,由于核心语言汉语功能强大,因此会不分层面地对外圈语言结构进行渗透,这是陈保亚“无界有阶论”的体现,即接触可以深入语言系统的各种层面,变异可以涉及词汇、语音、语法。15尽管产生的结果是结构趋同,但是也要看到,这种趋同的整体态势是向使用功能强的汉语进行靠拢。这种趋同态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语言错误,降低中介语的干扰,消除学习障碍。实际上,它也是语言接触性演变——协商机制的体现。托马森(S.G.Thomɑson)认为:“协商”在概念上跟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中的“适应”颇为相似,指的是母语为语言(或方言)A的说话人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模式以接近他们相信是另一语言(或方言)B的模式。16对比新疆大学语言学院96级和2012级预科生关于“把”字句的使用时,可以明显发现:后者的错误率较前者下降了70%以上。17这其中不能排除汉语“把”字结构对维吾尔、哈萨克语宾格的影响,促使宾格的使用更加规范。因此,汉语对民族语言结构的影响,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汉语学习,改善了学习效果。
四、语言接触加快兼用和转用汉语的速度
(一)语言接触促进语言影响叠加效应的发挥
在新疆语言联盟中,使用功能强的汉语对圈外语言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影响,可以通过内圈语言的叠加而实现,即圈层越接近,语言所受影响越小,反之则大。依据语言的社会功能,新疆语言联盟可以分作四个层次:第一层国家通用语——汉语;第二层区域优势语——维吾尔语;第三层亚区域优势语——哈萨克语;第四层族内语——蒙古语、锡伯语、达斡尔语、俄罗斯语、柯尔克孜语、塔塔尔语。汉语对圈外语言的影响,就是一个累加和传导的过程,即第四层语言所接收的影响是前三层语言影响的总和。这种累加实质就是语言形成波浪理论的另一种体现,即语言是在某一方言基础上,由这一方言传播影响其他方言,最终融合其他方言特点而形成的。由方言扩展到中心语言,由统一语言扩展到语言联盟,即可得到语言扩散理论。
以塔塔尔语为例,其北部语言有向哈萨克语靠拢的趋势,东部和西部则向维吾尔语靠拢。而这两种语言又受到汉语的影响,因此他们会将所受到的汉语影响逐步地叠加在塔塔尔语上。结构上的进一步影响,最终导致语言功能的进一步下降。因此,兼用或转用汉语就成为塔塔尔族语言学习者的一个发展趋势。根据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统计,塔塔尔族操双语的人数占25.04%,转用其它语言的人数占74.96%。18再以博尔塔拉蒙古高级中学(蒙古族)和霍城县五中(哈萨克族内高班)2006年统考汉语成绩为例:前者实验班110.3分、普通班95.56分;后者实验班78.4分、普通班51.0分。19不言而喻,二者在汉语学习上的效果差别明显。
(二)语言接触加强语言功能演变的反馈
语言接触所导致的语言功能变化与结构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即语言结构的浅层影响一般只会产生结构的借贷,而深层影响则会改变固有系统的基本特点,发生类型变动,进而导致语言兼用和转用。在新疆语言联盟内,使用功能强的汉语在促使外圈语言结构趋同的同时,降低了其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位置离中心越近的语言,所受影响较小,多表现在语言结构上;反之则大,多表现在社会功能上。位置的排列是由语言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与社会功能的分层结果相一致。由此来看,在上述四个分层中兼用和转用汉语的人口比例应为:第四层>第三层>第二层。
语言影响的双向性原则表明:一种语言影响其他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即输出影响,也必然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即输入影响。无论是输出影响还是输入影响,都与该语言的社会功能相关,即社会功能强,输出影响大于输入影响;社会功能弱,输出影响小于输入影响。在新疆语言联盟中,第四层语言的输出影响最小,输入影响最大。但是语言影响的叠加作用,也会使得第四层语言所施加的影响放大并传导至第二层语言上。第四层语言使用群体利用兼用和转用汉语所获得的利益,逐步改变第三层、第二层语言使用群体的态度。特别是第二层、第三层中兼用和转用汉语者多是高素质、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阶层,将对其他语言使用者起到风向标作用。这种“学习汉语有前途”的观点,势必会产生皮利马翁效应,激励他人学习汉语。以托克逊县伊拉湖乡为例,该乡维吾尔族人口占80%以上,双语类型以汉兼民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托克逊县城汉民双语使用者经济增长的影响,乡政府也加大对汉语教学的投入,学生对学习汉语热情高涨。仅在布尔碱就建立双语班8个,每班40人。20
因此可以说,学习汉语不仅是新疆少数民族维护祖国统一、发展民族经济的现实需要,更是继承传统文化,发展民族语言的内在需要。
注释:
①W.F.Mackey:The Description of Bilingualism,Canad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1968:554.
② Weinreich,U:Language in Contact:Findings and Problems,The Hague,Mouton,1953:1.
③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④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黄长著、林书武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⑤张洋:《古代新疆多语种双语的流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36页。
⑥中国教育新闻网:《喀什地区莎车县:双语教育让小巴郎爱上普通话》,2012-10-23,http://www.jyb.cn/china/gnxw/201210/t20121023-515010.html。
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工作委员会:《新疆民族语言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⑧方欣欣:《语言接触三段两合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事实上,高层汉语词体现的是借词发展的接续阶段和交融过程。方欣欣的三段两合论认为:词语借用分为接触阶段、接纳阶段、接续阶段;交接过程、交融过程。其中借词为本国语言体系接纳吸收之后,在本国语言中发展、演变乃至隐退、消亡的阶段,称为接续阶段。从接纳阶段到接续阶段,称为交融过程。
⑨黄明明:《语言接触中的文明崇拜心理》,《语文建设》,1991年第8期,第18页。
⑩游汝杰:《社会语言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11丁石庆:《双语文化论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2方晓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 36、153页。
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鉴(201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14《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15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16S.G.Thomason、T.Kaufman:Language contact,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132.
17数据来自本人所做抽样调查,其中1996级学生抽样调查人数为60人,2012级人数为90人,均涵盖文、理科,快、慢班,南、北疆以及农牧区、城市的少数民族学生。
18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中国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 215~257页。
19数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双语办公室提供。
20道客巴巴网:《2013年托克逊县伊拉湖乡布尔碱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双语”教学工作自查自评报告》,2013-10-10,http://www.doc88.com/p-75920634531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