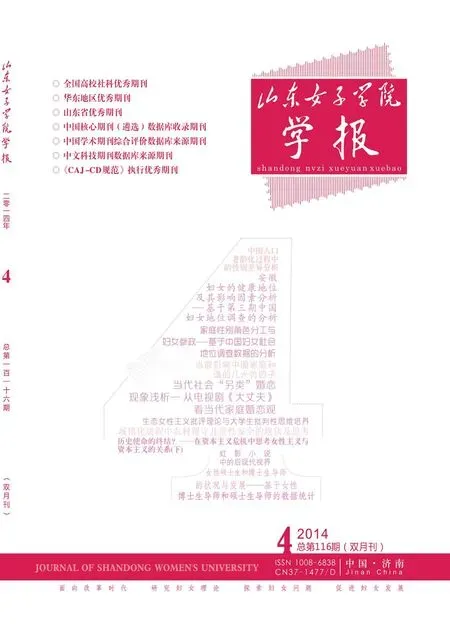历史使命的终结?
——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思考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下)
柏 棣
(美国德儒大学,美国 新泽西 07940)
基于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可将女性主义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持拥护态度的女性主义的右翼,她们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对女人有利,因为资本主义成功地挑战父权制的种种观念,使女性的主体意识、主体性得以建立。另一类是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左翼,她们承认资本主义相对于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人”才成为了一种社会身份,她们的诉求带上了社会性和政治性;女性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制度本身的矛盾日益加剧。贫富差距、劳动者同自己生产的产品的绝对脱离而导致的严重异化和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的三大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女性不是受益者,因为资本主义没有完全消除父权制,而是利用父权的意识形态,使女人的生活状况整体上不如男人①。
女性主义左翼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危机中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女性主义斗争的初衷和斗争的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女性主义30年来对社会批判所取得的实践成果,被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利用来剥削第三世界。他们原以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批判,却发现其批判成果不但没有削弱资本主义制度,反而使其更富有生命力。因此,“女性主义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构成了西方女性主义左翼在21世纪的主要理论议题。
近年比较活跃的霍姆斯特罗姆、佛里泽、爱森斯坦和巴米勒这4位左翼女性主义学者,在对女性主义实质的反思中,不谋而合地把20世纪的资本主义阶段化,分成“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前者是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式资本主义,后者则是兴起于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关于女性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她们的基本叙述是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在其中,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批判力量,而且她们的批判经常被制度接受、采纳,所以就有了以改变社会两性不平等关系为己任的风起云涌的女性运动。但是,1970年代后期国家资本主义被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替代。这种提倡高度个人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毁掉了女性主义的批判功能。这种“坏的”资本主义成功地“引诱”了女性主义,使其放弃了改变社会的“良好初衷”。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纲领被资本“利用”来改革自己,使自身更强大。就这样,女性主义不知不觉地在“历史的狡诈”中,转向极端利己主义,跟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逻辑合上了拍子,成了资本主义的“侍女”和同路人。
笔者在《历史使命的终结?——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思考女性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一文中指出了这种西方女性主义左翼叙述的理论误区。资本主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运作形式,它的基本的逻辑,也就是资本的逻辑是不会改变的: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的扩张。国家资本主义也好,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殖民地资本主义也好,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运作,保证资本利润扩大和资本积累。阶级的恶性对立,性别的、种族的严重不平等,帝国主义掠夺资源的暴力,对农民土地的强取豪夺,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人性的无限异化,无安全感的心理痛苦等,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至今5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怎么能有“好的”资本主义呢?
笔者在重读女性主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的过程中,对女性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思考。我们可以从两条有相互关联的线索去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一条是历史性,一条是阶级性。笔者认为,女性主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点前面提到的左翼学者有详细论述,而更重要的是:它是资本主义的衍生物和寄生物。做这个区分很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寄生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女性主义,从诞生的那个时刻起,它的社会批判就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精神。资本主义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制度,它允许批判,“只要能保证以利润为基础的动性继续运作,资本主义可以汲取各种建议,实验不同的制度”[1](P63)。更确切地说,女性主义社会批判的历史意义就是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精神,以扫清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妨碍资本发展的封建父权制为目的的。
关于女性主义的阶级性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刻意避开的,或者说是刻意解构的。“女性主义”这个命名本身就在宣扬普世性。女性主义一边用女人的欲望、女人的利益、女人的主体性、女人的身体身份、性别表演等等来组建一个抽象的女人,把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包装成所有女人的诉求,一边用“社会性别”的概念去替代阶级概念,把人类历史说成是男人“交换女人”的历史。然而,女性主义100多年的发展脉络却证实了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阶级利益。
西方女性主义把自身的发展史用“波”或“浪潮”来组织界定。“波”这个概念或者意象开始于1960年代。当时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女性主义者自封为“第二波”,以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波”女权运动建立起一种相关性。1990年代兴起而且延续至今的“第三波”承继了这个传统,用“波”这个概念来谈对“第二波”的批判与继承。女性主义独特的波状历史发展为我们认识其阶级性创造了一个契机。首先,自然界的“波浪”有涨潮有退潮,“三波论”要说明的是这100多年来,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三次高峰,三次高峰的间隙中就是低潮。有趣的是,比如在“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的属于低潮的1930年代到1950年代,正是美国的劳动妇女争取同工同酬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其次,“波”与“波”之间呈现的是一种代际关系,用代际关系解释历史,好像历史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对话,好像每一代人都有属于那一代人的意识形态,比如,“第一波”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诉求;“第二波”的主干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第三波”就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了。这本身就抹去了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也瓦解了女性主义代与代之间的传承关系[2]。“三波论”还涉及到理论的霸权问题。女性主义的“三波论”似乎被用来作为一种全球的普遍模式来断代和划分妇女运动发展的不同时期,这样,美国、加拿大的女性主义史就潜移默化地变成了全世界的女性主义史。
根据“三波”的历史叙述,女性主义的第一次高峰发生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女性主义以1848年的塞内卡瀑布会议(the Seneca Falls Convention)为起点。有大约300名男女聚集在一起,讨论妇女平等问题。由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主笔起草的《塞内卡瀑布宣言》概述了新的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战略。第一波的目标是开拓女性的法律权利(legal disabilities),争取选举权(women’s suffrage)。
在强调争取法律权利和选举权的第一波女性主义的叙述中,有意无意地省略了当时欧美各国大量妇女参加有报酬工作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农业社会向新兴的工业社会迅速过渡的时期。新兴的资本需要大量的“自由”人作为劳动力,因此,就从农村和农场招募工人,包括主要从事纺织服装工业的年轻女工。比如在美国东北部出现了很有趣的“劳动者文化”,这包括自由报纸刊物等工人自己发起的文化活动业。工人在出版物上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谴责控诉按时间工作的工厂制度,把它说成是一种摧残人自由生活的制度。工人们把小时工资制比喻为“新奴隶制”。所以,增加小时工资,缩短每日劳动时间,要求立法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是当时工人阶级,包括女工的斗争目标。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政治团体参与领导了工人争取权利的斗争,这种运动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
在这种大背景下,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妇女几乎是水到渠成地提出了女人的选举权,并很快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承认、接纳。轰轰烈烈的工人阶级运动因此就被第一波女性主义讲述成300个男女精英的故事,成功地把工人们反对“新奴隶制”对工人的剥削的斗争的成果通过女人争取选举权稀释了。的确,细读第一波女性主义的自传史,就可以看出它的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普世性,另一个是阶级性。女性主义打着“女性“的旗帜,却不涉及大多数女人——劳动妇女和底层妇女的利益。第一波女性主义的普世主义的思维方式特别表现在“一个女人就是所有女人”的叙事中:把个人——资产阶级的个人经历中的不幸,放大成全体女人的苦难,把个人性格上的弱点,说成是全体女人的品性,把个人的追求理所当然地想象成全体女人的理想。把易普生的《玩偶之家》中资产阶级妇女娜拉的困境说成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所有女人的遭遇,就是第一波女性主义普世主义的一个范例。
第一波女性主义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也就是强烈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很清楚地表现在女性主义对于反资本主义的女工运动的排斥和对同时进行的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拒绝。以色列女性主义者哈卡·克特夫(Hagar Kotef)2009年发表在美国《女性主义研究》学刊上的一篇文章《谈抽象性: 第一波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建构抽象女人》有助于我们了解第一波女性主义的阶级意识的理论表述。
为了回答“为什么说女性主义中抽象的女性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克特夫回到第一波女性主义的原始文献阅读中发现了萨拉·格力姆克(Sarah Grimke)在1838年发表的《关于两性平等的书信》(LettersontheEqualityofSexes)。很直白地表现出第一波女性主义有一个基础性矛盾:它认为有的女人应该有权利,有的女人不应该有权利。在一封为“女性的法律上的残障”(Legal Disabilities of Women)的信中, 格力姆克把当时法律允许的丈夫对妻子的“适当纠正权”(moderate correction rights)做了这样的解读:有三种级别的人,最下层的是奴隶,奴隶主对其奴役的女奴的“适当纠正”意味着女奴的生死;其次是贫困的底层,这里丈夫对妻子的“适当纠正”就是家庭暴力(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词汇);而在高层的所谓上等人中间,丈夫对妻子的“适当纠正”就是限制她们的活动范围,她们也缺乏自己的空间。格力姆克指出,女奴们面对的不是两性平等的问题,她们需要的是废奴运动(The Abolition Movements);贫困妇女的诉求跟她们的丈夫一样是物质上的,因此她们是“男性化”的;只有上层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妇女具有女人气质或女性气质(female temperament or femininity),唤醒建立在女性气质上的“女性意识”(feminine consciousness),争取扩大女人的活动范围和空间,也就是后来的伍尔夫所说的“自己的一间屋子”,这就是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奠基[3]。
这里的所谓的“女性气质”显而易见是上层资产阶级的阶级气质,“女性意识”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第一波女性主义用“女性气质”和“女性意识”来限定女性主义运动的主体和客体,也就是运动的参加者和运动的目标,完全排除了广大劳动妇女、贫困妇女、少数族裔(作为奴隶的黑人)妇女,因为她们过分男性化,不具备作为“女性”的资格。
第一波女性主义对“女性”的阶级限定似乎有着跨越时空、跨越文化的能力。在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时期所塑造出来的劳动妇女、无产阶级妇女的形象也被认为是过分男性化的,缺乏“女性气质”的。在“伤痕”话语中,中国革命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无产阶级化(社会主义改造)被说成是剥夺了她们做女性的权利。这些年我们所欢呼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说到底,就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性的阶级身份的重建。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在中国妇女研究里,第一波女性主义常常被用来论证这样一种观点:西方第一波女权运动是女性自发自觉的,而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从上至下的,解放不是妇女本身的诉求,而是由他者推进的,那么这种解放就是“被解放”。而相比之下,美国和西方女性主义是女人自己的解放诉求,她们通过自己的女权运动而得到的权利才是真正的解放。这里起码有几层错误:第一,西欧和美国的第一波的女权运动,都有男性的帮助,甚至是在男性的指导下进行的。另外,参与女权运动的人数很少,而且都是精英。按照“被解放”的逻辑,广大西方妇女也没有参加平权运动,也不想参加选举,也没有什么解放的诉求,她们的权利也是糊里糊涂地得到的,她们也应该是“被解放”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不但有男性提倡,也有很多女子参加和领导,比如参加辛亥革命的秋瑾、共产党员向警予等。如果说女人的权利是父权制社会给的,因此女人就是“被解放”,那么,从逻辑上讲,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女人都是“被解放”的。美国女性主义取得的所有成就和成绩不都是在说服父权/男权的国家机构通过立法而达到的吗?如果所有的解放都是“被解放”,那么这个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从更深的层次上说,人的所有的权利和权力都是“被”给予的,都是社会给予的。社会不承认你,你再争取,你再有所谓的主体性,也是没用的。
以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为主体的女性的诉求为运动目标的第一波女性主义,在1920年代开始落潮,而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包括女工的工人运动欣欣向荣的时期。根据女性主义运动史,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在1960年代后期,并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促成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的是这样一个事件。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地区的政治激进女性主义组织“红袜子”(Redstockings)在1968和 1969连续两年,到大西洋城抗议在那里举行的“美国小姐”的选美比赛。“红袜子”认为选美比赛充分地表现了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是被男人欣赏的“物”,把参赛的女人拉来一个一个出场,就像牛市卖牛一样。她们抗议的方式也很有独创性,组织了模拟游行,簇拥着一只被誉为“美国小姐”的羊,一边行走,一边把身上象征“压迫”“限制”女性的物件,比如胸罩、腰带、高跟鞋、化妆品和假睫毛等扔进垃圾桶。“红袜子”抗议作为第二波女性主义开始的标志不是偶然,前资本主义时期对“性”的各种定义和各种限制,都将受到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挑战。当然20世纪对性秩序、性伦理、性道德的挑战并不仅来自于女性主义,男人也参与其中,同性恋运动就是一种同第二波女性主义并发的而且相互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性革命。
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中心议题是“性”,这个“性”是一个广而泛的概念。为了界定“性”是什么,“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被制造出来用以区别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性”和人们头脑中对“性”的常规认识。可以这么说,第一波女性主义在理论上发明界定了“女性”,第二波女性主义在理论上发明界定了被她们称为“社会性别”的“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波之间的衔接和传承。
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于1960年代末至1970初,发达于1980年代,落潮于1990年代初。这20年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段,标志着社会历史意义上的革命的20世纪的结束和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开始和发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k Hobsbawn)把20世纪称为“短20世纪”(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有其足够的理由。20世纪的社会历史意义起始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之后出现了以苏联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始。接下来便是资本主义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结束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冷战架构内经历了20年重建和繁荣,然后便是前后相继的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1980年代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危机,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短20世纪”以冷战结束为标志而终结。当然,“短二十世纪”对于死里逃生的资本主义却是一个“长二十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 认为,全球资本主义通过自身的调整,成功地把资本渗透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这个正在上升的、乐观的全球资本主义会信心十足地迈进21世纪。在1980年代末,美国自由派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历史终结了吗?“我们现在见证的可能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一段特定的战后历史的过程,我们见证的是历史的终结。就是说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制度的最终形式。”[4]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消亡没有成为现实,历史就停留在自由市场加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
正是在这样政治经济体制日趋保守的背景下,女性主义迎来了第二次运动高潮。正像“红袜子”抗议所象征的,第二波女性主义集中对父权制进行文化的批判,目光聚焦在私人空间和再生产领域,打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时代口号。个人在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概念里是支离破碎的,包括性别、种族、阶级、年龄等多种身份交杂在一起的存在,这个存在由内在的“主体性”来驱动,来争取自身的以“性”为中心的权利和权力。“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无疑是一种概念的创新,因为一般常识是“社会的是政治的”。然而,“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却回应着19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把批判的目光从社会权力结构和经济制度转移到个人。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跟第二波女性主义同时出现的美国民权运动也带有同样的政治保守色彩。马丁·路德·金的纲领强调种族调和,把以阶级斗争为实质的种族压迫调和成民权问题。两种思潮都不触及资本利益,避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性矛盾。正如法国左翼批评家伊芙·奇亚贝罗(Eve Chiapello)所说,20世纪70年代的不触动资本逻辑的抗议活动被资本主义有效地纳入自己的制度更新,被资本主义社会承认[1](P61)。
当然,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不仅是武器的批判,也更是批判的武器,批判的锋芒直指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以“社会性别”为核心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建立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之上的。有趣的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把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可能是女性主义理论中最严重的命名错误”②。
1990年代出现的第三波女性主义严格地说不是什么主义,也不属于批判理论范畴。简单地说,第三波女性主义强调的是女性的自我赋权(empowerment),对生活的现在主义的态度,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把个人主体性(agency)推到极致。它是女性主义同当时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相交叉的产物。笔者称之为“生活方式女性主义”是为了迎合商品化的潮流而产生的。第三波女性主义完全融入后现代主义的逻辑中,强调当下的感觉和绝对的自由,有人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无政府主义在哲学和文化层面的表现,这种女性主义的表现是纵欲主义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列举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17种矛盾,并把这17种矛盾按主次分为基础性矛盾、变化中的矛盾和危险的矛盾。社会性别的矛盾的确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但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矛盾。性别之间的矛盾来自于残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前资本主义的父权和男权的意识形态。其实资本主义已经基本上摧毁了父权和男权产生的封建共同体,因为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和增值依靠脱离了家族束缚的自由劳动者。随着封建家族的解体,父权和男权在逐渐消亡。作为一种惯性和一种意识形态的滞后,父权和男权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在资本不发达的区域。灵活的资本为了取得最大利润,有时候也会跟父权联手,例如低工资聘用女工,这样本来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现在呈现出的就是性别之间的矛盾。女性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清除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残留的父权/男权,不是去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资本主义的衍生。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较之国家资本主义是更加成熟的资本主义形态,其几个突出的标志包括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的高度应用,成功地将一切包括人、人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劳动、自然资源彻底物化、商品化,以及人口流动等等。在这个社会中,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女性要进入社会空间的诉求基本满足。由父权/男权作为根基的性别矛盾对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女性来讲不再构成严重的性别矛盾,因此,女性主义社会批判的历史意义已经基本完成。
注释:
① 关于女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详细论述,请参考柏棣文章《历史使命的终结?——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思考女性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载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页。
②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实际上应该是“反阶级斗争/女性主义”。它不谈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攻击马克思主义是父权,要跟马克思主义离婚,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把人类的阶级斗争历史说成是交换女人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Eve Chiapello.CapitalismandItsCriticisms[A].PaulduGay,GlennMorgan.NewSpiritsofCapitalismCrises,Justifications,andDynamics[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63.
[2] Astrid Henry.WavesRethinkingWomen’sandGenderStudies[C].Catherine Orr, et al. Routledge, 2012. 102-118.
[3] Hagar Kotef.OnAbstractness:FirstWaveLiberalFeminismandtheConstructionoftheAbstractWoman[J].FeministStudies,2009,35(3):496-497.
[4] Francis Fukuyama.TheEndofHistory[J].TheNationalInterest,1989,(summer):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