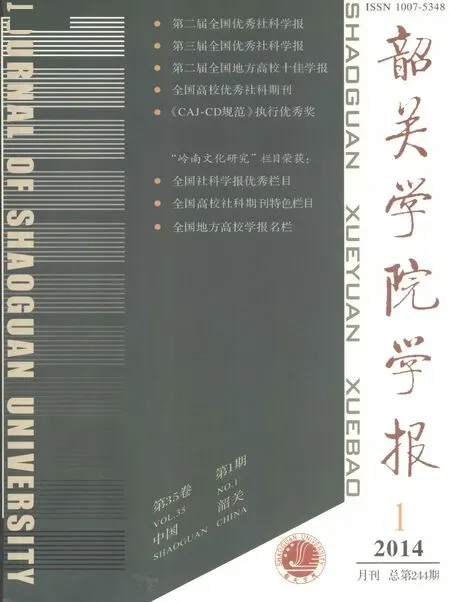生命与宇宙合流同化——方东美广大和谐的艺术意境论
胡兴艳,王兆谦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在中国美学史上,“意境”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朱立元在《美学》中指出:“意境主要是指运用艺术意象,在主客体交融、物我两忘的基础上,将接受者引向一个超越现实时空,富有形上本体意味的境界中。”[1]296意境,一般认为是抒情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称赞“意境”说是为中国文化的特殊贡献。我们一般认为意境是从大量的艺术创造实践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涵盖了中国人的宇宙观、艺术观、人生观,与中国人的整个哲学意识相联系,长期存在于中华艺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如唐杜甫的《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元代马致远的《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不仅勾画了一幅幅意境深远的图画,更融入了作者的生命情思。
方东美在著作中经常使用艺术意境一词,不但用来说明中国人的宇宙气象,也用来品评艺术作品,他将艺术与生命、与宇宙三者合一,认为艺术表现生命的生生不息,整体上呈现出广大和谐的艺术意境。同时审美的主要目的就是审美主体在宇宙的不断创进中感受生命的生生不息,艺术要同生命一样,要在生生不息之中,描绘大化流行之宇宙,把自我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合流同化,从而与自然相互协调,以至天人合一。我们认为意境强调主客体的统一,是审美主体的情意志对审美客体的内心体验而能达到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了整个自然的广大和谐之美。因而方东美讲意境时,主要注重的是意境的三个方面,即冲虚空灵、积极雄健和气韵生动。
一、冲虚空灵之美
在方东美的思想体系中,我们认为他把生命作为其本体论和价值论,生命所体现出来的美感就是艺术,即生命表现美感,美感来源于生命,他说:“中国人之宇宙,其底蕴多属虚象灵境”[2]107,“中国人之灵性,不寄于科学理趣,而寓诸艺术情思”[2]108,这种艺术的情思,表现为“冲虚空灵”之意境,也就是说中国人常常把有形的实体和现象化为空灵冲虚的意境,由此,实体得以隐藏,虚灵得以显现,从而真善美的世界得以创造。方东美以普遍生命涵盖宇宙本体,无论是在艺术价值领域和道德价值领域,他都追求的都是真善美的统一,他曾以画家在墙上作画为例,画家发挥艺术想像,在偌大的墙壁上寥寥数笔勾勒出了一个小孩临崖放风筝的图景,细细的风筝线把人引向高空,使人如置身于高妙境界,俯观天地,有自然参赞化育、万物与我为一之大气魄,这不仅是艺术上冲虚空灵的境界,亦是理想人格之最高精神境界。
在艺术领域内,“冲虚空灵”包括冲虚和空灵两个方面,这两方面不仅影响着中国的艺术创作,也是诸多美学家哲学家所探讨的问题。关于冲虚,关键在于虚,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3]100世界上很多东西的功用都不在于物体之实,而在于空虚之虚,杯子能盛水,汽车能乘客,大厦之所以能住人,皆由于其虚空,此乃虚之功用。也有“虚一而静”之说,老子“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庄子“唯道集虚”,方东美认为“实者虚之”是中华民族美好的性情和品格,因为能“实者虚之”,故而能涤除外物,用心之灵性来观照万物。当物质一着实讲,就会沾滞不化,艺术便显得索然无味。老子“大方无隅”,墨子“方不障”,朱子“至语所用,则以其至虚,而好丑无所遁形”等都是讲“实者虚之”的道理。“实者虚之”,故而能去迹存象,保持精神空灵,就会产生“芳菲翁勃”[2]101的意境,从审美的角度看,即审美主体能够排除主观的成见和欲望,使得客观对象的本来面目自然而然地呈现,也即用哲学心灵把物质世界点化成空灵的艺术境界。至于“空灵”,叶郎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引用严羽的话:“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4]556,认为这种镜花水月就是艺术的空灵,还有“风对于雅,兴多于赋”也为空灵。方东美则认为中国人之空间意识,是心情的灵府,犹如空中之音、镜中之相、水中之月,往往体现了形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意空间[2]105。“空灵”在于韵味的无穷,用有限之形体勾勒深远的意境。美学家宗白华认为美感来源于空,因为空使得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产生隔阂,主体得以从功利中抽身,这样美便是美,因而,艺术世界的空,并非为真正的空,而是由于与充实相对,由于主体与物之间产生了非利害的距离,“心远”接近“真意”,因此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是精神的淡泊。为什么要空灵?方东美认为生命的动力和才情要在空间中展开,但是空间被物质实体所占据,僵而不化,艺术家要抒发才情,进行艺术创作必然要确保生命的无挂无碍,就需要克服“空间”所造成的滞碍,所以要借助空灵,来玄览万物,也就是要“实者虚之”,把有限的实体点化成无穷的妙用空间。
方东美时常把冲虚和空灵放在一起而言之,之所以放在一起,是由于冲虚和空灵本身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由此及彼,不可分割。它们使得审美主体能够静观万物,使得自然万物均表现其本身的生命之美。此外,与冲虚空灵相对的是实,清代艺术理论家刘熙载把空灵与结实统一起来,“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著于以偏。试观韩文,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4]宗白华也认为空灵和充实是中国文艺一直所追求的极高境界。方东美强调冲虚空灵,认为“实者虚之”为吾民族之德性,但是在其著作中,较少提到“实”的具体之用,因而他在艺术的境界中更偏重的是损其体,去其障,至其虚的无穷空灵的妙用。
二、积极雄健之美
方东美所言的生命是万物之源,生生不息,他欣赏积健为雄的艺术精神,他认为宇宙一旦发挥出雄奇的生命气象,就能与自然合二为一,使万物刚劲有力,从而使人类受到感召,发挥生命艺术才情,就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这种“雄奇”的艺术精神,在道家看来是一种自然之大美,老子云:“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3]222;《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5]老庄的“大美”融合了道的艺术精神,要达到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是现实的生命超脱于宇宙的浩渺无垠,将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灌注生命,因而方东美十分赞赏五代画家的画所表现的无穷的雄伟意境。在儒家看来,美之体现为人的雄健之美,《易经》中君子的美好品格与孟子的充实之为美最能体现这一点。儒家认为能够真正了悟大美的人是圣贤,是君子,他们能体悟生命之道,不断地提升自我成为完人。我们认为无论是道家的“大美”,还是儒家的“人美”,所表现的是一种积极刚健,浩瀚雄伟的生命之气,在方东美看来皆需要人与宇宙大生机浑然同体,浩然同流,形成天人合一的艺术意境。
在表现方法上,方东美说:“中国艺术家擅长于以精神染色相,浃化生命才情,而将万物点化成盎然大生机。”[6]208他所说的“浃化生命”指的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交融为一,感应交合,是“神与物游”的审美境界,方东美也称之为“同情交感”。何谓“同情交感”?一方面表现为对宇宙之境的认识,即对宇宙交相感应,这源于中国的妙性文化,何为妙性文化?方东美认为所谓妙性文化就是审美主体与自然万物在无滞碍的审美境界中流衍互润、浑然一体,感受生命精神所溢发的美感。中国人何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他们始终能够提神于太虚而观世界,玄览宇宙,同时又能从美的境界中感受人世间的一切自然事物,故而总是把自然万物赋予生命之灵气,同时赞叹生命、歌咏生命,让生命与自然交相呼应,从而审美主体进入物我合一审美境界,所以《管子·五行》篇第四十一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亦如王国维的物我不分,庄周与蝴蝶的浑然不觉,陶渊明与南山的交融互视,皆分不清何者为我,我为何物?此所谓交相感应。另一方面,审美主体还需要寄予“同情”,他认为艺术创造活动来源于艺术家的同情仁爱之心,文艺家借物寓情,通过对物的描写来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实际上就是“以精神寄色相,以色相染精神”,从而使得审美对象具有了审美主体的情感,表现审美主体的意志,也就是说“文艺家触物以起情,索物以讬情,叙物以言情。”[7]15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方东美所说的“同情”,它不同于西方美学家的“移情”,移情是将审美主体的感情投射于外在的审美对象,方东美认为此类移情只能称作主观主义,它会使身心之间产生鸿沟,产生心理与物理的二元论,导致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间的隔阂。而“同情交感”更是一种天人合一或者说物我合一的理想的审美境界,也即创作过程中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在宇宙生命的乐章中,共享和谐生命之道。
三、气韵生动之美
南朝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首先提出绘画“六法”,并把“气韵生动”作为第一条和最高标准,“气韵生动”是指绘画内在的神气和韵味,中国画的精髓就在于表现自然万物的生命之气,追求内在的神韵。从生命哲学出发,方东美认为中国艺术就在于表现宇宙的盎然生意和灿烂活力,中国的艺术家发挥聪明才智,在艺术的创作中尽显气韵生动之美,哲人慧心思索,诗人抒发性灵,画家描摹自然,展现的是宇宙普遍生命之美及气韵生动的充沛活力,巧夺天工的艺术作品是将一切事物点化成“生香活意”[6]204的生命整体,中国历史上的陶器、玉器、铜器、雕刻、钟鼎以及唐宋以后的龙凤等,不仅“代表了宇宙的繁殖力”[6]205,也“充分表现了生命的韵律与旋律”[6]206。
另外,方东美认为中国的艺术作品所体现的是理想的境界美,往往能气韵生动,勾画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同时这高超的境界万物含生,交相辉映,生命浩荡不竭,是一个“大生机”世界。何以如此,方东美认为这是由于中国艺术从意味上看是象征性的,象征不同于描绘,而是接近理想性。描绘性的艺术以自然为“美”的对象,它们所表现的只是孤立的个体的生命,如希腊的雕刻、哥德式教堂等;而中国的艺术在于表现生命之美,高超的艺术作品必须注重生命的弥漫流通,必然要通过气韵生动的艺术意境才能表现,从而表达方式永远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因而在艺术意境中,理性的艺术不仅有哲学性的惊奇,更有诗一般的灵感。
在方东美看来,气韵生动还涉及到中国艺术的另外两个问题,即“表现”和传神。方东美所说的表现并不是西方美学中与再现相对的表现,他认为西方的表现说主张文学艺术作品呈现的是作家的内心世界,是作家自然情感的外在流露,忽视了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并且借助社会生活得以流传和传播,从而否定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性。在方东美看来,中国的艺术是真正的表现,画家作画最在意表现气韵生动,在于点化物质之实体,使其具有盎然生意,同时艺术家点化事物,通过想像和联想,不注重事物的表象特征,而在于其生命的创化力。诗词中最能体现这种韵致之美,它总有一股神妙的机趣,能点化万物,激励人心,如《毛诗大序》中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总而言之,艺术家通过慧心,将自己的生命悠然契合于大宇宙的生命,深悟大自然生命之雄奇,经过孕育和构思,最终创作出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命的艺术作品。
至于“传神”,一般指能生动逼真地刻画人和物的神情,追求神似的效果,《世说新语·巧艺》中有一则顾恺之画人的故事,说他十分擅长画人,但是数年不点睛,别人问其原因,他却认为眼睛乃神妙之笔,不可随便点之,也就是说他认为画人物时要想传神,不应该着眼于四肢体态,而应该着眼于眼睛。顾恺之之后,很多画家和画论家在论及顾恺之美学思想的时候,都会提到“传神写照”或“传神”。方东美则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传神”的,从反面来讲,他认为中国艺术就是要对物质性的否定,即化除主体和对象的滞碍,不以精确勾勒为能事。从正面来看,方东美认为通过直觉可捕捉到美的本质,体悟美的生命本色,能够浑然天成,毫无凿痕。
最后,在论述中国艺术理想的著作中,方东美还认为中国的艺术具有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不仅强调人,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生命了悟哲学,理解艺术的意境的生生之美。从方东美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生命本体贯穿于其哲学美学的各个方面,人文主义也不例外,因而他所说的人文主义与希腊的人文主义是不同的,希腊艺术是以人体来描写所有实体或者以神来表现众神,这样的人文主义把人作为衡量一切的依据,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宇宙自然的客观性,从而在艺术上,其艺术意境势必丧失,艺术作品将陷入主观的感性快乐之中,成为描绘性的艺术。而中国的文化是妙性文化,艺术精神表现为妙契人文主义,把人当作宇宙活动的参与者,生命与宇宙浩然同流,从而参赞化育,达于至真至善至美的艺术境界之中,艺术不仅仅表现人体的美,更重要的是透过空灵的艺术想像,把有限的物质世界点化成无穷的妙用空间,这样一切的蓝天、草木、野兽、风雨、日月星辰都充满生香活意的生命和谐之气。
[1]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
[2]方东美.生生之德[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56.
[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560.
[6]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7]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