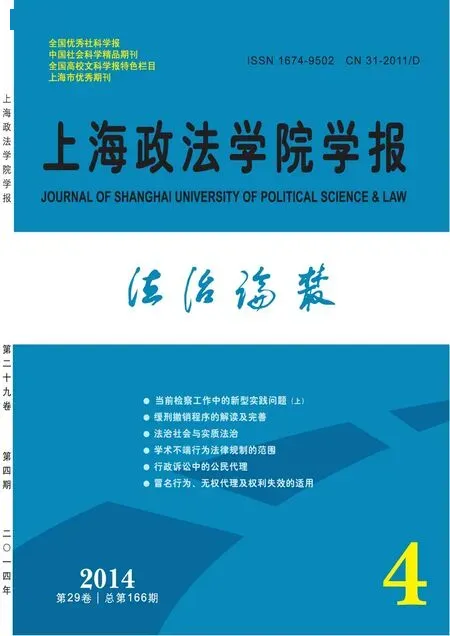论宪法最高效力的宣示
马树同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银川 750021)
论宪法最高效力的宣示
马树同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银川 750021)
宪法与其他普通法律相比,具有效力的最高性。但宪法最高效力的来源、表现及其效力最高性进行宣示的必要性,在学界并未达成共识。本文尝试通过对三个问题的阐述,论证了宪法最高效力宣示的必要性。
宪法效力;最高效力;信仰
法之生命在乎运行,宪法亦然。但宪法的运行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宪法本身的根本性、最高性的体现,而把宪法这种特性予以外化,就是对宪法最高性的宣示。
一、宪法最高效力的来源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所蕴含的最高性是宪法区分于普通法律的特性之一。一般而言,宪法的最高效力是指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法律地位,是其他法律制定和行为实施之准则。因为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保证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定和人民权利的实现,将宪法的效力最高化是应然之事。
“来源”一词意指起源、产生。有学者把法律效力的本源界定为“法律效力的本原是指法律产生效力的根本基础,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法律为什么会有效力,或者说它要回答的是法律效力的理由、根源、来源等问题。”①姚曙明:《论宪法最高效力的本源》,《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借此界定,宪法最高效力的来源是指宪法之所以具有最高性的理由、根据,它所要解决的是宪法这种最高性所面临的正当性问题。
宪法最高效力来源的正当性不仅在于形式上,更在于实质上。但片面的侧重一面也不能很好地突显出宪法最高效力的合理性。从近代宪法的产生、发展、不断趋向成熟来看,宪法的最高效力其实质是人民主权在宪法层面的体现,是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是自然法学思想和精神的体现。
(一)宪法最高效力的形式来源
宪法最高效力的形式来源,是与宪法最高效力的实质来源相对的,是以程序来断定宪法最高效力正当与否,是一种效力的外在授予,是由宪法典宣布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从形式上来表现宪法的权威高于一切国家机关和个人的权威。在世界宪政实践中,多数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宪法至上性的价值内容,从宪法文本上确认宪法规范本身的最高地位。1787年美国宪法第6条规定:宪法和依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的权力已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即使州的宪法和法律中有与之相抵触的内容。这一条款确立了宪法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为美国宪法以后之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宪法基础和理念。日本宪法第98条规定:本宪法为国家最高法规,凡与本宪法条款相违反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之全部或一部分,一律无效。同样,这款宪法条文也凸显了宪法作为最高法在日本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宪法的这种自我授权规定,在传统宪法观念之中,多被视为一种政治性宣示的规范,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但随着宪法实践的不断发展,民众宪法观念的逐渐转变,宪政之价值的普世化、宪政规范效力的最高性已不再被仅仅视为一种政治性的宣示了,而是日益体现出其独有的规范性作用。俄罗斯1993年宪法第15条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直接作用,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官员、公民及其团体都必须遵守。”
宪法效力的最高性并不当然地体现在宪法规则之中,宪法效力的最高性在这种程序性的自我授权中的体现、外化,有着深刻的理念支撑。这种理念就是宪政,就是法治。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理念的支撑,在世界宪政的进程中,宪法的最高效力才不断地得以显示,并在民众的心里得以沉淀。宪法最高性的形式授权,只是在程序上确认了宪法效力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在宪法实践中运行,一方面有赖于国家强力的保证,一方面也需要民众的内心认可。诚然,国家强制力是一国宪法得以运行的保障力量,但这种保障应该是最终的,不能在初始情况下当然的应用。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说过:“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证。”①[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如果一个国家把宪法的运行依托于国家强制力,那么这种宪法的运行只能说是一种暴政的体现。
在哲学意义上来说,形式与内容是统一的,形式是内容的体现,内容是形式的内涵。宪法效力的最高性在形式上是一种规则的体现、一种程序性的自我授权,而在这种形式之下的内容却是一种理念的贯穿。如果只注重形式的完美,即使把这种理念用美妙的语言表达出来,并用这种最高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也不能掩饰这种华丽外衣下所隐藏的卑鄙行径。程序的正当性为宪法实现其最高效力提供了可能,民众对宪法理念之认同方才是宪法最高效力之根基。
(二)宪法最高效力的实质来源
关于宪法最高效力的实质来源在宪法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有学者认为宪法最高效力的实质来源在
于制宪者拥有的国家权力和宪法规定的内容的正当性,且二者之间不能等量齐观。②韩大元:《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也有学者认为宪法最高效力的实质来源在于宪法是“高级法”观念物化的需求,是人们权利保护的需要。③参见姚曙明:《论宪法最高效力的本源》,《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学界的观点虽有不同,但就其实质而言,均不外乎宪法最高效力来源的权力界定。从近代宪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宪法最高效力的实质来源应为人民主权这一理念的发展和升华。
对人民主权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卢梭看来,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种自由和权利与生俱来,不可转让且不被剥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自然结果,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利的让与,是受人民之委托的。国家制定的法律具有普适性、正当性的根本在于人民授权。法国大革命时期,西耶斯将“人民主权”思想运用于宪法领域,首次提出了制宪权的概念。他说:“在所有自由国家中——所有的国家均应当自由,结束有关宪法的种种分歧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要求助于国民自己,而不是求助于那些显贵。如果我们没有宪法,那就必须制定一部;唯有国民拥有制宪权。”①[法]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张芝联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页。这种制宪权可以由国民自行行使,也可让渡于合法机关代为行使。由此可见,宪法是人民权力合法让渡的产物,人民享有一切权力是宪法最高效力的本质来源。
在现代宪政国家中,对人民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障是宪法的应有之意,只有在确保人民主权的情况下,才有实现宪政之可能。从现代世界国家中的宪法条文对人民主权这一原则的规定,可以窥见这一理念在指导宪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可以更深地理解把人民主权作为宪法效力最高性的实质来源之意义。1791年法国宪法以《人权宣言》为序言,宣告了人民主权原则。《人权宣言》明确宣告:“整个国家主权的本源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日本现行宪法也在序言中宣告:“主权属于国民。”意大利1947年宪法规定:“意大利为民主共和国,主权属于人民。”菲律宾宪法规定:“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我国现行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以前生效的世界上142部宪法有118部宪法提及了人民主权。②[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从而可以看出,人民主权不仅在理论上是宪法效力最高性的实质来源,而且在宪法实践中也体现了宪法效力的最高性。因为一个实行或预备实行宪政的国家中,如果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中确保人民主权这一宪法理念的实行,那么这种宪政只能是一种空谈而已。在一个欲追求民主、法治、人权保障的现代文明社会,把人民主权这一理念、原则宪法化是必然要求,是宪法效力最高性的天然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效力的最高性是人民主权的必然结果和逻辑结论。
二、宪法最高效力的表现
宪法的最高效力以宪法是关于国家权力之限制和人民权利之保障为基础的,是国家根本问题的体现。在宪法学界对宪法最高效力的表现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宪法是立法工作的法律基础,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另一方面,一般法律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内容,不能和宪法的规定相抵触,否则就没有法律效力,应该废除或修改。③参见王昕:《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法学论丛》2005年第11期。也有学者认为宪法效力最高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宪法规范规定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在法律体系中的等级和相互关系,处在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地位,对其他规范性法律起着调节之作用;第二,宪法是普通法律制定的依据,为普通法指明原则、方向、目的和任务;第三,宪法规范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其他规范性法律违反宪法时,要么被修改,要么被废除。④参见骆伟建:《宪法规范是法律规范》,《法学》1985年第12期。还有学者认为宪法效力的最高性表现在4个方面:第一,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反映的是一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故而应当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第二,宪法是普通法律制定的依据和基础;第三,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的根本活动准则;第四,宪法的修改比普通法律的修改在程序上严格和复杂。⑤参见催敏、于迟:《试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法学杂志》1982年第2期。
关于宪法效力最高性的分歧主要不在于宪法和普通法律的关系,而在于宪法能否成为一般行为判断的法律依据。这就涉及到宪法效力的直接运用问题,即宪法效力是否具有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判决功能。由于宪法规定的是国家之根本问题,为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制度的稳定性和免受破坏,不能把宪法的效力等同于一般法律效力。但是不能把这种最高性视为一种高高在上的不能运用的“圣神之物”,而应该让其走下“神坛”,一方面,把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与普通法律分开,另一方面又不能把这种效力的最高性束之高阁,而应该使其具有一般之判决功效。这样,宪法效力的最高性就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宪法与普通法的区别;另一方面是宪法最高效力在宪法实践中至上性,即宪法效力判决之权威性。
三、宣示宪法最高效力的必要性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在内容上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它是其他一切法律规范的依据,它的废、改、立无不遵循着特殊的程序和步骤,这一切的不同无不向人们宣示着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最高效力。所以,将宪法内在的最高效力通过宣示表现出来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宪法运行的需求
宪法之生命在于宪法的运行,设计的再良好的宪法,如果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运行,那也是徒然。宪法典是宪法精神和内涵的载体,作为一部书面的法律文件,只是在文本上享有效力的最高性。欲使宪法效力的最高性由应然转化为实然,则必须彰显宪法效力的最高性,而这一过程在宪法的运行中就会得以比较完美的体现。可以说,一部真正良好的宪法,应该是一部“活的”宪法,而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文本。
宪法的运行是一个动态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有各种问题的出现,比如宪法最高效力来源于哪里?宪法与下位法的具体关系如何?宪法的效力界限在哪?宪法与具体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的关系如何定位?“最高”可以表明宪法的重要地位,却没有办法表述宪法在法律结构中的作用。如果我们仅仅承认宪法效力的最高性,而没有在宪法文本中进行宣示,这种最高性往往会沦落为一句有名无实的口号。因此,通过明确的宣示,将宪法的最高效力表述得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以解决宪法运行中的此类问题,使宪法的运行更为平稳和流畅。
(二)法律普世价值的需求
近代宪法的产生、发展与西方文明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是分不开的,这种“高级法”观念是自然法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然法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也许用梅因的话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了。”①[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3页。可以这样说,众多的自然法思想家都认为,自然法是正当理性的天然尺度,自然法效力高于实在法。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设,自然法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检验法,而且应是一种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启蒙思想家们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就是将自然法规则进行转换,通过转换将自然法中的正义与理性、公平与自由转化为世俗国家机关的法律规则,并赋予这种规则更高的法律地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法。②参见姚曙明:《论宪法最高效力的本源》,《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可以看出,近代宪法与自然法的渊源关系是如此的深厚,要在现代社会彰显自然法所提倡的自由、平等、正义等理念,宣示宪法效力的最高性就是必然之要求了。
(三)社会现实的需求
美国著名的学者伯尔曼曾经说过,现代社会面临着一种整体性危机,这种危机是法律信仰之缺失的危机、是宗教信仰之缺失的危机、是一种精神性危机。③伯尔曼:《宗教与法律》,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在这种危机面前,人类如何才能获得重生呢?在伯尔曼看来需要一种整合,而不是分离,需要划一,而不是离散。在这种整合与划一中,什么将起着引领作用?是对法律与宗教的整合,是法律的神圣性和宗教的社会性。伯尔曼是以人类学、未来学和历史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的。单就本文所论述的宪法问题,面临的这种精神危机而言,就急需我们宣示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且不说社会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需要。可以说,现代人精神的彷徨,灵魂的毁灭,是一种信仰的缺失,是一种信念流失的表露。而要医治这种时代的精神之病,需恢复人的信念,健全现代人的灵魂。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能突围的局限,在这种既定的框架下,人类需要寻求生存的空间,这种空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一种表现,亦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人类也许有足够的能力和力量去改变现有的物质世界,我们可以以新貌换旧颜,但人类未必能够在任何时候都治愈心灵、精神的残缺。宪法典是一种精神的物化存在,这种存在寄托着人类对美好社会秩序的向往,我们一方面需要不断的完善这种宪法典的既存形式,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时代的步伐下,发展这种既存形式以外的精神内涵,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在一个精神缺失的时代构建起一个新的精神空间,在那里可以看到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宏愿。
以上着重从社会的精神层面来论说社会现实状况对宪法效力最高性宣示的需求,没有从其他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这主要是我们现代社会虽然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但我们也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诚然,从社会的其他角度来说,宪法效力最高性的宣示也是非常之必须的,但宪法效力最高性的宣示,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尤为重要,在宪法最高效力的宣示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树立起宪法之信仰、可以培育民众对宪法的推崇与遵守、可以为社会树立一种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昭示下,人类可以找到一种集体的互助感、需求感。
(责任编辑:马 斌)
DF01
:A
:1674-9502(2014)04-080-05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2014-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