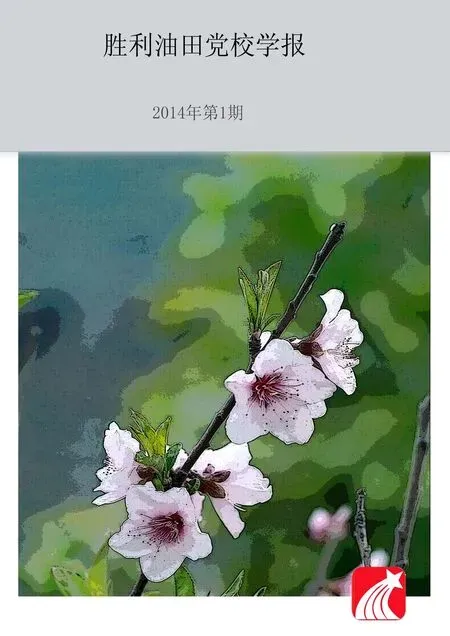新过失论对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完善的影响
孟祥微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一、 问题的提出
经《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罪由结果犯变为危险犯,使刑法对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制提前,同时也使环境污染犯罪由过失犯变为故意犯。虽然调整强化了对生态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但面对我国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以及环境犯罪自身的特殊性,在环境污染规制方面过失犯的缺失仍然导致刑法对生态环境法益保护的严重不足,与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和社会需求相矛盾。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的规定坚持了以“结果无价值”为导向的旧过失论,在这种立法体系下并没有过失危险犯存在的空间。为解决这一矛盾,有必要考察德日刑法中的新过失理论,探索环境犯罪中处罚过失危险犯的可能性,促使我国过失犯理论及立法与社会发展需求接轨。
二、我国刑法关于环境污染犯罪规定的缺陷
1.对修改后重大环境污染罪的重新审视。比较修改前,重大环境污染罪在法律条文上最明显的改动在于删除了结果构成要素“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而笼统规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即修改后该罪不再以发生“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事故”为条件,体现了由保护单一的“人类环境”向保护“生态环境”的立法观念的转变。这一修改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其一,修改后该罪是抽象危险犯还是结果犯,其二,修改后该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还是故意。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分歧在于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污染”是对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行为的概括性描述,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即行使了污染环境的行为,“严重”是对行为本身是否纳入刑法评价的程度限制,本罪成立与否不在于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危险结果而在于行为本身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而与之相对的观点认为,“严重污染”是指造成了环境被严重污染的实害结果。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可取,这与环境污染犯罪自身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反观刑法中规定的实害结果,通常表现为人员伤亡或能够以金钱衡量的财产损失,能够将对法益的侵害具体化、明确化,将“严重污染环境”这一抽象要素作为实害结果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认定。因此,笔者认为修改后的重大环境污染罪是抽象危险犯,污染可以表现为一种实害结果,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危险状态或危害行为。如果出现严重实害结果,则符合“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应作为该罪的结果加重犯处罚。
第二个问题分歧较少,通说认为修改后重大环境污染罪由过失犯变为故意犯。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为过失犯罪,导致对故意犯罪只能借道投放危险物质罪处理,刑(八)修正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在罪过形式上进行纠偏,根据立法目的应当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这种基于立法原意进行主观解释的方法虽然有利于全面保护生态环境法益,但却忽视了我国刑法总则对分则的限制,为了弥补法益保护不足的漏洞而突破罪刑法定原则。下面仅就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的规定,探讨重大环境污染罪的主观方面能否包含过失。
2.根据我国刑法,“过失”不能成为重大环境污染罪的罪过形式。首先,根据我国刑法第15条对过失犯罪的规定,不但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或过于轻信的过失心理,而且要求这种心理支配下的行为致使结果发生,这表明过失犯罪只能为结果犯。如前所述,重大环境污染罪为抽象危险犯,其成立并不以出现具体的实害结果为前提,因此主观方面不能包括过失。
其次,是不是在出现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就能以该罪处罚过失犯罪?答案仍是否定的,因为我国刑法第15条同时规定了“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法律有规定”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罪状中明确使用了“过失”一词作为构成要件,如过失致人死亡罪;二是罪状中虽没有直接使用“过失”一词,但根据字面含义可认定为过失犯罪的,如玩忽职守罪。也就是说在刑法以处罚过失为例外,在条文中没有明确体现的情况下,不能以法益保护的实际需要为由超出法条字面含义,处罚过失犯罪。我国刑法第338条并没有规定处罚过失犯罪,因此不能以过失作为罪过形式。
3.环境法益保护不足与环境污染犯罪化需要的矛盾。虽然传统观念中环境污染犯罪一般表现为,企业为追求利润而违背相关规定,简化或省略对废弃物的处理程序,直接将废弃物排放到生态环境中。但是在现代工业化生产中,操作工序日益复杂,产生的毒害物质种类繁多,行为人由于操作失误或监管不力等过失而导致毒害物质泄露、污染环境的现象屡见不鲜。修改后的重大环境污染罪虽旨在对环境法益予以充分保护,但实际上却将过失犯罪排除在犯罪圈外,在法益保护上顾此失彼。尤其是在因为行为人过失排放毒害物质而导致重大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无法通过环境污染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通过刑法第二章的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等途径使其入罪,又因两者在侵害的法益上并不一致,而失之牵强。
刑法具有谦抑性和不完整性,并非所有的法益侵害行为都必须由刑法规制,对危害行为犯罪化必须考察其必要性。在坏境领域强化刑法规制是西方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立法趋势,而如今我国也在GDP迅速增长的同时迎来了环境压力高峰,环境污染问题已严重危及国民的生存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中国当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堪比史上最严重,2012年,雾霾天气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1952年伦敦大雾。企业追逐利益不惜牺牲环境,而为之买单的却是整个人类社会,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不止于当下,更及于未来。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意味着不得不动用刑法这一道最后防线,而在我国刑法中对环境污染犯罪过失犯规制的缺失已不能满足控制环境问题的现实需要,如何弥补现有立法对环境法益保护的不足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新过失论引入对我国环境污染罪的立法完善
根据我国现有刑法规定,没有惩处环境污染犯罪中过失犯的空间,这不仅因为刑法分则中对重大环境污染罪的具体规定,更源于总则中对过失犯罪的原则性界定。只依靠修改分则条文就会出刑(八)修改前后拆东补西,捉襟见肘的困境,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对我国的过失论进行完善。
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的规定贯彻了旧过失论,而当今德日刑法的通说则为新过失论。新过失论是德日刑法为应对风险社会中涌现的问题,对旧过失论进行改进的产物。我国如今也走到了经济增长与公共安全矛盾激化的社会阶段,社会不安感剧增,对于新过失论的探究有利于为解决我国的发展问题提供思路。
1.新过失论与旧过失论的理论差异。新、旧过失论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别:第一,新过失论明确了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实现了从“结果无价值”到“行为无价值”的转变。旧过失论以刑事古典学派的道义责任论为基础,认为犯罪是基于人自由意志的产物,将过失与故意并列为心理事实,均为责任要素或形式,与成立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无关。由于旧过失论中过失只属于单纯责任要素,不涉及对实行行为的规定,犯罪认定往往以危害结果为逻辑起点,只要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危害结果,就考察行为人有无结果预见的可能性,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就成立过失犯罪。即使在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修正的旧过失论中,过失犯的实行行为也依赖于危害结果的存在,认为只有具备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一定程度的实质危险的行为,才是过失犯的实行行为。而新过失论以规范责任论为基础,认为责任的结构除心理事实外,还包括规范评价和期待可能性的内容。对过失进行非难的实质,在于行为人违反了“法期待行为者能服从其命令要求”的具有社会相当性的注意义务规范。新过失论的主干是将过失作为违法要素来把握的行为类型,违反注意义务本身就包含着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的属性,过失也就从单纯的有责性范畴转移到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的范畴。新过失论的最大发展在于明确了过失犯罪中实行行为独立于危害结果而存在,认为实行行为就是没有尽到具有社会相当性的法所期待的注意义务,即为回避危害结果发生而采取适当措施的行为。这就使得过失犯的认定不再需要以结果作为定罪的逻辑起点,使得抽象危险犯也有了成立过失犯罪的可能性。
第二,从旧过失论到新过失论体现了从侧重“结果预见义务”到侧重“结果回避义务”的转变。旧过失论对行为人的非难在于行为人不注意而没尽到结果预见义务,且以行为人注意能力的存在为前提。而在新过失论中,注意义务的核心变为结果避免义务,要求行为人为避免结果而采取适当的外部行为。一方面,随着“结果无价值”向“行为无价值”的观念转变,刑法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提前,在结果出现之前行为人就被刑法期待承担较高的义务以避免结果发生;另一方面,结果回避义务与“被允许的风险理论”密切相连,随着科技高度发展,工业生产密集而频繁,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社会置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而这些风险是难以预见且不可避免的,如果行为人尽其所能采取了合理的结果回避措施,即使出现危害后果也不应在刑法上非难,这避免了刑法对行为人过分苛责、强人所难而导致社会发展停滞。
2.新过失论对完善环境污染罪的适用价值。首先,新过失论为刑法惩处环境污染罪的过失犯提供理论依据。新过失论使过失犯罪不再依附与危害结果而独立存在,在行为人过失处置有害废弃物而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即使尚未出现严重的实害结果,也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填补我国刑法在环境法益保护方面的空白。其次,新过失论与环境污染犯罪本身的特点密切契合。环境污染犯罪的后果难以预见,而其潜在危害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难以在短时间消除,对于环境污染问题必须防患未然。新过失论对行为人的要求从履行消极的注意义务到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使注意义务提前化、具体化,有利于在生产环节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在行为人充分履行结果回避义务的情况下,即在没有结果回避可能性的情况下,不构成过失犯罪。这就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建立一种相对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新过失论的适用范围应受到严格限制。其一,新过失论的适用应限制在环境犯罪等与现代化生产相关的高风险领域。新过失论的提出以风险社会为背景,使得刑法的触角提前介入到社会生活,因此不应作为一般性原则用于传统犯罪领域。其二,新过失论不宜适用于对自然人的归责。新过失论加重了行为人的结果避免义务,为了防止刑法扩张,过度干预个人权利和自由,新过失论的适用应限于单位责任的归咎,而不宜用于对自然人的追责。结果回避义务具体体现为公司章程的制定、生产经营环节的控制、事故应急措施等单位整体对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控制行为。
我国刑法规定及其贯彻的旧过失论排除了环境污染犯罪中处罚过失犯的可能性,这与我国严峻的环境问题及法益保护需求相矛盾。对于该问题的解决不能局限于对分则的局部修补,而应借鉴德日刑法中新过失理论,对我国刑法总则中过失犯罪的规定进行完善,确立刑法在环境犯罪领域惩处过失危险犯的空间,加强对生态环境法益的保护。但新过失论也意味着刑法对社会生活的提前介入,因此应注意对新过失论适用范围的限制,防止刑法过分干涉公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