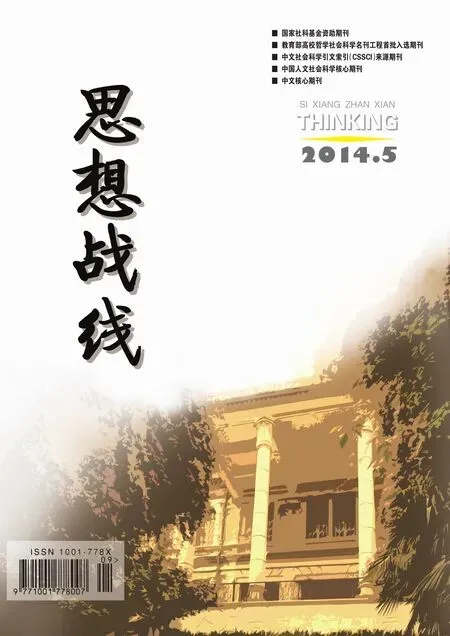明代中后期“银钱兼行”流通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
赵小平
在明代的货币变革中,先后经历了钱楮并用时期、短暂的单行钞和钞银钱共同流通时期、银钱兼行等阶段,其中,又以明初“钱楮并用”与明中后期“银钱兼行”流通格局的出现最值得关注。对前者本人已有拙作进行过专门研究,[注]参见赵小平《明初“钱楮并用”的再现及其原因》,《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探讨后者,无疑会涉及货币史学界长期争论的“白银货币化”问题,更关系到需要回答市场与政府两大因素在明中后期白银成为主导货币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因此,对明中后期“银钱兼行”问题仍然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禁银——弛禁——广泛流通:白银货币化的曲折历程
从明初推行的货币政策来看,政府是想恢复钱和钞并行的方法,故而一再禁用白银。然而,即使是禁银的明初,白银仍然禁而不绝,民间市场上一直有白银流通,这说明流通领域中使用白银已成为历史的大势所趋。
(一)从“禁银”到“弛禁”
白银在明代的合法流通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先后经历了从遭禁到弛禁,再到政府在全国推行的曲折过程。
洪武、永乐年间,从《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1375年)、洪武三十年(1397年)[注]《明实录》之4《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条记载:“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治其罪。”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670页。《明实录》之8《明太祖实录》卷251,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条记载:“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632页。和《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二年(1404年)、永乐十七年(1419年)[注]《明太宗实录》卷19,永乐元年四月丙寅条记载:“以钞法不通,下令民间有用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46页;卷27,永乐二年正月戊午条记载:“诏自今有犯交易银两之禁者,免死,徙家兴州屯戍。”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97页;卷211,永乐十七年四月壬寅条记载:“申严交易金银之禁。”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134页。的记载来看,两朝为了维护“大明宝钞”[注]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中书省印行“大明宝钞”,面额从一贯至一百文共六等。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四月,新增发行五十文至十文共五等小面值宝钞。“大明宝钞”自发行起就不断贬值,成化、弘治以后已经不再被民间所接受。的流通,曾数次颁布法令禁止金银在市场上的流通。后来,明仁宗初年 、[注]《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记载:仁宗监国时,“所增门摊课程,钞法通,即复旧,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禁止。”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4页。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注]《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宣德初年记载:“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乃益严其禁,交易用一钱者,罚钞千贯。”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4页。也行金银禁令,但明显比洪武、永乐两朝宽松。从多次颁布禁银令来看,禁银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相反,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大明宝钞”在流通中已开始不被民众所欢迎,二是银在民间市场上应当被民众广为推崇。这无疑是后来政府解禁白银的重要原因。
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即位后即下诏“弛用银之禁”。[注]《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4页。明政府长期以来的禁银政策开始改变。从英宗时开始放松白银禁令来看,“白银的使用,至少在洪武末年便已盛行。”[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4页。
开放用银无疑为政府进一步扩大在赋税折银方面的力度提供了契机。正统年间,明政府开始推行税粮折银措施,即所谓的金花银。张纯宁认为,《明史》卷78《食货二》将田赋改折为银的折银制度,主要推行于南直隶、浙江、江西等地,除了起运和边粮两项仍以实物征收外,其余依照粮四石折换银一两的比例折银,此即为金花银由来。[注]张纯宁:《明代徽州散件卖契之研究——并论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2003年)。金花银的实行,无疑说明民间用银已相当普遍。
(二)从民间市场到赋役折银:白银逐渐成为主导货币
自正统初“弛银禁”以后,白银已逐渐成为民间市场上事实上的主要通货。傅衣凌在对徽州散件土地买卖契约的研究中指出,洪武至永乐年间,徽州土地买卖以支宝钞为主,正统后以支银为主,成化以后卖契中支付已是全部以银为主。[注]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明代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1~251页。可见,明代徽州最迟在成化年间民间土地大额交易已全部用银,白银无疑受到该地区民众的广泛欢迎。
张纯宁所摘抄的景泰四年(1453年)徽州《休宁陈以成等卖田赤契》同样是用银支付:“休宁县三十一都陈以成,同弟陈以璇,承祖父有田二号……其二号田同弟合得分数田骨八分有零星,尽行出卖与祁门十一都程兴名下,面议时值价白银六两四钱正。”[注]张纯宁:《明代徽州散件卖契之研究——并论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中华民国九十二年(2003年)。从该地契中可以看出两条重要信息:一是交易全用银,二是土地买卖存在出售田骨、田皮[注]田骨,指的是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田皮,指的是土地经营者或耕种者的经营权或耕种权。两种不同交易情形。
赋役征银政策对于白银货币化进程无疑起到了加速作用。明代赋役改革与历史上历代改革最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赋役折银”方面,而改革无疑与白银货币化进程又密切相关。纵观明代赋役改革,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略有不同,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大多与折银有关。明初,在田赋折色[注]明初田赋征收主要包括本色和折色。其中,本色是指征米麦等农作物,折色是指可以用银、钞、钱、绢等代替米麦交纳。中就有白银,如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就曾“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注]《明实录》之4《明太祖实录》卷105,洪武九年三月已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756页。可见白银在明初就已在赋役征收中存在,只是白银与其他货币(钞、钱)及实物(绢)都可以折纳,即并不是以折银为主。明代赋役折银,经历了前期以地方赋役改革折银为主要形式,后期由局部向全国扩大的趋势,如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在苏、松等府推行的“平米法”(即以平米算出应征米粮和银两数额)、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初行于福建的“十段锦法”(着重于改革均徭,附带清理田赋)、明世宗嘉靖年间(1521~1566年)在苏州府试行的“征一法”、明中叶以后北方山东和北直隶等处实行的“一串铃法”、明中叶以后推行全国的“一条鞭法”等都涉及折银问题。不难看出,折银已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而这一特点在梁方仲、[注]梁方仲:《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6年4卷1期;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唐文基 、[注]参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万明等学者对明代赋役改革研究中皆进行了专门探讨,其中,万明更是认为:“在‘一条鞭法’于全国普遍实行之前,伴随着一系列赋役改革,白银已经基本奠定了流通领域主币的地位。”[注]万 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随着明代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上对白银的需求量大为增加,白银的供给无疑又成为政府和民众关注的重要问题。明代白银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内自行开采银矿以获得白银,二是通过对外贸易以中国货物换取国外白银(即外银的流入)。
就国内而言,明代征收金银课税,皆因为产银地[注]明代银矿主要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浙江、福建、湖南、河南、江西、甘肃、陕西、山东、北直隶等处,其中,云南产银量最大,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五金第十四卷》云:“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这里的八省,即四川、贵州、浙江、福建、湖南、河南、江西、甘肃)参见马跃东主编《龙之魂·影响中国的一百本书》第35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968页。较多之故,因此,明代白银的开采情况可以从征收的银课量多少得到体现。据全汉昇的研究,太祖洪武年间银课收入为75 070两,太宗永乐年间为934 898两,仁宗洪熙年为212 864两,宣宗宣德年间为2 308 058两,英宗正统年间为930 833两,宪宗成化年间为1 424 020两,孝宗弘治年间为983 312两。[注]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下册,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第602~610页。从中可以看出,明太祖至孝宗朝期间,太宗和宣宗两朝征收的课银最多,说明这两朝是明代银矿开采较好的时期。但平均下来,“明朝每年平均银课收入,大约在10万两左右。进入明后期,实际上已不足10万两。”[注]万 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因此,虽然明代产银地较多,但从绝对开采量来看,本土白银供给量并不足以满足日益增加的白银需求量。
随着白银需求量的日益扩大,在国内白银开采有限的情况下,[注]梁方仲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本土产银数量不多。参见梁方仲《明代银矿考》,《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0页。外银进入成为又一重要来源。[注]对于明代外国白银输入问题,史学界有许多相关研究:如梁方仲对明代白银输入中国及其成为主要货币过程的论述(参见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179页);全汉昇在《中国经济史论丛》中有数篇文章专门论述(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年,第365页、第417~435页、第435~450页);万明在《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中也有考察(万 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有两个来源:首先是日本,其次是美洲。其中,日本白银进入中国时间最早,早在明嘉靖以前就已有日本白银的零星进入,只是从嘉靖以后日本白银才大量涌入中国而已,如万明综合日本岩生成一和美国学者艾维泗的估算,认为“在1540~1644年的一百年间,如果以平均每年75吨计算,那么,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 500吨左右”。[注]万 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美洲白银进入中国则是在隆庆、万历以后(即明中后期以后),绝大部分是经欧洲转运而来,如全汉昇认为美洲白银最终有三分之一流入了中国。[注]全汉昇:《明清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66本),1995年。
从上述白银供给的两大来源来看,明中期以前基本靠国内自己开采。换言之,在明代白银货币化进程中,明中期以前白银事实上已成为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但其供给基本上依赖中国内部的白银开采,外银流入较少。外银大量进入中国是明中期以后的事,因此,并不是外银流入导致了中国明代的白银货币化,而是中国白银货币化所出现的白银需要量的巨增,为外银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和需求空间。
二、购买力的持续稳定:铜钱广泛流通的基础
明景泰三年(1452年),政府借口钞法不通,“命申明钱禁”。[注]《明实录》之33《明英宗实录》卷216,景泰三年五月壬寅,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659页。此次禁止铜钱流通,完全是想通过禁钱方式来挽救宝钞的继续行用,由于宝钞不被民众接受已成为事实,因此,此次禁钱之举势必难以持久。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再次开放用钱,但却并未新铸年号钱。虽未能新铸钱,但在恢复和提高铜钱的法偿地位方面仍然作出了努力,“凡征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注]《明实录》之40《明宪宗实录》卷19,成化元年七月丁巳,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85页。“令天下诸司,凡征收支给之额,钱钞兼用。”[注]《明实录》之41《明宪宗实录》卷41,成化三年四月已未,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45页。同时,规定宪宗以前所铸钱与历代旧钱都可以流通:“令民间除假钱、锡钱外,凡历代并洪武、永乐、宣德铜钱及折二、当三,依数准使,不许挑拣。”[注]《大明会典》第1册卷31《户部十八·钱法》,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585页。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年),再次正式铸造“弘治通宝”,而接下来的再次铸新钱到嘉靖时期才又开始。从铜钱的使用来看,仍然实行新铸“弘治通宝”钱与“大中通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宣德通宝”及历代旧钱混用方式,但不允许薄小伪钱流通。并规定赎罪和收税,洪武等钱与历代旧钱兼收,如果没有洪武等本朝铜钱,则以历代旧钱以二当本朝钱一折交。[注]《明实录》之59《明孝宗实录》卷196,弘治十六年二月丙辰,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622~3623页。
就官方铜钱的购买力而言,与宝钞购买力不断下降相比,官铸铜钱的购买力总体较高,且较为稳定。洪武初期500文至1 000文就可以购买1石米。成化十八年(1482年),因为灾荒在大江南北普遍发生,即使在如此缺乏粮食的情形下,1斗米也才卖到七八十文。[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98页。官铸铜钱购买力在明代不但较为稳定,而且还有所上升。这一点可以通过与钞、银比价的变化看出来。洪武八年(1375年)时“每钞一贯准铜钱一千”,[注]《明实录》之4《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669页。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贯,而钞法益坏不行”。[注]《明实录》之8《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417页。可见160文钱就可以在两浙、福建、两广、江西等处折钞1贯了。宪宗成化时(1465~1487年)则钞一贯已不值1文钱。[注]《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4页。不难看出,铜钱与宝钞的购买力相比,在不到100年间铜钱购买力上升了1 000倍。
如果说钱钞比价变动因为宝钞购买力持续下降原因而无法准确说明铜钱购买力的稳定性的话,我们拿铜钱与白银再进行折价比较,仍然能看出铜钱购买力的持续稳定这一特征。从彭信威先生辑录出来的“大明宝钞价格表”中官方每贯钞折白银和铜钱的比价来看,当时银钱比价为:洪武年间铜钱1 000文折银1两,永乐年间铜钱960~980文折银1两,宣德至景泰年间又恢复至铜钱1 000文折银1两,成化年间基本上是铜钱800文左右折银1两,弘治以后维持在铜钱700文左右折银1两。[注]上述数据依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大明宝钞价格表”整理而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94~495页。可以看出,与白银相比,铜钱的购买力不但有较为稳定的维持,而且在成化以后还有所上升。
至于铜钱购买力较为稳定甚至略有上升的原因,彭信威先生的观点较为全面:一是铜材价格的上涨。彭信威先生按洪武元年的计赃时估来推算,“当时一百斤铜值银五两;景泰四年(1453年)红铜是每百斤六两;万历五年……每百斤是银七两;万历二十五年以后是每百斤十两五钱”。[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98页。二是制钱份量一再增加。“洪武通宝”小钱最初重一钱。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改定为“每小钱一文,用铜一钱二分”。[注]龙文彬纂:《明会要》(下)卷55《食货三·钱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040页。弘治钱重一钱二分,嘉靖钱重一钱三分,[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99页。隆庆四年(1570年)定钱重为一钱三分。[注]《明实录》之94《明穆宗实录》卷43,隆庆四年三月辛巳,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088页。总体来看,每枚铜钱自身的重量后期比初铸“洪武通宝”时有所增加,铜钱自身价值增大。三是铜钱数量不足。政府为了维护宝钞信用度而铸钱较少,且时有禁钱措施。加之铜钱还不时外流,“朝廷岁令天下织锦、铸钱,遣内官买马外蕃,所出常数千万”。[注]《明史》卷164《列传第五十二·邹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437页。因此,铜材料价格的上涨、铸钱重量增加、铜钱数量不足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无疑会抬升铜钱的购买力。
从有明一代来看,铜钱虽然经历过禁止通行的时期,但与银、钞两种货币相比,铜钱仍然是明代流通时间最久的货币形态。明代铜钱的流通先后经历了“主导货币[注]在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之前,流通领域中主要以“洪武通宝”、“大中通宝”和历代旧钱为主。——宝钞辅币——白银辅币”的演变历程。铜钱适合小农经济的交换和有较为稳定的价值,为其可以两次作为不同主币的辅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毋庸置疑,铜钱的再次开禁和稳定流通,无疑为接下来“银钱兼行”时代的开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银钱兼行”流通格局的全面确立
明中期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步,同时也影响到货币形态和货币材质的发展。明中期宝钞不被民众接受以后,正如弗雷德曼所说:从人类经济理性角度来说,在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必然会选择另外一种替代货币,而不会回到直接的物物交换状况。[注][美]米尔顿·弗雷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安 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5页。在宝钞贬值和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现状下,“明代约自正统以后,白银逐渐成为流通通货,至隆庆年间白银逐渐取得合法货币的地位。银两成为本位货币,交易价值大者多用白银计值,民间亦是普遍用银;但小额交易还是多用钱”。[注]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从明代货币经济发展史来看,明中期以前是“钱楮并用”时期。但是,从成化、弘治以后,白银逐渐由民间上升为事实上的主要货币,市场和民间的自然选择迫使政府随后承认了白银的货币地位,并且取代宝钞上升为流通领域中的主导货币。就像明前期出现的“钱楮并用”时代一样,明中期以后进入了“银钱兼行”的新时代。事实上,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起,“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注]《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4页。风气已经形成,“银钱兼行”的货币流通格局已经正式出现。
“银钱兼行”格局下虽然铜钱与白银同时行使,但以银为主币是关键。万明通过对明代白银流通状况进行考察,提出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观点。[注]关于白银货币化问题,代表性学者有两位:王文成认为宋代开始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万明强调明代白银货币化(万 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载纪宗安主编《暨南史学》第2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黄阿明结合上述两人的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应该曾经有过两次白银货币化过程,即第一次发生在宋金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明代中后期。就这两次白银货币化的进程而言,第一次的历史进程明显要比第二次所费时间长得多”(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我认为,白银货币化进程的确早在宋代就开始了,但是,这一进程真正意义上的完成时间在明代中后期,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纸币失去信用后之所以由白银取而代之,其原因何在?我认为,以下几方面因素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白银的货币化是从民间开始的。明中期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峰,许多学者认为,明清时期是继春秋战国、唐宋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时期。[注]方 行:《再论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林文勋,杨华星:《也谈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思想战线》2000年第6期。因而明中期白银在民间广泛流通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选择的结果。万明指出:“白银货币化自民间崛起,不是国家法令颁行的结果。” “明代白银货币化经历了民间自下而上到官方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历程。”[注]万 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其次,白银在民间的流通也冲击到上层社会。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孝宗即位后,丘濬上《大学衍义补》时对货币问题有专门论述:“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注]丘 濬:《大学衍义补》第2册,卷27《铜楮之币》(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02页。丘濬之所以主张以白银为上币,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朝野率皆用银”[注]《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4页。的趋势。
再次,明代赋役征收由折银到全部征收白银的演变,使白银流通在国家层面得到推广。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曾进行了无数次赋役改革,这些改革名称不一,推行地区不一,但是,却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改革中最主要、最有突破性的内容。万明认为:“大量史料说明,在‘一条鞭法’于全国普遍实行之前,伴随着一系列赋役改革,白银已经基本奠定了流通领域主币的地位。”[注]万 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换言之,赋役改革以征银为主,政府以自上而下的形式无疑有助于推动白银货币化在全国范围内的进程。
此外,白银主币地位的逐渐确立还与长途贸易、转运贸易等大额贸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并与海外市场连接起来,在这一点上,白银货币需求量的增加起了重要作用”。[注]万 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随着大额贸易的发展和民间普遍用银,白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致使社会各阶层皆产生了对白银的需求。不可否认,白银需求量的巨增,又为外银流入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外银的流入,则标志着“中国市场的极大扩展、超出国界、走向世界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注]万 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正如黄阿明所言,“大明宝钞体系崩溃的过程,同时也是另一种货币——白银逐渐崛起的过程,这决非偶然因素所致,而是社会经济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结果。但是,这一过程最终得以实现,国家又起着关键性推动作用”。[注]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也就是说,白银代替宝钞成为主导货币,是市场与政府共同推动的结果:民间用银与大额贸易的发展是市场自发抬升白银货币地位的举措,而赋役征银则是政府政策性的导向。
“银钱兼行”流通格局的出现,同样是市场与政府两大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如前所述,铜钱曾在明代初期(更准确地说是在洪武八年大明宝钞发行之前)是流通领域中的主币,只是在大明宝钞发行后才失去了流通领域主要货币的地位,“不再是最重要的计价和流通手段。但铜钱作为民间日常交易支付所普遍使用的小额货币,在货币经济结构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注]王裕巽:《明代钱法变迁考》,《文史哲》1996年第1期。也就是说,在政府为维护宝钞的流通而多次申禁铜钱流通过程中,铜钱在民间市场上仍然大量流通,受政府禁钱政策影响并不大,这就为后来银钱二元结构货币体系的出现奠定了市场和民众基础。在民间普遍使用铜钱习俗推动下,铜钱的解禁势在必行。而白银的解禁和最终取代“大明宝钞”主币地位,同样是民间市场逆政府禁银政策而持续流通白银的结果。而隆庆年间以国家法定的形式确立银两本位制后,大额交易用银、小额交易多用钱的“银钱兼行”制度正式确立,并在全国范围推行。
综上所述,明中期前就已自民间崛起的白银,到中期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奠定了主币的合法地位(即建立了银本位制),嘉靖以后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兼行”制度在国家层面得以正式确立。白银的货币化无疑是中国国内市场不断拓展的产物,反过来,白银的货币化又使中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开始紧密联系起来,中国的商品走向世界,世界的白银流入中国。[注]输入中国白银的来源地主要有日本、美洲、欧洲。其中,欧洲主要是作为美洲白银的中转地。白银作为货币与国内市场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共同将在中国已占据主导地位的白银纳入世界货币范畴之内,并促使中国市场融入到世界市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