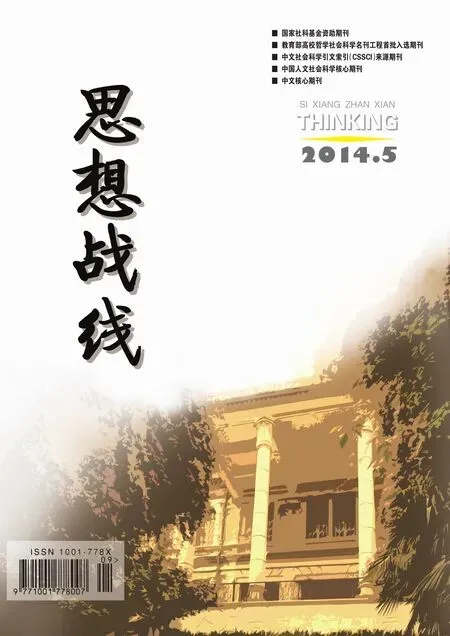焦虑的思
——对穆旦与英美现代诗关系的再探讨
杜心源
在20世纪30~40年代,通过瑞恰慈(I.A.Richards)、燕卜荪(William Empson)等新批评派人物在中国执教这条途径,新批评派有关现代诗必须建构“诗篇人格”的超越性,打破固定抒情主体的主张给了《中国新诗》和《诗创造》同仁们巨大的启发。正如袁可嘉所说:“(现代诗) 批评以立恰慈(即瑞恰慈) 的著作为核心,有‘最大量意识状态’理论的提出;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意识活动的获致。”[注]王圣思:《“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页。作为“九叶派”的佼佼者,穆旦将自身的怀疑主义气质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超越性精神合流后,拆解了自身所处的恒常世界,把日常经验置入文本符号之中,使之产生讽喻的效果,生发出了多重性的意义。本文拟追踪穆旦是如何凭借 “诗篇人格”的精神主体与现实的既成话语体系进行持续斗争的轨迹,并探寻这一斗争如何导致了其诗作在精神上的丰富性。
一
穆旦在1947年的诗作《时感》里写道: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它说:我并不美丽,但我不再欺骗,
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
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注]《穆旦诗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25页。
穆旦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往往表现为怀疑其 既有权威和价值观,更进一步的是,他拒绝了“血里奔流着勇敢”的青年的“希望”。当我们说现代诗与现实的关系由“传达”转为“反省”时,就包含了对“期待视野”——主观情感期望的未来美好图景的拒斥。
叶维廉把郭沫若等人歌颂“希望”的文学称作“假想的完美世界的文学”,[注]《“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1页。一旦感到现有秩序的无意义,就把自己寄托到某种不可知的、未来的纲领蓝图上,可说是这批诗人的普遍做法。但穆旦不仅看到了希望的“茫然”,还认识到“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是不能被忽略的。不加批判和反省就套用某一“未来权威”的纲领和教条来解释实存世界的态度,在穆旦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依附于任何权威(不管现存的或是将来的)都意味着以庞大的概念、教条取消主体的思维存在。这样,诗的“自足”将丧失殆尽,依然改变不了自己从属的、“传达”的地位。穆旦的原则是, 即使主观的情感已倾向于某种明确的纲领、概念,诗人知性的“诗篇人格”仍然要抵制这一倾向,行使自己反省和“拷问”现世经验的职权,例如在他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创作的《葬歌》:尽管穆旦有把过去“小资产阶级”的“我”彻底“埋葬”的愿望,但这意味着把“我”献身到“希望”手里去,按“希望”的模式去图解现实。这时,“诗篇人格”对诗人企图舒舒服服去信仰的心情发出了斥责:“要是把‘我’(能动主体)也失掉了,/哪儿去找温暖的家?”
无论《时感》或《葬歌》,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出辩论的性质,不妨说,“希望”不仅是外在权威的华丽口号,甚至也是诗人自己的“希望”,期冀一个“黄金世界”的出现。但是,每一个单纯的“希望”旁都有“诗篇人格”的影子在守候,催请“希望”去看一看“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把“希望”的热情冷却到零度。与其说“诗篇人格”反驳的是权威,不如说是在反驳诗人的相关心情。
在现代主义诗歌的话语体系中,作为诗人能动主体的“诗篇人格”是从现实的常规性里分离出来的,现在又杜绝了让主体逃逸到政治乌托邦式的“黄金世界”中去。穆旦把自己从历史和未来中独立出来,获得了主体彻底的“自由”,但这是一种无家可归,没有任何身份的“自由”,传统、现实、未来、个人……都纷纷从主体身上剥落,成为被对象化的客体。穆旦之所以仍期望“希望”是真实的,值得自己投入的,也可以说是基于对丧失身份的主体虚无性的焦虑。我们在他的《从空虚到充实》中,可看到这种焦灼的情绪:“大风摇过林木,/从我们的日记里摇下露珠,/在报纸上汇成了一条细流,/(流不长久也不会流远,)/流过了残酷的两岸,在岸上/我坐着哭泣。”[注]《穆旦诗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7~18页。在这里,传统的、文化的深根已被琐烦的现实之流带走,但“我”知道,现实是纷坛的、变动的,“流不长久也不会流远,”“我”是被抛的,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我”的“哭泣”,是对虚无的恐惧。
在西方,现代主义所对抗的语境是:以前稳固的、有价值可信性的现世经验已经成了破碎的、四散的“物化”存在。主体要保存自我的价值,务必和这一切断绝关系,屹立在现世的废墟之上,因此,现代主义诗人创造了精神乌托邦的诗化语言世界(文本)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认为对艾略特(T.S.Eliot)来说,“诗性感觉的特质就是形成一个新的整体,把繁杂的经验融入到一个有机整体中”,[注]Astradur Eysteinsson,The Concept of Moder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0.在这一整体中“历史的想象转化为神话的想象——一种时间已不存在的想象”。[注]Astradur Eysteinsson,The Concept of Moder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0.
所谓“时间已不存在”,是指主体已完全摆脱、排除了自然的、物化的经验世界对他的烦扰。主体不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的血肉之躯来感知世界的,而是作为超越了所有物质关系的纯思想,纯精神的存在在“心理”世界中“建构”一个本质世界的。比如艾略特《枯叟》里的一节:“神迹被当作奇迹。“我们要看个神迹!”真言中的真言,不能够发一言,被包在黑暗之襁褓中。在岁月的青春期基督这只虎来了。”[注]《英国现代诗选》,查良铮(穆旦)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这几句诗依据的完全是精神逻辑,物质的客观世界根本接触不到超越神性的真义,把“神迹”错当“奇迹”。虽然是在现代社会,包在襁褓中的基督身上却寄托了神圣的真言,对此现代人实际是处于“黑暗”中不可能认识到的。但基督这只“虎”仍然以“真言”压迫、抵制着被拘禁在物化关系中的现世实存。
与艾略特在诗中以精神逻辑建构的“本质世界”相比,客观物质世界是堕落的、被 “虚无”的世界。在艾略特用纯粹思维自由聚合的精神中心面前,客观世界是从属性的、是主体的对应物。换句话,客观世界完全成为了主体的“环境”或“背景”,它与主体的关系是“建构”和“被建构”的关系;而主体与现代经验是隔绝的,它带着超然的、真空状态的眼光审视敌意的一切。所以,现代主义诗对世界的 “反省”是建立在“颠覆”的基础上的——颠覆并在语言符号中重构一个内在的、陌生化的自律精神空间作为主体的心灵栖居地。这样,主体虽然从历史和时间中独立出来,但仍能进入精神空间的安全港,避免了无家可归的被抛状况。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一解决方法都蕴涵了危机——把自己同时代割裂,过于强烈的精英意识使他们高踞于公众之上;否定现世的一切,在假定的精神世界中求得存在依附。这些都使现代主义诗愈发走向与世界的疏远和本身的狭隘。理查德·谢帕德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困境:“现代主义诗人在他们与世隔绝的、唯我论的可怕世界里的处境,似乎与卡夫卡笔下饥饿的艺术家处境相同,这个艺术家无论在社会内部或社会外部都找不到合适的食物。或者,与托马斯·曼笔下的艾德里安·利弗库恩的处境相同,在他冷冰冰的智力活动背后,是绝望的沉默不语。”[注][英]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05页。
为了主体的安全不惜牺牲物质世界的实在性,至少在穆旦看来,这是过于沉重的代价。要记住,穆旦当初从浪漫主义的象牙塔之梦里醒来,正是出于体验社会,认识现实的要求。中国知识分子深切的社会责任感束缚了他的手脚,说到底,他写诗的初衷仍是基于对社会的实用效能,这使他很难接受英美现代诗的纯美学解决方式。但是,穆旦既已获得超出一般性的现代主义“诗篇人格”,就意味着现实坚实性的大厦在他脚下坍塌了,而“希望”——穆旦浪漫理想的最后残余——也被证明只是小布尔乔亚对“未来权威”的妥协。也就是说,如果穆旦不遵循英美现代主义诗人“克服”自身危机所采取的现成路径或探索一条“中国式”的新途径,他将会把自己悬空到一无所有的孤绝状态;如果什么都不信任的话(包括‘希望’和符号化的精神空间),他将怎样抵挡虚无主义和“绝望”的侵袭?没有存在的依据,诗人凭借什么来写作呢?请看穆旦的《我》:
从静止的梦想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注]《穆旦诗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这里的“我”,是现代的、“诗篇人格”的“我”。“我”的独特视力看到了一般性、常规性看不到的隐晦层面,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确定性、概念、价值、希望……被“我”的眼光一审视就变成了空的、假的、破碎的。这样,“我”成为了那些快乐的、创造性的秩序的不和谐音,不管“我”的视力看到了什么,“生活”照常进行,现实的人依然“正常”而健康。那么“我”是什么呢?“我”人为地把自己隔绝在历史的整体性外面,时间、空间、群体均与我格格不入。因此,“我”只是唯我论的“我”(“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是自闭的、断绝了和外界一切“交往”的“我”。甚至这个孤绝的“我”也不过是“幻化的形象”,因为它毫无存在的理由,不错,“我”有优越的,独特的“视力”(纯粹认识力),但视力终归只是一种认识论能力 (西方现代主义则有着内在超越时空的“文本”本体),绝不可能做存在的根据。因此,“我”的焦虑不仅是对被幽闭,抓不住“时流”的恐惧,也是对“我”本身将陷于“绝望”的虚无主义空气中的恐惧。在这时,要是诗人不大声呐喊,冲出这充满了毒气和鬼气的“樊篱”的话,他恐怕会变成将外界和自身统统“虚无”化的颓废诗人。情势逼迫着穆旦——中国的现代主义诗人——交出自己的答卷。
二
穆旦在谈到他诗歌创作的理想时说:“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因为它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了。”[注]《穆旦诗选·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50页。
从这段话再联系到他在《打出去》中的诗句“我们由幻觉渐渐往里缩小,直到立定在现实的冷刺上显现”,我们看出,穆旦哪怕明知道现实(时代)是充满了恶浊和虚伪的空气的,他仍坚持冲出唯我论的“樊篱”去拥抱现实。就穆旦来说,他投入现实洪流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他不是根据现行价值观念和未来的希望来看待现实的,也不是被动地、“如实地”描绘现实面貌,而是“立定在现实的冷刺上”,只靠自己“诗篇人格”的认识力探索时代精神的各个层面(不被现存和未来的教条正视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穆旦的态度,难道不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吗?
奥登(W.H.Auden)对英美现代诗的效用的解释,正好有助于说明穆旦诗的现代性,他说:“诗,……绝不是证明生活的,也不是像宗教一样去修正生活。诗是认识生活的,认识生活的复杂性以及所有的卑微和崇高。”[注]Babette Deutsch,Poetry in Our Time, Westport: Green Wood Press,1975, p.428.再结合艾略特的论断:“一个人必须看进大脑皮层,神经系统,还有消化道。”[注]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1页。就足以说明穆旦“清醒的现实主义”与英美现代诗的契合。我们注意到,穆旦欣赏的英美现代诗人,都是深入体察现实,尚未完全退入符号化的、“神秘主义”的纯意义领域的作家,包括前期的奥登和写《荒原》之前的艾略特。拿奥登来说,他被称为:“在所有奥登诗的背后,都潜藏着一种紧张:在客观世界贵族化的鄙视和诚挚的爱混杂在一起。”[注]Stan Smith ed.,20th Century Poetry,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83,p.51.他的诗作有着“心理治疗”(psycho-diagnose)的特色,即对现实生活的复杂层面进行剖析的非凡兴趣,如他的《诗xx》中的一节:
当你想到时已经晚了;更接近的那一天
远远不同于那个遥远的下午
在外套的窸窣声和纷乱的脚步中
他们向被击垮的孩子显示了骄傲,
然而你不能离开,不能
哪怕你打了包打算一小时之内离开,
隆隆地沿着大路乘车逃走。
奥登惯于使用的寓言般充斥着隐喻、暗示的语言技巧在诗里得到了体现。我们在是诗中得到的现实是难以捉摸的、具有多层意蕴的复杂结合体。读者进入迷宫般的语象世界,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希冀获得明确的口信的阅读习惯,而只能以自己能动的主体思维破解诗中的隐晦深意。
奥登有着比上一辈现代主义诗人更浓厚的认识现实的兴趣,但依旧带有现代主义的极端精英主义气息 ——他对现实的态度是建立在颠覆与否定基础上的“认知”,自我的主体意识是他思维的唯一源头,这就决定了他省察现实的性质是带着“贵族化的鄙视”的俯瞰,而他自我则超然于这“混乱和喑哑的年头,冰川的时代”[注]Stan Smith ed.,20th Century Poetry,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83,p.49.之上。就像在《诗xx》见到的,文本高度形式主义化,是完全不遵从客观世界规律的艺术本体世界;语言符号按照主体的思维逻辑对世界进行浓缩和重组,得到复义的、满含玄机和隐喻的密码式的诗歌意象,从个人的不同观察角度理解,将会得出不同的答案。这种把对自己思维纯粹性的考虑优先于对现代经验的投入,使奥登的眼光最终脱不了“局外人”的视角,举个明显的例子,他的诗剧《为了时间的存在》中有一段诗是这样的:“这个孤单的家庭对贫穷的体验/与隔壁的那家毫无二致/无论谈话,吃饭,穿衣,爱和憎/彼此都完全一样。”为了批判现实平庸化和均质化的主体意识需求,不惜嘲讽贫困的家庭,这怎么说也是过分的贵族化,评论家乔治·弗莱瑟(George Fraser)曾尖锐地批评奥登的这一倾向:“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普通人的生活,虽然外面看平板枯滞,但如果能不抱成见地亲身体验,深入到生活的细节中,就会发现其中意蕴丰富、兴味无穷。”[注]George Sutherland Fraser,Essays on 20th Century Poets,Totowa: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139.
所以,“奥登被眼前的景象触动,但并不会因为想得太深落泪,而是发出嘲讽的笑声”。[注]Babette Deutsch,Poetry in Our Time,Westport:Green Wood Press,1975,p.423.但穆旦却是一位“落泪”的诗人,因为他无法把现实“虚化”和“颠覆”,虽然他严酷地反省和批判现实价值,但现实生活在他笔下有触手可及的质感:“ 因为我们的背景是千万人民,悲惨,热烈,或者愚昧的,他们和恐惧并肩而战争,自私的,是被保卫的那些个城……”[注]《穆旦诗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由此,我们才能了解穆旦为何没有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纯粹精神世界作存在依据,也没有堕入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中。因为穆旦虽然拒绝不无批判地接受任何既成的教条和口号,同时站在冷静的“诗篇人格”的高度对民族命运作拉开距离的反省,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他对现实存在本身的肯定。易言之,他不是把自己视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的、完全独立的主体存在,而是首先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既然生活在社会中,就是一个“社会人”,即无法超越血与火的现实,只是社会群众中普通的一员。
因此,穆旦虽否弃“被保卫的那些个城”(指城里那些‘价值秩序’的代表),却拥抱“悲惨,热烈, 愚昧”的人民,他们虽看起来“平板枯滞”,惹人厌倦,穆旦却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和自己是息息相关的。如他著名的《赞美》中的一节: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
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注]《穆旦诗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这首诗最触动人心的是其“体验的震荡”,诗人不再是独自觉醒的,凌驾于现世情感上的先行者和超人,而是浸润了个人的主观感受,被生活的平凡和伟大感动的普通人。诗人并未站在一个安全的观察角度上去评述处于战争阴影下的人的状况,相反,他将自己也设置在同一经验中,去经历诗中角色的经历。为此,他把经验发生时体会到的气氛及发生的程序都一一还原、呈现出来。这样,诗里的经验就有了可触可感的实质。
在奥登和艾略特的早期诗歌中,当诗人暂时忘记反讽的距离时,也往往会忽略文本否定大众 认识的需求,放弃冷峻“审视”的立场,而和诗中的角色,和读者建立起“合作”(complicity)的关系,艾略特在《阿·普鲁弗洛克情歌》里写道:“当我被公式化了,在钉针下趴伏,当我被钉着在墙壁上挣扎,那我怎么开始吐出我的生活和习惯的全部剩烟头?我又怎么敢提出?”[注]《英国现代诗选》,查良铮(穆旦)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体验”深深侵入了诗人安稳的主体意识中,现实经验不仅是被主体对象化的“客体”或“背景”,主体自身也成了被动的、易感的、受苦痛冲击的现世经验的一部分,评论家斯瓦尼(Erik Svarny)注意到早期现代诗的这一特征,他指出:“诗人,和我们一样,有时离痛苦和个人情感太近了。艾略特提出的‘传统’概念中包含了对现实两种态度的奇妙折中:要么存而不论,要么进行揭示暴露。当倾向后一种态度时,就导致了美学距离的消失。”[注]Erik Svarny,The Men of 1914: T.S.Eliot and Early Modernism,Berk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0,p.20.
对世界作“美学英雄主义”(aesthetic heroism)的颠覆与反省虽是更具主体性和“文学性”的做法,但现世实存毕竟是不可轻言否定的。穆旦确距“痛苦和个人情感”太近,现世的感性生存毋庸置疑经不起审美主体推敲的,是一种残缺的不完美存在,然而诗人自身确实生活在这一种残缺中,他无法再独自觉醒后就高踞于批判性的主体意识上。因为,一旦处于脱离客观世界的状态,这个世界上便没有自己承担责任的地位了。只有接受“我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社会里”这一命运,诗人才有可能在客观世界里获得一席之地,即在社会中作为能动的主体的紧张和责任感。
在这里,我们可以又一次看到穆旦“延宕”的本色。虽然有和西方现代主义诗人一样的对堕落的现实整体性的反感,他仍坚持把诗的存在依据置于现实社会中。于是,不同于英美现代诗的“自律”——主体自身成为最终目的,他的诗总带有“社会——历史”的身份。唯其如此,穆旦的诗才具备如此鲜明的特色:深入到现实的人的内心去理解他们的经历和心路的轨迹,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感受这变动不居的社会对内心的影响。
三
但穆旦毕竟是较完整地接受了英美现代诗观的熏陶,他的抒情诗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流行的“抒情”腔调有质的差异。如他的《防空洞的抒情诗》,诗里自我的主观感情是次要的,或说是隐蔽的:
谁胜利了,他说,打下几架敌机?
我笑,是我。
当人们回到家里,掸去青草和泥土,
从他们头上所编织的大网里,
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
而发现我自己死在那儿
僵硬的,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 息。[注]《穆旦诗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让人们感到扑朔迷离,“我”可以是多元的,分身为别人的。“我”可以是打下敌机的胜利者,又是“死在那儿”的失败者,且死尸的脸上还能挂着丰富的人类表情。要是对比如郭沫若等新诗人强烈表现个人主观情绪的抒情诗,就不难看出穆旦抒情诗的特异之处,个体的情绪,无论怎样强烈或“真挚”,都是粗糙的、私人性的同情、怜悯,惋惜……等等,穆旦却消解了这一个个体情绪的优越性,“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他”不是固定的某个人物,而可以是复指的,变动的,可以是既生且死,带有各式各样的表情的。惟其如此,诗人才可能超脱自己狭隘的主观感性,而变成他人中的任意一员,去体验各个角色不同的心情和命运。在穆旦的抒情诗里,“我”与“他”是混杂的、并置的,任何想从中区别出一个“我”的主观实在的努力都毫无意义。
由此,我们能够更深地理解穆旦“坚定在现实的冷刺上”的心情,主体不愿退出令人生厌的现实,为了对抗自己否定一切的绝望情绪,他选择了返回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道路,对生存在世上的小人物作出贴近的关注。正如艾略特指出的,诗人应力争把“个人的、不为人知的痛苦”转化为“某种丰富而陌生的东西,某种普遍而非个人的东西”。[注]Rene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950~1950, English Criticism,1900~1950,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185.
不同的是,艾略特是站在绝对主体性的立场上要求诗人摆脱现世规定性,而穆旦则依凭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希求突破小我的情感,去讲出民族、国家命运的客观真实情况。请看他《从空虚到充实》里的一段:
疲倦地,走进咖啡店里,
又舒适地靠在松软的皮椅上。
我该,我做什么好呢,他想。
对面是两颗梦幻的眼睛
沉没了,在圈圈烟雾里,
我不能再迟疑了,烟雾又旋进
脂香里。一只递水果的手
握紧了沉思在眉梢:
我们谈谈吧,我们谈谈吧。
生命的意义和苦难,
朱古力,快乐的往日。
于是他看见了
海,那样平静,明亮的呵,
在自己的银杯里在一果敢后,
街上,成队的人的人们在歌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他的血沸腾,他把头埋进手中。[注]《穆旦诗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现代主义诗的一个特点是:因为不再相信客观世界建立的实证主义体系、理性逻辑、价值系统和外在公理,它反而能够摒弃所有的束缚来探索事物的本真面貌。穆旦很多的诗篇里的人物,如《从空虚到充实》中找不到生活目标的小资产者,《赞美》里的老妇,《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和《农民兵》里的士兵,《漫漫长夜》里的老人等等,都是被社会价值体系忽略,甚至抛弃的形象。这里蕴涵的现代意义在于:当穆旦冷峻的“诗篇人格”看到了那些主流模式并不像它们表面呈现的那样动人时,他乐于去展示未被主导情境认识的个体存在境遇。所以,《从空虚到充实》里的小资产者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想投入火热的抗战中却又顾虑重重的“踌躇”的形象也有了意义。这不是依从某种既定的明确概念从现实生活中剥离出的“典型形象”,而是没有任何教条约束的点滴的存在真实。
在《葬歌》、《五月》、《裂纹》等诗里,我们看到了穆旦是一个承受着世界对他的压力,但决不放弃自己复杂的主体意识的“永不甘心的刚强的英雄。”(穆旦《诗》)而当他把自我推向广阔的时代后,他处理的角色和生存现象都定位在其内在真实性。故有人也许会感到他诗中的角色形象过于内向化,只注意自己的复杂和丰富性而没有社会价值的“普遍意义”。但对穆旦来说,他关注这些无力影响外在世界的小人物的内在感受,是因为他相信这些细小而琐碎的心理活动才是人的存在实际,任何信仰和主张最终要由人切实地感受和消化后才会有效。归根到底,穆旦诚恳地把对自己适用的准则也推广到诗中的角色身上——他坚信只有主体的意识,自我的感受半径是最终的裁判者。
出于相信内在的主体意识和个人具体存在的价值,穆旦有意识地深入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异质、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经验层面中去体验它们各自存在的理由。在《神魔之争》里,他先后把自己化身为神、魔、林妖、东风等角色,想象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该怎 样为自己生存的合理性辩护,在没有任何外在道德制约的情况下,各个角色经验均从自我的处境出发进行对话和辩论,结果谁都可以被批判,但谁也占不了上风。
公刘评论穆旦时说:“我不怎么喜欢穆旦的诗,他的诗太冷。不过,我也发现,他总是在同自己辩论,——没有任何结论的辩论。过多的内省,过多的理性,消耗了他的诗思。”[注]王圣思:《“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不错,穆旦在现代中国的诗史上确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一面根据主体内面的意识感受对外在价值体系作持续不断的追问,一面又不厌其烦地考察和反省现实生活中各种角色的内在丰富性,这使他的诗凸现出歧异多姿的色彩。穆旦并不会找一个既成观念来负载自己的主体,他总是根据以主体的能动精神来看待他所倾慕的英美现代诗,所以他的接受并不是一种法则、教条的移植,而是经过主体批判性地深思之后形成的,既对陈腐现实产生新鲜的冲击力,又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真正 “自己”的东西。穆旦,正如他给自己的诗集的命名,是一个《探险队》队员,他的力量源于他惊人的真诚——一切都要反复追问,成为真正在内心“发生”的信念。正如唐湜评价他的精神时说:“辩证的发展不允许有一个真正的‘至善’的终结,一个绝对的理念;一个自觉的超越的心灵史不该停滞了的……”[注]王圣思:《“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2页。这是他在毫无现代诗前例可援引的中国土壤上探索的艰辛,也是他与现实作疲乏的、坚韧的斗争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