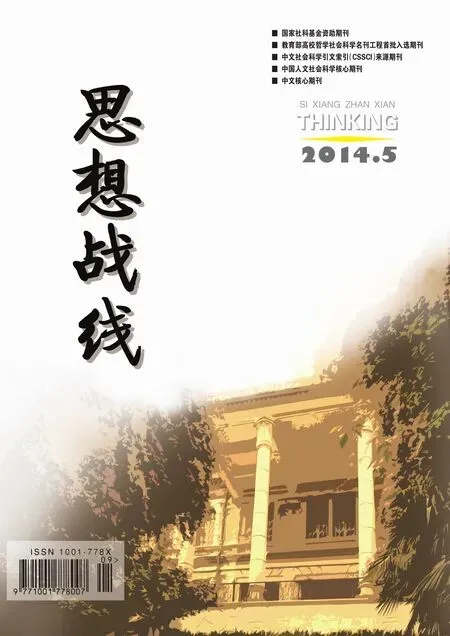民族旅游社区治理:概念关联与内部机制
白 凯,杜 涛
近年来,在发展地方经济与凸显地方文化的倡导下,民族旅游社区不断增加。此类社区不但具有一般社区的特征,还凸显了社区的民族性、地方性和旅游功能,其更易受到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从而使社区边界受到冲击,社区内部构成因素(边界、群体关系和信任、群体认同)受到牵制和干扰。
如何使此类社区在旅游发展、文化保护、群体受益的前提下保持社区的基本特质?笔者认为,应引入治理的视角对其加以分析,原因如下:首先,社区治理是治理研究的核心与灵魂,是地方与全球建立支持和联系的必要环节;[注]Mike Richardson,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ource Kit, Christchurch City: Christchurch City Council Paper, 1999, p.1.其次,社区治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地方的主导,同时还强调了公民的自我治理;[注]Box, Richard C, Citizen Governance: Learning American Communities into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p.132~138.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社区治理的核心是依托社区自主来实现社区群体在社区(地方)中的价值。为此,笔者通过本文拟说明如下问题:民族旅游社区为什么需要治理?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是有意义的?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内部机制是什么?本文主要基于两个层面的思考:一是鉴于民族旅游社区的社会功能、空间区域和外部认同等功能,审视治理理论在民族旅游社区中加以应用的可行性;二是依托民族旅游社区独特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尝试在其中建构一种适用的治理结构,以此来弱化社区矛盾,维系社区的自我运行状态。
一、从地方、民族和旅游看社区治理
地方理论着重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等角度来看待和认识“人与地”之间的关系。[注]陈蕴真:《浅议地方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该理论中定义的“地方”是根植于原真的,[注]Massey D,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p.146~156.是某个主观的客体。[注]张中华,张 沛等:《地方理论应用社区研究的思考——以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例》,《地理科学》2009年第1期。按照瑞夫(Relph)的观点,地方与社区的概念是类似的,[注]参见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作为地方的社区,“人地关系”就是群体与社区的关系。空间上具有明确地理边界的社区,更易使生活在其中的“人(群体)”产生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人(群体)的主观感受赋予了社区的“地方”意义,使社区成为一个有意义和价值的空间。
民族与社区是交叉存在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生共存。克拉瓦尔(Claval)认为,民族、认同与地方客位是角锥体的三个镜面,在折射中彼此呼应,通过身份认同来建构民族,通过语言来塑造地方,通过地方再认同民族,[注]参见[法]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郑胜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认同是沟通民族与社区的内部桥梁。因此,在民族与社区(地方)重叠的层面,就会形成由不同亚文化群体所构成的,[注]Fischer C S,“Towards a Sub 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0,no.6,1975, pp.1319~1341.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注]李亚娟,陈 田等:《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综述》,《地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10期。——民族社区。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民族社区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独立性和封闭性,[注]陈 旖:《浅谈贵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其中,独特性对社区的民族性与地方性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民族元素是民族旅游社区开展旅游的主要吸引力。
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旅游与社区的关联是多元和建构的,旅游地的社区化和社区的旅游化是两个主要表现特征。[注]孙诗靓,马 波:《旅游社区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旅游科学》2007年第2期。旅游地的社区化强调了社区的重构,即在旅游地中强化社区功能、包容性和参与性;而社区的旅游化则凸显了社区的符号,即旅游是社区体验和社区价值的有效整合。在被重构和符号化的社区中,社区群体、旅游者和社区三者之间是多元互动的关系。民族旅游社区是典型的多层次复合社区,是旅游社区的子集,也是民族社区的子集。一般而言,民族旅游社区既有民族社区的特性也具有旅游社区的功能。从地方理论的角度看,民族旅游社区是一个兼具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地方,是一个有意义且能使社区群体产生认同的空间。其中,社区的民族性是一种对社区或族群的归属感,[注]参见Bradley H, Fractured Identities: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而社区的地方性则是一种独特的地方特质,使该社区有别于其他,[注]韩光明,黄安民:《地方理论在城市休闲中的应用》,《人文地理》2013年第2期。民族旅游社区的外部吸引力则来自社区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整合与互动。
二、民族旅游社区治理内部机制的提出
社区治理是全部治理系统的基础,[注]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是对特定区域异质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的操控和把握。对社区的治理不仅是要组织并实现地方的自我依赖,[注]参见罗秀华《文山社区由充权到治理的发展历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而且是保持地方特质抑或是保持地方性和民族性的有效途径。本文所探讨的治理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宏观表达,而是对民族旅游社区中治理的内生方式、运作过程及产生影响的探究,尝试在微观层面发现并协调促进社区(地方)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建构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内部机制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是对治理的概念、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关注,包括研究对象、适用尺度等方面;第二是提出治理的内部机制,包括内部机制的构成、运作方向等方面;第三则是回答治理内部机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如何保持民族旅游社区的地方性、民族性。
第一,内部机制的基础——治理的概念、理论和实践应用。从宏观、大尺度(旅游目的地)的视角出发,治理是分析与研究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益平衡,如约克塞(Yuksel)等认为,治理就是政府、私人和志愿部门所形成的网络;[注]Yuksel F, Bramwell B, Yuksel A,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Tourism Governance in Turke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32,no.4,2005, pp.859~886.抑或是不同治理模式对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效用,如弗农(Vernon)等提出的治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新模式。[注]Vernon J, Essex S, Pinder D, et al, “Collaborative Policymaking: Local Sustainable Project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32,no.2,2005, pp.325~345.但是,宏观、大尺度的治理研究在民族旅游社区中存在两方面的缺失:其一是在相对封闭和独立的民族旅游社区中,这种具等级观念的宏观治理理念通常是不适用的;其二是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对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保持,通过社区群体对社区的重新建构来实现地方的独特性,而宏观的治理理念与模式却没有涉及对地方性的思考。因此,以民族旅游社区的民族性和地方性为基础,探索并建构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内部机制,不仅有益于为研究社区治理提供新的发展思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丰富民族旅游社区地方性的研究视角。
第二,内部机制的提出。与以往社区治理对权力、层级和模式建构的研究不同,笔者认为,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内部机制是外部驱动因素对社区内部关系的影响,或者说是包含了民族旅游社区物质因素(社区实体)和精神因素(社区精神)[注]张中华,张 沛等:《地方理论应用社区研究的思考——以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例》,《地理科学》2009年第1期。的重构过程。一般而言,外部驱动直接作用于民族旅游社区,进而对社区边界和社区群体产生影响;内部因素一方面是对外部驱动的回应,另一方面也会促使社区选择最优的治理模式,进而产生一种合理的民族旅游社区内部治理机制。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内部机制主要包含载体、驱动力、内部因素与外显结果四个部分。其中,民族旅游社区不仅是形成内部机制的载体,也是联系外部驱动与内部因素的中介变量。驱动力主要包括全球化、商业化和在地化,但三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旅游社区的社会性、地方性和民族性产生影响。内部因素是针对民族旅游社区本体而言的,包括边界和群体,其边界包括地理边界、社会边界和民族边界,群体则包括群体关系与信任及群体认同。外显结果是建构民族旅游社区自组织治理的结构,同时也是对民族旅游社区治理内部机制的运作方向的回应。
第三,内部机制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内部机制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变动的世界中如何保持社区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内部机制是将治理视角社区内部化,主要有两层内涵:其一是民族旅游社区的治理是以社区边界为内缘,即社区边界划定了治理的“地方”尺度;其二是社区的内部群体是治理的重要对象,也是社区开展治理的基础要素。如果民族旅游社区中的群体认同程度低,同时社区边界的流动性也较大,那么治理就将面对“基础”薄弱的挑战,或形成民族旅游社区的脆弱性。因此,民族旅游社区治理是一种手段而并非最终目的,通过对内部机制的探索有利于社区的研究从空间走向地方,[注]白 凯:《自我叙事式解读回族宗教活动空间的意义》,《地理学报》2012年第12期。并进一步了解人与社区的互动关联,以及旅游对社区的能动作用。
三、民族旅游社区治理内部机制的构成及关联
(一)全球化、商业化和在地化是形成治理内部机制的驱动力
全球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一个或者一系列包含了社会关系和交流的转变过程。这些转变持续表现在其影响的广度、深度与速度,由此而产生出洲际或者区域间的活动、互动及权力行使的流动与网络。[注][加拿大]威廉·科尔曼:《世界秩序、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周思成译,《中国治理评论》2013年第1期。因此,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将促使国家、种族界限消失,各种文化相互渗透、互相影响,融为一体。[注]参见和 平,俞景华等《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北京:中央编译社,2008年。商业化,特别是旅游商业化,学界对其一直都持有不同的态度。其中,消极的态度认为商业化将导致地方特色文化资本的流失,[注]Greenwood, Davydd J, Culture by the Pound: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ourism and Culture Commodification in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pp.171~185.并且目的地会受到过度商业化的侵蚀。[注]何佳梅,许 峰等:《论旅游经济利益的外力创造》,《经济地理》1999年第2期。而持积极态度的学者认为商业化不但可以为当地人提供商机,还能复兴地方的传统文化,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注]Erik Cohen,“Introduction Investigation Tourism Art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20 ,no.1,1993, pp.1~8.如果说全球化和商业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消极色彩的话,在地化则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制约,其作用在于避免社区被边缘化或被无可预期的全球化市场所瓦解。[注]参见Sachs W,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London:Zed Books, 1992.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典型特点是同质化,即形成均质的社会;而在地化则是在寻求特殊性,追求地方的独特定位和自我风格。
全球化、商业化和在地化三者之间是一种内生的博弈关系。一般而言,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全球化和商业化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旅游经济的商业化,旅游文化的商业化以及旅游地的商业化。对于民族旅游社区而言,社区的地方特质以及民族的独特性是形成旅游吸引力的主要动因,但在全球化“流动”、[注]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之崛起》,夏铸九等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年。“多样化性格”[注]参见[美]杭廷顿,伯格《杭廷顿&伯格看全球化大趋势》,王柏源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以及商业化的消极影响下,民族旅游社区的本质和社区特色受到侵蚀,如何保持民族旅游社区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成为有待破解的难题。在地化是因全球化和商业化冲击所产生的,民族旅游社区所具有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是在地化的根本追求。如霍布瓦克(Halbwachs)所言,在地属于较小的空间,人们都可以互相认识,乡土人情味浓,其核心价值是仪式、宗教以及分享原初经验的集体记忆与认同等。[注]参见Halbwachs M,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因此,在地化能有效避免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负面影响,使民族旅游社区地方性得以保持,并成为阻挡民族性消弭的重要动力。综上,全球化、商业化和在地化三者对民族旅游社区的影响互不相同,三者博弈使社区地方性和民族性呈现流动与转变,与此同时,三者博弈也构成了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基本驱动力。
(二)边界与群体的互动决定了治理内部机制的运作方向
边界是地理学研究区域问题时不可回避的概念。一般而言,边界是人为划定的,是物质的,也是想象的,[注]参见Gregory D, Johnston R, Pratt G,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Oxford: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9.但在不同的情境中,边界也呈现出其他特性。针对民族旅游社区的边界而言,其不仅受到地方特性的影响,也受到旅游发展的影响,其可划分为三类即地理边界、社会边界和民族边界。三个边界的划分体现了三个角度:基本尺度、主观建构和客观呈现。细化而言,作为基本尺度的地理边界,其明确了民族旅游社区的区域范围,是政治思想下的地理区域;作为主观建构的社会边界,其被用以划分和区隔不同社会群体的界限,用来分别“我们”与“他们”的分界,一种情感和主观认同上的身份的判断;[注]刘志扬:《洁净与社会边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作为客观呈现的民族边界,其是在社区中区分我族与他族的界限,用以强调群体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这种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克雷斯维尔(Cresswell)所指出地方的三个基本面向:区位、场所和地方感。[注]Cresswell T,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London: Blackwell, 2004, p.34.当把三个基本面向对应到民族旅游社区的边界划分时,地理边界是对区位的呈现,是对社区客观位置的表示;社会边界则是对场所的回应,体现出对地方社会物质环境的界定;民族边界则是场所和社区感的综合,不仅是对社区社会物质环境的界定,也表现出对特定群体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空间。
社区群体(居民)是民族旅游社区的核心,是开展社区旅游的关键因素。群体在社区中表现为两个方面:群体与群体的互动,群体与社区的互动。群体与群体互动的基础是群体间的关系与信任,二者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选择性和稳定性。群体与社区的互动是群体从认识社区到认同社区再到体验社区的过程,是强调地方(社区)意义镶嵌于人类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意动。[注]参见Seamon D, A Geography of the Life World:Movement, Rest, and Encount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人是关系的动物,而关系又有助于民族旅游社区治理手段的执行和操控。信任不是群体内生的,而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重复博弈的产物,[注]参见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也是使关系趋于稳定的重要保证。此外,群体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所体现出的另一个面向,就是群体从意识到认同再到参与的主观呈现过程,认同是该过程的核心。民族旅游社区的群体认同,建构在个体自我及其对他人(或者他群、其他理念、凝集方式等)是否拥有共同起源或共同分享的认知之上,[注]参见Hall S, Who Needs Identity? Questions of Culture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6.是透过群体的经验和情感对社区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能动过程。在民族旅游社区中,鉴于全球化对社区的冲击以及在地化对民族的影响,群体认同中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成为回应全球化和在地化的重要维度。身份认同是群体内部产生基于本体的自我意识,是形成民族认同的基础;民族认同是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上的民族自豪感,是保持民族性的重要前提;地方认同则是一种态度、价值、思想、信仰、意义和行为意图,[注]Bricker K S, Kersetter D L,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hitewater Recreationists”, Leisure Sciences, vol.22, no.4, 2000, pp.233~257.是个人自我层面对自然环境的认可。[注]Williams D R, Patterson M E, Roggenbuck J W,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 Leisure Science, vol.14, no.1, 1992, pp.29~46.不论是关系、信任还是群体认同,三者的互动共同对民族旅游社区的民族性和地方性产生影响并共同决定了治理结构的可行性。
(三)自组织网络结构是对治理内部机制的有效回应
为确保旅游活动的有效开展,确保全球化、商业化和在地化驱动下的民族旅游社区内部稳定,选择有效的治理结构十分必要。罗茨(Rhodes)列举了六种治理的定义,其中之一认为,治理就是自组织网络,[注]Rhodes R,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vol.44, no.4, 1996, pp.652~667.而狭义的治理也专指自组织网络。[注]李 霞,陈伟东:《社区自组织与社区治理成本——以院落自治和门栋管理为个案》,《理论与改革》2006年第6期。在民族旅游社区中,社区的封闭性和独立性,决定了社区是一个由群体组成的自主领域,群体在社区中可以进行自我建设、自我协调和自我整合,这种“自我维系”的状态强调了参与者可以平等协商,消除分歧,达成基本一致,增强信任,体验资源共享的倍增效应,采取共同行动,[注]参见陈伟东《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这便是民族旅游社区的自组织网络。从宏观的角度看,自组织网络强调了宏观政策、民族、宗教与地方的共生;从微观的角度看,自组织网络是保持社区本体地方性和民族性的有效方式。
在民族旅游社区中,自组织网络结构的运作方式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政府的分权,这是实现自组织网络结构的前提。政府的分权意味着权力下放到社区的自组织部门或群体中,这使得社区拥有了话语权和自治权,能够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来决定社区的发展模式和方向;第二,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民族旅游社区中的协调机制表现为群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社区之间形成的紧密关系,保证了在民族、宗教和地方三重因素作用下的民族旅游社区从无序走向有序;第三,增强社区群体的合作。民族旅游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自组织网络的疏密决定了社区群体的合作强弱。社区自组织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注]周大鸣:《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思想战线》2012年第5期。那么社区群体往往会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合作,因为在民族旅游社区中同样存在着利益主体的博弈。[注]参见陈 昕《旅游地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分析》,《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因此,基于上述三方面的思考,笔者认为, 建构民族旅游社区自组织网络结构不仅要考虑政府的权能大小,更重要的是要权衡社区的民族、宗教和地方三重因素对民族旅游社区独特性和吸引力的影响,以及社区协调机制与合作对自组织网络结构可行性和独立性的影响。
四、结 语
冈斯(Gans)认为,少数民族群体在一定空间区域内形成自己的社区,并设立起社会栅栏以避免与周边社区居民的联系,避免受到其他社区异质性的影响,[注]Gans H, Urbanism and Sub Urbanism as Ways of Life: A Revaluation of Definitio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2, pp.507~521.这种自我保护性有利于民族原真性的保持和社区结构的稳定。但是随着旅游活动在民族社区中的开展,社区群体与外部社会出现互动,社区群体所设立的社会栅栏就会受到冲击。当社区边界和群体认同不再保持“原生”状态时,自组织网络结构就会对社区产生很大的影响,会使社区从无序到有序,并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注]参见陈伟东《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而四个“自我”也是社区自组织治理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民族旅游社区的自组织网络结构在体现社区自治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同时,有利于参与者之间进行面对面协商、频繁沟通,体验合作价值、欣赏合作喜悦、增进相互信任、降低交往成本,以获取更大收益。[注]陈伟东:《邻里网络:自组织的社会结构——解读城市社区自治的一种分析框架》,《湖湘论坛》 2010年第2期。
不论是基于对社区“原生”状态的维系,还是对社区栅栏的保护,民族旅游社区治理都是以社区本体为基础,从驱动力、内部因素到自组织网络结构,从社区边界到社区群体,其最终结果是要在社区中形成善治。在民族旅游社区中,自组织网络结构下形成的善治主要表现在:通过社区自组织来增进社区主体意识;通过社区自组织来增进社区参与,从而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通过社区自组织网络结构来有效整合社区资源;通过社区自组织来沟通社区关系,调解多元利益相关者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社区自组织网络结构来降低社区治理成本。因此,善治是民族旅游社区自组织网络结构建构的目的,也是治理的结果。善治的基本目的在于使民族旅游社区的社区、民族和旅游三者形成良性互动,使社区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得以保持。
笔者认为,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避免外部冲击使社区出现碎裂化。社区治理的本质就在于使不同阶层的群体平等地使用社区资源、参与社区建设,最终实现社区的包容与和谐,民族旅游社区的治理也必然如此;第二,保持社区原有的地方性与民族性。社区治理在权衡社区外部影响和社区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了社区地方性、民族性与旅游发展的共生共存,既保持社区原有风貌,又使社区地方性和民族性成为其旅游发展的必要吸引物;第三,弱化社区冲突,提高社区的安全性。发展社区旅游意味着其他不同民族的进入,语言、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通常会引起不同群体间的冲突,而社区治理则能有效化解上述矛盾,使社区从无序走向有序,提高社区的安全性与活力。
本文将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以及“地方”和“地方性”等思想融入到民族旅游社区治理中,并从地方理论的角度出发,建构并初步探讨了民族旅游社区治理的内部机制。在全球化、商业化和在地化的影响下,民族旅游社区的治理应以社区内部的边界问题和群体问题为分析突破点,进而形成自组织网络的社区治理结构,促使社区治理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形成良好的结合与互动。民族旅游社区中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保持是形成社区旅游的重要前提。因此,有必要从社区治理的内部机制角度来分析和解读民族旅游社区的发展,这不仅能为民族旅游社区地方性保持提供新的切入点,也在一定层面有益于扩展社区治理研究的广度和丰度,为民族旅游社区的地方、民族和旅游三者的和谐发展提供新的探索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