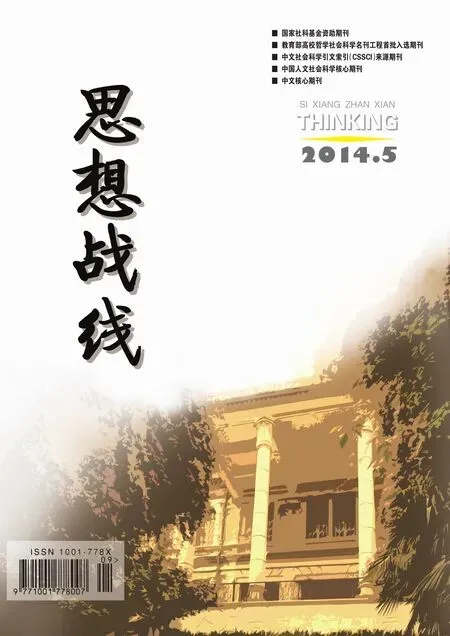体制外群体行动的“结构性”与“反结构性”考察
胡仕林
从行动的视角看,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属性和表现形式是体制外群体行动。所谓体制外群体行动,本文认为是指群体一方或双方逾越既定制度规范,在常规运行的政治和法律体制之外采取的群体性上访、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罢工、暴力等不为政府支持、鼓励,受到限制或禁止的行动。[注]这一界定参考了宋维强的观点。参见宋维强《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12页。体制外群体行动的出现往往意味着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社会的失序,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考察体制外群体行动的特征及其背后的逻辑、策略,对认识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具有积极意义。
一、“结构性”与“反结构性”: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的启发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是在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传统社会学存在着两种彼此对立的认识社会方法:一种是从个体、主体视角出发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论)。个体主义起始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行动为理论基点、探求行动者主观意义解释的“理解社会学”。在他看来,“行动”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而“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社会行动”只是个体行动中的一部分,社会学的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注][德]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由此,理解行动者主观意义的意图、动机等因素得以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也得以彰显。总体说来,个体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起源都以人的行动为基础、都可以化简为个体行动,结构是行动的结果,行动体现人的能动选择,只有通过个体才能理解整体。该方法论受到的指责主要是,具有浓厚的唯意志论色彩,夸大了个体的能动性,忽视了结构对个体行动的约束与限制。另一种是从社会、客体视角出发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整体论)。整体主义作为有影响的方法论是从马克思和涂尔干(Emile Dukheim)开始的。涂尔干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和观点是,社会虽来自于个体的组合,但超越了个体,拥有独特的性质而构成一个实体,不但不再受个体的影响,相反个体反而受到它的支配和影响。因此,他主张社会现象只能依据对社会本身的研究来解释,反对依据个体或心理因素去解释。[注]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7页。在整体主义立场下,分析单位不是个体而是社会,社会现象只能由抽象的、普遍的“结构”等整体性概念加以说明,“结构”之于个体及其行动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亦即行动受制于结构甚至由结构决定,并不体现为个体的主观选择。一般认为,这种方法论有社会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色彩,夸大了结构对个体行动的制约性而小视了个体的认知能力和行动的能动性。
为解决上述二元对立之争,吉登斯试图进行理论综合。他首先进行了一个重要的转换,即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解答从认识论角度转向存在论,从“应然”论证转向“实然”考察。[注]张兆曙:《非常规行动及其后果:一种社会变迁理论的新视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在他看来,二元对立是方法论和视角不同造成的,现实的存在并非如此,与其在“以个人为出发点还是以社会为出发点”之间争论不休,不如直接考察现实的存在,因此,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一样,他试图通过“实践”来统一“结构”和“行动”,他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 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1页。在“实践”的基础上,他提出“结构化理论”,并用“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代替二元论。根据“结构二重性”的观点,“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 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9页、第526页。在吉登斯这里,“结构”不再是结构功能主义者眼里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 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8页。而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 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2页。它既是行动者行动的结果又是行动者行动的条件,“总是同时兼具制约性和使动性”。[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 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9~90页。换而言之,在循环反复的实践过程中,结构和行动自身都具有建构和被建构的二重性;结构虽然制约行动,但在结构面前,行动者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他们能够能动地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
经由结构二重性理论的观照,本文对行动的基本理解是:结构制约下的能动。行动者的行动既受有形或无形的规则、资源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有结构性、被动性的一面,也受行动者自身的意图、动机等主观性因素的影响,有能动性、自主性甚至反结构性的一面;这两类因素的共在和效度不同的影响,使行动者的行动选择具有了不同的可能,并由此而导向矛盾、冲突或秩序两种不同的结果。具体到体制外群体行动,其以逾越体制“界限”为标识,因此其首要特征是“反结构性”。当现存“结构”无法满足群体行动者的利益诉求、价值诉求或者说其在体制内行动无法实现其利益诉求、价值诉求之时,行动者的能动性就会彰显,除非放弃诉求,否则,以反对“结构”、打破规则为核心的体制外行动就会成为当然选择。但是在正常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并不会完全失效,理性的群体行动者通常要考虑体制外行动的风险与代价,由此,其行动就会带有某种程度的策略性,也就是说,体制外群体行动往往是一种“不完全反对”、有节制的行动,体现出一定的结构性、服从性。概而言之,体制外群体行动以“反结构性”为首要特征,但同时兼具“结构性”,这种“一体两面”的二重性行动可形象描述为“七分反对、三分服从”。
当前,我国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是由具体的物质性利益矛盾引发的,鉴于此,本文着重分析利益型体制外群体行动。对于此类行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来说,始终存在着维护、争取利益的共意和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的、作为手段的体制外群体行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在体制内行动没有奏效或预计不会奏效的情况下,必须能动地逾越界限,尽可能通过各种体制外行动把事“闹大”,以求得利益目的的最大化实现,这是“反结构性”特征的体现。另一方面,体制外行动本身具有高风险,需要一定程度上考虑对现有正式制度的服从,能动地约束自己的行动,以求风险最小化,这是“结构性”特征的体现。
二、“闹大”的逻辑与策略:“反结构性”的实践考察
“闹大”是一种施压解决问题、达到目的的逻辑,即群体一方通过体制外行动施加压力,迫使矛盾另一方让步或迫使政府出面解决问题。通常,把事情“闹大”会直接对另一方或属地政府产生压力,迫使其采取行动;同时,也可能会引起上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上级“重视”产生的体制内压力和社会关注带来的舆论压力都会传导到属地政府,在此情形下,属地政府不可能再无所作为,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契机和理由。这正是实践中体制外行动“闹大”后所可能取得的把局部矛盾“问题化”为影响一方稳定的群体性事件的效果,也正是各类群体在长期实践和反复印证中形成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行动观念的基本原因所在。“闹大”总是能够推动问题的加速解决和目的的实现,因而人们当然会就此而不懈努力,想方设法扩大影响、制造压力,下面就是现实中几种“把事闹大”的行动策略:
(一)规模化策略
规模化策略体现的是一种“人多力量大”的数量逻辑,10人、100人、1 000人行动对政府和社会的压力和影响完全不同。因此,组织者总是力求动员更多的成员参与行动,有的还试图跨区域、跨群体联合行动。而体制内的规模化行动,如“联名上书”,几十人上百人在上访材料上签字或按手印并由代表提交有关部门,虽然也向政府展现了群体的意愿,但并没有对其产生现实的紧迫压力,因而通常得不到重视解决。与之不同,体制外的规模化行动直接外化为现实压力,在压力型维稳管理中属于“不敢拖”、“拖不得”的“危机”,因此政府对群体诉求通常是实质性的开展对话和快速回应,这明显区别于政府对体制内行动的敷衍和“躲”、“拖”、“推”等策略。在这个意义上,体制外的规模化行动比较容易打破体制内行动陷入的问题长期悬而不决的困境。
(二)暴力化策略
暴力的使用是体制外群体行动中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在群体上访、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等不以暴力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体制外行动的过程中,也时常会伴随着围堵、冲击、打砸等暴力行为。暴力体现的是一种损害逻辑,它通过伤害和破坏制造出公共影响、向政府施加压力,暴力程度越烈,社会影响和政府压力越大,问题解决的可能越大,这正是群体暴力普遍化和激烈化的基本原因。但在一般情况下,暴力毕竟是一种“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亏损性行为,一种极易招致打击高风险行动,群体行动者缘何愿意不顾风险以暴相搏?从实践看,这种选择多与以下因素相关:其一,有效替代选项缺乏。群体客观上没有替代选项或者替代选项已经穷尽使用,但问题仍得不到解决,以及主观上认为并没有可资替代的有效选项,除非放弃,在这种情势下,暴力就成为惟一的也是无奈的选择。其二,冒险赌博。在某种巨大利益的预期下,群体可能弃风险不顾而采取一切包括暴力在内的行动争取。其三,组织因素。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曾指出,个人(政治大亨)或组织(松散或紧密)从事激活、连接、协同和代表工作是集体暴力发生的一个条件。[注][英]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 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39页。当组织者“偏好”暴力时,其从事的激活、连接等组织动员工作势必推动暴力的产生或推高暴力的程度。其四,以暴抗暴。实践中,除主动使用暴力外,群体被动使用暴力的情况也很常见。在遭受相对方或政府暴力相向时,作为特定情境下的应激反应,群体通常也会以暴力予以回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暴力能量是守恒的,那些施加给社会或个人的暴力即便是合法地施加,最终也会反弹回来,施暴者与受害者同样会受到损害。[注]陈良咨:《论暴力与群体性事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三)择机策略
根据西方政治过程理论的基本观点,一个组织或政府的内部或外部条件往往会发生变化,一旦这种变化提高了集体行动群体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时,这种变化对于该群体来说就是一个政治机会。在中国的维稳实践中,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建党节、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春节等重要节日期间,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运动会、博览会等重要活动期间,以及上级领导调研视察期间、党政领导换届或变动期间等等,政府及其官员的良好形象、社会的良好秩序被提升到很高的位置,那些表征不和谐的行为(如上访)被严密防范和控制。对于政府及其官员来说,特别害怕这些特殊时点会“出事”,而一旦“出事”,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摆平”。对于“维权”的群体来说,这些特殊时点恰恰为他们维护和争取利益提供了机会,只要在此时冲破阻碍采取行动,政府的高大形象就会被抹黑,官员就会出丑难堪,喜庆就会被注入颠覆性内容,由此群体的行动就比平常更能取得“闹大”的效果,问题也比其他时候更易获得满意的解决。当特殊时点成为政府的“软肋”时,也就成为群体“揭丑”的良机,而政府一旦“露丑”就不得不迅速摆平以“遮丑”,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群体往往刻意选择特殊时点采取群体行动(特别是聚众上访)的基本逻辑。
(四)持久战策略
“闹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拉长体制外群体行动的时间,随着时间的延长,行动者可能会越来越多并形成更大的规模,而处于开放空间(尤其是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的群体行动将受到更多人关注并在更大范围形成社会影响,相对方或政府由此而承受更大压力并不得不采取恰当行动。持久战策略体现的是一种“坚持就是胜利”的时间逻辑。但总的来看,这种策略的使用并不普遍,这主要是由于体制外群体行动发生之后,大多数地方政府在维稳压力之下的处置理念和行动都是尽快将其“摆平”:要么及时通过对话协商等温和方式,一定程度上满足行动者的要求或承诺一定期限内解决问题,这样行动就失去了延续的基础;要么快速出警、强行处置,这样行动就被压制下去而无法持续。
(五)悲情策略
悲情策略体现的是一种道义逻辑,群体行动者通过某种边缘性的行为来展现甚至放大自己的苦难、冤屈、无奈,将自己作为受苦受难者的形象推到道德制高点上,并同时将相对方或地方政府置于伦理上的不利境地。悲情容易取得公众的同情,赢得媒体的关注,在此情形下相对方或地方政府若再无举动,就会成为“不仁不义”、“冷血”的代名词而被“千夫所指”,这恰恰不是他们所愿承受的否定评价。悲情的策略及其使用往往具有文化上的传承性,下跪、“闹尸”就是传统的“催泪”手法,并为今天的群体行动者经常采用。在人们的观念中,下跪是一种“吝啬”的行为,若非有冤有苦,谁愿在官员面前下跪?因此,当群体行动者集体下跪时,他们就已挣得了官员和公众的“同情分”,问题也就有解决的希望。借助死人也是民众表达抗议的一种传统手法,停尸抗议、抬尸游行、集体送葬、拒绝下葬等等,都是制造社会影响、施加压力的利器。因为不管什么原因,死了人肯定是另一方不对,这是人们通常不会细加分析就作出的判断,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极易使“闹尸”一方赢得旁观者和社会舆论的同情。因此,但凡有人死亡的纠纷(特别是医疗纠纷),争抢尸体以及把尸体当做工具使用比较常见。除传统悲情手法之外,博人眼球的新手法也不断被创造出来。如大理市的“娃娃讨薪”事件,13名5~20岁左右的儿童和学生手举“我要喝牛奶,我要吃蛋糕,还父母血汗钱!”、“我要钱,我要上学!”等字牌帮助父母讨要工资,并取得了成功。[注]柏立诚:《13农民工子女替父母讨薪》,《春城晚报》2012年8月16日。“娃娃讨薪”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娃娃”被作为悲情催泪的“道具”使用,迎合了媒体的“卖点”,媒体借悲情发力产生社会轰动效应,而政府在社会压力之下强力介入协调帮助农民工迅速达到讨薪目的。
三、风险控制的逻辑与策略:“结构性”的实践考察
体制外群体行动合法性空间狭窄,如5人以上“集体访”或“越级访”不被允许、集会游行示威需审批、罢工缺乏法律依据等,这就意味着其行动者需要承担可能遭受政府打击制裁的风险。实践中,风险最有可能实际落在组织者和积极行动者头上,他们一般会被处以治安拘留,而严重的则被处以刑罚。对此,群体行动者(尤其组织者)或者事前就有相当的认知,或者虽没有明晰的了解但“与政府作对”、“不听政府招呼”的后果常常是他们通过常识和经验就能估计得到的,因此,他们在体制外行动的过程中往往会掌握分寸,降低风险,力求达致目的实现而又不“引火烧身”的效果,为此他们通常会采取以下策略:
(一)构造正当性话语
就政府而言,无论是“有理取闹”还是“无理取闹”,都会对秩序造成破坏,因此它的基本立场都是不支持、不赞同。但当体制外的“取闹”行为真的发生时,它的打击态度和界限则有所不同,“有理取闹、情有可原,无理取闹、难以饶恕”是其实践的真实写照。因此,群体行动者要降低风险,首先就要为自己的行动准备政府能够接受的理由。同时,这种理由最好也能够说服公众,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因为在此情况下,政府一般不会“一意孤行”、强行打击,风险由此而进一步降低。偱此逻辑,群体行动者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诸多正当性话语策略,通过把自己的行动“正当化”来阻却行动的“违法性”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注]这很像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是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罪名的一种违法阻却事由,能够起到免责或减责的作用。这些策略包括:其一,只问经济不问政治。这是最根本、最常见的一点。行动者的话语中只主张具体的经济利益诉求,很少提出政治性诉求。不质疑政权合法性,不提出、不呼喊那些令政府不舒服的政治性标语、口号,政府就只能把问题和行动定性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其二,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行动者往往把中央的要求、政策的规定、社会的期待与自身的境遇联系起来构造正当性话语,突出其行动的合理性,以取得上级政府和社会的谅解与支持。比如,拆迁户打出“支持政府工作、反对暴力拆迁”的标语,既表明了自己合作的态度、讲理的形象,又指出了自己遭受的暴力、反抗的合理。其三,宣示生存伦理。生存是伦理的底线,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对政府的正当要求。因此,“生存”往往被作为“弱者的武器”来使用。当弱者在体制外行动中打出“失地农民求生存”、“下岗职工要吃饭”的标语时,相信很多人(包括官员)都不会对这样的诉求以及为实现这样的诉求而行动作更多的非难。其四,“逼上梁山”。被逼无奈、情非得已,既是人们广为接受的体制外行动具有合理性的一个理由,也是官员们心知肚明的一个普遍事实,他们往往视其为“事出有因”之一而“网开一面”。由此,通过话语塑造无助、无奈的形象就成为行动者正当化其行动的一个重要策略。
(二)行动渐进升级
虽然在制度“表达”层面,各种体制外行动都是政府所不期望的“越界”行动,其合法性欠缺或模糊,都存在被政府制止的可能。但从实践情况看,政府对不同的体制外行动容忍程度不同,因而不同的体制外行动实际发生被制止的风险也不同。通常,政府对严重群体暴力(如打砸抢烧)容忍程度较低;而和平式行动虽然可能违反某些程序性规定,但其实体上属于公民权利(如上访、集会游行示威权)或不被法律明文禁止(如罢工罢课罢市),因此,这类行动如果没有发生严重暴力,政府一般不会给予制止。也就是说,和平式行动还是暴力式行动、低度暴力还是严重暴力,是政府实践中掌握制止与否的基本尺度。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组织性、预谋性较强的体制外群体行动往往体现出一种从和平到暴力逐步推进的特点,这是行动者不断策略性平衡目的实现与手段风险紧张关系的反映:当低风险的和平行动能够达致目的时,高风险的暴力行动自然不会采取;而当低风险的和平行动不奏效时,规模性的低度暴力、严重暴力就可能随之产生。
(三)组织者不可见
“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组织者对此心知肚明。因此,若非必须登上“前台”,他们往往会刻意隐藏或淡化自己作为组织者、带头人的身份。常见方法有:一是慎言组织。对外往往强调行动的自发性,一般不承认存在组织动员尤其是“领导小组”、“指挥部”之类的临时性组织。二是幕后策划指挥。这在组织性较强的群体行动(如退伍转业军人“维权”行动)中较为常见,政府难觅其组织者。有的组织者在事前作策划,但并不到现场而是遥控指挥;有的则通过网络即时通讯工具隐藏真实身份、传递信息、策划行动。三是订立“攻守同盟”。如何保证不被内部人“出卖”,是组织者通常要考虑的问题。一些谨慎的组织者在事前策划或事后“风声紧”的时候,常常会通过开会商量等方式统一口径、说辞并传达,以尽可能堵住政府可能的各种“突破口”,达到保护安全的目的。同时,他们还可能会对如果自己被抓,如何“营救”或向政府“要人”作出预先安排。
四、启示与治理
(一)体制外群体行动本身具有内在的冲突抑制力
体制外群体行动隐含着“闹大”和风险控制的双重逻辑,为达目的,行动者必须逾越体制界限,把事“闹大”,但现行规则之下的风险又决定了“闹大”并非无所顾忌、肆意而为,行动者不会“越界”走得太远。由此,体制外群体行动“反结构性”一面对秩序的消极影响总是会受到行动“结构性”一面的抑制。基于此,并考虑到当前体制外群体行动极少指向政权合法性,且大多为小范围孤立存在,难以构成对社会整体秩序的颠覆性破坏,政府应当以更加从容自信的态度将其视作正常现象应对,而不应反应过度地一味压制甚至采取违法的所谓维稳措施。
(二)提升利益规则的合理性
行动者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欲求,当其视利益规则不合理时,就容易产生反规则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公平”既是行动者对利益规则进行评判的依据,同时也是抑制自己利益欲求的依据。公平的利益规则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欲求,但一定能够得到社会成员普遍的认同和服从,反规则的行动由此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因此,治理体制外行动带来的群体性事件特别需要从制度上、程序上保证“产出”的利益规则具有合理性。
(三)提高体制内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闹大”的逻辑表明:正是由于体制内常规的纠纷解决机制无能,才逼使群体行动者走上体制外“维权”的道路。因此,只有畅通和完善纠纷常规解决机制,确保行动者不需“闹大”施压就能获得问题的及时合理解决,才能真正把矛盾纠纷纳入制度化的渠道控制,才能阻止行动者越界采取体制外行动。
(四)加大群体暴力行动者的风险
风险控制的逻辑表明:制裁规则的存在能够使群体行动者谨慎行事,不轻易使用暴力。故要坚持法律底线,依法严惩,警示潜在的各种群体暴力。另外,“组织者不可见”的策略大大降低了组织者实际被惩罚的可能,故应支持发展行业协会、经济合作社等利益代表组织,其首先能够代表群体以“组织化个体”的形式“维权”,同时,由于风险责任指向明确,其组织发动的体制外群体行动更可能被限制在理性化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