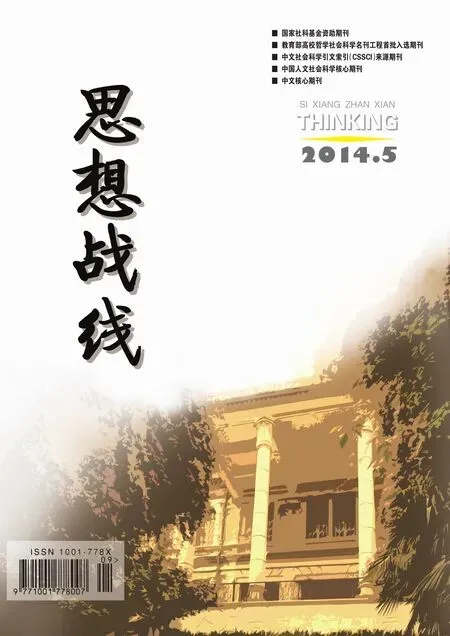信仰与艺术:村落仪式中的公共性诉求及其实现
——鲁中东永安村“烧大牛”活动考察
李海云
新时期以来的乡民艺术研究,[注]张士闪曾对“乡民艺术”与“市民艺术”、“民间艺术”等相关概念予以界定。他认为,广泛意义上的民间艺术可大致分为市民艺术与乡民艺术,市民艺术是指风行于城市社区的一些具有修身养性、娱乐性等功能的艺术活动,乡民艺术则是指与乡土生活(节令、祭祀等)有关并凝结为稳定乡土传统的艺术活动。参见张士闪《乡民艺术民族志书写中主体意识的现代转变》,《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显然,张士闪对于“乡民艺术”的界定,主要是从空间(“乡土”)与主体(“民”)出发,并具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凝结为稳定乡土传统的”),然而,乡土生活中的“艺术”发生及“艺术”认定其实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本文限于篇幅不拟对此探讨,而是通过考察村落仪式中的“艺术”因素,分析其对村落“公共性”生成的推动作用。最活跃的莫过于秉持一种“田野研究”与“整体文化观”的研究模式,即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理解乡民艺术的“发生”过程,从乡土生活与文化体系的角度对乡民的艺术活动与其他民俗事象的关联予以探究。纵观众多研究成果,主要是从两个向度展开的:其一,从艺术学角度出发的、致力于田野个案的艺术发生学研究,以傅谨、王杰等较具代表性。傅谨通过对台州戏班的长期田野调查,围绕民间戏班的内部运作与市场生存,对民间戏曲的艺术自律性与公共性特征予以阐释,并进而提出以田野作业为基础建构艺术学理论体系的设想。[注]参见傅 谨《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杰以黑衣壮族民歌为个案,关注“地方性审美经验”与少数民族艺术的内在联系及当代变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化意义的产生。[注]王 杰:《地方性审美经验中的认同危机——以广西那坡县黑衣壮民歌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的呈现为例》,《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他们面向本土艺术现象,凭借某种艺术感悟力予以生活化的阐释,因而在一种程度上形成了对传统艺术学研究模式的超越。其二,是从人类学、民俗学角度出发的对民间艺术活动的研究,以刘铁梁、方李莉、何明、张士闪等较具代表性。刘铁梁关注村落集体性的文艺表演活动,认为乡民艺术并非仅仅是乡民的“闲中扮演”,而是为了现实生活的有序与精神的完满而进行的主动文化创造。[注]刘铁梁:《村落生活与文化体系中的乡民艺术》,《民族艺术》2006年第1期;《作为公共生活的乡村庙会》,《民间文化》2001年第1期。方李莉通过对贵州黔西北长角苗的考察发现,社区生活中的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审美,还是一种被编入集体表象或者公共空间中的文化符号。[注]方李莉:《艺术田野工作方法中的文化思考——以长角苗人的艺术考察为例》,《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何明以云南芭蕉箐苗族基督教中的唱诗活动为个案,注意到其中仪式与音乐的共生关系,认为其代表着该社区的一种自由民主的文化交往方式。[注]何 明:《基督教音乐活动与艺术人类学阐释——以云南芭蕉箐苗族为个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张士闪则将乡民艺术研究视为“艺术民俗学”的核心区域,试图呈现乡民艺术与所属整体民俗生活的互动关系,以此突破过去对于乡民艺术的静态化、割裂式的研究模式。[注]参见张士闪《民间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他们都关注乡民艺术活动的发生现场,试图通过对活动的组织、运作、展演等整个过程的分析,探讨其中民俗与艺术、事象与区域、活动与主体的内在关联。
整体看来,上述学者在试图阐释乡民艺术的发生状况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乡土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公共性”问题较多地与社会世俗化相关联;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公共性”作为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的一种方法论,却无法回避与社会神圣传统的纠缠。[注]“公共性”研究作为一种学术传统,产生于欧美学术界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观照,主要以哈贝马斯、阿伦特、罗尔斯等人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包含着较为浓厚的政治哲学意味。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性”等观念舶来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同时也在本土适用性等方面引起较大争议。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公共性问题的实质是人们的公共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公共性问题产生于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事务,因而可以有不同类型的公共领域;公共活动构成公共性的社会基础;公共理性是公共性得以发生的主体性条件;公共价值是公共性的本质。而当代公共性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公共性及其危机,都是极具历史性和复杂性的问题,必须经过进一步深入挖掘才可能理清(参见晏 辉《论公共性的原始发生》,《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公共性问题的哲学前提批判》,《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本文即以村落仪式为个案,试图从这类神圣传统所搭建的公共活动平台中,理出乡土公共性的发生契机与实现路径,为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公共性重建提供参证。与西方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缺乏深刻彻底的现代化进程,完全的社会世俗化从未真正实现,相反,弥散于中国日常生活体系中的神圣传统却持续存在。当以“公共性”的视角分析乡土社会之时,就必然会出现“公共性”与神圣传统的纠结。以此观照上述乡民艺术的两种研究路径,它们不仅都涉及乡土社会中的“公共性”问题,而且都会面临对“公共性与神圣传统”的阐释问题。也正是在这方面,上述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局限。它们多侧重对乡土社会的“公共性”作为外在建构力量的考察,却无暇对其内在诉求与实现方式进行集中性的讨论。笔者认为,惟有从中国村落的内在公共性诉求切入,观察这一诉求在村落神圣传统中的存身与呈现,才能获得对中国乡土公共性的具体发生与存在态势的理解。
就本文所选取的个案而言,在地理空间有限的东永安村,一村之内两庙并置,分属于村内不同家族的“烧大牛”、“烧大马”两种游神表演仪式在农历正月间次第展开,以村落仪式中信仰与艺术的同构,满足着乡民的公共性文化诉求。从这类历史悠久的村落神圣传统入手,关注其搭建乡土公共性平台的意义,可以更好地理解乡土公共性的发生机制。
一、村落与家族
(一)村名:从“蓉岸”到“永安”
东永安村位于山东省昌邑市西北部,东与远东庄相距1里地,西与西永安村距离1.5里地。该村有860多户,人口约2 700人。该村主要有三大姓氏,齐、吕和丛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人口,另外还有王、赵、陈、马、张等少量家户。东永安村地势低洼,俗称“永安洼”,曾名“蓉岸村”。这其实与该村曾位于芙蓉池[注]芙蓉池又名“莲花湾”,消失于清朝后期。参见山东省昌邑县志编纂委员会《昌邑县志》,昌邑:昌邑县印刷厂,1987年,第58页。北岸的洼地有关,村北至今仍有古湖岸遗址。
地势低洼的东永安村,东临瀑沙河,北濒渤海莱州湾,每年三四月间或秋季易发生海水倒灌。[注]如1964年4月这一带曾发生过一场特大海潮,村民至今仍记忆深刻。当时水位达3.8米,侵入内地东西宽29公里,南北长6.5公里,最长30公里,昌北一带大量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潮水过后,不仅房屋倒塌,而且耕田变为盐碱地,3年不长庄稼,当地流传着“春天盐碱白茫茫,夏天雨涝水汪汪;年年见种不见收,黄蓿野菜当主粮”的俗谣。尤其是自芙蓉池消失以后,这一带种植水稻的历史终结,池下所沤黑土以及因海水倒灌所形成的潮土,使得这一带土质偏碱性,仅适于棉花等农作物的生长,村民只好通过外出经商以贴补家用。村名从“蓉岸”到“永安”的变化,或许正与当地自然灾害频发所形成的苦难记忆有关。而村中最著名的两座庙宇即孙膑庙和玉皇庙,都将“国泰民安”、“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旗帜悬挂在庙门上空;以两庙为依托而举行的“烧大牛”、“烧大马”仪式活动,也特别凸显“国泰民安”的祈愿,并非偶然。
(二)村落中的家族:“齐家”与“丛吕家”
走进东永安村,经常会听到“丛吕不分”的说法。据东永安村《吕氏宗谱》记载,丛、吕家族于明朝洪武年间由文登县一起迁移至此,居住于鲇鱼埠西部高地。稍晚来此定居的齐家,则居于鲇鱼埠以东洼地。时至今日,丛、吕家族和齐氏家族的聚居区大致以鲇鱼埠相隔,有着明显分界,村民习用“埠东”、“埠西”来代指齐家和丛、吕家族。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丛、吕两家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合作的情形的确较多,而齐家则往往自行其是。
在接受访谈的过程中,村民都对本家族昔日的辉煌津津乐道。在他们的记忆中,历史上东永安村达官显贵颇多,尤其是丛家和齐家。特别是在明朝时期,丛家曾出现了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丛兰,官至右都御史三边总制兼南京工部尚书、太子少保,还涌现出一批举人、秀才等。此外,东永安村旧有练武传统,吕氏家族的拳法曾在这一带颇有声誉,吕家十五代曾有中过武举的。而齐氏家族的显赫历史则延续至今,有多名在外担任要职的齐家族人,曾为本村引进各种经济、文化资源,扶持村办企业,齐家人对此甚感自豪。
在东永安村,丛、吕、齐三大家族都曾建有祠堂,“文革”期间均被毁。各家自有茔地,吕家位于村西南角,丛家位于村北部,齐家则在村东南角。东永安村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村落政治具有超稳定性。有四位吕家人短期出任村书记,加起来任期不过10年;另有四任书记均出自齐家,共有55年的任期。显然,在村落政治权力格局中,齐家处于强势地位,而丛、吕家族则相对边缘。然而,丛、吕家族却在日常生活中,以“丛吕不分”的名义活出了另一种滋味。
在诸多人生礼仪场合,丛、吕、齐三大家族有着一定的边界。每个家族都有红白理事会,由本家族年长者担任总管。在东永安村,丧礼是以家族为单元而运作的。相形之下,婚礼则在家族内部的有序参与中,呈现出面向整个村落敞开的狂欢色彩。此外,东永安村有较多的内部通婚现象,使得村内丛、吕、齐三大家族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不过,日常生活中的密切联系,并未淡化家族之间的边界;而家族之间边界的清晰存在,使得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密切联系尤为必需。
在村落信仰生活中,亦呈现出明显的家族化倾向。村内主要有两座庙宇,即位于村东的玉皇庙,[注]1997年11月修建,动工较孙膑庙晚4个月。分为前殿、后殿和东殿,神灵较全。前殿正神位为观世音菩萨;后殿牌匾为“无极天尊”,正神位为玉皇大帝;东殿正神位为路神爷。如今的庙宇神像设置主要由村民齐乃瑞所设计,与旧时玉皇庙所奉神灵差异较大。据他讲述,旧时庙宇内仅有玉皇大帝,因玉皇大帝身边一般是文武百官,因此在1997年修庙后,于后殿设置了关公与孔圣人。和位于村西高埠上的孙膑庙。[注]其址在村西高埠之上,始建年代无从得知,村民仅是听老一辈传说始建于元代。据碑文记载,第二次重修为清光绪二年(1876年),目前的孙膑庙是1997年所修。其主要分为三殿,即东殿、西殿和南殿。西殿为孙膑庙,正神位为孙膑;东殿为老母殿,正神位为地宫老母;南殿较小,只有路神爷和王灵官两位神灵。前者主要为齐氏家族所掌管,后者则属于丛、吕两家共管。谈及两庙,村民都习惯于称“齐家的东庙”、“丛吕家的西庙”。在每年进行的庙会捐款活动时,家族边界表现得较为明显。东玉皇庙基本全是齐氏家族捐款,丛、吕家族捐款甚少;同样,西孙膑庙也主要是丛、吕家族捐款。每到年底,东西两庙都要扎制圣物予以焚祭,一边扎大牛,一边扎大马,互不参与。在每年除夕夜,丛、吕家族的村民多去孙膑庙祭拜,而齐家人则多去村东玉皇庙祭拜。
我们发现,农历正月里的“烧大牛”、“烧大马”活动作为东永安村最大的村落仪式活动,它们对于村落生活影响甚大:一方面,仪式基本上是以家族为单元而组织运作的,仪式活动的定期举办就意味着家族边界的不断强调,这是对村落“竞争”态势的凸显;另一方面,以家族为单元而组织运作的仪式活动,面向全村乃至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而敞开,表现出超越家族边界的一定的灵活性,从而体现出在“竞争”态势掩盖下的“合作”契机。特别是“烧大牛”活动,其仪式规程相当完整,既具有相对稳定的仪式设置,又随处可见村民自由发挥的艺术创造精神,是我们展开“深描”的理想文本。下面兹以“烧大牛”仪式活动为例,从信仰与艺术的层面予以分析。[注]对于东永安村村落生活而言,“烧大牛”、“烧大马”大致具有相似的文化意义,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烧大牛”活动予以描述和分析。
二、仪式表演中的信仰与艺术
(一)扎大牛
每年一进腊月,村民便开始操持扎大牛活动。据村民讲述,旧时所扎牛的颜色为黑色,体型较小,长约2米,高仅1米,20世纪80年代改为扎制黄牛,体型逐年加大,特别是自1997年重修庙宇以后更是猛长,现今体型从牛角到牛尾约有13米长,牛蹄至牛角的高度约为7米,以至于村民抬着大牛游行时需要有专人负责支挑街道上的电线。村民惟大是求,对此并不满足,然而,代表着“现代生活”的电线却成为遏制其“大牛”圣物无限膨胀的理由。村民说,目前的大牛的尺寸已到极限,再大就没法巡游了。
整套扎制活动有着明确的分工,男性主要负责用竹竿、竹枇、铁丝等扎制大牛骨架,妇女则用黄纸剪出“牛毛”,用布缝成“牛皮”,用银箔纸糊成“牛角”,用各色彩纸剪出铃铛、牛鞍等牛身部件及装饰品。牛毛剪制技艺虽不复杂但很费工时,一般分散在多户村民家中进行。大牛骨架、剪牛毛、牛耳朵、牛角等扎制工作,则在孙膑庙南专门为此建造的一处宽敞房间内进行。特别是大牛骨架的扎制,是波及全村的事件,场面很是热闹。大牛骨架旧时主要采用玉米秸、高粱秸等材料,在屋内扎好后,再挪到院子里用白金纸、黑纸糊好,最后缀以花灯为饰。如今大牛的体型加大,骨架要以更结实的粗竹竿、竹枇和苇秆为材料,再用铁丝绑定衔接。牛脖子下部,须采用一根直径约10公分的较粗的大竹竿,以支撑高高昂起的牛头。因大牛太高,村民在扎制牛头和牛脖子部分时,需要站在高高的木架上,下面有四五位有经验的老人在出谋划策,估量尺寸是否合适,还有一些热心的中年妇女帮衬着递竹竿、铁丝等物什。
无论是大牛部件的扎制,还是从农历年初六开始、正月十三结束的大牛“组装”,老少村民都是集聚一起,边干活边拉家常,欢笑声不绝于耳。显然,共同协作“扎大牛”的过程,为村民营造了某种迥异日常的情感交流平台。无论是参与扎制哪个部件,做灯笼、扎制骨架还是做牛鞍,都是整个“烧大牛”仪式所不可或缺的。在村民的心中,他们在“烧大牛”仪式活动中的必然“在场”,似乎也象征着其在村落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或缺,其村落认同感由此得以增强,自豪感油然而生,这大约是村民都乐于义务参与的真正原因。
(二)农历正月十三“晚会”
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晚上,丛、吕家族会联合举行庆祝活动,村民称之为“晚会”。舞台临时搭建于孙膑庙东侧,参与者、表演者均为本村人。晚会节目包括歌曲、舞蹈、小品、戏曲等,很是热闹,本村在外打工、求学、当兵的人员往往是晚会的活跃分子,大家都借这个机会相互拜年问候。此时,也有邻村村民赶来摆摊,晚上便借宿村中。大约在凌晨时分,村民开始进庙烧香磕头,燃放鞭炮,相邻的西永安村、远东庄等村村民也结伴前来祭拜,鞭炮声不断。据村民讲,这一晚历来都是通宵达旦的娱乐,以迎接第二天孙膑庙会的举行。
在东永安村,农历正月十四的庙会比除夕还要隆重、热闹,而庙会前夕农历正月十三的晚会则是这一高潮到来之前的助兴。为什么东永安村的年节高潮不在农历除夕、初一而是正月十三、十四?对于村民而言,除夕作为节点是以年度生活为周期而设置的,是人们告别过去一年而迎来新年的时刻,这种告别仪式的设置对于当地乡民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然而相形之下,“农历正月十三、十四”不仅具有以年度生活为周期而设置的“年尾”的象征,且以对本区域地方神(孙膑)的奉祀为旗号而尽情狂欢,以此完成由神圣时段向世俗世界的返归。[注]在传统年节仪式中,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自然担当着这样的角色,元宵节的游乐其实是人们从神圣世界还复世俗世界的重要节点。而在东永安村,村民借助“孙(膑)老爷诞辰”的说法,将元宵节的狂欢活动定格于农历正月十四日这一天。
(三)游大牛
农历正月十四早上8点钟,孙膑庙上一阵鞭炮响过后大牛就“起驾”了。整个游大牛队伍浩浩荡荡,前面由鞭炮队开道,其次是锣鼓队、秧歌队、高跷队,再就是三四十位青壮年组成的抬大牛队伍,最后是跟随游行的拥挤的乡民。大牛游行的线路,是沿着村委东邻的南北街道至十字路口,然后拐至西侧,直至孙膑庙西的空场。显然,游大牛活动是围绕丛、吕家族的聚居区而进行的,并非围绕全村。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游大牛队伍路遇农户、商贩、店铺,对方都会放鞭炮贺年,以图吉利。特别是经过村内主街道时,要穿过街道两旁摆得满满当当的香火摊、鞭炮摊,一位老人手提一个大袋子走在前头,商贩们纷纷往袋里扔进成挂的鞭炮。现场赠送的鞭炮,现场点燃,巡游者、观演者和摊贩共同营造出这一乡土仪式的热闹。此时,在神圣的旗号下,大牛的游行就成为一种散播吉祥和福惠的手段,并进而彰显出家族-村落的荣耀和优越。
(四)祭大牛
农历正月十四上午10点左右,游大牛队伍来到孙膑庙西的空场上,人们在空场上摆好供品,开始给孙膑烧纸烧香、磕头祈愿。与此同时,村民自发组织的扭秧歌、舞龙、打腰鼓、唱吕剧等活动,也井然有序地于此上演。在这一带乡土社会中,一村举办庙会,邻村乃至外地的文艺队都会前来助演。纵观演出现场,肃穆的孙膑庙、威武的大牛和庙前空地上热闹非凡的文艺表演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年节期间神圣与世俗交织在一起的乡土公共空间。
(五)摸大牛
各项祭拜活动告一段落后,在场人群一拥而上,争相“摸大牛”,乞求神牛将疾病带走。当地俗谚说:“摸摸老牛头,吃穿不用愁;摸摸老牛腚,到老没有病。”“摸摸牛角不生痘,摸摸牛鞍不生瘢。”村民认为,在农历正月十四这天摸牛会带来一年的好运气。
(六)烧大牛
“烧大牛”又称“发牛”,一般在中午11点至12点之间举行,火光冲天,烟雾缭绕,蔚为壮观。大火开始燃烧的那一刻,人群开始沸腾,似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烦扰也随“圣物”的燃烧而逐渐消散。在村民看来,只有“大牛”焚化升天,才能将人们虔心愿望传达给孙膑。熊熊大火,引导人们瞬间进入一个别样的狂欢世界。而层层围观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以烧化之物为中心的神圣祭坛,其神圣感在人与人共在、人挤人互动的狂欢态势中不断得以强化。在此时刻,人神关系与人际关系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神圣信仰与艺术体验混融一体,互动而生。而其本质,则是人与人互动的村落公共性的瞬间生成。
显然,“烧大牛”仪式在村落语境中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意义。它不仅是东永安村年节期间的一项悠久的传统工艺和表演活动,而且凝结着丰富的村落知识,如孙膑信仰、村落家族关系以及周边村际关系等,寓含村民的公共性建构需求和群体情感的表达需求。在村落仪式活动中,作为仪式整体中技术构架的提供者,传统工艺和表演活动从一开始就处在“神圣”与“世俗”的二元身份的争夺中:一方面,它们作为向神圣体系的奉献之物,其自身必然是神圣的;另一方面,作为人之于“物”的劳作,它们又与世俗生活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从仪式的衍生物的角度来看,这些仪式活动用品的逐渐讲究,就喻示着信仰活动中艺术因素的不断增长,以及越来越强烈的艺术因素对于仪式活动的支撑。反之,从乡土生活的角度来看,仪式用品既然来自村民的亲手扎制,其中必然寓含着村民的身体性记忆,已经成为其情感的物化载体。[注]刘铁梁通过对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沿村编筐技艺的考察,认为“一定村落劳作模式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必然是村民彼此之间不断交流身体经验的过程,因此那些被口传身授的日常劳作的知识、技能和各种故事等,都可以看做是表达他们身体经验的不同民俗形式”。参见刘铁梁《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以北京房山农村为案例》,《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因此,村民年复一年的扎制与表演过程,既是参与一种信仰仪式的体验,也是其独特的情感重温与艺术体验的过程。在东永安村民的心目中,“烧大牛”既是庙会中特有的神圣活动,又是农历正月里特有的“耍景”或“耍好事儿”,而没有庙会、没有“耍景”的年节是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过年的。
三、村落仪式中的公共性生成
东永安村“烧大牛”之类的村落仪式,在其公共性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既借助于信仰的传统规仪,也要借助于其现场操作中自由发挥而产生的艺术感染力,“宗教信仰经常需要借助艺术表演以增强感染力,艺术则常以宗教信仰为旗号,增加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与权威性”。[注]张士闪:《论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艺术化趋势》,《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
在东永安村,大牛扎制的过程便是意义生成的过程,而村民对大牛的抬游、叩拜和焚烧等行为,则为其赋予更多的价值。仪式意义的生成,既通过特有的信仰活动,也借助一定的艺术形式。信仰与艺术,有机地融汇在同一个仪式之中。就像在东永安村人看来,扎大牛的过程既是在做一件好看的工艺品,也是通过自己的创造让一件圣物显形的过程。
在这一带乡土社会,村落庙会一般都具有跨村落参与的性质。[注]在东永安村一带,“焚烧圣物”的现象较为普遍,邻村之间相互参与。该村东邻的远东庄在农历正月十二日设有菩萨庙会,届时要烧掉两台花轿;村西的西永安村则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娘娘庙会,扎两台大轿以纪念老母娘娘;村南的渔埠村每年农历正月十六为孙膑庙会日,以传统的生产队为单元扎制三头独角黄牛烧掉。庙会期间,面对外来的参观者或者媒体,村民总是乐于夸说本村庙会的悠久传统和无可辩驳的神圣感,并在与他村庙会进行的对比中凸显自身优势。不过,东永安村“烧大牛”仪式活动所树立的权威力量,只是增强了村民内心深处的优越性,而并未指向一种物质利益的诉求。这其实与中国村落传统中蕴藏至深的公共性诉求有关。
我们注意到,东永安村丛、吕两姓村民一进腊月就开始操持“烧大牛”活动,关于这一仪式活动的传统记忆也会应时发生,它以村落“历史”的庄严形式出现,与艺术活动本身具有的“神圣性”结合在一起,成为村落传统中强大的律令传统。因此,延续“烧大牛”的传统就不仅是个体自愿自觉的问题,而是律令内化而成为村落宗族的集体无意识。在此意义上,“烧大牛”不仅仅是人对神负责,更是个体对村落传统、对其他村民的责任,“烧大牛”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具有了村落公共性传统的内涵。参与烧大牛活动的丛、吕两姓村民,此时就是这一律令传统的主人,是这一堪称荣耀的村落传统的共享者。村落中的其他姓氏以及外村人,则被相对“隔离”在圈外。然而,当东永安村其他姓氏前来观看烧大牛活动,或东永安村村民前往他村赶庙会,虽然无缘于庙会活动的主体创造,却能以观者的身份进入庙会现场。领略庙会仪式,既是信仰观摩,又是艺术欣赏,共同汇成一种神圣性与世俗性兼具的混杂的情感体验。事实上,遍布中国乡村的庙会活动,都离不开在民众的主体创造与客体参与,既是信仰活动滋生的温床,也是艺术发生的现场,乡土社会中的“公共性”便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生成。其生成的具体情形如何?
首先,庙会仪式为艺术情感的产生预留了空间。在举行仪式的过程中,仪式的操持者和观者之间有一种神圣的默契,操持者需要恪守仪式的种种规仪,才能获得观者的认可。除此之外,仪式操持者只要不破坏既定规仪的神圣感,即兴做一些自由发挥,是可以被观者所接受的,甚至比一味刻板地遵从规仪更受欢迎。“烧大牛”的仪式意义的顺畅生成,与它所营造的神圣性与充满艺术因素的表达形式其实是分不开的。笔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对“烧大牛”仪式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意外、突发情况,民众群体都能给予宽容、体谅甚至是鼓励。此种仪式参与心理,正是仪式活动中情感滋生的基础。
其次,当仪式活动宣告结束,庙会中的热闹渐渐远去,重归日常生活的村民依然保留着关于庙会的记忆。在庙会上,人们将日常的烦忧、小我暂时退隐到次要的位置,而产生一种神圣性与世俗性相互交织的心理体验。烧大牛仪式,基于村落家族的传统律令而发生,经由村民的灵活操持与自由发挥,最终产生了超越原初功能的文化意义。
再次,“烧大牛”活动还意味着村落之中不同的人群,以此为话题而反复交流与磋商的过程。“烧大牛”代表着村落生活的一个特殊时段,从腊月十六开始的组织扎制、启动到“游大牛”、“烧大牛”等仪式程序的展开,村民不仅广泛参与,而且众议沸腾。一年之中,“烧大牛”都是村民的热门话题。这种谈论夹杂着民间社会的各种意见,蕴含着与村落日常生活实践相联系的种种知识。人们谈论的是大牛,寄托的是个人心事,最终凝结的是活色生香的民间哲理。或者说,以大牛为话题而形成的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已在村落生活中搭建起一种特别的公共空间。
可以说,乡土仪式以“神圣降临”的方式创造了村落集体中的趋同情感、节律化生活与公共性议题,并由此产生了村落公共性传统,这是传统乡土社会中至为珍贵的文化生态。中国传统村落中的乡土仪式,借助村落群体与神圣之物的交流,落实到村落群体中人际关系的交流,其实质是以“神圣传统”为前导而引出了“公共性传统”。循此领悟,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民众总是努力为各类神灵寻找“在地化”的依据,乐此不疲地将文物遗迹、传说、仪式、日常体验、非常经历、外来人的造访等予以“神圣化”、“传统化”。这曾被长期视为村民“迷信”的证据,但如果能领悟其中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公共性诉求传统,我们就能明白,一般民众对于种种所谓“迷信”并不是真正地“执迷于信”,而是在且信且疑中找寻、创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契机,崇神是为了联众。人们对于“烧大牛”活动的反复品评与回味,是为了寻找与强化它对于乡土社区的表征意义与文化生产能力。这是一种知识的磋商与生产、传播的过程,伴随着情感的共鸣,最终成为营造神圣、塑造灵物的资本,落实在乡土公共性的实现。
时至今日,乡土庙会的神圣感日益淡化,赶集购货、情感交流、人际交往等世俗诉求日益成为庙会最重要的公共职能,这是乡土生活变迁与文化调适的结果。以此为背景,村落仪式虽然依旧是以神灵崇拜为主题,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一种村落—家族传统的共同参与和磋商,从而产生了一种更富有弹性的公共性。信仰的神圣性与情感的世俗化,两者在庙会上并不矛盾,同样是以村落—家族为单元的表达,只不过前者是面向神灵的对于仪式细节的尽量恪守,后者则是面向仪式传统的自由发挥。此外,在面对外来者的更具开放性的社会语境中,当代乡民通过这类“烧大牛”仪式对村落悠久传统的展现,以及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祈福心愿的表达,更多的是在仪式表演名义下对其意志情感的表达、对日常生活的评价、未来合作的预期等。如上种种,都可视为当代村落公共性的生成样态。
四、结 语
东永安村以“烧大牛”活动为代表的村落仪式传统,在农历正月间次第展开,借助信仰与艺术的交织同构,为一方水土搭建起至为珍贵的公共性平台,满足着乡民的某种公共性文化需求。具体而言,这是一村之内不同家族借助信仰仪式划分家族边界,通过与“焚烧圣物”有关的多种仪式表演,连缀而成的不同层级的文化象征体系。在庙会所营造的公共空间中,村民在体验神圣性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同形式的情感体验。乡土社区的公共性,离不开信仰与艺术的交织,离不开神圣感的营造与身体性的灵性发挥。信仰与艺术,在同一个仪式中呈现出一体两面、相向共生的关系,这或许是烧大牛个案的最引人入胜之处。年复一年,焚烧圣物的仪式表演逐渐成为社区内部的一种生活过程,正是借助于乡民在庙会及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乡土生活的公共性意义得以生成。
大致说来,像“烧大牛”这类村落仪式公共性诉求的实现,主要包括三层涵义:其一,仪式活动中所内含的“信仰与艺术”因素是营造出热闹“耍景”的重要内容,这是与村落神圣传统相关的公共性诉求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其二,村民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其意志情感得以释放与提升,从而为这类村落公共性的生成提供内应。其三,焚烧圣物仪式在社区中表演年复一年的举办,使得某种村落公共性缘此而生,绵延为传统。尽管人们面对“烧大牛”这类仪式时所产生的心理并不一致,呈现出相当的个性差异,但正是由这种个性化差异所构成的多种样态,导致了人们在参与、磋商、评价这一仪式活动时产生多元的公共性话语,进而促使村落公共性真正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