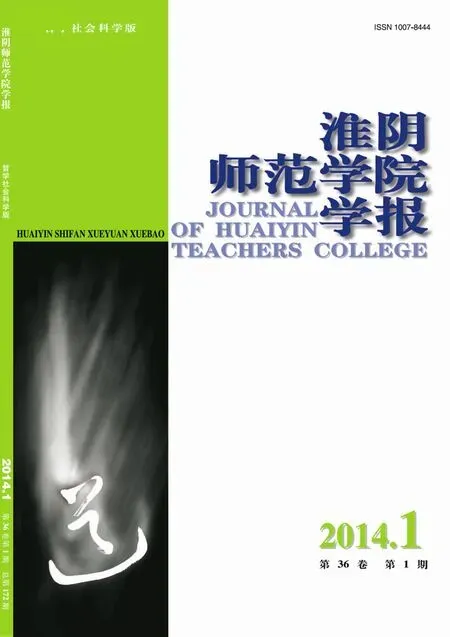现当代学者评析正史《五行志》综合研究
——以《后汉书》等为中心的考察
胡祥琴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5)
自《汉书》首创《五行志》以来,该志体为历代正史所沿袭,并得到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史学著述的重要内容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行志》的撰述成为不少史家追求的目标,成书于此期间的四部正史——《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均保留有《五行志》或与《五行志》名异实同的其他志书等。具体而言,《后汉书》、《宋书》、《南齐书》中专设《五行志》,《魏书》设有《灵征志》,《宋书》、《南齐书》除设《五行志》外还分别撰有《符瑞志》、《祥瑞志》。由于撰写者的基本思路均是将天命与人事联系,大力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因而以上各志在思想来源、体例乃至功能等方面基本一致。这是本文将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的重要理由所在。
《五行志》以撰述、宣扬神学迷信思想为宗旨,这是20世纪以前诸多史家的基本看法。不少史学评论家对《五行志》的价值持否定态度,因而将之束之高阁,少有问津。其中的代表有刘知幾、龚自珍等。刘知幾《史通·书志》专门讨论《五行志》的成书情况及其价值,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竞相撰写《五行志》,虽有缺憾但比之班固《五行志》则更显详实:“自汉中兴已还,迄于宋、齐,其间司马彪、臧荣绪、沈约、萧子显相承载笔,竞志五行。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1]67同时,论者对《五行志》所载内容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对其中关于“天命”与“人事”的分析加以批判,如认为“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1]63。尽管刘知幾个人并没有从唯心主义的窠臼中完全脱离出来,但他质疑“天命决定人事”的思想,对后代的《五行志》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清人龚自珍甚至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2]211刘、龚二人对于《五行志》的质疑及否定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
20世纪以来,学者对《五行志》的研究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两种倾向。80年代以前,学者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五行志》的性质进行界定,而对其具体内容很少专门研究。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一书有关章节详细论及近代学者对魏晋玄学、佛教等层面的研究概貌,却未涉及该时期与《五行志》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等情况。80年代以后,随着史学史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在肯定前辈对《五行志》性质论断的基础上,有学者对其具体内容进行考察,得出关于《五行志》的更丰富认识。该时期发表的一批新论著,内容主要集中于《五行志》与童谣、自然灾害史、自然科学史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很可能是受当时《汉书》研究热潮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大都讨论《汉书·五行志》,有关《宋书》、《南齐书》、《魏书》等书《五行志》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南齐书》、《魏书》之《五行志》、《灵征志》的专门讨论几乎属于空白。
就笔者所了解的一般情况而言,目前学术界专门讨论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论著还很欠缺,相关研究多散见于其他主题的各种论著中。本文将按照研究主题(而不是时段)进行归类评议,希望这种处理方法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认识。*专门讨论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论著还很欠缺,相关研究成果只散见于各种论著之中,并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由于不同时期的五行志性质是雷同的,因此我们在讨论时并未严格区分时段,只要与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研究相关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
一、《五行志》性质与内容讨论
五行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尚书·洪范》。该文向我们呈现了古人如何将外界各种现象和事物归为五类,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推理自然界、人类社会存在、发生、发展的规律及逻辑过程。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将五行与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并提出“五德终始”说,使五行学说成为替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辩护的有力工具。西汉大儒董仲舒等人又将五行与儒家思想融合起来解释人类社会,于是政权交替、权臣更换等都成为五行理论重点关注的对象。顾颉刚指出:五行志是关于古代自然变异的情况[3]77。这个论断仅仅点到而止,但留给后学继续探索的空间。李宗侗、金毓黻等一批早期的史学史研究专家在各自的《中国史学史》中,对《五行志》只简单提及,并未下任何结论。杜维运在评价《宋书》时指出:“《宋书》的八志,是精辟之作。”并总结性地说明其他各志的价值,但在讲到《五行志》时说,《符瑞志》、《五行志》中荒诞之说充斥,则有“疣赘”之感[4]392。王树民指出,《宋书》除在《天文》、《五行》等志中极力宣扬天人感应等谬说外,又特立一篇《符瑞志》,内容远及传说时期的伏羲、神农、黄帝等事,大量散布了虚伪的历史和荒唐的迷信[5]77。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认为,《宋书》的天文、符瑞、五行三志,以12卷的篇幅,集相法、星占、望气、阴阳、灾异、符命、图谶、僧谶等神秘记录之大成,总的目的不过在证明皇权神授、天命有数。在沈约笔下,汉魏、魏晋、晋宋之际,一如五帝三王之受命,没有什么两样;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先后以外藩入继大统,与齐高帝的自立,在受命为帝这一点上也没有什么两样[6]151。瞿林东指出,《宋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宣扬天命、佛教、预言。《符瑞志》鼓吹“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天文志》、《五行志》多有此类记载。这反映了沈约的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他还认为,《南齐书》之《天文》、《祥瑞》、《五行》等竭力宣扬天人感应和星占、谶语、梦寐等,使该书在历史观上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7]259-261。仓修良指出,《宋书》所存在的问题很突出。由于沈约在历史观上是个有神论者,因而书中充满着神秘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天文》、《符瑞》、《五行》三志,以12卷的篇幅,集中地宣扬了天命思想,用隐语、谶书、相术、星占、阴阳、灾异、望气、符命、巫卜等神秘的记载,来证明皇权神授和天命有数,宣扬汉魏以来的帝王无一例外都是“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在《符瑞志》中,沈约还全文引录了班彪的《王命论》,来说明“神器之有授无贪”,“贫穷亦有命也”的宿命论观点,一切都由上天安排,命中注定,“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是历数所至,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8]175。
总结以上学者的论断,可以概括为:第一,《五行志》的志趣在于通过大量物异来宣扬皇权神授、天命有数,作者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史观;第二,《五行志》内容庞杂,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尽管早期史学家对《五行志》的性质皆持批判态度,但该志其他方面的丰富价值也被察觉并论及,这对于后学进一步研究《五行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白寿彝就总结得出:《宋书》的天文、符瑞、五行三志,以12卷的篇幅,集相法、星占、望气、阴阳、灾异、符命、图谶、僧谶等神秘记录之大成。瞿林东也认为,《宋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宣扬天命、佛教、预言。这些凤毛麟角的论断给予我们的信息是丰富的,即《五行志》包含的内容庞杂,涉及领域广泛,既是各种神秘记录的大成,也宣扬天命、佛教、预言。
从现代科学的立场看,《五行志》中所举的例子违反常识,甚至荒诞不经,实际上,通过它们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某些真实状况。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行志》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再现,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就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很高地位,这对于魏晋南北朝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五行志》运用自然物象的变化来解释当世或前代的政治事件,从本质上讲是将毫无瓜葛的两类事物加以人为的神学化的解释。然而,五行本身起于物质、来自自然,因此对自然物象的观察记载在所难免。尽管这些被赋予神学色彩的自然物象是荒诞的,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在剥掉披在自然物象身上的神性外衣后,人们竟发现很多客观真实的东西。因此,重新认识《五行志》的价值十分必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于《五行志》的研究视野日益开阔,主要成果集中在对其价值、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和自然灾害史等方面的讨论。
二、《五行志》价值讨论
关于该时期《五行志》的历史价值,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教本》中讲到:《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是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了,这反映出当时史家的一个共同的思想趋向[9]118。《续汉书》为晋司马彪所著,其八志被补编在范晔《后汉书》中,以补《后汉书》无志的缺憾。白先生指出八志的撰述思想是将“历史”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了,这是该时期史家的共同思想趋向。实际上,白先生在这里给我们指出一条研究《五行志》的路径,即史学著作的现实需要正是史学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体现,而《五行志》所包含的社会功能正是史家热衷撰写的原因,而撰写材料的广阔宏富正反映出该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复杂多变。
陈其泰以全新的视角概括《五行志》的研究价值。他认为,五行说的起源是用物质现象解释世界,所以在《五行志》中又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和例证,故为近代天文学史、自然史、灾害史等学科的研究者所重视,这就是《五行志》的文献价值所在[10]。仓修良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也讲到,《魏书·灵征志》上卷保存了北魏建国以来一百五十年间各地地震的记录,是研究地震史的珍贵资料[8]181。俞晓群《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谈》一文指出,《五行志》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他引用李慈铭的话说,伏生《洪范五行传》、京房《易传》、刘向《五行传记》、刘歆《左氏传说》,皆幸于此志存其梗略。欧阳、大小夏侯之《尚书说》亦可考见一二,盖皆西汉经学大师所遗鳞爪,深可宝也[11]。《五行志》保留了部分已遗失的典籍,但这方面的勾稽研究明显不足。王培华《中国古代灾害志的演变及其价值》一文指出,从科学研究角度看,《五行志》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重要文献[12]。赵濛《〈汉书·五行志〉的历史价值》一文讨论《五行志》的研究价值,认为《汉书·五行志》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首先是为自然科技史研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其次是为汉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其三是《五行志》所创立的编撰体例和方法对后世文献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3]。
按照以上学者的看法,《五行志》的研究价值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在典籍保存方面,今已亡佚的部分资料尤其是两汉时期的纬书,在各部《五行志》中可以部分地钩稽整理出来;第二,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方面,《五行志》对于了解中国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地域分布、程度以及特点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第三,从某种程度上讲,《五行志》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写照,对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五行志》所记童谣研究
“童谣”作为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化现象,通常流行于街头巷尾,是人们对现实政治的预测或总结。它以神学迷信为外衣,以“童言无忌”为人们的心理依托,将时人对政治事件的看法通过通俗易懂的歌词或对偶句表达出来。这不仅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反映,也是专制制度下民间呼声得以宣泄的渠道之一。《五行志》收录了当时社会流行的童谣,数量较多,内涵丰富。由于童谣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较强的政治意图,因此《五行志》所载各类童谣对于认识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世纪以来有关《五行志》童谣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汉书》、《后汉书》所载内容的考察,而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童谣研究还较欠缺。
王子今认为,汉代童谣承担了社会批评的职能,作为政治预言形式,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童谣是一种特殊的舆论方式,其形成和影响,都透露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相关现象,可以有重要的发现[14]。江庆柏指出,中国古代童谣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尖锐地暴露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收录于历代正史《五行志》中的童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思潮[15]。宋抵认为,童谣表面虽罩着一层浓重的封建迷信的面纱,但在面纱后面却可窥见丰富的时代内容[16]。陈秀娟认为,五行志家利用童谣作为占卜,成为封建上层建筑的补充。因此在正史中保存下不少谶语式的童谣。它们鲜明的政治特色笼罩着一层浓重的谶纬式的封建迷信的面纱,在面纱后又永远可以窥见强烈的时代内容[17]。
以上各位学者的意见可以概括为:第一,童谣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它以政治预言的形式反映着人们对于政治的关注和评判;第二,童谣本身以封建迷信为外衣,以孩童口头吟诵的方式折射政治、文化发展的特征,对其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有关历史。
四、《五行志》所载自然史、灾害史资料研究
《五行志》包含大量有关自然史、灾害史的记录。反映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正史中包括《五行志》的就有5部,加上司马彪《续汉书》的《五行志》,通过对这6部志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公元2至6世纪400多年中国的思想文化、自然灾害、奇异物相、民族融合、中外交往的情况,这是《五行志》留给后人很有价值的材料。近些年,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五行志》所载自然物象进行梳理,相关研究成果日渐增多,目前所见成果主要集中于灾害、气候变迁、疾疫、“怪异”等方面。
卜风贤认为,剔除《汉书·五行志》中附会灾异的成分,符合现代灾害学要求的灾种有30多种,涵盖气象灾害、生物灾害、地质灾害三大类型的主体范围。他同时指出,《汉书·五行志》对后代史书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正史著作仿效《汉书·五行志》体例格式记载灾害。《后汉书》、《晋书》、《宋书》、《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灾害专史篇章——《五行志》,中国古代的灾害史料也因此长期被收录保存并延续至今,形成举世无双的、内容丰富的灾害资料库[18]。王春光指出,《汉书·五行志》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灾害和当时的奇怪现象,从自然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价值的材料,所包含的时间跨度之长、空间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都是以前的史籍所没有的。举凡天文学、地学、气象学、生命科学、物候学、技术史都有所涉及[19]。上述两位学者从自然灾害史、自然科学史的角度对《五行志》的价值进行肯定,个别文字或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其基本结论却是可取的,对我们认识《五行志》的自然科学价值有一定裨益。王培华认为,《五行志》作为一种历史体裁,有其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汉书·五行志》具有开创中国古代灾害物异记载之功。第二,《五行志》反映了封建国家灾害物异雨泽的奏报职能。第三,从科学研究角度看,《五行志》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重要文献[12]。作者对中国古代灾害志发展演变作了梳理,认为中国古代灾异观,主要体现在五行学说里,自班固《汉书》立《五行志》,又主要体现在各史《本纪》、《五行志》及明清实录、各种方志中。进而指出《五行志》无论著述内容和形式如何变化,其记载灾异的职能都始终如一,因此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有学者选取《五行志》的部分具体灾害材料,并对这些灾害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该时期的某些具体自然灾害情况。如陆人骥在《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引用不同时期的《五行志》材料,对我国历史上蝗灾出现的地点、产生原因及政府或民间的救治措施作了分析总结[20]。《六朝火灾论略》的作者主要从《五行志》中截取材料,对六朝火灾发生的概况、影响以及政府的赈灾措施等问题进行阐释,并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21]。田艳霞《论魏晋时期的疾疫》引用部分《五行志》材料,对魏晋时期疾疫的分布范围、产生原因以及政府的救治措施进行了总结[22]。也有作者对《五行志》中所载沙尘天气、怪异天象进行讨论,并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王社教认为,在《五行志》中,有许多与沙尘天气有关的记载。由于二十四史自身的连续性和它们在我国史籍中所处的地位,因此其中有关沙尘天气的记载,基本囊括了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要的沙尘天气现象,根据这些记载,可以对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发生的规律进行比较科学的研究[23]。陈倩《何谓“雨毛”、“雨石”、“雨血”、“雨土”?》一文,对于《五行志》所见几种怪“雨”作了推测与考察[24]。《五行志》所记众多怪异现象,令人匪夷所思,例如服妖、鸡祸、男女互变等,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时人附会的可能,但也不能一概将其否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其中有些材料很可能会被证实或阐释清楚。
五、其他研究成果
近几年来,出现了某些专题研究的成果,朱毅《〈宋书·五行志〉研究》一文,对《宋书·五行志》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肯定了该志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生态环境史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乔霞在《〈魏书·灵征志〉的历史价值初探》一文中,对《灵征志》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思想政治史、生态环境史等方面的价值进行了总结与分析[25]。游自勇的博士论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讨论《五行志》的创立及其演变过程,中古《五行志》怪异记录的思想主体,中古《五行志》怪异书写模式与社会的关系[26]。作者对于从《五行志》作为史书书写体裁的设立及演变,到《五行志》所反映的思想主体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都有较深入的剖析,是进一步研究《五行志》重要的参考资料。然而,该文还存在值得商榷的观点:首先,从总体看来,游自勇只是对《五行志》的内容进行总体粗线条总结与分析,并没明确指出各时段《五行志》之具体内容的不同。史学著作的出现总和它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即使是同一体裁在历史的不同时段也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其次,关于《五行志》历史价值的讨论存在一定的误区。我们知道,史书的历史价值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种是该著作所代表的它那个时代的价值,一种是该著作对后世的价值。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当时价值”与“超时价值”的统一。*参见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载《文史哲》1987年第5期。而作者在研究中将两者混为一谈,从而出现对学术前辈有关《五行志》研究价值的讨论一概否定之现象。其三,作者认为服妖、人屙、诗妖(童谣)等是一种社会的“变态”、“末世”的气息。其实不然,上述文化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客观写照。服妖实际上指的是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下服装的变化。人屙则指的是当时的一些流行疾病。诗妖指的是所谓的恶言怪谣,是自秦汉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些正常的现象被某些政客或史学家赋予神学化的解释,从而使我们看到一个“怪异”的世界。
综上可知,目前的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研究还留有诸多空白。首先,《五行志》作为一种史学撰述体裁,为魏晋南北朝学者所尊崇,这一时期史学家不仅自觉传承《五行志》的著述,且多有发挥,出现《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等,这些具有新内容的志书与传统意义上的《五行志》有何异同,这种比较研究还未充分展开。其次,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形式多样化和内容日趋复杂化必然与该时期的政治活动、社会思想关系紧密,将史学著作置于其产生的社会土壤中加以分析必然会得出更加客观理性的研究结果,这也是至今未充分进行的研究领域。第三,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中大量引用志怪小说材料,这一独特文化现象是何原因引起的,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该时期的文史关系、史学家与历史著述等问题。第四,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是研究该时期民族融合的一个新视角,魏收《灵征志》就是北魏鲜卑族接受汉文化的明证,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体现,对其深入研究将是该时期民族融合研究的重要补充。
[1] 刘知幾.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龚自珍.与陈博士笺[M]//龚定庵文集类编:卷七.夏田蓝,编.北京:中国书店,1991.
[3] 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M].何启君,整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4]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2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 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 陈其泰.《汉书·五行志》平议[J].人文杂志,1993(1).
[11] 俞晓群.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谈[J].文史知识,2006(11).
[12] 王培华.中国古代灾害志的演变及其价值[J].中州学刊,1999(5).
[13] 赵濛.《汉书·五行志》的历史价值[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3).
[14] 王子今.略论两汉童谣[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3).
[15] 江庆柏.试谈古代童谣[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1).
[16] 宋抵.《后汉书·五行志》中的童谣与东汉政治[J].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7(2).
[17] 陈秀娟.童谣与五行——兼论东汉政治历史[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4(6).
[18] 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J].史学理论研究,2005(3).
[19] 王春光.《汉书·五行志》所记自然现象[J].史学史研究,1990(3).
[20] 陆人骥.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开明版《二十五史》中蝗灾记录的分析[J].农业考古,1986(1).
[21] 谭书龙,李曼曼.六朝火灾论略[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4).
[22] 田艳霞.论魏晋时期的疾疫[J].医学与哲学,2007(10).
[23] 王社教.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3).
[24] 陈倩.何谓“雨毛”、“雨石”、“雨血”、“雨土”?[J].华夏文化,2006(4).
[25] 乔霞.《魏书·灵征志》的历史价值初探[J].鸡西大学学报,2012(3).
[26] 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