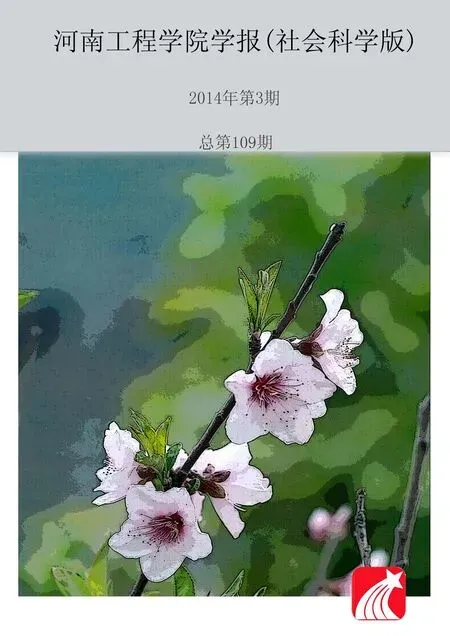从《飞鸟集》看郑振铎的翻译理论与技巧
张 娟
(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74)
一、引言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学者,他不仅在文学、美学、艺术、考古、编辑等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也不容小觑。郑振铎翻译了众多的文学作品,而且就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对翻译事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翻译活动的大力倡导以及对翻译理论的积极探讨。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诗集,因语言优美质朴,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本文拟从《飞鸟集》的翻译探讨郑振铎的翻译理论与技巧。
二、郑振铎的翻译理论
1.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被介绍到国内,然而人们对译作是否能忠实地表达原作的思想、维持原作的风格表示怀疑。尤其是在诗歌翻译上,译作很难完美再现原作在思想和意境上的诗意表达。而郑振铎认为,这种 “文学不可译”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如果文学的翻译是难以进行的,那么世界文学何以在国际进行交流?“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唯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地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地移植于译文中——固然因翻译者艺术的高下而其程度大有不同——不独理想告诉我们如此,就是许多翻译家的经验的成绩,也足以表现出这句话是很对的。”[1]51郑振铎的翻译实践进一步证实了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飞鸟集》近乎完美地再现了原文的形式、内容、诗意。
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2]82
使生如夏花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The birth and death of the leaves are the rapid
whirls of the eddy whose wider circle move slowly among stars.[2]84
绿叶的生死,是旋风急速的飞转,
而更广阔的旋转,是繁星之间的缓缓转动。
《飞鸟集》中的诗较为短小,为散文体,这种诗歌形式能表达瞬间的思维片段。郑振铎在译作《飞鸟集》的例言里写道:“泰戈尔的诗歌多用美丽的文句,这种字眼是‘诗的’‘美的’以及‘有生气的’——就是那些不仅仅为报告用而能融化于我们心中,不因市井常用而损坏它的形式的字眼;诗歌的文句总是含蓄的,暗示的。”[3]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保留了原文的散文体,并且在选词造句上满足译文读者的需求,从而再现了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创作出让读者易于理解和喜爱的译作。
2.翻译的目的
郑振铎提出翻译的两种目的:“现在的介绍,最好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1]503他反对把翻译与创作对立起来,认为翻译等同于创作,并且翻译的作用不仅是“媒婆”,还类似于“奶娘”。[1]在论述翻译与创作的关系时,郑振铎认为,仅仅阅读《西游记》《红楼梦》及诸家诗文集不能使文学创作有所突破,只有对外国文学进行译介才能给中国文学注入新鲜血液。[1]关于郑振铎的翻译,陈福康如此评价:“无论是血和泪的文学的俄国革命文学作品,还是其他的印度文学作品与古希腊罗马神话作品,都是经过他选择的,或是其内容对中国读者有参考意义,或是艺术上有鉴赏学习价值,或是外国文学史上的名人名作。”[4]当时中国文学正处在转型期,外国文学的引进对中国新文学的初期发展和成长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五四”时期,几乎所有作家都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们阅读和学习外国文学作品,从而拓宽眼界,提高文学创作才能,给后世留下了不少伟大的作品。随着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引入,新的内容、形式和思想一起涌入中国文学,旧的文体急需变革,白话文是这场变革的产物。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白话文是这场浩大文化革命的先锋。陈独秀是翻译泰戈尔诗歌的第一人,他采用的是文言文,而郑振铎采用白话文来翻译《飞鸟集》,为白话文的推广起了积极作用。郑振铎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作为引进新的文学样式的重要途径,因此,他摒弃了传统的诗歌形式,引入散文诗这一全新的文学样式。“小诗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它的出现正是在文学传统的枝丫上开出的一个现代的新萌芽”[5],《飞鸟集》中的小诗和日本的俳句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诗的发展。
三、郑振铎的翻译策略
1.直译和意译
“五四”之前的小说翻译,译者讲究文采,主要采用意译,直译很少被采纳。“五四”时期,许多译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主要在于介绍,把外国文学引入国内,从而帮助国内新文学的发展。郑振铎认为,翻译应尽量忠实地呈现原作的原貌,“译书自认为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于中文为不可解,则亦不好。而过于意译,随意解释原文,则略有误会,大错随之,更为不对。最好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1]71。由此可见,郑振铎并没有使直译和意译完全对立,他主张直译为主,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流畅则可采取意译。在翻译《飞鸟集》时,郑振铎主要运用直译,忠实再现了原文的意思、形式和风格。
“Moon, for what do you wait?”
“To salute the sun for whom I must make way.”[2]72
“月儿呀,你在等候什么呢?”
“敬礼我将让位的太阳。”
The fish in the water is silent, the animal on the earth is noisy,
the bird in the air is singing.
But man has in him the silence of the sea,
the noise of the earth and the music of the air.[2]75
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
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
但是人类却兼有了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
从第一首小诗的翻译可见,郑振铎完全是采用直译的方式,再现原诗的意思。 这两行诗中有两个意象,“Moon”, “the sun”,被翻译为“月儿”和“太阳”。其中“Moon”直译可译作月亮,而郑振铎在采用直译的同时巧妙地将其翻译成为“月儿”,更具诗意,更能表达出“月儿”“等候”“敬礼”“让位”“太阳”的意境。翻译第二首小诗时,郑振铎主要仍是采用直译的方式,但他把“The fish”“the bird”译作“游鱼”“飞鸟”。虽然此处郑振铎添加了“游”“飞”,但总体上郑振铎没改变全诗的意思及内涵,反而让这两个意象更加生动,使译文更具诗意。
2.欧化
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英语对白话文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欧化”现象随之产生。“欧化”主要指在句法和词汇上受到印欧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影响。“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而白话文在初期虽具有简单易懂的特点,但表现能力较低,不能很好地传达思想。翻译在介绍外国作品内容、思想、情感的同时引入外国人的语言表现方式,从而有利于白话文的发展和成熟。郑振铎对“欧化”表示支持,“中国的旧文体太陈旧而且成滥调了。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与情绪都为旧文体的成式所拘,不能尽量地精微地达出。不惟文言文如此,就是语体文也是如此。所以为求文学艺术的精进起见,我极赞成语体文的欧化”[1]413。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中就有不少欧化现象。
I cannot tell why this heart languishes in silence.
It is for small needs it never asks, or knows or remembers.[2]73
我说不出这心为什么那样默默地颓丧着。
是为了它那不曾要求,不曾知道,不曾记得的小小的要求。
The moon has her light all over the sky,
her dark spots to herself.[2]111
月儿把她的光明遍照在天上,却留着她的黑斑给她自己。
英语的中心词可以有前置定语和后置定语,一个中心词可以被多个定语修饰。汉语的习惯用法是定语在中心词之前,因此,在译文中,如果中心词前有过多、过长的修饰成分,则容易让译文显得冗长。在第一首诗中,“needs”前有定语“small”,后又跟了一个定语从句,译文“要求”前就出现了较长的修饰成分。在第二首小诗的译文里,三次出现“她”,而在白话运动之前,汉语中第三人称表达只有“他”。翻译家通过引进外语的表达来丰富白话文的表达方式,就出现分别对应“he”“she”“it”的“他”“她”“它”。
四、结语
郑振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上对我国文学的贡献都不容小觑。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和论述,对我国近代翻译理论的建设增添了宝贵的财富。他提出文学作品的可译性和翻译的目的, 并大力主张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为翻译事业的发展和新文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充分体现了他的翻译理论与技巧,他用简单质朴却富含深意的文字完美再现了原诗的内容和情感。译诗散文体的形式为白话文的发展和小诗运动的兴起起到了积极作用。
[1]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三卷) [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2]〔印度〕泰戈尔.飞鸟集[M].郑振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3]郑振铎.飞鸟集例言[M]//〔印度〕R.泰戈尔.泰戈尔诗选.冰心,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157-158.
[4]陈福康.郑振铎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376.
[5]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