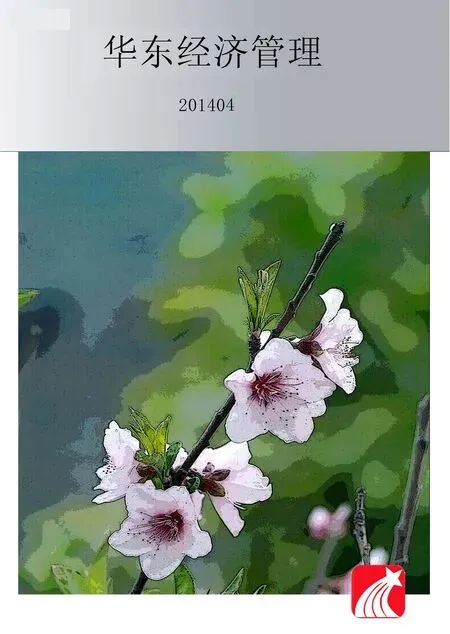农村劳动力迁移、老人照顾需求与社会支持介入方式分析
宁满秀,荆彩龙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引 言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口预期寿命得到普遍延长,出生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家庭中老年人口数目不断增长,加剧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1]。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11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已达1.23亿人,占总人口的9.1%。另外,根据全国老龄委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总量将超过4亿人,占总人口的30%。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会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2]。显然,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必然引发老年人照料服务需求量的急剧增加。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地区与行业之间的要素流动壁垒逐渐消除,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已成为一种长期趋势。据统计,2010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1.5万亿,其中大多数是15~3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致使大量老人留守农村。由于成年子女的外流,潜在照料提供者的数量减少,农村留守老人既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又要承担照看孙子女的责任,更为严峻的是,原先由外出子女耕种的土地自然而然地转嫁到农村留守老人身上,加重老年人的耕作负担,弱化了子女照料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功能。此外,在社会生育率降低的同时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攀升使潜在的家庭照顾资源愈发减少。因此,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引发了由家庭提供照顾服务的现实困境,传统上单纯依靠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来解决农村老年人照料问题已越来越不具备现实可行性[3]。
在社会经济结构、人口结构转型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多重背景下,本文基于农村老年人照顾需求的变化,试图探讨传统家庭养老体系是否能给老年人提供适时且足够的照顾支持?现有的家庭照料体系是否需要政府支持政策的协助?而未婚或丧偶的独居老人又是通过何种途径满足其照顾需求?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将如何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照顾需求,各类型长期照顾服务如社区式、机构式等正式服务体系如何补充非正式照料体系的不足?
二、基于社会支持理论的分析农村老年人照顾需求
Gallo[4]将社会支持体系分为社会关系的量与社会关系的质,就是由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所组成。然而,高迪理[5]认为“社会支持”与“社会网络”是两种不同又相关的概念,并指出有社会网络存在不见得有社会支持,但社会支持的提供与感知必须在社会网络存在时才能顺利进行。“社会支持”是属于主观感知的概念,当事人能够感受到某些支持性行为满足其需求、解决其问题的功能。而“社会网络”则属于客观结构的概念,即与当事人相关的各成员在网络中是如何组成与分工。因此,本文根据不同的社会网络带来社会支持功能的差异来区分不同的老人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支持网络满足其照顾需求。农村老年人照顾需求分析视角的实质即是将老年人照顾需求与社会支持网络相结合,在社会支持网络的基础上关注老年人照顾需求与需求满足的互动关系,即:农村老年人照顾需求分析视角依托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相关理论。
(一)层级补偿模式
层级补偿模式主张近亲(特别是配偶和子女)是社会支持的核心,老人需要帮助时首先会寻求近亲协助。正如Shanas[6]所解释:当老人没有子女时,一项家庭替代原则将会启动,其兄弟姐妹、侄儿外甥、及侄女外甥女通常会履行子女的角色及责任。即老人在使用社会资源时会有选择的偏好,他们会首选与自己最亲近的人,即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当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并不能满足老年人照顾需求时,老人才会转向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求助。同时,层级补偿模式说明,老人照顾工作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并不是基于职务、金钱等因素,而是在于心理程度上的亲近疏远,如果老人能够获得家庭子女与亲属的照料支持,那么,他就不会转向正式照料体系寻求支持。通常而言,老年人在非正式支持体系中所获得的帮助越多,尤其是从接触最亲密的家人包括配偶和子女获得的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满足度越高,生活质量越高。
(二)任务分工模式
任务分工模式认为,在满足老人照顾需求层面,亲戚朋友以及邻居对配偶和子女的替代效果是有限的。一般而言,朋友或邻居提供的协助通常是小规模且短期性的项目,如购物或提供交通协助;需要长时期且个人层面的协助则由亲属履行;特定职务则由配偶或子女提供协助。根据任务分工模式,当某一特定支持来源无法获得时,除非有类似特征的支持体系予以替代,否则会导致某些照顾需求无法获得满足。以无子女者为例,子女具备的特定功能虽然可通过某些类似父母-子女关系者予以执行,但亲戚朋友以及邻居却无法完全替代配偶及子女的照顾功能。实质上,任务分工模式涵盖了层级补偿模式的观点,当缺乏某一可执行特定任务的理想照顾者时,个人将会选择结构相似的照顾者予以替代;与其不同的是任务分工模式认为当个人缺乏执行特定职务的理想照顾者时,选择另一功能近似的照顾者予以替代可能导致照顾质量的降低[7-8]。
(三)压力缓冲模式
Sharkey是压力缓冲模式的开创者,他认为,当老年人受到压力冲击时,如果社会支持网络给予老年人适当的帮助使压力冲击得以缓冲,老年人就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反之,压力长时期得不到缓解和消除则会造成老年人抑郁等身心疾病。可以说,包含传统家庭养老体系在内的社会支持的介入在老年人遭遇严重生活事件冲击时具有压力缓冲作用,能够缓解老年人的不满情绪,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压力的作用效果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直接模式,即不管压力是否发生,老年人都可以直接从社会支持中得到益处。如果农村老年人接受社会支持能够增强老年人幸福感并且促进老年人对团体的归属感与自尊,那么,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直接的积极效果,但没有缓冲效果[9];另一种模式是压力缓冲模式,即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经历压力事件后产生的负面影响有缓冲效果[10-11]。缓冲模式主张当压力不存在时,社会支持对老人忧郁并无特别影响,但是当老年人遭受严重的生活打击,老年人心理和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时,社会支持的介入可以降低老年人所承受的压力,间接降低老年人身心受到的负面影响,并且压力愈大,缓冲效果愈显著。
三、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照顾需求与社会支持介入方式
(一)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照顾需求
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未满足需求是导致老年人增加医疗服务利用及疾病恶化的关键,也是决定老人是否需要使用长期照顾服务的重要因素[12]。因此,本文从生活照顾需求、经济支持以及情感需求三个层面分析农村老年人的照顾需求及其差异性,以期通过对农村老年人未满足需求的了解探讨农村老年人的长期照顾服务问题。
1.生活照顾需求
按照生命周期规律,老人达到一定年龄时身体机能退化的趋势明显加剧,遭受疾病困扰、日常功能缺损的可能性增大,自理能力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代际之间空间上的分离使得外出务工的子女难以为父母提供经常性的照料支持,影响了老人照料资源的可获得性。一旦老人身体健康恶化,子女对老人的照料感到力不从心。与配偶同住的农村老人,配偶可能会提供生活上的照顾,缓解子女照料上的压力;膝下无子女和丧偶的空巢老人一旦遭遇重大疾病的冲击更将无人照顾,严重降低老年人独立生活的能力进而加速老年人的死亡。由此可见,当老人因身体机能障碍需要料理家务(洗衣服、准备餐食及打扫房间等),或个人照顾(协助梳洗、洗澡、如厕)等劳动密集型的照顾需求时,子女在身边更便于提供生活照顾[13]。毋庸置疑,研究农村老人生活照顾需求满足问题是对家庭养老思考的应有之义。
2.经济支持
随着老人年龄增大及其健康状况恶化,劳动时间的供给大幅减少,收入不断降低。身体机能衰退和劳动能力的丧失使得农村老年人无法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支撑生活,需要依赖子女的经济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迁移使得成年子女收入增加,子女可能会通过收入转移使父母退出农业劳动,改善老人的经济福利水平并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但是,通常情况下,农村老年人并没有因子女外出打工而增加收入。外出打工的成年子女在建房、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经济压力以及他们收入的有限和不稳定,外出成本较高等都限制了外出家庭成员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14]。因此,可交换资产或可流通财富的缺乏限制了农村老人的退休,他们不得不延长劳动年龄以增加储蓄养老。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空巢老人经济上的依赖性加强,虽然家庭可能具备响应这些危机的能力,但其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却可能在长期缺乏社会机构支持的情况下随时间延长而递减。
3.情感慰藉需求
人到垂暮之年,一方面,需要面对丧失亲友、爱人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老年人缺乏对死亡的了解也加重了其对死亡的焦虑。此外,劳动力迁移加剧家庭分化并改变了“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代际居住安排的分离使得老年人不能够享受子女膝下承欢。“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成为农村空巢老人的真实写照。空巢老人处于孤独、寂寞需要向别人倾诉、“排遣”时,情感支持需求无人满足,长此以往空巢老人容易患上抑郁症,更有甚者患上“空巢综合征”。显然,劳动力外流致使农村空巢老人增多凸现了农村老年人情感和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能在农村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提供老人继续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来维持老人与他人的互动交流,老人可能不会面临自我价值感丧失的危机。国外研究也指出,老年人与朋友、邻居交往似乎比家人更能增加信心,更有利于老年人排遣孤独寂寞。这是因为同代同龄老人似乎有更多的共同点,且交往不是强迫的,而是友谊维持的[15-16]。
(二)社会支持网络在老人照顾中的介入方式
社会支持网络由政府、社区以及家庭三方组成,能够提供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工具性社会支持。工具性社会支持是指得到具体的帮助与支持,如提供服务、金钱支持或生活物品等[17]。支持接受者对于所得到支持内容类型,根据接受者需要情况有不同重视程度,如对于经济匮乏者,物质与金钱支持重要性较高;行动不便的人,外出交通的协助重要性较高;失能不能自理生活的老人,日常生活协助的重要性较高。②情绪性社会支持。情绪性社会支持是指个人感受到他人对自己的关怀、尊重并强化自我价值[18]。③信息性社会支持。信息性社会支持是指他人帮助个体了解压力事件,使个体相信本身拥有的资源与应对的策略能够处理此压力[19]。
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经济、心理以及身体等不同功能的维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良好的社会支持是老人健康的保护性因素。有研究指出,老人的社会支持在老年生活中具有缓和生活压力的功能[5],让老人得以面对生理的病痛及生活环境或角色的改变所带来的冲击。具体而言,在身体健康方面,充足的社会支持可以减缓身体功能的退化,使老人维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在心理健康方面,社会支持与老人的心理适应能力、忧郁程度等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缺乏社会支持的老人明显有较高的忧郁程度[20],尤其是遭受严重生活打击。
社会支持网络的理论基础在老人照顾类型的研究中是沿着婚姻居住状态发展的照顾网络而侧重不同层面,“层级补偿模式”强调各种支持来源的可获得性,“任务分工模式”和“压力缓冲模式”则分别关注不同婚姻状态、居住状态下老年人的照顾需求。本文期待藉由三种理论模式理顺婚姻居住状态对老人照顾需求的影响,并通过社会支持网络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来探讨不同婚姻居住状态下社会支持与农村老人照顾需求的内在作用机制。
拥有婚姻关系且与子女居住的老人,家庭养老体系可以供给老年人物质上的资助、生活信息的提供以及情感支持,使得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不虞匮乏,并在人际互动中感受到爱与尊重,有助于老年人应对严重生活事件以及维持健康生活,最终将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避免过早进入长期照料机构并减少对公共及医疗资源的依赖。所以,这种类型的农村老年人较少使用社区式服务和机构式服务。应当指出,对有配偶者而言,婚姻状况的解体(如配偶死亡或离婚)或配偶无法继续提供照顾功能时,老年人照顾需求提供者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也导致传统家庭养老体系的改变。Tennstedt等人[21]指出,传统家庭养老体系失效通常发生在配偶死亡或子女外出无法继续提供照顾。在这种情况下,独居者即为机构式服务和社区式服务使用的高危险群,也是长期照顾政策应重点关注的目标人群。农村劳动力外流致使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发生改变,亲子居住安排空间上的远离使传统家庭养老体系失效,农村空巢老人并不能完全依靠外出务工子女回家照顾。对于未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来说,社区可以针对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提供各种福利服务,例如,居家服务,营养膳食服务,白天照顾或者是短期照顾或临时照顾以及咨询提供等等,这样能够使空巢老人在所熟悉的环境中就近取得资源获得协助来满足需求。对于子女外出务工,丧失配偶,自己无生活能力的老人,养老机构可以提供老年人住宿服务、紧急送医服务、社交活动服务、教育服务、保健服务、医疗服务等,提高了空巢老人对公共资源的依赖,也有助于老年人应对严重生活事件以及维持健康生活。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弥补了家庭养老的不足,针对不同居住安排下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社会支持,满足了老年人的照顾需求,推动多种养老方式共同协调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22]。
已有文献在讨论老人照顾需求与社会支持关系时,似乎都直接或间接立基于一个基本假设:老人拥有社会网络资源就一定会得到相应的社会支持,其照顾需求将得到满足。事实上,老人拥有的社会网络并不代表他们的照顾需求就能获得满足[23]。特别是,生育率下降和家庭规模缩小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尤其是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攀升以及正式照料制度的缺失导致老年人面临日益严重的“看护”危机。虽然这并不必然导致家庭成员间关系的急剧减弱,但代际之间的生活互助肯定会受到制约并趋于弱化[24]。尤其是当农村老年人年老病衰的时候,所谓的“亲奉汤药”已无可能,只能请人代理。家庭失灵导致成年子女无法继续发挥照顾功能,其他资源(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的适时介入与配合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为了弥补家庭照顾的落差,以便老人能在熟悉的社区中得到安养照顾,政府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办理相关的社区照顾服务或者鼓励提供机构服务,尤其是对独居老人或因行动不便而其子女均在外务工无法提供家庭照顾的老人来讲显得尤为迫切。当子女外出打工无暇顾及老年人时,社区可以根据老年人的具体需求提供居家服务;同时在家庭经济允许的条件下也可以将老年人送往正式的养老机构照顾。同时,由于农村基础设施不健全,缺乏必要的休闲娱乐设施,加上子女外出务工老人无人陪伴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机构和社区应该提供必要的情绪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丰富农村老年人生活,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四、结论与启示
“以家庭为中心”的照顾模式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养老的基本模式。我国政府部门及社会舆论也不断宣扬我国是以家庭和孝道为中心的儒家伦理模式,期待通过儒家伦理的强调将照顾问题家庭化及道德化;但我们却不能忽略儒家伦理对家庭孝道观念的理想化,尤其是目前社会变迁已经重塑了家庭关系与家庭功能、夫妻之间的权利格局,儒家传统价值观在代际间传递日益减弱,理想家庭在现实社会中具体实践的可行性微乎其微。
基于传统家庭养老体系与农村劳动力外流所引致的代间交换力量不足以满足农村老人照顾需求的现实,本文从农村老人需求差异性角度出发,在审视老人在家庭主义及国家意识的夹缝间获得照顾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满足老年人照顾需求的政策途径,即通过农村老年人照顾需求以及我国社会支持网络体系构建分析我国长期照顾政策发展的定位与方向:
(1)主张我国长期照顾政策应以家庭为照顾服务提供单位,对此,通过城镇化、现代化建设带动本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以提高本地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从而保证成年子女在家庭照料与劳动就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关系,在不影响成年子女就业的同时也满足老人的照料需求;与此同时,创新“喘息服务”等居家养老模式,尽可能通过社区以及机构将服务输送到农村老人所在家庭,避免让老人迁就照顾现实而不得不进行晚年居住安排的变迁,让老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圈内就近获得照料与关怀,实现老人“就地老化”的目的。
(2)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就业的宏观背景下,相关决策部门一方面可以通过破解农村老人与成年子女随迁的制度障碍,鼓励老人与成年子女随迁,在不降低成年子女就业流动性和增加其照料机会成本的情况下保障老人能够得到应有的照料;另一方面,应当完善社会医疗与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与接转,从而保障农村老人在随迁以后能够在社会保障体系内享受相应的福利保障。
总而言之,与其在传统家庭养老体系和正式照料体系之间划下一道鸿沟,更务实地作法应是构建“政府-社会组织-机构-社区-家庭”多中心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真正实现在地老化、健康老化、积极老化的养老目标,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1]董力堃.强化政府养老保障责任的理论模式与路径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0(9):133-137.
[2]胡宏伟,时媛媛,肖伊雪.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中国养老保障方式与路径选择——居家养老服务保障的优势与发展路径[J].华东经济管理,2012(1):119-123.
[3]刘晓梅.我国社会养老服务面临的形势及路径选择[J].人口研究,2012(5):104-112.
[4]Gallo Joseph J.The effect of support on depression in caregivers of the elderly[J].Th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1990,30(4):430-436.
[5]高迪理.社会支持体系概念之架构之探讨[J].社会发展季刊,1991,54:24-32.
[6]Shanas E.The family as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in old age[J].The Gerontologist,1979,19(2):169-174.
[7]Barrtee A E,Lynch S M.Caregiving Networks of Elderly Persons:Variation by Martital Status[J].The Gerontologist,1999,39(6):695-704.
[8]Wu Z,Pollard M S.Social support among unmarried childless elderly persons[J].The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98,53(6):324-335.
[9]Thoits P.Conceptual,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studying social support as a buffer against life stress[J].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82,23(1):145-149.
[10]Caplan G.Social support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Lectures on Concept[M].New York:Behavioral Publications,1974:143-147.
[11]Cohen S,Wills T.Stress,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5,98(2):310-357.
[12]Pendry E,Barrett G,Victor C.Changes in household composition amongthe over sixties: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health and lifestyles surveys[J].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1999,7(2):109-119.
[13]Tennstedt S L,Crawford S L,McKinlay J B.Is family care on the decline?A longuitudi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ubstitution of formal long-term care services for informal care[J].The Milbank Quarterly,1993,71(4):601-624.
[14]贺聪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3):46-53.
[15]Gottlieb Benjamin H.Social Support Strategies[M].Sage Publication Inc,1983:239-241.
[16]霍曼N R,基亚克H A.社会老年学——多学科展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16.
[17]Christopher T Whelan.Relationship of age,education,and occupation with dementia among community based sample of African[J].Arch Neurol,1993,53(2):134-140.
[18]Taylor D H,Schenkman M,Zhou J,et al.The relative effect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ementias,disability,and comorbidities on cost of care for elderly persons[J].Journal of Gerontology:Social Sciences,2001,56(5):285-293.
[19]Wills T.Supportive funct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5:61-82.
[20]Cheng S,Chan A C M.Filial pie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well older Chinese[J].Journal of Gerontology:Psychological Sciences,2006,61:262-269.
[21]Tennstedt S L,McKinlay J B,Kasten L.Unmet need among disabledelders:A problem in access to community long term care?[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1994,38(7):915-924.
[22]汪大海,张建伟.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问题——“鹤童模式”的经验与瓶颈[J].华东经济管理,2013(2):118-122.
[23]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1):96-108.
[24]叶菲菲,宁满秀.居住安排对农村老人照顾需求满足的影响——兼论我国老人照顾政策选择[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2(6):44-48.
——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