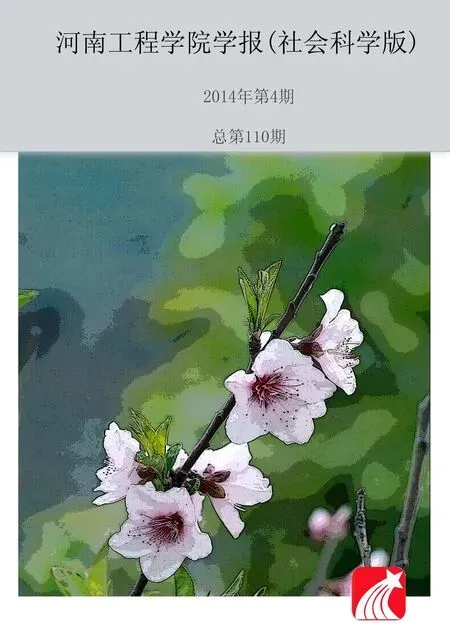沈从文、孙犁文学世界的水之气质
李慧媛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水自古以来孕育着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不同地域的水使不同文明刻上了特有的文化符号,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孕育着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雄心壮志,长江之水天际流包藏着千古风流人物的博大宽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在滋养人气质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而这种人之气质、人之生活都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独特气韵,以致由水而生的作品都散发着水淡雅、清甜的气息。沈从文和孙犁就是创作这种似水作品的两位作家。
沈从文和孙犁与水的缘分由来已久,曾经的水畔生活给了两位作家水样的情志和气质,他们把自己的真性情融入生活,升华为作品。就如沈从文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写的一样:“……我学会用小小脑子思考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的深一点,也亏得是水”。[1]42孙犁也说:“我看着那里的河水,也像看着亲眷一样。”[2]364他们共同出现在我们的世界正是因为相似的水样气质。
一、水育人,人似水
沈从文的水以湘西沅水为依,孙犁的水则来自河北滹沱河,虽然一南一北相距甚远,但这并不阻碍他们作品中临水而居的人们具有相似的气质。
1.女人之纯真、柔情
女人如水般通体纯真。纯真是沅水和滹沱水共同塑造的女性气质之一。无论是沈从文笔下的萧萧、翠翠,还是孙犁笔下的水生嫂、九儿,这些女子的年龄有所差距,人生经历有所不同,但纯真是她们的共同之处。随沅水流动,我们看到那里的女子或如萧萧般遭受落后习俗的摆布,尽管已是“媳妇”,却仍和孩子一样“常常做这种年龄人所做的梦,梦到门后角落或别的什么地方捡得大把大把铜钱,吃好东西,爬树,自己变成鱼到水中各处溜”[3]12。她们或如翠翠有“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3]52,以纯真的目光看待自己与天保的爱情,不掺杂丝毫物质的污秽。沅水围绕着湘西土地,使这里免受纷杂的物质侵害,纯粹地保持着天生的真善美。沅水将外界入侵的杂质隔离、沉淀,只保留最清明、纯洁的江水流入湘西女子的血液中,得以使这些女子在被命运摆布下更显楚楚动人。穿行于荷花淀,看到的则是战地妇女的纯真。即使是描写战争,作家孙犁也极力追求美感。钱谷融先生说:“在我的眼里和心中,孙犁最可贵的艺术品质就是对于美的崇尚和追求。”[4]而这种追求最能给予荷花淀女性真我的实质。战地女人对于丈夫的爱是至真至纯的,这爱不仅让她们甘愿为夫打理家庭上下,而且能让她们奋不顾身地到前线探望丈夫的同时与敌人战斗。这种纯真美是朴实,是勇敢,是对善的执着。孙犁在《创作随想录》中说:“美即真与善之结合,无真诚,无善念,尚有何美而言?”[4]98正是由于孙犁先生对美的推崇,才有了荷花淀女人的纯真善良,才能在战地中吟唱胜利的诗歌。
女人如水般柔情。水能呈现多种形态,如瀑布被地势改变,如涓涓细流分岔,如大河奔腾径直涌动;女人也有多种性格,如萧萧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如翠翠爱情左右殊途,如水生嫂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但无论是哪种女人,都有柔情。萧萧做媳妇时仅12岁,还不懂情,她抱着“弟弟”四处玩耍,在“弟弟”肮脏的小脸上亲亲以逗他开心……在对世事认识模糊之时萧萧所做的只是一个孩子发自内心地去照顾比自己年幼的孩童,不是被逼迫的,是心灵的柔软做出的自然行为。而萧萧面对花狗的引诱,在被指责的同时,我们更能感到一个懵懂少女对于异性所表现出的柔情似水:萧萧会喊着“花狗大”向其讨歌,也会“带着歆羡的口气”夸赞花狗。在无知的爱情面前,萧萧所表现出的是完全不同于对待小丈夫那种亲人的柔情,而是几许你侬我侬的爱恋柔情。与其说是花狗的引诱迫使萧萧做了糊涂事,不如说是青春期女性特有的对模糊爱情的向往在作祟。是这般柔情牵动萧萧甘愿做“弟弟”的小媳妇无微不至,也是这般柔情迫使萧萧忘记礼教约束奔向糊涂的爱情。水边生长的女人,哪怕是果断坚毅的水生嫂也满腹柔情。开篇所描写的妇女编织草席场面就能看出女人柔情的一面。作者写水生嫂劳动时有这样一句描写:“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5]39,而苇叶就像“在她怀里跳跃着”。作者笔下的水生嫂完全不同于北方人剽悍的外貌,而是一个娴静温柔且心灵手巧的水边女子,这些细腻是水赋予水生嫂的,水同时赋予她的还有对丈夫深爱的柔情。水生嫂得知丈夫要投入大部队,魂不守舍时手指“震动”了一下,不小心被苇叶划破了,又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这一“震”一“吮”是对丈夫抗战的无限担忧,是对成全丈夫前线战斗的不忍和思量,也是纠结过后的包容和支持。而具有如此柔情的不只是水生嫂,荷花淀女人个个都是:对丈夫的牵挂“藕断丝连”,没有找到不对就暗暗骂着自家的“狠心贼”,送完补给后又唠叨丈夫们爱答不理的“横样子”……女人的柔情,如水般外露,也如水般内蕴。
2.男人之坚毅、执着
水之气质不仅局限在女性角色身上,沈从文和孙犁笔下的男性也都具有水一样的性情。并且,无论作者持怎样的态度去刻画这些男性人物,或同情或颂扬,深入发掘都有对其的肯定和欣赏。而这值得欣赏的地方正是水赐予水边男人的独特气质。
男人如水般坚毅。水是坚强的,无论高山断崖如何阻挠,它都能找寻自己的出路;水是刚毅的,它能汇聚无穷的力量开拓自己的道路。水边的汉子也如水般坚毅。沈从文笔下的柏子是他刻画的男性人物的代表,柏子同其他以船为生的男人一样被岁月磨炼成了“飞毛腿”,而桅子上的难度活正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好机会。长年的磨炼使得他们早已对生活的艰难有了足够的能力去克服容忍,再多泪水汗水只不过是船桅上的一首自由之歌。再如翠翠身边的男人,尽管生活阅历不同、性格迥异,但是对于生活,个个都是坚忍刚强的汉子。水边生活的艰难,很容易就让那里生活的人们学会吃苦希冀美好并为之努力。而孙犁笔下给人印象最深的男性形象就是《芦花荡》里的老头子。“鱼鹰”一般,是作者对老头子外貌的刻画,老头子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在枪林弹雨中不畏艰险,找寻敌人发现不了的线路,冲破封锁线,使部队与外界互通往来。在两位作家的文中,男性总是背负着人生意义上的重担,或为生活卖力,或为至亲过活,生活的艰辛使他们变得更加坚毅。
男人如水般执着。水滴石穿的坚持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坚持的关键在于有石穿的信念。柏子的信念是河街小楼的一夜柔情。河街小楼的灯光红红,“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存在”,我们姑且把这东西称作爱情。柏子对妇人的执着有些勇敢,有些糊涂,也有些值得尊重,他将一整月黄泥汗水换来的金钱一股脑地倾泻于妇人身上,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在柏子心里,生活的快乐和感情的寄托就是他为之执着拼命的信念,这信念尽管不登大雅之堂,甚至略显悲悯凄凉,但水边人对于心中所认定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义无反顾的,是值得肯定的。而孙犁笔下的男子信念更加明确,更多地倾向于革命。对于长年忍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来说,革命的胜利是他们毕生的追求。水生为了革命的信念不顾上有老下有小的牵挂第一个报名到大部队去,同其他淀边人家一样,不管女人们怎么表达恋恋不舍,他们都坚定执着,舍小家顾大家。“鱼鹰”一样的老头子也对革命执着,执着于出入水淀保证人员物资安全,这种执着不仅是对战士的保证,更是对敌人的蔑视。水边男子的执着带有一股子蛮劲,满是水赋予他们的勇往直前和无所畏惧,是世世代代的水生活给予他们的性格特质。
沈从文和孙犁笔下的水边人虽有相似气质,仍存在差异。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带有原始气质,他们游离于世俗之外,凭借人性的本真对生命进程做出不加修饰的回答,这也是作者为坚持自己的文学观、政治观而刻意为之的。孙犁则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人物刻画的前提是受到一定的革命思想熏陶,具有现代人的自觉。二人文学价值观念的各自坚持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
二、水成文,文质如水
沈从文和孙犁的作品同时注入了水的血液,水对作者性格气质的形成是潜移默化的。对两位作家来说,水不仅是素材,更是生活,这也是二人作品风格虽有差异却能拥有相同水般质感的原因。
文如水般忧郁。忧郁如沅水般浸透着土地,滋养着土地上的人们。《萧萧》中的萧萧是忧郁的,孤苦的身世、被诱时的无知、命运的无奈……哪怕是写萧萧在池边林前与“弟弟”无忧欢喜,写她与花狗的打情骂俏,都只是在反衬悲凉的故事情节。这悲不是喷涌的,而是在淡淡模糊中让我们看到了萧萧孕中等候发落的无能为力,生子后不由自己的无奈忍受,抱着孩子看另一个“自己”入门的无知冷漠。妙龄少女如此这般无可奈何、浑然不觉,写者怜悯、读者哀婉,作品于写读之间尽是忧郁。而《边城》尽管纯洁无瑕,至善美好,却也摆脱不了忧郁的基调。爷爷的去世、天保的意外、傩送的出走、翠翠爱情的无果,都使作品在表达湘西人民不被物质侵蚀的真善美的身上印烙了忧郁的伤痕。而孙犁的作品表面上看是积极向上、斗志昂扬,但仍掩盖不了战争给滹沱河两岸人民带去的创伤。《荷花淀》中水生嫂不得不支持丈夫上前线打仗是忧郁的,《芦花荡》中老头子誓死不让我方受到敌人伤害的坚毅是忧郁的,《采蒲台》中对粮食的渴望也是忧郁的。作品虽有对不屈不挠的战地生活的歌颂,但更有对普通百姓想方设法于战争中生存下去的艰难境遇的痛惜,而这种痛惜也是作者在水边生活与生俱来的忧郁的转化。
文同水美。沈从文和孙犁二人作品之美是少见的。作者不停地刻画美景、美人、美事,三美结合起来使文章内外都蒸腾着美的气韵。沈从文的文章是水般空灵剔透、朦胧缥渺的美,这与他刻画的人物、描述的情节、设置的结尾有很大关系。沈从文笔下的女子都是内外美兼具、真心实意对待他人的女子,然而就是这样人人喜爱的女子却总受到命运无情地打击,而这些打击也使她们的善良纯美更加捉摸不定、惹人怜爱。《边城》中的女人们凭借简单执着的信仰生活,无论是翠翠还是其母亲乃至河边的娼妓,都对爱情有着执着的渴望,然而她们原本美好的爱情最终都以无果的悲剧而告终。悲剧的结果不仅使女人的美丽刻骨铭心,更为作品的美感画上了句号。而孙犁的文章却是水的另一种美:清新自然、明丽欢快。接触孙犁先生的文章能体会到一种“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4],这种东西能带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愉悦感。作品中淀水盈盈、苇荡摇曳,河景之美尽收之中。而所写水边之人更是具有美好的品质。妇女们勤劳持家、勇敢坚毅,男人们机智果断、无所畏惧,他们都对革命和生活有着坚定的积极心态,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向往之情。虽写战争,却无凄惨哀痛的血腥场面,而是水边人傍水而居、以水为乐的乡村之景。
二人作品都写水边生活,沈从文写的是原始生命,孙犁写的却是时代人性。前者之美以少数民族未经沾染之真为场域,特表现被风俗伦理侵蚀下的生命变数。后者将战争的残酷作为背景,以此来衬托大时代中的男女昂扬向上的生活情景、热情洋溢的意识觉醒,歌颂苦难面前人们的美好品质。
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是在“五四”之后的文学中,像沈从文、孙犁这样以浪漫的笔触集中描绘特定地域文化的作品并不多见,把水作为创作的中心框架和文化背景的更是凤毛麟角。正是作家对水至深的情义才能把“一定的人类文化和一定的地理环境”[6]融为一体,也正是这至深的情义造就了作品种种水样的人、水样的情以及水样的气质。我们透过水来研读他们的作品,能够看到共通共融的东西,而这些共通共融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探究之路。
[1]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M]//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42.
[2]孙犁.风云初记[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364.
[3]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4]孙犁.孙犁选集·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孙犁.孙犁选集·小说[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9.
[6]赵世育.文明的足下[J].读书,1985(7):2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