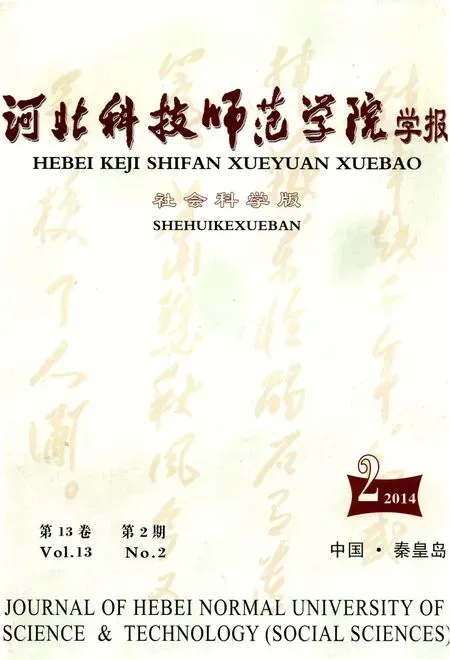程乃珊作品中的旗袍书写
母华敏,滕朝军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a.学报编辑部,b.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
一
说起上海的服饰,上海女性的衣着装扮,我们立刻就会想起上海旗袍,它是上海女人的象征,在旧时的上海滩风靡一时,在中国的服饰文化历史上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一时间旗袍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那股对旧上海的怀旧潮流中,旗袍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尤其是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花样年华》的热映,更是对旗袍的重新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家卫表示,他非常喜欢中国的旗袍,他认为旗袍最能够体现中国女性的美感[1]。影片拍摄之前,他特别请上海的老裁缝为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张曼玉定制了24套旗袍,旗袍通过张曼玉的风情演绎,为影片增色不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花样年华》里,旗袍不仅仅是一件可以让人增色的服装,还是一种意象,一种象征,具有了某种功能性:一方面,通过旗袍不同花色、不同款式的变换表现女主人公内心的孤寂、落寞及对爱情的向往、对美好的渴求;另一方面,旗袍的变换还暗示时间的流逝和推进故事的发展:“这部影片大胆地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对故事情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剪辑,如果没有旗袍的存在和变换,观众就很难明白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比如两人在西餐厅就餐的一个场景,苏丽珍刚开始穿的是一套乳白色点缀有百合花的旗袍,后来则换成了棕黑色带竖条纹的另外一件,从苏丽珍旗袍的变换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两人吃饭已不是一遭,旗袍的更换在这里就承担了暗示时间变化和推进情节发展的功能。”[2]王家卫就这样非常巧妙地利用旗袍款式和颜色的变化来展现苏丽珍微妙的心理活动,刻画人物形象,真正做到了人物合一,相辅相成。
二
程乃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小见惯了身边的女性一袭典雅端庄的旗袍,对旗袍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之感。尽管她长大成人之后,旗袍在她的生活中几近绝迹,但依然抹不去旗袍在她脑海中的深刻印象,因而在作品中,每每写到她所熟悉的上海女人,总少不了曾经与上海女人形影不离的旗袍。在《旗袍呤》中,她说道:“要说上海女人的经典形象,十有八九仍脱离不了斜襟上插着一块麻纱绢头,手执一把檀香扇的旗袍女士。近百年来,不论在战火的硝烟中,还是黑白颠倒的乱世,直到百花齐放的今天,上海女人就是这样,在历史板块的碰撞下,在传统与现代间、东方与西方间、约束与开放间、规范与出位间,一身承载着历史的沧桑和现代的亮点,婉转而行,迂回展步,那婀娜的旗袍身影,弥漫着浓郁的上海百年风情,成为注入西方元素的东方文化最感性的写照,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温柔的注释。”[3]78
得益于久沐西风欧雨,上海人的精神里有一种自尊自强、不甘人后的劲头,他们都知道上海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只要努力必定会有收获,所以他们都想获得社会的承认,都想在事业上做出一番令人刮目相看之事,表现在衣着服饰方面便是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非常注重仪表。上至达官贵妇,下至平头百姓,不论经济能力如何,不管社会地位高低,他们一定都要尽最大努力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世情练达也让他们深知这个社会“先敬罗衫后敬人”。犹记得一部反映老上海的影片《乌鸦与麻雀》,在电影中上海滩著名影星上官云珠饰演一位教师的太太,几乎是最底层的平头百姓,每天奔忙于生计,日子过得很是困窘,但即便如此,每每出门,那怕只是去市场买菜也务必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端庄大方的发型,略施粉黛的面庞,合体的旗袍,必备的高跟鞋。
旗袍在中国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是满族妇女的民族服饰,非常宽大,也没有婀娜多姿的腰身,只是一件随性的女性服饰而已。进入到上海之后,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服饰文化的浸染,上海的服装师傅非常富于创造力,他们在旗袍原有的基础上,揉合进很多西方时装的要素,如打裥、收腰、装垫肩等,把传统的中国服装打造成充满西方元素的国际服饰,自此,上海旗袍终于摆脱了中国传统服饰“包”的特点,从“包”到“放”,充分展现出女性的形体美和曲线美,由中国而进入世界的时装舞台,成为中国服装的时尚代表。
旗袍之所以能够在上海滩风生水起,跟上海的旗袍师傅们的努力密不可分。上海人在衣着服饰方面非常讲究,他们衣着光鲜,观念前卫,长时间内引领着中国服饰的潮流,成为万千瞩目的焦点。在解放前的旧上海,时装业成为旧上海最庞大的一个行业。据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成衣铺大约有2 000多家,裁缝有4万多人,约有20多万人从事服装行业,差不多占了当时上海人口的十分之一[4]。正因为如此,服装师傅成为上海滩最热门的职业。要成为一个服装师傅不容易,成为一个好的旗袍师傅更是不易:首先要拜师,当学徒,至少要给师傅打10年的下手,才能熬出头,自立门户,其间需要付出的辛苦与努力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而一旦成为一个名师傅,名利自然接踵而来,在解放前,有名师傅的主顾一般都是有钱人家的太太,这些太太们一般都有自己固定的、相熟的旗袍师傅,即使在解放后,旗袍近乎销声匿迹的时候,他们彼此也是“不离不弃”的,解放后,即使大街上流行的都是蓝灰色的列宁装、中山装,这些资产阶级的太太们在私底下还是喜欢穿旗袍,那怕只能在家里穿。难怪程乃珊会说:“上海女人和他们相熟的理发师、裁缝师的关系坚贞不移,稳定过‘明媒正娶’的老公,是一种一辈子的相随。”[3]80
今天,要让旗袍生活化难度非常大,因为当代女性要比旧上海的女性交际面更广泛,生活更丰富,出席各种场合穿着旗袍总是不大方便,有很多局限之处。在《旗袍吟》中,程乃珊充满感怀地说出了自己的希望:“旗袍已成经典,但凡经典,总万万不能随便改良。旗袍的切、嵌、滚、镶等工艺确实繁冗,但这正是其灵魂。旗袍要改良,只能从工艺剪裁上考虑引入先进手法,如立体裁衣,纸版作样,在款式上,是轻易动不得的。……上海旗袍只有80余年历史,还很年轻,它不应如日本的和服那样已游离生活,她应成上海一道流动的丽色,既可在社交场合闪现,也可在上海大街小巷迂回。”[3]82-84但愿上海旗袍能够如程乃珊所希望,随时随地地出现在上海女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三
在程乃珊的代表性作品《上海街情话》中,则讲述了一个和旗袍有关的爱情故事,在作品中,旗袍成为主人公爱情的信物与见证,借由旗袍这一意象,一段终老不变、一往情深的故事也便由此展开。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裁缝师傅小毛。小毛师傅是浦东人,老家专出裁缝,他9岁就开始跟着师傅学手艺。师傅在上海滩赫赫有名,他的当家绝活便是做旗袍腰身不靠打折裥,而全靠手指的软硬功夫在衣料上扯出来,师傅把这手绝活都传给了小毛师傅。小毛师傅不到20岁便已在静安寺路上那专做女洋装的“绿屋夫人”时装公司做当家师傅,在那个时候非常受顾客的欢迎。那时年纪小,对女人还谈不到男女之情,女人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工作对象而已。可是作为一个裁缝,他认为最好的衣服架子、最适合穿旗袍的身材便是可口可乐玻璃瓶的样子,而这些顾客里一个跟他同年叫阿英的女人就有这样的好身材。
小毛师傅永远都会记得第一次和阿英相见的情形:那天,阿英拿着一块普通的阴丹士林面料怯怯地来到公司里,要求做一件旗袍。老师傅平时做的都是平锦幛绒这样的上等面料,哪里会把阴丹士林面料放在眼里,于是便让小毛替阿英来做,这是小毛第一次为顾客裁制衣服。旗袍做好后,众人都赞不绝口,阿英也非常喜欢。阿英穿着这件旗袍先是去应聘永安公司的售货小姐,被录取,因为穿上旗袍后很有一种文艺气息,还被派去百货文具组卖文具,她的可口可乐瓶样的身材给她增添了万种风情,吸引了众多公子哥围着她转。从此后,阿英的每件旗袍都是小毛师傅做的。而小毛师傅也最乐意给阿英做旗袍。即使后来小毛师傅名气极盛之时,手下有五六个伙计,阿英的旗袍还仍旧由他亲自来做。
小毛心里暗暗地喜欢阿英,可他很羞涩,阿英又有男朋友,所以这份喜欢一直深埋在内心深处,在给阿英做旗袍时越发动用了心思。与阿英相处时,小毛师傅经常会想起那个充满了悲剧性的寓言故事:一个木匠发现一块上好的木头,便把它精雕细刻成一个美丽的女子,一个裁缝又为她做了一套非常漂亮的衣服,可是后来,来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为她唱情歌,美女便复活了,跟着小伙子走了。
上海解放前,阿英曾约小毛一起去香港,因为阿英与男朋友约好了一起在香港会合。小毛师傅因故没能成行,两人便就此分离了。
1957年,小毛师傅在友人的帮助之下来到香港,到香港后就四处打听阿英的下落,可是音讯全无。有一日,阿英忽然来访,原来她从女伴处听说新来了一个上海旗袍师傅,旗袍做得非常漂亮,她就猜测可能是小毛师傅,一看果然是故人,两人都非常欣喜于再次的重逢。当小毛师傅再次给阿英量衣时,真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一切都翻天覆地了,不变的是阿英永远1尺9寸的腰身。
交谈得知阿英来香港后仍在永安公司做事,她的飞机师男朋友再没听她讲过,来来往往仍是形单影只,小毛师傅也不好细问。很长时间之后,小毛师傅才知道,阿英初来香港时去找过那个男人,但那个男人已经结婚了,帮助岳父打理生意,两人私下来往,后来,被那个男人的太太发现,那个男人便叮嘱阿英说暂时不要来往,等以后再联系,谁知这一等就是20几年。最初还能偶而见到他的人,后来只等来他按时存入阿英银行户头的钱,再后来,连钱也没有了,多年之后,阿英才知道他们全家早已移民南美洲。阿英说,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是一直等他,因为从小妈妈就说男人不好逼的,越逼他,他就走得越快,所以阿英不逼他,只耐心地等他,但最终他还是没有回来。
多年来,小毛师傅一直都和阿英有来往,因为阿英的旗袍一直都是他做的。多年来,他也从来没有搬过家,因为小毛师傅一直记得自己对阿英的承诺:“有阿英在一日,我就一日不搬。”[5]244他担心万一自己搬家,阿英找不到自己可怎么办呢?
到了20世纪70年代,集团性世界名牌成衣大批量地涌入香港,小毛师傅的日子不好过了,因为穿旗袍的人越来越少了。按理说他也到了收手养老的时候了,可是他始终不舍,除了对裁剪旗袍的热爱之外,很重要的原因便是阿英:“阿英要时时做旗袍,如果自己不干了,那阿英怎么办?”[5]244心里想的念的都是这个女人。
说起养老之事,小毛师傅建议阿英把香港的房子卖掉回上海养老,阿英却反问他:你自己为啥不把这间铺子卖掉回上海养老。其实只有他内心里知道,自己之所以不肯离开,守着这间铺子,就是为了阿英。
在作品的结尾,阿英等了一辈子的那个男人死了,要在香港举办葬礼,阿英来找小毛师傅做一件旗袍去参加葬礼,并要求小毛师傅陪她一起去,小毛师傅问阿英:“你还为他戴孝?”阿英回答到:“讲出来你也不信,我是为我自己的痴心戴孝,人家早就不要你了,我还痴痴地等他回头,毕竟他死了,我还可以送他,赢得还是我,是吗。”[5]252
尽管内心替阿英不值,可是守候阿英已成了小毛师傅多年来的习惯,难得的,一大早,小毛师傅第一次在自己的门面房挂上了“店东有事,休息一日”的告示,陪阿英出席葬礼。走到街角看到一个花摊,有非常新艳、美丽的花朵,小毛师傅抱回一大束白玫瑰,这是送给阿英的。小毛师傅16岁时就认识阿英了,可直等到阿英70岁才第一次约会,还是相约去殡仪馆送别阿英的旧情人,但总归也是约会。
作品最后,小毛师傅和阿英两个人终于一起回到了上海,小毛师傅的坚持等来了回报,小毛师傅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他的坚持、他的痴心让读者感动,永远都不会忘记作品中小毛师傅的这段话,正是因为这段话,他才终于收获了自己迟来的爱情:“人活在世上,总该有个盼头,我也日日在盼着明日,明日或许会来笔大生意,或者利孝和夫人碰巧会走过我店铺来望一下,至少,你总归常常会来的,你今日不来,我就等明天,明天还有明天,比如你这次回上海去了两个礼拜,我就一个明天一个明天地等。”[5]252其实不但是爱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旅程何尝不是一段长期等待的旅程,等待指向未来,更指向希望。
结 语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程乃珊的确是当代上海文化书写的一个独特个体,由《旗袍呤》可以看出,程乃珊对上海的服饰文化尤其是上海女性最喜爱的旗袍情有独钟,颇有研究,对上海服饰文化尤其旗袍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特点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上海街情话》则演绎了上海、香港的双城爱情故事,故事的主角当然是她最为熟悉的上海普通小市民,尽管时间、空间在不停地游移变动,不变的却是细长绵远的情感,在悲欢离合的故事叙述中,上海旗袍、痴情男女、沪港双城、俗生众相都跃然纸上,让人感慨唏嘘。程乃珊就这样地用她善于思考的笔触,借助旗袍这一服饰意象,通过小毛师傅和阿英,记录了新旧时代交替下那些被历史抛出主流之外的上海小人物的生存挣扎和爱情追求。旗袍这一意象既是爱情的象征,又是爱情的见证,一袭旗袍串联起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张会军,朱梁,王丹.与王家卫谈《花样年华》[J].电影艺术,2001(1):43-46.
[2]母华敏,滕朝军,刘燕.此情可待成追忆——电影《花样年华》评析[J].电影评介,2008(9):34-35.
[3]程乃珊.上海 fashion[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4]刘业雄.旧上海时尚外壳:一千家当,八百身上[J].上海采风月刊,2006(5):88-91.
[5]程乃珊.上海探戈[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
[6]滕朝军,母华敏.程乃珊作品中的怀旧情结[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3(4):48-51.
[7]滕朝军,母华敏.海派文学背景下王安忆与张爱玲之比较[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