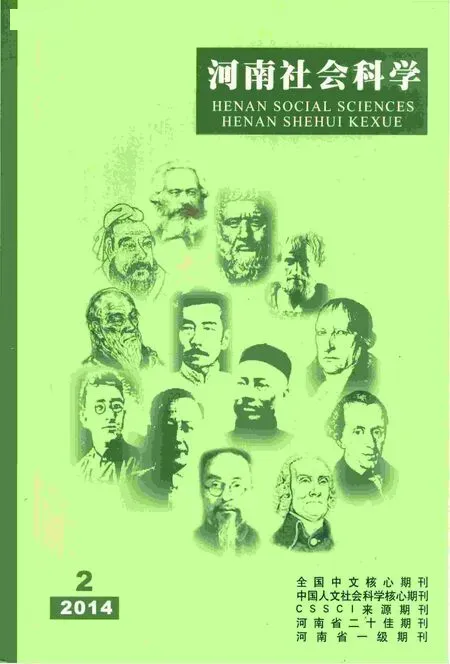论浙江精神及对中原人文精神构建的启示
李宜馨
(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58)
改革开放35年来,“浙江现象”在中国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浙江精神概念的提出以及内涵的阐发,标志着浙江精神的自我激励从自发的追求走上了理性的自觉,对于河南构建中原人文精神、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文明河南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浙江精神的提出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必将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浙江精神与浙江人民的历史生命同行,与浙江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未来创造相随,深深融汇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中,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浙江在改革开放30多年艰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闯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一个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活力都居于全国前列的省份,成为在全国闻名的“经济大省”“市场大省”和“民营经济大省”。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浙江非常重视对浙江精神的提炼和概括。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浙江人形成了以“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为内容的“四千精神”。后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为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又提出了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新四千精神”,这就是“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2000年,浙江精神被概括为“十六字精神”,即“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这十六字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人民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然而勇于创新的浙江人民意识到这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体现在浙江人身上的典型特征,必须与时俱进。于是2006年,习近平同志亲自将浙江精神界定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十二个字。如果说“十六字”精神体现的是浙江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时期的创业意识,那么“十二字”精神体现的则是浙江人民适应市场经济转型而形成的价值导向,标志着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从自发发展到自觉发展的转变。
我们可以看到,从“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到“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再到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以及“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浙江一直十分重视浙江精神的培育和提炼,因为这是进一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开创浙江未来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拓展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的价值诉求,对培育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浙江人意义重大。
二、浙江精神与浙江文化、中原文化的关系
浙江精神与浙江文化紧密相联。浙江山水秀美,人文荟萃。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说到浙江精神,就不得不提起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浙江精神时的那一段动情的描述:“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无论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诚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善举等都给浙江精神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精神得以凝练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1]“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的浙江文化精神,是浙江人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求真务实的精神、诚信和谐的精神、开放图强的精神在浙江人身上都有着深刻的展现。浙江人追求真理、遵循规律、崇尚科学;他们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他们重规则、守契约、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他们具有全球意识、世界胸襟,能够适应开放的世界全球化竞争的需要,具备积极参与全球化合作和竞争的勇气和胆略;他们勇于拼搏、奔竞不息;他们自豪而不自满,昂扬而不张扬,务实而不浮躁;他们心忧天下,服务大局,认清目标不动摇,抓住机遇不放松,坚持发展不停步。在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背后,始终跃动着、支撑着、推动着和引领着他(她)们的力量,正是浙江人民的精神。有着这种精神的人,有着这种精神的省份,有着这种精神的民族,其发展动力必然是无与伦比的,其成就也必然是无以替代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凡表现,应该说与这种精神的“核动力”有着深切的关系。
浙江精神与中原文化也有着极深的渊源。浙江精神和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具有一脉相承、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大宋南迁,都城由汴州而杭州,其文化血脉相通相连。“暖风熏得游人醉,错把杭州当汴州”,生动地展现了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具有的传承关系。可以说,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随着北方移民的南迁,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推动了浙江地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政治调整、经济更新、文化重建等各种要素相互整合,将浙江地区的社会整体发展提升到了全国的最高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造就了各个领域的精英。到了明、清两朝,以及民国时期,浙江已经成了全国无可争议的经济命脉和文化重镇。近现代以来,在中原文化发生文化断层、辉煌不再时,浙江精神、浙江文化因获得了文化新质而展现出了动人的风采。浙江精神所蕴含的以人为本、创新创业的理念,浙江精神所贯穿的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原则,浙江精神所具有的诚实守信、开放图强的品格,对于中原文化建设和中原人文精神的提炼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当然,浙江文化中也有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过于重视现实利益、内敛不够等局限性,与中原文化的“大智若愚”“道法自然”“中庸”“留余”等有着很大的区别,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努力加以超越。儒家经典《大学》里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一价值系统以“公而忘私”和“以义制利”为终极追求,而浙江文化却有着逐利的鲜明价值取向,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有着极大的一致性,使浙江文化与市场经济有着深刻的契合性,从长远来看,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这一行为的短视性需要正视。应当承认,浙江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重功利、讲实效的传统,但是功利主义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进一步提倡科学发展、公平正义和和谐有序。
总之,浙江精神是在浙江文化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而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传承关系,二者一脉相承。可以说,浙江精神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的因子。但是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却有着质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浙江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升级版”。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面对不同的时代和国际背景,浙江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孕育生成了许多新的特质。这是河南在构建中原人文精神的过程中需要认真考量的。
三、浙江精神对中原人文精神的启示
我从小生活在中原,对中原文化的厚重有着深刻的体会,于是灵动的浙江文化对我来说充满了新鲜感与神秘感。我一直认为,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河南人更是具有“平凡之中的伟大,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责任感”。在浙江,我发现浙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原文化的很多东西。如若不是两晋之际的永嘉之乱、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导致了政治中心南移,从北宋到南宋,从汴州到杭州,经过大宋南迁,使得“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2],是不会有如今浙江地区的繁华的。虽然远在数万年前,浙江大地就已经出现了“建德人”的足迹,河姆渡、良渚文化等更是进一步呈现出了文明的曙光,但是,夏、商、周三代以降,由于生产力水平、人口数量,以及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因素,浙江地区的开发总体上相对落后于北方黄河流域。然而究竟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原文化在大宋南迁之后落后于浙江文化呢?事实上,河南现代文化建设,当代河南人文精神的构建在今天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一直在思考,究竟用什么样的中原人文精神才能引领河南走向未来?到浙江求学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生成于历史“源头”的中原人文精神可以到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浙江精神中去汲取“活水”,从而使中原人文精神推陈出新并焕发出生机活力。为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为了中国梦的实现,只有让这“源头”与“活水”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够不断滋润我们的生命,进一步开拓我们的未来。
在我看来,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浙江精神与中原人文精神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巨大的区别或者质的不同:
(一)地理位置的差异。中原文化是一种内陆文明,和南宋以后风云际会的浙江文化相比较,中原文化就多了一分厚重,少了一分灵动,少了一些创新,少了一个巨大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国际化背景。浙江地处沿海,在外国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最先接触到外来先进事物,使得浙江文化的生成是在中西文化冲突、全球竞争与合作的背景下展开的。晚清以来,在欧风美雨的洗涤之下,浙江儿女中涌现出了颇多学贯中西、独步一时的大师级人物。
(二)浙江文化、浙江精神的生成与工商文明息息相关。中原文化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农抑商是我国几千年来的一项重要国策,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历代帝王莫不把农业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与此相反,商业发展则不受重视,有时还受到抑制。河南是粮食大省,有着深厚的农耕文明的背景,而浙江文化、浙江精神集中生动地体现了浙江人民在由传统农业文明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精神世界所发生的深刻裂变,它的孕育生成既有着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性,又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演变的走向。浙江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大胆突破了几千年被统治者奉为基本国策的重农抑商政策,形成了“讲究功利,注重工商”的传统,形成了浙江人“做大事要敢于冒大险”“赢得起更要输得起”的冒险精神和商业经营“不拘古法,不唯习惯”的创新精神。先秦时期的陶朱公范蠡是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早期典型代表。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主张“义利双行”“以利合义”,黄宗羲则坚持“工商皆本”。
(三)浙江文化更加开放,敢为天下先。中原地区,由于处在天子脚下,人们的思想更趋进于保守,很难跳出思想的牢笼,追求新的解放。历史上的浙江文化就是在不断吸收吴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大胆吸收异质文化的开放精神成为浙江文化很重要的特色。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浙江知识分子和其他区域的知识分子相比,往往不囿于以往的经验,不照搬别人的做法,在接受外来文化中也更勇敢、更少顾虑。在明清以来两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杭州人李之藻、杨廷筠和海宁人李善兰都成为吸收和传播西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直到今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改革开放使浙江人更注重创新和实践。中原文化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更注重“守成”的力量。就创新实践而言,浙江精神在体现优秀的历史传承的同时,注入了改革开放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因而充分显示了其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浙江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促使浙江精神有了新的飞跃。我们知道,社会历史是人的自觉活动过程及其结果,人在历史中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浙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这一真理得到了生动体现。浙江人民具有脱贫致富的创业热情、勇于探索的创新激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壮举。可以说,浙江精神既渊源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又根植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五)浙江文化、浙江精神具有“务实”的特点,而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因受北宋理学思想的影响,具有“务虚”的特点。可以说,浙江文化和浙江精神,体现了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性,其中内含的现代性价值对于所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区都具有文化启示意义。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等,都是其“务实”特点的体现。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明确表示“务实而不务虚”“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知府林启主张“讲求实学”。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精神作为引领浙江走向繁荣和富强的重要价值理念,在推进浙江经济腾飞和社会和谐发展方面显示出了巨大优势。浙江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源就在于浙江人有一种独特的精神理念。
总之,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多次的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具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文化特质,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和崇文厚德、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研究浙江文化和浙江精神,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与浙江文化、浙江精神是“接茬”的,而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与古老的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却有“断气”的一面,从而在一定层面上影响河南发展的“气象”。中原文化具有兼收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特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原文化、中原人文精神要与时俱进,就应该认真研究借鉴浙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文化基因,抽象传承,并使之内化为中原文化的特质和中原人文精神的元素。在中原人文精神构建的过程中,如何植入如下文化基因,是河南文化建设需要格外重视的:一是遵循规律、崇尚科学的求真精神。中原人文精神,要崇尚科学,遵循规律,追求真理。二是真抓实干、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浙江人具有稳固的思维模式,以现实为思维的基点,以讲求功利为其思维目标,以灵活多变为其思维特征。中原人文精神建设,也要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三是诚实立身、信誉兴业的诚信精神。诚信,就是要重规则、守契约、讲信用。中原人文精神要适应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着重强化诚信意识,视诚信为现代文明之基,不断加强现代诚信体系建设,使现代诚信意识深入人心。四是和美与共、和睦有序的和谐精神。中原人文精神要强调在现代竞争的基础上如何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努力打造自强而不失温和的文化因子,进一步加强平安河南建设。五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开放,就是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要有全球意识、世界胸襟。要通过航空港经济区的建设,不断提高河南的对外开放依存度,进一步树立开放意识和兼容胸怀,使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精神素质不断适应开放的世界和全球化竞争的需要,与时俱进,与世界俱进。六是励志奋进、奔竞不息的图强精神。图强,就是勇于拼搏、奔竞不息,就是奋发进取、走在前列。中原人文精神要按照“打造河南经济升级版”的要求,始终保持上进的势头,努力做到“先人一步”“高人一招”。只有这样,中原文化才能赢得新的发展境界,中原经济区建设才能获得强大精神动力。当前,认真学习并借鉴浙江精神和浙江文化,对于中原人文精神和中原文化的建设具有巨大意义,对于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河南的文明河南建设也有重要借鉴作用。
[1]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J].哲学研究,2006,(4):4—9.
[2]陈正祥.中国人文地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