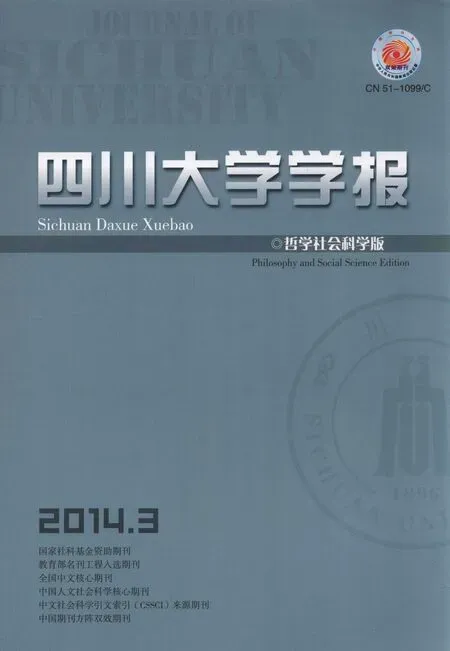“三一律”的时间整一与戏剧叙事
谭君强
(云南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一
在文艺作品中,对叙事时间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并制定出严格的规则以限制作家创作的,莫过于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了。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创作,都必须遵循事先规定的准则,这就是“三一律”。法国古典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布瓦洛在其《诗的艺术》中从理性的规范出发,以西班牙的戏剧创作为对照,阐明了戏剧创作的要求:“比利牛斯山那边诗匠能随随便便,/一天演完的戏里可以包括许多年:/在粗糙的戏曲里时常有剧中英雄/开场是黄口小儿终场是白发老翁。/但是我们,对理性要服从它的规范,/我们要求艺术地布置着剧情的发展;/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①布瓦洛:《诗的艺术》,任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2-33页。最后两行诗句,便是他对三一律的概括。作为一种创作规则,它在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创作的实践中得到了严格的遵守。1660年,法国古典主义的重要代表高乃依在其《论戏剧诗的用处与作用》中明确声称:“戏剧家绝对必须遵奉行动、地点、时间的三一律。”②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徐士瑚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41页。
实际上,“三一律”的肇兴并不由法国始,而源自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与评论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专注于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诠释、翻译与整理,这在当时的意大利是时兴的学术研究,在此过程中,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自然属于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从对亚里斯多德《诗学》的研究与诠释中,意大利学者开始构想此后影响深远的“三一律”。在对戏剧时间以及与之相伴的对戏剧地点的阐释中,意大利学者可以说是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
三一律相关意念的形成与发展始于意大利语言学家罗伯特里 (1516—1567)对亚里斯多德《诗学》的评注和意大利作家、文艺评论家吉拉底·琴提奥 (1504—1573)的《论喜剧和悲剧》(1554)中。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说过,与史诗相比,悲剧有一个限定的故事时间。由此他们确认,应该限制虚构的行动的时间——规定最大限度为12小时。此后有人将时间长度引申到24小时;也有人提出更为严格的限制,提议在3小时左右;还有人认为在例外的情况下,时间可长至2天。同时期的意大利文学评论家卡斯特尔韦特罗 (1505—1571)于其1570年出版的在戏剧史和评论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亚里斯多德〈诗学〉诠释》一书中,维护戏剧时间、地点和情节的一致性,他指出:“演出的时间与剧中行动的时间必须完全一致,……行动的地点必须固定不变,不仅限于一个城市,或一所房子,而且必须仅仅限于那个为一个人物所能看见的地方。”①参见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第42-43页。由此为“三一律”的规则打下了基础。此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创作所要求的“三一律”,是对以卡斯特尔韦特罗为代表的意大利学者在对亚里斯多德《诗学》阐释基础上所制定的规则的遵从与发展。以拉辛、高乃依、莫里哀为代表的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在其创作中都以“三一律”为圭臬,创作出在戏剧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剧作。
对“三一律”这一戏剧创作的严整规则,尤其是对其中的时间整一,当时的一些剧作家和学者并不赞成。早在1598年,法国学者代加里尔 (1575—1629)就对这一当时流行的正统观念表示反对,他说:“第一,古代戏剧家自己并不经常遵守这一时间法则;第二,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受他们的写作方式的约束’;第三,对时间整一性的遵守只能导致荒谬的地步;第四,当我们以共同接受的古典标准分析一出理想的悲剧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能使命运的变化局限于虚构的一天的时限内;第五,凡是遵守这一法则写出来的剧本,显然次于忽视这一法则而写出的剧本。”而西班牙戏剧家齐尔索·德·毛利纳 (1571—1648)则以形象的说法,指出其不便之处:“写一位谨小慎微的时髦绅士……爱上了举止端庄的小姐,向她大献殷勤,向她求爱,向她求婚——这一切行动却要发生在一天之内。你看怪不怪,他在要求她明天就成为他的妻子之后,还必须当天晚上就和她结婚。”但也有一些杰出作家对“三一律”表现出认同态度,弥尔顿1671年在《〈力士参孙〉序言》中就宣称:“整个戏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限制,根据古代的规则和卓越的范例,应在二十四小时的时限内。”②以上引文参见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第45-46、41页。
总之,关于三一律,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一直存在争论,毁誉不一。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一位崇尚思想与创作自由的作家,认同并遵守三一律。一个半世纪之后,伏尔泰仍然极力捍卫三一律。德国作家歌德则不赞同绝对服从三一律,他在谈到拜伦在生活中从不妥协,不顾什么法律,却服从于“三一律”时说道:“拜伦和一般人一样不大懂三整一律的根由。根由在便于理解 (fassliche),三整一律只有在便于理解时才是好的。如果三整一律妨碍理解,还是把它作为法律来服从,那就不可理解了。就连三整一律所自出的希腊人也不总是服从它的。”③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62页。对于三一律最激烈的反对者无疑是法国作家雨果。作为一位以浪漫主义开始其创作的作家,雨果明确反对古典主义及其法则“三一律”,在《〈克伦威尔〉序》中他指出,诗人只应该“从自然和真实以及既自然又真实的灵感中得到指点”,就此而言,希腊戏剧与法国戏剧是截然不同的:“希腊戏剧只服从对它适合的法则,而我们的戏剧则给自己加上一些和它本质毫不相干的清规戒律。前者是艺术的,后者是人工的。”因而,在他看来,三一律毫不足取。雨果之所以激烈地反对三一律,不纯粹是一种艺术上的考虑,也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密切相关。雨果自19世纪30年代转向自由主义,他认为艺术应该与时代合拍,在其1831年撰写的《〈欧那尼〉序》中他提出“新的人民应该有新的艺术”,而这一新的文学艺术,就是他所崇尚的浪漫主义,在他看来,“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并且艺术上的自由与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是相通的:“艺术创作上的自由和社会领域里的自由,是所有一切富于理性、思想正确的才智之士都应该同步亦趋的双重目的,是召集着今天这一代如此坚强有力、如此善于忍耐的青年人的两面旗帜。”④以上引文参见《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9、50、92-93页。由此可见,对三一律的严厉态度与雨果的思想和艺术观念一脉相承。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五幕戏剧《欧那尼》完全无视古典主义的规则,该剧在1830年2月的上演形成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激烈斗争,演出获得很大的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戏剧的胜利。
二
从三一律最初的构建开始,意大利以及后来的法国学者都将诠释的源头延伸至亚里斯多德,均认为其对三一律的概括源自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的论述。实际上,在三一律中唯一可以从中找到依据的只有行动即情节一律。亚里斯多德《诗学》中多有涉及这一问题的阐述,如他在谈到组成悲剧的六个成分即情节、性格、思想、语言、形象、歌曲时指出,“六个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他指出“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并认为情节必须“有条不紊”,“只能允许事件相继出现,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能由逆境转入顺境,或由顺境转入逆境,就算适当了”。他认为情节有简单的,有复杂的,因为情节所摹仿的行动有简单与复杂之分;但不论是简单的行动,还是复杂的行动,都必须“连续进行,整一不变”,“必须由情节的结构中产生出来,成为前事的必然的结果”。由于强调事件的完整与承前启后的序列,亚里斯多德最反对那种无法表现出因果联系与时间先后的情节的穿插:“在简单的情节与行动中,以‘穿插式’为最劣。所谓‘穿插式的情节’,指各穿插的承接见不出可然的或必然的联系。”①以上引文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1、23、26、32、31页。情节整一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已经毋庸置疑,因而雨果戏谑地将“三一律”称为“二一律”:“我们说‘二一律’而不说‘三一律’,是因为剧情或整体的一致是唯一正确而有根据的,很久以来就无庸再议了。”②雨果:《〈克伦威尔〉序》,《雨果论文学》,第48页。可以说,三一律中的行动或情节整一不过是对亚里斯多德相关论述的肯定与重复而已。
地点一致即三一律中涉及地点一律的问题,在亚里斯多德《诗学》中并未提及。古希腊戏剧的演出在巨大的露天剧场中进行,地点受到限制,不易变换,因此大部分古希腊悲剧地点并无变换,只有少部分戏剧例外。如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阿伽门农》、《奠酒人》、《报仇神》),其中第三部《报仇神》开场时,地点在得尔福。此前剧中人物俄瑞斯忒斯为父亲阿伽门农复仇,杀死了杀夫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受到报仇女神的追逐逃往雅典,因而下一场开始时,地点换成了雅典。以后,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成立了一个法庭来审判这一案件,地点又换成战神山法庭。歌德也注意到,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菲通》以及其他剧本里的地点都更换过。③参见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62页。因而亚里斯多德以史诗和悲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诗学》未提及地点整一的问题就不足怪了。而在意大利学者从对《诗学》的诠释中所归结出的三一律中,时间整一的问题是核心。三一律中的地点整一实际上是伴随着时间整一而来的。按照罗伯特里和琴提奥的理解,需要限制虚构行动的时间为12小时,并相信虚构行动的时间应该大致限制在与舞台演出同样长的时间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行动的地点就难于大幅度地变换,这样一来,虚构行动的地点就只能在一个地方,或如卡斯特尔韦特罗所言,必须限于“为一个人物所能看见的地方”。因此,“要求时间整一性就必然要求地点整一性。”④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第42页。
《诗学》中涉及时间问题的探讨并不多,主要的论述在于:“就长短而论,悲剧力图以太阳的一周为限,或者不起什么变化,史诗则不受时间的限制;这也是两者的差别,虽然悲剧原来也和史诗一样不受时间的限制。”在古希腊,悲剧供演出,史诗供朗诵,都需要在观众或听众面前进行。同时,古希腊悲剧都有12至15人组成的歌队,与悲剧演出相伴相随,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古希腊悲剧的演出或史诗的朗诵都需要确定一定的时间。不仅演出需要有时间的长度限制,故事情节也需要有长度。亚里斯多德在后面再次提到时间的长度时指出,“情节也须有长度 (以易于记忆者为限),…… (长度的限制一方面是由比赛与观剧的时间而决定的 [与艺术无关]——如果须比赛一百出悲剧,则每出悲剧比赛的时间应以漏壶来限制”。⑤引文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第17、26页。由此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所指的时间长度是“观剧的时间”、“比赛的时间”亦即“演出的时间”以及情节的时间三个方面。“太阳的一周”指的是白天,古代希腊的每次演出都是四联剧,由三部悲剧和一部萨提儿剧组成,此惯例直到欧里庇得斯中期仍旧盛行,⑥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这样的演出时间显然可以“以太阳的一周为限”。而史诗无论《伊里亚特》的一万五千余行,还是《奥德赛》的一万二千余行,本身都很长,无法在“太阳的一周”之内在听众面前朗诵完毕,但它可以在第二天以及之后继续朗诵,故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16世纪意大利学者将亚里斯多德“就长短而论,悲剧力图以太阳的一周为限,或者不起什么变化”的言说诠释为“演出的时间与剧中行动的时间必须完全一致”,罗伯特里和琴提奥据此将虚构行动的时间限定为12小时。以后这一时间的长短稍有变化,而最后达到较为一致的认同,即悲剧的“长度”指剧中行动的时间,其长短是12小时或24小时。这可以说是构成三一律基础的最重要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和误读。
这一误解或误读的原因在于混淆了不同的时间。在亚里斯多德所提及的三个方面的时间中,“观剧的时间”与“比赛的时间”可以等同,因为这是演出与观看演出、比赛与观看比赛,双方都须同时在场,无疑可以包括在同样的时间限制之内。而将“演出的时间”与“剧中行动的时间”亦即“虚构行动的时间”相同一,则显然是误解。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必然无法实现“逼真”,必然会在戏剧中出现许多让人难以相信的情境,如前述西班牙剧作家毛利纳所说的,一位时髦绅士须在一天内完成向一位举止端庄的小姐求爱、求婚,直至结婚。
包括史诗、戏剧在内的叙事作品所表现的时间不是单一的,可以基本区分为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前者是叙事作品中整个虚构故事所延续的时间,即故事中诸事件发生、发展、变化以致最后结局所耗费的时间;后者是叙事文本中叙述故事情节的时间,它在时间的长度上并不与前者相等同,并不相互平行。比如几行诗句可以叙说10年的故事,也可以只叙说顷刻之间的事。就如法国电影符号学家麦茨所说:“叙事是一个双重的时间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以及叙事的时间 (所指的时间与能指的时间)。这种双重性不仅使在叙事文中极为平常的所有的时间畸变成为可能 (主人公三年的生活在小说中用两句话或者在电影中‘反复’蒙太奇的几个镜头就可以概括等等),更为根本的是,它使我们将叙事的功能之一视为将一种时间构建为另一种时间。”①Christian Metz,Film Language:A Semiotics of Cinema,trans.Michael Taylo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8.《伊利亚特》所讲述的是延续大约10年时间的故事,但整个情节叙述的主线延续的时间约为50天;《奥德赛》的整个故事也延续了约10年时间,而情节叙述的主线所延续的时间约为41天。围绕这一时间主线,诸多前后发生的情境、事件等穿插其中,回旋往复。提出三一律时间整一的意大利学者显然混淆了这两类不同的时间。
实际上,在提出时间一律的意大利与法国学者那里,12或24小时的限制不过是戏剧舞台上所表演的事件的时间限制,它并不包括所有的故事时间,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不包括通过人物之口所讲述的故事中“追述”所涵盖的时间。就故事时间来说,不少遵循三一律的剧作家的作品远远超出了24小时的限制,只不过这些超出的时间是由剧中人物所讲述出来的,而不是由剧中相关人物在舞台上表演出来的。如莫里哀的五幕喜剧《达尔杜弗或者骗子》,这是一部按照三一律所完成的杰作,舞台上所表演的戏剧行动未超过一天,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故事发生的所有事件的时间均被限制在一天之内。中心人物达尔杜弗在第三幕第二场才出场,但是从第一幕第一场开始他就被谈论,这个在白尔奈耳太太眼里的正人君子,在女仆道丽娜看来却是:“一个不相识的人,居然在人家里发号施令;一个叫化子,来的时候,鞋也没有,全身的衣服就六个铜钱,居然忘记本来面目,摆出作主子的架势,样样事干预,也是的确让人看不下去”;“他在您心上是一位圣人,其实呀,他一举一动,全是做给人看的。”②《莫里哀喜剧六种》,李健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道丽娜的话,追述了达尔杜弗的所作所为,并从中得出“他一举一动,全是做给人看的”结论。很明显,道丽娜的观察以及达尔杜弗的行为,绝非是一时一日所进行和表现出来的。
在无三一律之类规则要求的中国古典戏剧中,可以直接在舞台表演中看出故事时间的变迁,如元代关汉卿的悲剧《窦娥冤》,在开头的“楔子”中,上场人物蔡婆叙说了窦秀才上年向她借了20两银子,如今本利该40两,窦秀才贫而无力还钱,蔡婆道:“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接着窦天章带着七岁的女儿端云上场,窦天章十分酸楚地说道:“这个那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般”;女儿端云则不胜悲伤道:“爹爹,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儿去也!”接下来的“第一折”,蔡婆上场道:“老身蔡婆婆。我一向搬在山阳县居住,尽也静办。自十三年前窦天章秀才留下端云孩儿与我做儿媳妇,改了他小名,唤做窦娥。”此后上场的窦娥已是20岁的媳妇了。到第四折,窦娥已冤死三年,窦天章上场自叙“自离了我那端云孩儿,可早十六年光景”,又叙说他“自到京师,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眼下则以“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随处审囚刷卷”,最后为窦娥雪冤。①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7-9、22-23页。剧中前后延续时间达16年之长,类似的情况在三一律限制下的戏剧中是不容许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三一律限制下的戏剧的故事情节没有超出一天以上的时间变化,只不过这样的时间变化不像《窦娥冤》是在舞台表演中直接展现出来,而是如《达尔杜弗或者骗子》那样通过人物的追述表现出来。歌德认为,三整一律只有在便于理解时才是好的,“法国诗人却力图极严格地遵守三整一律,但是违反了便于理解的原则,他们解决戏剧规律的困难,不是通过戏剧表演而是通过追述”。②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63页。歌德显然已经看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是以追述的方式来解决那些从时间上与三一律相悖的事件与情景的叙说,这样便可在严格遵循三一律的同时,叙说事件发展、变化的过程,不至于只将突兀的结果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三一律的奉行者看来,剧中人物的追述是不包含在戏剧表演所要求的一天时间之内的。这只能说是一种对叙事时间的“古典”的理解。在古今中外的叙事作品中,出现时间的倒错是常态,它主要以倒叙亦即“追述”或者预述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叙事文本中,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叙事与叙述层次。热奈特在谈到时间倒错时区分了第一叙事与第二叙事:“任何时间倒错与它插入其中、嫁接其上的叙事相比均构成一个时间上的第二叙事,在某种叙述结构中从属于第一叙事,……与其相比构成时间倒错的叙述时间层称作‘第一叙事’”;“与一个时间倒错相比,整个上下文可以被视为第一叙事”。由第一叙事与第二叙事分别形成不同的叙述层次,即第一叙述层与第二叙述层;由第一叙事直接承担的处于第一叙述层,而“由第一叙事的一个人物来承担”的,则处于第二叙述层。③引文见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5、24页。
戏剧通常是顺时而进的,总体上与时间顺序的布局相一致。但是,戏剧中同样可以出现错时,出现倒叙或预述。因而,无论是作为阅读的剧本还是舞台表演的脚本,或者在舞台上的直接表演,都与其他叙事文本一样,可以区分出第一叙事与第二叙事、第一叙述层与第二叙述层。在戏剧中,可以将剧中人物看作参与故事的人物叙述者,这样的叙述者分别在叙述与故事这两个层面上表现出来,并统一为一个人物。在剧本或演出中,顺时而进的叙事是第一叙事,构成第一叙述层,而当第一叙事或第一叙述层中的一个演员亦即“人物叙述者”在对话或自白中叙说并不发生于其当下在场的事件,而是叙说过往的事件时,就出现了倒叙或追述;而如果预先叙说其当下在场之后将发生的事件时,就是预述,两者都属于第二叙事,发生在第二叙述层。以追述而言,上述道丽娜叙说达尔杜弗的言行即为一例。这样,我们就知道,三一律所要求的时间整一,只限制在第一叙事与第一叙述层内,而并不顾及由人物口中所出现的第二叙述层中的第二叙事。就故事中的事件来说,无论是倒叙时间还是预述时间都应该包括在总的故事时间之内,因而从现代叙事理论的角度来说,三一律的时间整一是不完整的。
三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兴起都有其原因,三一律也不例外。从文学上说,它对当时那种散漫而不集中的戏剧能够起到收束的作用;从思想上说,它适应了强调集中的中央王权、尤其是法国中央王权的需要,因而得以在法国大行其道,成为戏剧创作的正统。就三一律本身来看,情节整一固不必说,它是三一律最重要的基础,是保证三一律得以确立的灵魂,而时间与地点整一可使戏剧显得简洁明快,剑指要害。莱辛指出: “行动整一律是古人的第一条规则;时间整一律和地点整一律只是它的延续,……他们诚心实意地承受这种限制,但以一种韧性,以一种理性来承受,九次当中,有七次以至更多的时候获得成功,而不是失败。他们承受这种限制是有原因的,是为了简化行动,慎重地从行动当中剔除一切多余的东西,使其保留最主要的成分。”①莱辛:《汉堡剧评》,张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41页。从古典主义戏剧、尤其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所取得的成绩就可看出这一点。以拉辛、高乃依、莫里哀为代表的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在戏剧史上留下了别具一格的戏剧作品,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这与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三一律是分不开的。
歌德对莫里哀给予了极高评价:“莫里哀是很伟大的,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喜剧作品跨到了悲剧界限边上,都写得很聪明,没有人有胆量去摹仿他。”歌德说自己“自幼就熟悉莫里哀,热爱他,并且毕生都在向他学习”,他还指出:“就我们近代的戏剧旨趣来说,我们如果想学习如何适应舞台,就应向莫里哀请教。”②引文见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88、124-125页。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三一律并非完全是束缚创作的紧身绳,它有合理之处,可以在严整的规则中表现出创造力。由此看来,意大利、法国文学家与学者对亚里斯多德《诗学》相关内容的诠释及其形成的三一律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创造性的误解与误读,而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式的要求下,也产生了文学史上富于意义的前所未有的新作品。尽管此后在戏剧创作中,无论是法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剧作家都不再以三一律为圭臬,但在一些有意无意遵循这一规则的创作,或与三一律的要求相仿的剧作中,仍然可以看到不少成功之作。这里,以缅甸19世纪著名作家吴邦雅的代表剧作—— 《卖水郎》为例,分析该剧与三一律的内在关系。
《卖水郎》约创作于1856年,题材取自于《罔偈摩拉本生》(Gangāmālā Jātaka)。这个本生故事说的是:古时波罗奈城有一雇工,白天辛勤工作,晚上虔诚持戒,积下功德无量,死后投胎王室,长大为王。波罗奈城北有一个卖水郎,靠辛勤卖水为生,后与城南一卖水女结为夫妻。为了观看国王加冕盛典,卖水郎奔赴城北取钱。国王见卖水郎在烈日下奔忙,劝他不要为几个小钱奔命,并许诺给他数千数万倍于其所藏的钱,但卖水郎始终不愿意舍弃自己的劳动所得。国王深为感动,最后赐他以王位,分享一国财富。后来,他与国王同游王家花园,忽然萌发杀王之心,以独霸王业,但最终善良之心抑制了邪恶之念,向国王如实坦言后,国王决定逊位给卖水郎,但这时卖水郎已意识到私欲之恶,毅然出家为僧。戏剧《卖水郎》与《罔偈摩拉本生》故事大同小异:一卖水郎路遇一卖水女,共同的生活和命运使二人一见而相爱。卖水女请求卖水郎将他的全部积蓄——藏在城北城墙中的四个铜板取回,以与她的全部财富——同样是四个铜板合在一起,以显示他们爱情的严肃和真诚。卖水郎随即在烈日之下奔赴城北取钱,后面的情节几乎与《罔偈摩拉本生》中的情节完全相同。
《卖水郎》共分七幕,具有整一的情节、完备的形式以及充分的戏剧冲突,结构紧凑,情节发展环环相扣。第一幕“城外”,三个主要戏剧人物出场。刚从国外大学归来尚未登上王位的王子——未来的国王首先入场,坐到舞台一角。随后卖水郎与卖水女先后上场,分别向观众展示了自己贫穷的生活,坐在一旁的未来国王目睹了这一切。第二幕“觐见室”,只作为过场,国王去世,王子被加冕为王。第三幕仍为“城外”,卖水郎与卖水女相遇,相互表示爱情,卖水女要求卖水郎取回所藏的四个铜板,以作为爱情的明证。第四幕回到“觐见室”,国王令人召来在烈日下奔跑的卖水郎,许以重金,却未能改变卖水郎的初衷;从中看到卖水郎好品性的国王许他以权力和王国的一半,使之成为王储。第五幕与第六幕均为“觐见室”,分别为卖水女被迎入王宫作为公主,卖水郎-王储的四个铜板被取回。第七幕为王家“林地”,地位发生巨大变化的卖水郎-王储产生了邪念:“两个人统治一个国家是那么复杂,那么令人不惬意。”因而,当他陪同国王到王家园林游玩,国王因一天劳累而枕在他的腿上睡着了时,他拔出剑来,想杀死国王,但其内心的善仍在发挥着作用,抽出的剑又插了回去,如此反复数次,最终善战胜了恶。他请求离开王宫,退隐林中,卖水女请求与之同行。
《卖水郎》的创作形式与三一律的要求非常相符。剧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一天:第一幕是清早,太阳尚未出山,最后一幕是同一天的傍晚。地点分别有三处:城外、觐见室、王家林地都在同一个城中,剧情则由一条主要的情节线索贯穿始终。尽管尚无证据足可显示19世纪的缅甸戏剧家吴邦雅了解欧洲古典主义戏剧的创作规则三一律,但这并不重要,引人注目的是这两个不同时期、东西方相距遥远的国家的戏剧创作出现了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三一律对于戏剧创作并非仅仅是束缚。《卖水郎》形象地显示出人性的贪婪、野心与善良的尖锐冲突,尤其是最后一幕中,卖水郎大段内心自白表现了其内心善与恶的搏斗,使戏剧发展达到了高潮。这段充满矛盾的心理自白可以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中女主人公美狄亚的一段自白相比:为报复丈夫伊阿宋的背弃,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美狄亚准备亲手杀死三个年幼的孩子,以作为对丈夫的惩罚。但是,眼见一无所知含笑望着自己的孩子们,美狄亚动摇了,几次想动手而不忍动手,一段充满矛盾的自白,形象地展示出她复杂而又痛苦的心理活动。而卖水郎-王储的自白也具有同样的效果。缅甸知名学者貌丁昂认为,《卖水郎》是缅甸戏剧中最富艺术性的作品,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卖水郎》的情节整一是一大特点,它保证了全剧前后衔接,张弛有度,合理发展。而时间的高度集中和地点的相对整一又可使它抛开枝节,凸显出最核心的主干,干净利落,形象鲜明,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卖水郎》的成功及其与三一律的暗合,说明这一在文学史上起过突出作用的艺术形式是不乏生命力的。实际上,像三一律这样毁誉交加的形式,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地利用它,以化腐朽为神奇。如前所述,保证三一律成功的基础在于情节整一。而在任何叙事作品中,这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故事中属于所叙或被叙述的部分由事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因素构成,其中的核心部分是事件。叙述的内容可以多种多样,但在叙事文本中,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内容,都离不开事件。单个的事件如何结合成为序列并进而贯穿始终呢?结合的原则,或者说叙述的一般性是与那些制约人类思想与行为的一般原则相一致的。这些规则包括逻辑的原则与常规的限定。逻辑原则是一切有意义的行动及事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常规限定则与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文化息息相关,可以看作是由历史与文化所决定的群体规则在具体情况下的说明与解释。用法国学者布雷蒙的话来说,这些特殊的事件系列“具有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文学体裁、一定的作者风格、甚或仅仅这个叙事作品本身所规定的特性;因此,这些规律除了反映那些逻辑制约以外,还反映这些特殊叙事领域本身具有的约束”。①布雷蒙:《叙述可能之逻辑》,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53页。除逻辑原则与常规限定之外,在叙事文本中,具体的结合原则主要体现为时间顺序的原则与因果关系的原则。这些相应的规则,在三一律中、尤其是在情节整一中都在严格的限定中被遵循,甚至被放大。与此同时,它又在严格的限定中,表现出与特定文化、特定时代的相适,因而三一律在展现出僵化的一面的同时,也显现出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相适的具有活力的一面,从而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叙事作品中,仍可找到闪现出三一律的影子、对三一律合理吸收与运用的成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