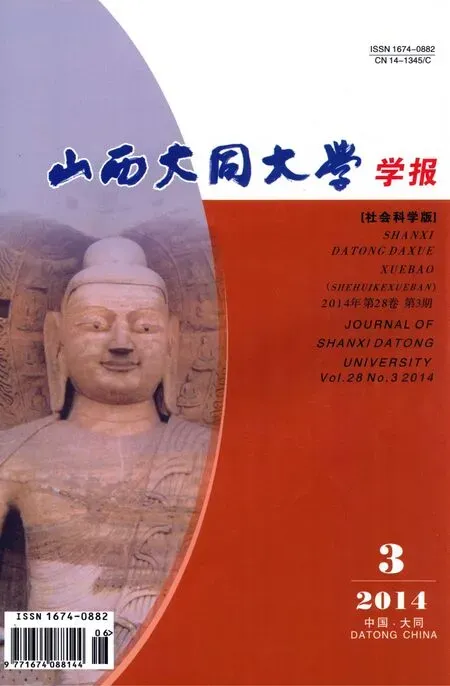战后香港方言文学运动考论
侯桂新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战后香港方言文学运动考论
侯桂新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1947至1949年,南来作家于香港开展了以大众化为目标的方言文学运动,包括理论论争和创作实践。在理论上,作家们讨论了方言文学的写作目的、读者对象与写作方式,提倡为了普及而写、为了工农而写以及完全用方言写作。在创作上,出现了一批用广州话、潮州话和客家话写作的各类文体的作品,但它们在艺术上并不成功。方言文学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既由于作家们对大众化的理解不够清晰,也和他们过于重视读者的阶级性而忽视了香港本土现实有关。
香港;方言文学运动;大众化;阶级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众多内地作家南下香港,其中大部分 (尤其是左翼作家)在港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引发过几次大的文学论争。这当中最主要的有战前的“民族形式”讨论和战后的“方言文学”论争(这里所说的“战前”、“战后”是针对香港本地而言,分别指1941年底香港沦陷之前和1945年8月香港“光复”之后)。这两次论争至今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尤其是后者,现有研究并不充分,是以本文对其进行考论,梳理和探究与其有关的几个核心问题。
一、背景与主张
战后香港的“方言文学”论争,不限于理论思辨,同时包括文学创作实践,以及由相关组织机构开展的文艺活动,因此一般被统称为“方言文学运动”。论者一般将运动开始的时间推回到1947年,事实上,这场运动中被普遍讨论的采用方言土语的话题,在战前“民族形式”讨论过程中早已成为重点话题之一。例如,齐同就曾提出:“在提高大众文化水平或利用旧形式的时候,是要把方言看做第一重要的。”[1]黄药眠讨论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也认为“必须从方言土语中去吸取新的字汇”,他甚至设想“也不妨以纯粹的土语来写成文学,专供本地的人阅读”。[2]这一看法,已经和后来“方言文学”论争过程中的主流观点并无二致了。黄绳则专门讨论过“民族形式”和语言的关系问题,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还在采用大众的语言”,“我们主张向大众学习语言,主张批判地运用方言土语,使作品获得一种地方色彩,使民族特色从地方色彩里表现出来。”[3]过了八九年之后,黄绳又积极加入“方言文学”的讨论,虽然观点有所改变,但也说明他对此问题的关注持续有年,而这两次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脉相承。
关于“方言文学运动”兴起的背景,茅盾当年曾经总结是由于受到了三个“有力的刺激”:第一个是“无论就内容或就形式而言,都可以说是向大众化的路上跨进了大大的一步”的“解放区文学作品的陆续出版”;第二个是“香港的市民作家的‘书仔’”远比南来作家作品畅销的事实;第三个“最强有力的刺激”则来自“时局的开展”,为了“有效地配合人民的胜利进军而发挥文艺的威力”,就必须缩短“作品的语言和人民的口语其间的距离”,而这,“最低限度得用他们的口语——方言。”[4](P16)这一总结比较全面,不过为了更准确地理解,需要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香港的传播及影响结合起来考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等著作,因产生于香港沦陷时期,未能在香港同步传播。香港“光复”后,借助中共的宣传组织力量,于1947年前后在香港集中刊行。《讲话》将文艺队伍比作党的另一支军队,要配合拿枪的军队,为此强调普及、大众化、为工农兵写作,与此相关的则是要求作家积极改造思想意识,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可见,文艺的普及和大众化问题,在这时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性。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在香港的文艺工作者开始了自我改造的历程。因此,茅盾提到的三个刺激,事实上背后无不具有政治意味的严重性:第一个刺激来自解放区文艺作品在香港的风行,这直接证明了实践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解放区文艺不仅革命性强,而且有利于普及,因而在这些方面已经“落后”的南来作家只有奋起直追,而学习、追赶的途径和突破口,很快就被确定为方言土语的运用。第二个刺激来自香港市民作家作品的畅销,而这些畅销作者在政治上和南来的左翼作家并非同路人,因此南来作家面临和他们争夺读者的任务。要体现左翼作家作品在掌握群众、获得“人民”支持方面的优越性,就需要将作品普及到香港大众中去,在和市民作家的比拼中占得上风。第三个刺激更是由来已久。长久以来,作家们一直公认,文艺运动总是大大落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而到了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革命形势”日新月异,双方的距离越来越大,更令作家有落伍的紧迫感,以至有人疾呼“不能仅仅惊异于伟大新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追形势,追上去!”[5]这几重因素叠加起来,使得“方言文学”一旦被提及,众人很快省悟到其中具有的丰富内涵,因而纷纷起而辩论,并发展为一场运动。
论争的源头在华嘉担任文艺版编辑的《正报》,而华嘉更是参与和引导论争的第一员大将。1947年10月11日,林洛在《正报》第57期发表了一篇《普及工作的几点意见》,最后一段谈及“地方化”问题,明确反对“方言文学”,蓝玲随之响应。华嘉则针锋相对,主张纯方言写作。双方论争了三个月,至1948年1月1日,《正报》第69、70期合刊发表冯乃超、邵荃麟执笔的《方言问题论争总结》,对论争中涉及到的各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解答。这以后,相关讨论并未停止,事实上一直持续到1949年。与此同时,一批来自广东和福建等省方言区的作家(同时也是论争的参与者),纷纷尝试方言写作,用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来写诗歌、小说、杂文、短论、歌词,或传统的民间形式的文艺如说书、龙舟等。在这过程中,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了专门的“广东方言文艺研究组”(1948年夏天改为“方言文学研究会”,由在达德学院任教的钟敬文任会长)来推动方言文学的创作、研究、出版等工作,影响所及,连达德学院的学生亦成立了各类方言文学研究会。报刊方面,1949年3月9日开始,《大公报》开辟《方言文学》双周刊,《华商报·茶亭》亦于3月13日及6月3日出了两期“方言文学专号”。一时,“方言文学运动”颇有如火如荼之势,俨然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最具规模及影响的文学运动。
“方言文学”初期论争的核心问题是:需不需要方言文学?为了什么目的、什么对象,在哪一种意义上需要方言文学?其他问题都由此派生出来。反对方言写作的林洛说:“我们发现一种偏向,把方言当作时髦的货色,不经选择便搬来应用,因此搬了许多可口而坏胃的东西,许多内容有毒而不经淘汰的东西。而且,写出许多广东方言来,和现在应用的文字完全脱离,连读了几十年书的人,也摸索不通,仅能认字的人就更不必说了。”[6]蓝玲也有类似意见。应该说,他们两位都是从对创作实践的批评出发,认为用方言写作更不容易普及,而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势下,所谓“普及”主要成了一种政治需要。对此,华嘉的批评文章《论普及的方言文艺二三问题》一开头就引用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文中所提出的“改造自己的意识”,以及毛泽东《讲话》对“大众化”的论述,然后针对林洛、蓝玲文章所提出的部分方言字难认的问题,指出方言文艺作品原是为了那些读书不多“甚至根本没有读过书的工农大众而写的”。[7](P5)针对蓝玲以浅近文字夹杂方言去写的主张,华嘉同样引用周扬的说法,认为不仅是对话要采用民间口语,在做叙述描写时也该运用群众语言,也就是整个作品完全用方言来写。而且,“方言文艺作品不能满足于写在纸上或印在刊物上,一定要以广大的工农大众为对象,拿到他们中间去朗诵和表演,拿到他们中间去考验,根据工农大众的意见去求得进步,和求得完美。”[7](P10)联系到华嘉其他的几篇论文,可以看出,他在讨论方言文学时,始终紧紧抓住《讲话》的精神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要求,以此来衡量方言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服务对象:广东的工农大众,或主要是农民阶级;作品形式:完全采用方言,如用杂糅文体写作,就是否定方言文艺,写出来的仍然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殊文体”;[7](P13)写作态度:要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彻底改造,彻底解决创作上的苦闷和矛盾,而这“只有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把自己变成工农大众的一分子”。
华嘉的讨论可能有过于政治化、口号化的地方,不过他的基本观点——为了普及而写、为了工农而写、完全用方言写作——为后来许多论者所认同,成为论争中的主流观点。冯乃超和邵荃麟在总结文章中提出,对于一般能懂普通话的读者,用普通话夹一些方言来写也是需要的,不过以工农群众为对象来说,“仍以方言文学为主”。[8]这一总结性文章很快得到两位重量级作家郭沫若和茅盾的明确支持。郭沫若表示自己对“方言文学”“举起双手来赞成无条件的支持”,[9]茅盾则强调必须在“大众化”的命题下去处理方言问题,他认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不妨视为‘北中国的方言文学’”,指出“在目前,文学大众化的道路 (就大众化问题之形式方面而言)恐怕也只有通过方言这一条路……在这里,问题的本质,实在是大众化。大众化从没有人反对,而对方言文学则竟有人怀疑,这岂不是知有二五而不知有一十么?”[4](P17)
也有人比较细致地阐述方言的文学效果,以作为推动运动的根据。钟敬文的长篇论文从历史上的方言文学谈起,再联系现实看方言文学对眼前政治要求的适应,接下来专门论述从艺术表现效果来看方言文学的优越性。他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用以创作的语言,必须跟他有着深切的关系。……我们懂得最深微,用起来最灵便的,往往是那些从小学来的乡土的语言,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有无限关联的语言,即学者们所谓‘母舌’(Mother tongue)。这种语言,一般地说,是丰富的,有活气的,有情晕的。它是带着生活的体温的语言。它是更适宜于创造艺术的语言。”而另一方面,“作品所用的语言,和所表现的事物或心理等(即作品的内容)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更好地表现民众的“劳动、受难、斗争的场景”和“苦恼、愤怒、决心、同情……等心理”,无论使用“跟民众生活远离的知识分子欧化的语言”还是“普通的国语”都难以胜任,此时唯有“各地民众的方言”才是“最有效力的手段”。[10](P59-60)也就是说,无论是就方言写作者对语言的熟悉程度而言,还是就主要写作内容而言,都要求使用方言。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无论是由于政治的理由还是艺术本身的理由,都需要用方言去写。
当然,既称为论争,自然会有不同观点。例如有的论者就认为应当取消“方言文学”这一称谓,因为既称“方言”,自有相对的一种“正言”在,然而“白话文”和“国语”都不过是北方方言,并不足以成为“正言”。总之,广州话和别的地方话一样,或者都是“方言”,或者都是“白话”,或者都是“国语”,不能以某一地方为本位,生出“方”与“外”来。作者提议,在“国语”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要自轻,——自称为‘方言文艺’,不要自偏——以为方言文艺是地方化的东西,这些观念,赶快抛弃”。[11]不过这样的声音,并未得到什么响应。
二、实践及影响
“方言文学”是一个充满实践性的课题,伴随着理论方面的论争,部分作者还采用新旧形式,尝试各种文体的写作。华嘉、楼栖、丹木、薛汕、李门、符公望、黄雨、芦荻、黄谷柳、陈残云、司马文森等纷纷加入这一阵营,结集出版的作品主要有楼栖的客家方言长诗《鸳鸯子》、丹木的潮州话叙事诗《暹罗救济米》、薛汕的潮州话中篇小说《和尚舍》。鼓吹最力的华嘉更是尝试用方言写作各类文体,例如,他有一篇短论《写乜嘢好呢?》专谈服务于既定的读者对象,可以用广州话来写各类文章:“譬如讲,我地可以用广州话写讲时事嘅文章,甚至讲道理嘅文章;亦可以用广州话写故事,写小说,写戏剧,写诗歌。乜都得。”[7](P62)其实,这一段话本身作为粤语写作而言就不够地道,当中夹杂了不少普通话词汇。再如华嘉有一首歌词《人民救星毛泽东》,第一段是:“太阳红,红冬冬,/人民救星毛泽东,/你来左,耕田佬,/家家户户有米舂。”后面三段,前两句不变,第三句分别把“耕田佬”替换成“乡下婆”、“打工仔”和“好工农”,第四句则分别改为“个个簪花又戴红”、“唔使再食西北风”、“个个都系国家主人公”。[7](P93-94)这样的歌词非常简单,通篇不过出现了两三个粤语词汇,而其主题内容则和解放区文艺非常相似。不过,篇幅较长的作品,因为采用新字记音等问题,就连一般的目标方言区读者都读不顺畅,而内容方面也令评论者失望。这些创作方面的同仁们,新的作品出来后,往往都不满意,因而或自我检讨,或坦率批评,不过在创作方面始终没有拿出杰作来。
例如,薛汕的《和尚舍》发表后,丹木撰写批评文章,在艺术方面基本持否定意见。在他看来,“正因为作者写惯了白话文,对于潮州大众语言的不纯熟,在全文的叙述和描写上,词汇表现得非常贫乏,而且也写得有点生硬,令人有点读不下去,……”不止如此,“在《和尚舍》的许多对话中,还是存在着许多白话文的翻译,未能很恰切地把握住大众的语腔,这一点,也就是因为作者平时太少接触潮州的大众生活的缘故”。[12]司马文森也坦承对其感到失望,并回忆自己两年前写的《阻街的人》,“用白话作说明,对白用广东方言,结果惨败。惨败原因之一,是我对广东语言的缺乏认识,在运用上过于酸硬,有时甚至于像翻译小说一样从这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13]楼栖对《鸳鸯子》的自我批评同样指向语言,他说作品一改再改仍然失败,是由于“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我现在却分明是一个知识分子。要用农村的语言来写诗,只好向记忆里去搜寻”。[14]华嘉也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加以反省,认为自己感觉到的“痛苦”原因有二:在生活实践方面,“自己离开农村太久,很多实际情况都不熟不懂,颇有‘闭门造车’的客里空倾向”;在读者对象方面,这些作品“‘流年不利’,目前还不能到农民读者手里,得不到他们的批评和意见”。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华嘉认为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到农村去,不过在去农村之前,也有补救的办法,例如在香港找一些来自农村的人去“听他们的谈话”,另外还可以对“一切进步的报章杂志上刊载的农村通讯”加以收集研究,在这样的过程中尽量多人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7](P34-35)
纯方言写作没有产生公认的佳作,后世论者对此曾有如下解释:“这次方言文学运动,看来不从香港文学本位考虑问题,而以华南文学为本位。……这便形成了好些内在的矛盾。文艺工作者与其工作对象不能像北方那样有直接的接触与交流;而意想中的接受者(华南工农群众)与实际的接受者(香港读者,包括一些工友)也有一定距离。”[15]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这些作品并没有到达工农大众手中,现实中的主要读者还是香港的市民群体,他们总体上并不喜欢看这些写农村农民的故事。还有人发现,“事实证明,方言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比蓝玲主张用的‘揉杂语言’来创作,相差甚远”。[16]例如同一个作者黄谷柳,他以清一色广州话写的《寡妇夜话》早已湮没无闻,而以“揉杂语言”写出的《虾球传》出版后一纸风行,令他声名大振,在文学史上留名。从实际结果看来,尽管受到本地作家和解放区作家刺激后雄心勃勃,然而“方言文学”的实践者们在创作方面无疑打了败仗。
“方言文学”运动展开不久,参与者和支持者曾抱以极大期望。1948年初,茅盾曾称赞“在去年的几次文艺论争中,(那是发生在国内的),这最后的一次成绩最好”。[4](P16)钟敬文则在运动刚刚开展半年之际就试图为它在五四新文学史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史上谋得一个崇高位置,断言它是一次“新的文学革命”,“是我们新文艺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人民文化演进上的一件大事。”“从人民的观点看起来,它比起过去世界文学上的几次新语文运动,(例如文艺复兴期意大利等的语文运动,或浪漫主义时期欧洲各国的语文运动,乃至日本维新时期和我国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等,)是具有更重大的意义的”。[10](P56、58)如今有了后见之明,我们当然会非常惊讶,当时的论者何以如此乐观——是受到整个“革命形势”的巨大鼓舞所致?客观地看,整个“方言文学”运动中,论争的部分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包括方言写作与大众化的关系、与普通话发展及统一的关系,以及方言对增强艺术表现效果的功用,等等。但因为创作方面没有贡献出令人信服的成果,因而这些理论成就也是打了折扣的。
就在“方言文学”运动将要掀起新的一个小高潮时,由于国共内战形势的急剧变化,南来作家多数纷纷北上进入解放区,这一运动无形中也就停了下来,而且出人意料,参与者后来大都对此保持缄默。郑树森认为,这是由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广东的地方主义加以批判和打压,“如果提倡方言文学,肯定地方的色彩,便明显与政策相违。”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京召开,茅盾负责报告整个国统区革命文艺的发展,然而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距离很近的声势浩大的“方言文学”运动只有简单的一两句话。据说曾有人专门起草了一节关于“方言文学”运动的报告,但未被采用。卢玮銮据此分析,“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不能再强调地域性文艺,我相信这批南方文化人所推动的方言文学,与五十年代初期的政策不尽相符”。[17]
除了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可以从现代语言与民族主义发展的关系上去看这一问题。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方言和普通话的矛盾纠结关系始终存在。概括而言,普通话有助于形成民族认同,“‘国语’运动在语言上为现代统一国家提供依据和认同的资源,而方言及其与地方认同的内在关系,则有可能是进行国家动员的障碍。”[18]国共内战时期,提倡“方言文学”运动有利于方言区域的地方动员、阶级动员 (运动的参与者一再强调以工农大众为对象),其时因共产党属于在野党,地方动员有利于打破国民党的全国统治,阶级动员更是直接针对国民党政权,因而这一文学运动和共产党的政治取向极相吻合。但当大局已定,共产党夺取政权,成为全国性的统治当局,这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广泛的民族认同,“统一”成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这时再大力提倡“方言文学”,就背离了这一取向,因此对其进行冷处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大众化迷思
“方言文学”运动以文艺“大众化”为目标,但这一预期目标并未实现。这令我们有必要思考文艺“大众化”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并考虑把香港作为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所在地的复杂情形。
自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大众化”方面得到肯定的,基本上只有20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解放区文艺。也就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尽管多次发起过“大众化”运动,此目标却只在极小范围内实现了。更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停留在理论倡导上,而在这方面也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首先是“大众”一词的含义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五四时代,陈独秀、周作人等人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大众”是指一般平民。后来左翼文学一直宣传的“大众”,则越来越和某些特定的中下阶层联系在一起,到了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更是被明确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可见,从五四至四十年代,“大众”的概念由普通国民逐渐向某些阶层的民众转变。“大众”的所指发生了变化,“大众化”的对象和方式自然也要随之而变。
其次,文学“大众化”的含义和标准,也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从内容到形式,不一而足。当茅盾指出“新文学之未能大众化,是一个事实”,[19]他是指由于新文学形式欧化,无法深入各阶层民众,读者范围不够广泛。可是,这样理解“大众化”,那么中国的传统章回小说和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早已实现“大众化”了,在香港,被南来作家贬为“黄色文艺”的通俗小说在“大众化”方面也是成绩斐然,然而它们都是新文学的敌人。当向林冰等“旧瓶装新酒”论者认定五四新文化在内容上是“大众化”的,而形式则为“不通俗化”,旧文化在内容上“不大众化”,形式则能做到“通俗化”,[20]“大众化”和“通俗化”截然分途:前者是指内容方面具有“革命性”,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后者则专指形式方面易为普通百姓所接受。这样,“大众化”就具有了意识形态属性。而当许多“方言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一再强调方言写作不仅是个形式问题,也包括内容方面的要求时,他们对“大众化”的期望更高了:不仅内容上要是“革命”的,形式上也应当是易于在工农群众中普及的。要制作出符合这样双重要求的文学作品,其难度可想而知。何况,就算有这样的作品,对于工农大众中的文盲半文盲——“方言文学”的主要服务对象——来说,也不可能一篇一篇拿去读给他们听,或在他们面前表演,在这方面,华嘉的设想不无幻想色彩。
再次,就算作家们明白他们支持的“大众化”的所指,他们作品的意想读者也不一定能和实际读者相重合。鲁迅等五四作家试图启蒙民众,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祥林嫂、阿Q们既看不到,也不可能看懂这些以他们为主人公的作品。所以结果是,启蒙文学家的作品在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中流传,却很难到达启蒙的对象。抗战后,因为客观现实的改变,众多作家不得不离开城市,进入民间,和下层民众直接接触,在一定程度上“打成一片”,但多数作家还是生活在大后方城市,对工农大众的生活是陌生和隔绝的,因而一般仍无法面向工农大众而写作。
在这方面,香港尤其具有劣势。南来作家们不仅远离了内地的民间,甚至远离了战争这一当时最具时代性的现实,让他们来创造写工农兵、为工农兵而写的文学作品,难度尤大于内地作家。倘若他们发现此路难行后,能够对香港本土现实多一些关注,以学习调查的精神深入此地生活,也许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创作上有所成就。然而他们偏偏又因某种狭隘的“大众”观念,将香港市民排除在视野之外,至少认为对他们的了解不如对工农兵的深入了解来得迫切。主观上既没有接近的迫切性,客观上也难有写香港而写得好的作品出现,乃至有人替这些南来作家着急起来,甚而献计献策,给从北方来的小说作家提出了写作建议:“在华南写小说,不论文言白话,只要大众化,有场面,事实广而曲折,对上中下人都能有所描写,尤其,注意一点总标题,要醒目,能引人入胜,那自然博得读者去看!”[21]不过教也是白教,因为多数作家岂止是写不好,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表现香港。如果说,在战前讨论“民族形式”的创造时期,香港问题因其“地方性”不被重视,到了战后实践“方言文学”的时期,香港的民众则常因其阶级性被忽视。就这样,虽然内地作家几度大规模南来,却在总体上对本地现实一再错过,因而在无法实现面向华南工农群众的文艺“大众化”的同时,也始终未能在香港本地实现文艺“大众化”。
[1]齐 同.大众文谈[N].大公报·文艺,1939-05-19.
[2]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N].大公报·文艺,1939-12-10.
[3]黄 绳.民族形式和语言问题[N].大公报·文艺,1939-12-15.
[4]茅 盾.杂谈方言文学[J].群众,1948(总53):16-17.
[5]杜 埃.追形势[A].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编.文艺卅年[C].香港: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1949.
[6]林 洛.普及工作的几点意见[J].正报,1947(总57):8.
[7]华 嘉.论方言文艺[M].香港:人间书屋,1949.
[8]冯乃超,荃 麟.方言问题论争总结[J].正报,1948(总69-70):33.
[9]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J].文艺生活,1948(总37):2.
[10]静 闻〔钟敬文〕.方言文学试论[J].文艺生活,1948(总38):58-60.
[11]严肃之.取消“方言文艺”的称谓[N].华侨日报·文史,1948-05-22.
[12]丹 木.读《和尚舍》[N].大公报,1949-03-7.
[13]司马文森.谈方言小说[N].星岛日报,1949-03-28.
[14]楼 栖.我怎样写《鸳鸯子》的[A].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方言文学研究会编:方言文学(第一辑)[C].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
[15]黄继持.战后香港“方言文学”运动的一些问题[A].黄继持.文学的传统与现代[C].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8.
[16]黄仲鸣.政治挂帅——香港方言文学运动的发起和落幕[J].作家,2001(11):112.
[17]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国共内战时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文学资料三人谈[A].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C].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
[18]汪 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A].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9]茅 盾.再谈“方言文学”[A].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C].香港:生活书店,1948.
[20]黄文俞.“旧瓶装新酒”[N].大公报·文艺,1939-12-11.
[21]王幽谷.怎样在华南写小说?[N].国民日报·新垒,1939-08-18.
Study on the Dialect Literature Movement in Postwar Hong Kong
HOU Gui-xin
(School of Literatur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510006)
From 1947to 1949,the writers who had emigrated from the mainland to Hong Kong carried out the dialect literature movement, which took literary popularization as its goal and included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writing practice.In theory, the writers discussed the purpose of writing, the target audience and the way of writing, and advocated to write for popularization, write for workers and peasants,and write completely in dialect.In literary creation, they wrote a number of various kinds of literary works in Guangzhou dialect, Chaozhou dialect and Hakka dialect, but they did not succeed in art.The dialect literature movement did not achieve the desired goal, not only because the writers did not have clear understanding of popularization, but also because they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class nature of readers,thus ignoring the Hong Kong local reality.
Hong Kong;dialect literature movement;popularization;class nature
I209.9
A
1674-0882(2014)03-0043-06
2014-04-15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2012WYXM_0019)、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海外书写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侯桂新(1976-),男,湖南安仁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book=48,ebook=359
〔责任编辑 郭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