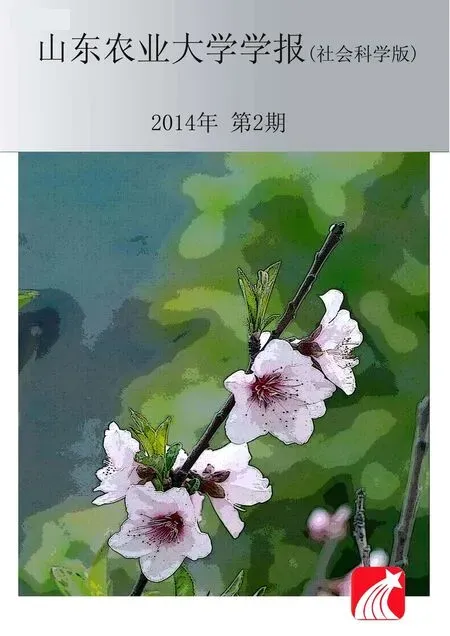中国苹果传播与栽培沿革初探
□丁燕燕 沈广斌
中国栽培的苹果包括中国苹果和西洋苹果两大类。中国苹果古称“柰”,①原产新疆,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虽然在近代走向衰落,但它是中国特有的地理亚种,在种质资源保存、开发利用方面具有重要科学价值。[1]其传播沿革的历史尚不明晰,现有果树史专著②对于此问题已有所涉及。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爬梳相关文献记载,以期厘清中国苹果传播沿革的路径与概况,初步探索影响其传播沿革的因素与规律。
一、汉武帝时代之前的传播与栽培
绵苹果何时传入内地,目前并无定论。现有果树专著大多依据《上林赋》中“楟柰厚朴”的记载,将上林苑引种作为绵苹果传入中土的起点。《上林赋》是为皇帝所作,虽然讲求“铺采摛文”,但也要遵循“体物写志”原则,故其内容必有所本;况且其中的名果异木,大多能在《西京杂记》《三辅黄图》中得到印证,故其可信度很高。结合史实看,上林苑扩建始于建元三年(前138),《上林赋》创作于建元六年(前135)至元光元年(前134)之间。[2]因此,柰的引种只能是在建元三至六年间,而这期间河西走廊恰恰在匈奴控制之下,显然无法直接从新疆、河西走廊引种,引种只能来自西北其他地区,最有可能的是陇西、北地或上郡某地,绵苹果可能在先秦或秦汉之际传入该地区,并在汉武帝时进献移植关中。依据如下:
首先,从相关文献记载看,上林苑所植柰是边郡属国进献的栽培种。《三辅黄图》记载:“帝初修上林苑 ,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记载了这一史实。葛洪辑《西京杂记》记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柰三:白柰,紫柰(花紫色),绿柰(花绿色)……林檎十株。”更是明确提到苑中所植柰有白、紫、绿三种。两则文字都提到“群臣远方”,“群臣”即属臣,“远方”指边郡属国。可见,西汉建元年间能够进献绵苹果的边郡属国,必须是汉朝控制的边郡或者能够纳贡的荒服之地,而且是绵苹果产区或毗邻地区,具备这些条件的只有秦以来就控制的陇西、北地、上郡。
其次,从先秦史实和农业发展来看,绵苹果具备在秦汉之际传入该地栽培的条件。早在丝绸之路开辟前,中原与西域之间已存在经贸通道,西域物产早就输入内地;秦代为安置降附的龟兹人,曾在上郡设龟兹县,此类西域人的内迁为绵苹果传入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先秦是蔬果驯化和引种的高峰期,驯化的果树近20种,各国之间作物引种频繁。前272年,秦收取陇西等地,经营河西走廊,并将中原作物引入该地,也为苹果的引种和栽培提供了充要条件。
再次,出土文献的记载也提供了相关线索。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马王堆医书《杂疗方》记载:“每朝啜柰柰 二三果(颗),及服食之。”[3]有学者认为,“柰柰”与“柰”是战国常见异构字,柰的出现是古文字定形的结果。[4]照此理解,这句话大意是:(预防蜮射之方)是每天早晨吃柰二三颗,再吃早饭。苹果并不具备杀虫解毒功效,显然此方并不科学。不过,联系“撮米投之”的前方来看,两方显然都是带有巫术性质的祝由方。据考,马王堆医书的抄写年代在战国至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在前4至前3世纪之间。[5]这表明先秦就有了绵苹果利用的先例。另外,1965年出土的湖北江陵望山二号墓曾出土过保存良好的苹果核,一同出土的还有板栗、生姜、樱桃和梅等栽培种。[6]这里的苹果属植物可能为沙果,是否栽培种无法确定,至少表明战国晚期楚地苹果属植物已用于随葬。
综合上可知,汉武帝之前新疆、河西走廊一带出产的绵苹果栽培种在先秦至迟在秦汉之际,随中西商贸或由内迁西域人携带,传入自秦以来便有效控制的陇西、北地或上郡某地,并在建元年间移植入上林苑。
二、汉魏南北朝时期的传播与栽培
汉代绵苹果栽培以关中为中心开始向东、向南扩展。上林苑是当时最大的植物栽培园和果树引种驯化中心,苑中栽有白、紫、绿柰三种,定位以皇家种植、观赏为主,不在大面积栽培果树之列。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流频繁,绵苹果始与其他西域其他物种大量传入。汉元帝时,史游所作启蒙字书《急就篇》把柰与大量栽培的桃、梨等常见果树并举:“梨、柿、柰、桃待露霜”,表明前1世纪中,柰走出皇家苑囿,传播至长安周边。随着西南的开拓,柰开始向南传播。扬雄《蜀都赋》出现了“枇杷杜樼栗柰”,“扶林檎”的句子,记录了前1世纪成都绵苹果的栽培。两汉之际,随着政治重心东移绵苹果栽培东扩至洛阳,魏晋时期逐步向周边辐射。高诱在注《淮南子》时,提到北方八、九月柰“复荣生实”的现象。刘熙《释名》则记载了“柰油”与“柰脯”的加工。傅巽《七诲》将南阳“宛柰”与“蒲桃”等果品并称天下至味。
魏晋时期,柰尤其是西北的白柰、冬柰仍是珍贵果品,仅在祭祀、廷赐等重大场合使用,或供贵族官员享用。比如曹植曾为祭祀先王乞请白柰二十枚,卢谌《祭法》记载夏祠法要用白柰,秋祠法要用赤柰。曹植《谢赐柰表》、庾肩吾《谢赉林檎启》、刘潜《谢始兴王赐柰启》都是因受赐苹果的谢恩之作。周兴嗣《千字文》有“果珍李柰”之说。北魏宣武帝元恪面赐奚康生枣柰以资鼓励。皇甫谧《元宴春秋》记载了卫伦取柰、杏、李汁杂糅作糗的故事。
绵苹果的稀缺推动了上层的栽培。这一时期,洛阳成为北方栽培中心。从《晋宫阁名》《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来看,仅华林园中就栽有白柰400株、林檎12株,洛阳承光寺、法云寺中皆有柰种植。另外,《晋书·王祥传》《北齐书·杨愔传》还记载有“王祥守柰树”、“杨愔独坐”的故事,表明此时柰在民间庭院亦有栽植。到6世纪,绵苹果栽培已扩展到黄河中下游,《齐民要术》对此前的栽培进行了总结。南渡以后,人口南迁,庄园经济兴盛,南方苹果栽培也有进展。左思《蜀都赋》在描绘蜀都风物时写到:“其园则林檎枇杷,……朱樱春熟,素柰夏成。”王羲之在《来禽帖》中向远在蜀都的周抚讨要来禽种子:“青李、来禽、樱桃、日给藤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谢灵运《山居赋》则描写了会稽始宁丰富的果蔬生产:“百果备列……枇杷林檎,带谷映渚。”至迟在5世纪中,镇江等地也有栽培,刘损《京口记》记载:“南国多林檎。”陶弘景纂揖《真诰》记载镇江茅山种植有“福乡柰”,可以除灾疠。
西北仍是重要产区。民丰尼雅遗址干枯的果园、“尼雅95一号”墓地随葬品中都有苹果的残留物。[7]北魏初,昙摩密多在敦煌建精舍,植柰千株。西北大量栽植白柰、赤柰等优良品种,并畜积做脯,如同中原贮藏枣、栗一样。酒泉出产的嘉柰“一蒂十五实”,座果率非常高。西北绵苹果良种在文献中也频繁出现,如郭宪《洞冥记》、左思《蜀都赋》、王逸《荔枝赋》、孙楚《井赋》、潘岳《闲居赋》、庾信《移树》、禇澐《咏柰诗》、谢瑱《和萧国子〈咏柰花〉》、王嘉《拾遗记》等均描绘了朱柰、素柰、紫柰、冬柰的优良品质。
这一时期绵苹果栽培快速发展,栽培范围不断扩展,由关中向东、向南扩展,并以洛阳为中心向河北、山东、江南发散;南北朝时已经遍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及蜀地亦有分布;西北成为主要产区。优良品种涌现,栽培技术和加工利用有所进步,出现了总结性的农学专著《齐民要术》。
三、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传播与栽培
隋唐五代苹果栽培更加普及。徐坚《初学记》卷28收录12类最常见水果,柰是其中之一。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8也辑录了大量关于绵苹果的记载。唐诗中涉及柰的有20首,林檎4首,其中不乏杜甫《竖子至》、白居易《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郑谷《水林檎花》等佳作,记录了夔州、忠州等地的苹果栽培,反映出唐代苹果栽培范围的扩大。另外从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中“果则桃、梅、李、柰”的记载看,洱海地区已有柰种植。不少西行游记都记录了西北丰富的苹果资源。如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了新疆焉耆、库车等地的栽培盛况。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都记载了“阿里马城”(今新疆霍城)的由来,及此地丰富的林檎资源。《酉阳杂俎》《游仙窟》等提到的“脂衣柰”、“兔头柰”、“敦煌八子柰”均出自西北,甘州、凉州出产的冬柰仍是重要贡品,绵苹果仍是典型的北方水果。
由于柰口味不佳,人们一直努力试图进行改良。张鷟《朝野佥载》[8]和郑常《洽闻记》[9]都记载了柰改良的故事。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唐初,地点在魏郡临黄、顿丘(今濮阳)等下游临河区域,情节大体相似:都是有人从黄河边拾得树苗精心栽植,结出硕果进献因而得到赏赐,因为进献人被封文林郞而得名“文林果”“联珠果”。“朱柰”很可能是临黄居民偶然发现的野生良种,经过枝接和人工栽培,品质远超河东、秦中、河西诸郡的林檎,被称作“频婆果”。故事反映出在黄河下游临黄区,在苹果栽培中使用了“枝接”技术。翁洮的《赠进士李德新接海棠梨》诗甚至记载了江东海棠梨的嫁接。陈仕良《食性本草》记载:“林檎有三种,大长者为柰,圆者林檎,小者味涩为梣。”首次从形态上对绵苹果进行了区分。
宋代果树在种类、产区及栽培、消费诸方面均有较大提升。京西路苹果栽培发达,洛阳是北方苹果栽植的中心,品种繁多,仅《洛阳花木记》中就记载有“蜜林檎、花红林檎、水林檎、金林檎、橾林檎、转身林檎”6种,“蜜柰、大柰、红柰、兔头柰、寒球、黄寒球、频婆、海红、大秋子、小秋子”10种。临太湖地区也成为重要产区,《咸淳临安志》《吴郡志》《新安志》《会稽志》《吴兴志》等方志皆有相关记载,如《嘉泰会稽志》记载镜湖有佳品“马面棎”;《吴郡志》记载苏州有蜜林檎与平林檎,河南等地的金林檎品种经过嫁接传到临安后传到苏州。不过从《至大金陵志》《大德南海志》《茅山志》《至顺镇江志》的记载看,直到元代江浙的栽培状况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另外,宋代苹果消费发达。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看,东京汴梁苹果消费盛行,如林檎旋乌李、成串熟林檎都是常见水果零食。在《梦粱录》中,柰香新法鸡、小鸡假花红清羹、花红等茶食果子随处可见,足见临安水果消费盛况。
元代后期,绵苹果的一个新品种由西域输入内地,首先栽植在以大都为中心的燕地,经过改良,其外观、口味已与柰有较大区别。[10]这种苹果比柰大,味甘微有香气,忽思慧《饮膳正要》称之为“平波”,熊梦祥《析津志》称为“频婆果”,大如桃,上京出产者最佳;八月作为时果发卖。元末贾铭的《饮食须知》中正式出现了“苹果”名称:“苹果味甘性平,一名频婆。”
这一时期得益于果业的专业化,苹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产量增大,品种增多,生产和消费日趋专业化、多样化;栽培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如韩鄂《四时纂要·春令卷》记载了正月接树之法,首创“砧”的术语,指出种子相似则亲和力强;温革辑《分门琐碎录果类·接果木法》记载“空中压条”法并用于老林檎,为后世沿用。
四、明清及近代的传播与栽培
明清时期,绵苹果的栽培遍及全国多数宜栽地区,又以北方为重,京畿、河北、山东均是重要产区。据统计,明清方志中河北、北京、天津地方志91种,山东地方志74种,江苏地方志25种都有关于绵苹果栽培的明确记载。[11]除了传统的西北、华北产区,东北、西南、东南都有种植。从马毓林《鸿泥杂志》、黄本骥《湖南方物志》、施鸿保《闽杂记》、《弘治八閩通志》、《万历福州府志》、《兴化府志》的记载来看,至清中叶,云南、福建、湖南等地均有栽培,昆明苹果、花红、林檎均有栽植,但苹果品质远不及北方所产;黔阳栽有林檎,长沙、芷江、贵州花红最多。明任洛《辽东志》卷一地理记载有花红。由于各地栽培条件的差异,出现了“苹婆果雄于北,来禽贵于南,柰盛于西”的格局(《鲒埼亭集》卷48),最终形成了一个以绵苹果及其近缘栽培种为主的品种群,其中像出自上苑、青州的苹婆,出自濮州的花谢(《五杂俎》卷11),出自新疆的“冰蘋婆”,“色青红如冰冻琉璃”(《回疆通志》卷12),均是时果佳品。随着栽培进展,王象晋《群芳谱·果谱》对苹果分类总结,此后“苹果”逐步取代了“频婆”“苹婆”等名称。
明清关于苹果的记载繁多,有的作品专门咏叹或探讨其得名,如曾棨《频婆果》诗,徐渭《频婆》诗,周履靖《柰赋》、《林檎赋》,张岱《咏方物·苹婆果》,阮元《频果》诗、李渔《频婆赋》。其他作品如谢肇淛《五杂俎》、孙點《历下志游》、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及小说中也多有记载。栽培方面,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徐光启《农政全书》对果树栽培的原理进行提升,对栽培技术有重要补充。俞贞木《种树书》、宋诩《竹屿山房杂部》、方以智《物理小识》、杨屾《豳风广义》对栽培和病虫害防治都有专门研究。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苹果种植范围遍及全国的大部分宜栽地区,栽培品种繁多,形成了以绵苹果及其近缘种为主的中国苹果品种群,产后利用记载增多,绵苹果栽培达到顶峰。
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日益频繁,1871年倪维思夫妇将西洋苹果引入烟台,此后西洋苹果陆续引入中国并大量栽培,形成了胶东和辽南两大苹果产区,苹果的产业化雏形开始诞生。20世纪初,西南、西北也逐渐开始栽植。在西洋苹果的冲击之下,中国苹果栽培逐渐式微。
五、结论
梳理中国苹果传播分布和栽培沿革可以看出:中国苹果起源于新疆,其栽培种形成于新疆、甘肃一带,至迟在秦汉之际经中西商道或由西域人东传至陇西等地,并在汉武帝时传入关中,然后向东、向南传播,形成了以绵苹果及其近缘种为主的中国苹果品种群。近代西洋苹果传入后,中国苹果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苹果的传播沿革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由上至下传播。传播与分布与帝王的提倡密切相关,主要是为满足祭祀、廷赐或上层社会的需要,先在皇家园林中栽植,然后在民间传播。如柰和林檎传入后先是在上林苑中栽植,然后才随着政治重心的转移和西南的开发向东、向南传播;元代传入的频婆也是先在禁苑栽植,后传播至大都周边地区。第二,先城市后周边传播。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存在,城市苹果栽培兴盛,技术领先,是生产和消费的重心,先进的栽培技术和品种往往先在长安、洛阳、汴梁、临安、大都这些城市间传播,再向城市周边扩散。[12]第三,由西北向东、向南,多波次、多策源传播。中国苹果的传播大致遵循了从西北向东、向南,再由次级中心向周边辐射的路径;同时,又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产生了多个次级的策源中心。如绵苹果在张骞通西域前已经少量传入,但在张骞通西域后始与其他西域物种大量传入;元代频婆作为绵苹果的一种经“兴和西路”传入燕地;清代又出现内地良种向新疆的传播。第四,栽培以个体栽培、四旁栽植为主;分布范围因人的活动而定,与技术密切相关。如施鸿保《闽杂记》记载的邵武李氏“寡妇果”,即是由先人为官时从北地带回闽西北的先例。唐代河南北部出现的枝接技术,推动了德、贝、博等黄河下游临黄区域的种植。
注 释:
①古代文献中的柰主要指绵苹果,后来还泛指沙果、香果、槟子等小苹果类。
②辛树帜:《中国果树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56页。孙云蔚:《中国果树史与果树资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69-71页。束怀瑞等:《苹果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15-17页。陆秋农等:《中国果树志·苹果卷》,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11-19页。李育农:《苹果属植物种质资源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第133-136页。吴耕民:《中国温带果树分类学》,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99页。
[1]束怀瑞.苹果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43.
[2]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00-105.
[3][5]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772.8.
[4]黄文杰.马王堆简帛异构字初探[J].中山大学学报,2009,(4):72.
[6]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J].文物,1966(5):54.
[7]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M].巴蜀书社,1991:109.
[8][唐]张鷟.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1979:68.
[9][宋]李昉.太平广记足本三[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1964.
[10]张帆.频婆果考:中国苹果栽培史之一斑[A].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13期[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7-238.
[11]陆秋农.中国果树志·苹果卷[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14-19.
[12]曾雄生.宋代的城市与农业[A].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C].河北学出版社,200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