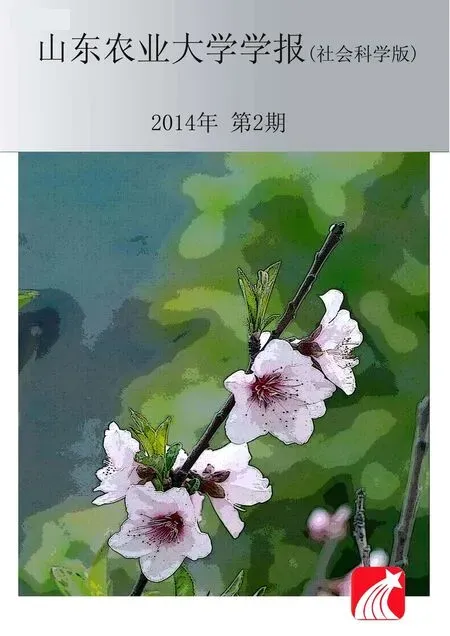山东酱历史起源研究
□于 林 陈义伦 吴 澎 李洪涛
一、研究酱起源的逻辑分析方法
中国的酱的含义,与它的生产工艺历史发展相关联,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动植物捣碎制成的糊状食品或调味品;二是以大豆或麦面、米、蚕豆等发酵而成的调味品。所以中国的酱,广义上泛指一切以发酵工艺制作和虽非发酵而呈糊状的调味品;狭义上指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制曲,经酶变、加盐等基本工艺制成的发酵食品。
最初的酱是史前人类因贮藏而发酵成风味的食品,是史前人类食品贮藏过程中的意外收获。三代时期的酱称作醢,是包括各种动物性原料和许多植物性原料的咸、酸类食品的统称,是风味副食品、调味品。醢类食品的突出工艺特征是发酵和通常有酒的参与。汉代以后直至近代,酱是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制曲,经酶变、加盐等基本工艺制成的发酵食品,大豆、小麦以及其他植物性原料是中国酱的原料特征,发酵工艺和风味是其本质特征,因此,酱给人们的直感是由大豆以及其他几种比较单纯的植物性原料发酵制成。
历史上“醢”、“酱”的最初出现,也就是“醢”、“酱”的起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和必须具备的历史条件。
首先,“醢”、“酱”的最初出现是基于食物保藏的目的。先民最早制作的“醢”、“酱”,可能是简单的盐渍,后来发现这种简单的盐渍有时会出现发酵现象,这种发酵现象多次重复,人们逐步掌握这种发酵技术。人们一旦使用了这种发酵技术,继之不久,就会发现它的风味特殊,制作“醢”、“酱”就成为一种特殊风味食品,它既可以食用也可以用来“调味”,于是“醢”、“酱”就又成为一种特殊调味品。也就是说,随着原始农业社会出现不久,同时也因为陶器(甚至更早的其他自然形态器皿物)的出现和使用,最早的中国“醢”、“酱”就可能出现于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
历史地来看,史前社会生产力低下,食物原料匮乏且不稳定,先民们面临的是“民艰于食”的食事形势。“民艰于食”的食事形势,促使先民们在发现盐以后,尝试用盐保藏食料,于是各种盐渍物接踵出现,最原始的“醢”、“酱”也就应运而生。最初的酱类食品“醢”主要是取自各种动物性原料这一基本特点,足以说明它是基于重要食料保藏目的的产物。先民们由此开始了对食物原料和食物种类努力拓展的普遍尝试,用盐保藏食物原料。因为鱼、肉等动物类食品,得来不易,稀缺而珍贵,人们就倍加珍惜,制作“醢”、“鲊”能保存更长时间,于是就生产出了腊肉、鲊肉、豆豉、盐渍蔬菜等各种盐渍物。现在偏远的农村中还流行着在年节之时制作鲊肉、腊肉的现象,这正是历史上人们对于这种对重要食品珍惜、保存的映照。
其次,“醢”、“酱”的出现,还有满足人们日常饮食生活中对盐的生理需要和对咸味食品(同时也是咸味调味品)丰富的需求。人们的日常饮食和生命维系毫无疑问离不开盐(其他动物和几乎所有生物的生存也离不开盐分),酱类食品的发明,显然还是基于这种生活需求和生命依存需要的结果。对于近海或近陆地盐源(如池盐、湖盐、岩盐、土盐、井盐等)的先民来说,盐料的认识和获取自然不困难。但对于远离盐源地的先民,在运输艰难和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获得盐则十分不易。
我国历史上历代国家政权几乎都对盐实行垄断专卖政策。因为盐是天下百姓不可一餐离之的生活必需品,于是盐就自然而然成了有力量治民者强加诸人民身上的最牢靠、最广大、最持久的财税来源。汉武帝时,国家就明确制定了“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釱(di帝)左趾,没入其器物”的严厉禁断之法令。盐如此珍贵,为了调节普通家庭一年四季盐的供给和摄入,必须改变盐的存在形式,在充分发挥盐的食品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存盐,就成为了中国普通庶民的内在需要。于是创造了盐类的“替代品”——酱,酱改变了盐的保存方式,创造了更为丰富的使用形态。用造酱来延长盐在庶民一年四季中的使用时间,无疑是非常可取的聪明方法。
由上所述,研究“醢”、“酱”的起源发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我们必须通过史籍和考古发现资料,考察探明下列历史条件因素。这些因素,既是“醢”、“酱”开始出现的客观条件,也是历史证据。这就是我们研究酱起源的逻辑分析框架。
1.制作“醢”、“酱”要有保藏原料所用的容器、盛器。为此,要探明何时、何地先民们开始初步掌握了制陶技术,有了制陶业,较早出现了陶罐、陶坛等陶器。
2.制作“醢”、“酱”要有保藏所需的盐。为此,要探明何时、何地先民们较早发现和使用盐,开始初步掌握了制盐技术,出现制盐业。
3.制作“醢”、“酱”要有动植物产品原料。为此,要探明何时、何地先民们开始栽培谷物和牧养家畜、家禽,从采集狩猎业进入到种植畜牧业社会,饮食日益丰富稳定。
4.制作“醢”、“酱”要有“制曲”和发酵技术。为此,要探明何时、何地先民们较早发现和初步掌握了发酵技术,出现“制曲”技术。初步掌握了酿酒技术应该是一个重要证据。按照包启安先生的观点,人们只要会制造酒、制作酒曲,就可以作酱。[1]
5.制作“豆合面”的“酱”要有要大豆(豆类)、小麦原料。为此,要探明何时、何地较早出现大豆(豆类)、小麦的种植栽培和历史起源发展。
6.“醢”、“酱”从最初出现到人们较为普遍食用,制作工艺的逐步成熟,由一家一户简单腌制,到小作坊制作、再到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这样的历史条件应是: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社会兴起,粮食出现剩余,手工业生产出现分离,文明社会出现,大型聚落、城镇和“通邑大都”形成,“醢”、“酱”的社会需求增加。为此,我们要考察这些历史条件何时、何地开始出现和繁荣发展。
二、山东地区酱起源历史条件因素考察结果
山东地区先民在齐、鲁立国之前被称为东夷人。“东夷人”是夏、商时期中原地区对其东部地区先民的称谓。山东地区东夷人创造了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具有独立系统、独立风格特点的,持续稳定发展的灿烂文化。考古发现,早在四五十万年前的远古时代,这片土地上就生活着与“北京人”同时代的“沂源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十分丰富,以后李文化(距今8000年左右)—北辛文化(距今7000—61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岳石文化(距今3900—3400)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谱系脉络清晰,说明这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2]同时这也为我们考查酱起源的历史因素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1.山东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制陶技术和使用陶器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就发明了制陶技术,至少早在8000多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陶罐、陶坛等容器就已经出现在山东地区先民日常生活中,[3]这为制作“醢”、“酱”提供了容器条件。
2.山东地区先民最早发明了“煮海为盐”技术,制盐历史悠久,早在距今5000多年的炎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食(使)用海盐,[4]殷墟时期成为商朝的制盐中心。[5]事实上,山东先民尝食食盐的情况应当更早一些,只是个人自然煮海取盐食用算不上生产,这为制作“醢”、“酱”提供了醃渍条件。
3.山东地区农业历史悠久,早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后李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原始种植畜牧业,种植谷类、饲养家畜,距今7000—61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已出现早期鋤耕农业,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了比较发达的锄耕农业和普遍的家畜饲养业,先民们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进行农业生产,种植粟、黍和水稻等农作物,有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为制作“醢”、“酱”提供了原料条件。[6]
4.山东地区酿酒“制曲”发酵技术历史悠久,酿酒始于7000—61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成熟于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一般认为考古出土的高柄杯是一种酒具,山东地区高柄杯的发现最早始于北辛文化时期,此时期山东东夷人已发明了人工酿酒方法。[7]这为制作“醢”、“酱”提供了“制曲”条件。
5.山东地区小麦种植历史悠久,距今至少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龙山文化时期考古发掘,在山东地区的茌平教场铺、日照两城镇、山东胶州赵家庄等多处遗址发现了小麦的碳化遗存。[8]大豆栽培距今也应该有4000多年的历史。《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庆四方。”郑玄注:“五种,黍稷菽麦稻也。”[9]这为制作“以豆合面而为之”的“酱”提供了原料条件。
6.山东地区先民早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后李文化时期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聚落,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已进入初期文明古国时代,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社会的兴起,粮食有了剩余,阶层、阶级出现分化,手工业开始从农业畜牧业中分离出来。[10]这为“醢”、“酱”由一家一户简单醃制,到小作坊制作生产和酱园经营提供了前提条件。
7.山东齐地临淄文化历史悠久,临淄较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制盐业、手工业,人类聚落等的出现一直走在山东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前列。
临淄后李官村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后李文化时期齐地临淄就已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人类居住聚落,制作陶器,出现了先进的原始农业。[11]
临淄桐林(田旺)遗址的发现,说明据今4000-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临淄就成为山东地区的文明古国、中心方国城(城市最初萌芽),[12]表明临淄地区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后李文化时期已经具备了“醢”、“酱”出现的历史条件,并且在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具备了较为普遍食用,制作工艺逐步成熟,由一家一户简单腌制到小作坊制作,再到具有一定规模酱园经营的历史条件。
临淄在距今2600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当时全国最发达的“通邑大都”之一。[13]《史记·货殖列传》中“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通邑大都,酤一岁 ,醯酱千瓨”、“糵麹盐豉千荅”[14]的描述,表明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齐都临淄呈现出包括酒、醋、豉等发酵食品在内的酱品、酱园、酱文化的昌盛繁荣景象,“醯酱”的生产、市场交易数量已经相当可观。
8.《齐民要术》,是山东酱历史文化丰厚的重要标志,也是临淄酱历史文化丰厚的重要标志。《齐民要术》系统总结记录了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可以上溯到西汉)包括山东地区、临淄地区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作酱法”。书中“制酱法”和“固态法两种曲制酱,再补充酶浸出液及盐水进行稀发酵”酱油制作工艺,[15]既是对山东乃至于中国酱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是山东具有深厚酱文化的历史证据,同时也是临淄具有深厚酱文化的历史证据。
三、结论
1.山东地区是我国酱及酱油的起源地之一,是重要源头,历史悠久。
(1)山东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制陶技术和使用陶器的地区之一,至少早在8000年左右的后李文化时期,陶罐、陶坛等容器就已经出现在山东地区先民日常生活中,同时也出现了原始农业,这为制作醢、酱提供了容器和原料条件。如果从此时算起,山东地区醢、酱出现应有8000多年的历史。
(2)如果从距今7000—61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已出现早期锄耕农业,为制作醢、酱提供了充分的原料条件算起,山东地区醢、酱出现应有6100多年的历史。
(3)如果从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出现海水制盐技术和较成熟的制曲发酵技术算起,山东地区醢、酱应出现有5000多年的历史。
(4)如果从开始栽培利用大豆、小麦算起,山东地区“以豆合面而为之”的酱及酱油出现应有4000多年的历史。
(5)如果从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已进入初期文明古国时代,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社会兴起,粮食有了剩余,手工业开始从农业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算起,大型聚落、城镇的形成,山东地区酱及酱油生产出现小规模手工小作坊“酱园”,应有50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的临淄初步形成工商业发达的“通邑大都”,醯酱的生产、市场交易数量相当可观算起,山东地区出现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作坊“酱园”,应有2600多年的历史。
(6)如果从《齐民要术》记载“固态法两种曲制酱,再补充酶浸出液及盐水进行稀发酵”酱油制作工艺算起,山东地区酱油形成独立的生产工艺,应有2100年的历史。
2.山东临淄是我国酱及酱油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重要源头,历史悠久。
(1)山东齐地临淄文化历史悠久,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后李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人类居住聚落,制作陶器,出现了先进的原始农业。临淄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制盐业、手工业,人类聚落等的出现一直走在山东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前列。这表明临淄醢、酱出现应有8000多年的历史。
(2)临淄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就成为山东地区的文明古国、中心方国城(城市最初萌芽),出现小规模手工小作坊“酱园”,应有5000多年的历史。
(3)临淄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通邑大都”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通邑大都,酤一岁,醯酱千瓨”、“糵麹盐豉千荅”的描述,表明在距今2600多年的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临淄就呈现出包括酒、醋、豉等发酵食品在内的酱品生产、酱园、酱文化的繁荣景象,醢、酱的生产和市场交易数量已经相当可观。
(4)齐地人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山东临淄酱文化历史文化丰厚的重要标志。《齐民要术》系统总结记录的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可以上溯到西汉)包括山东临淄地区在内的我国“作酱法”和“固态法两种曲制酱,再补充酶浸出液及盐水进行稀发酵”酱油制作工艺,是对山东乃至于中国酱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1]包启安.酱及酱油的起源及生产技术[J].中国酿造,1982,(1):3 -14
[2]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与发现[M].济南:齐鲁书社,2004:2-10.
[3]王永波,王守功,李振光.海岱地区史前考古的新课题——试论后李文化[J].考古,1994,40,(3):247 -255
[4]吕世忠.先秦时期山东的盐业[J].盐业史研究,1998,(3):10 -15
[5]李慧竹,王青.山东北部海盐业起源的历史与考古学探索[J].管子学刊,2007,(2):43 -46.
[6]何德亮.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试论[J].农业考古,2004,(3):58 -69.
[7]逄振镐.东夷人的灿烂文化[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4):1 -8.
[8]何德亮,张云.山东史前居民饮食生活的初步考察[J].东方博物,2006,(2):51 -61.
[9]郭文韬.试论中国大豆栽培起源问题[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15,(4):326 -333.
[10]张光明,芦琳琳.海岱地区文明形成进程的考古学研究[J].管子学刊,2004,(4):70 -80.
[11]王永波.淄博市后李新石器时代至宋元遗址[J].中国考古学年鉴[M].文物出版社,1990:3-8.
[12]魏成敏.桐林田旺遗址简介[J].管子学刊,1987,(1):82.
[13]李埏.《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考[J].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1999,25,(2):71 -76.
[14]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贾思勰.齐民要术校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