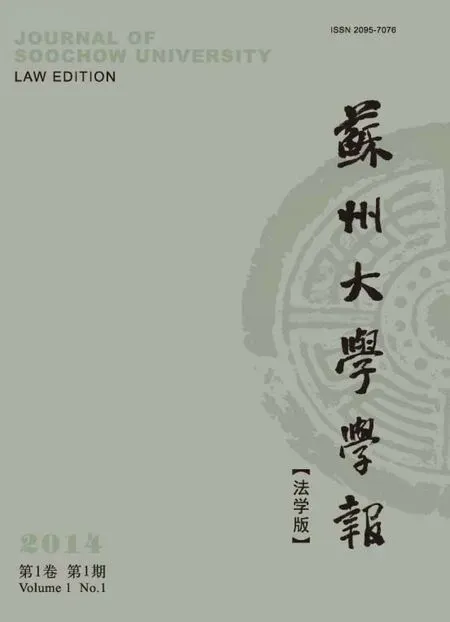行政推诿研究
关 保 英
行政推诿研究
关 保 英*
行政推诿是行政法治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瑕疵行政行为,其影响行政一体化、迟延行政过程、加大行政成本、形成行政内部冲突,发生概率和危害性都不亚于行政越权。然而,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和行政实在法都重在关注行政越权,却忽视了行政推诿。将行政推诿纳入我国行政法治的调控范畴是当今理论和实务界不可回避的问题。行政执法中的推诿不能仅仅通过一个机制来解决,而应当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予以进行,应以宪法精神统摄行政法治、以体制行政法完善职权归属、以行政程序法规范执法模式。
行政推诿;消极行政;规范执法
行政越权与行政推诿是行政法治中两种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状态,我国行政实在法对行政越权及其违法性作了明文规定,并规定了行政越权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等。①与之相比,行政推诿还没有受到行政实在法的调整和规范,学界对此也是一个理论空白。在我们看来,行政推诿在行政法治实践中所发生的概率并不比行政越权少,其对政府法治破坏的程度也不会小于行政越权。基于此,将行政推诿纳入我国行政法治的调控范畴是当今理论和实务界不可回避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拟对行政推诿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加以探讨,并希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重视。
一、行政推诿的概念界定
行政推诿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对行政相对人的请求或者对自身应当行使的职权予以或软或硬的拒绝,并将行政相对人的诉求或者自己的固有职权推给其他行政主体行使的一种行为状态。这是我们对行政推诿的一个简单的定义,该定义应当有下列切入点:
一则,行政推诿的行为对象是特定的。行政推诿的发生应当存在于两个行为范式之中:其一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执法中发生了联系,该联系大多是因行政相对人的诉求引起的。在这个诉求中,行政主体有了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方式。在行政执法正常情况下,行政主体会理性地对行政相对人的诉求予以受理进而做出处理。而在行政推诿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则做了一个将行政相对人推入其他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①在行政推诿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作出了一个意思表示,即是说,在行政推诿中,行政主体是存在意思表示的。但是行政推诿中的意思表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关系是需要探讨的,我们还不能够简单地将行政推诿中的意思表示与行政主体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作出相同理解和认识。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对于行政主体的行政推诿行政相对人是否有提起行政救济的权利,在行政相对人对所有行政推诿都能够提起行政救济的情况下,行政推诿中的意思表示应当与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作相同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推诿都没有作出可以纳入救济途径的规定。其二是行政主体依据行政组织法和部门行政管理法有权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或者其他行政管理行为,②自1999年宪法第13条修正案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下来以后,我国有学者认为在行政主体的职权履行中,行政执法的概念代替了行政管理的概念,那么行政执法与行政管理在行政主体履行职责时,究竟是什么关系,还是需要认真探讨的。在笔者看来,行政执法并不能够完全代替行政管理的概念,这既因为行政系统在有些情况下承担着制定行政管理规则的职能,同时在行政法治实践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行政行为并不能够完全归入到行政执法的范畴中。其实施这样的行为应当是在行政法中承担的一项义务,③行政系统所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从国家权力行使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职权或者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力,但同时我们必须强调行政系统的职权行使是它所承担的责任,是它在法律上的一项义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行政系统都不能够把国家赋予的相应职权自由处分,所以行政主体从组织法和部门管理法中取得的职权也应当是它在行政法中承担的一项义务。但行政主体既没有实施相应的行政执法行为,也没有实施相应的行政管理行为,而且将这些行为不适当地推入到了其他行政主体手上。上列两个方面是行政推诿发生的场域,这个场域决定了行政推诿的对象是特定的。一个对象是行政相对人,即是说行政主体将行政相对人的诉求作了拒绝,而行政相对人也就成为行政推诿中的当然当事人,或者说是当然对象人,④行政推诿就所涉及的相关对象而论,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其他行政机关因为在行政推诿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将自己的职权无端地推到了其他机关之手,另一个方面是行政相对人就是与行政主体发生直接关系的当事人。由于行政推诿从总体上讲是一个外部行政行为,因此行政推诿的对象人主要是行政相对人,总而言之,行政推诿所发生的行政法关系还需要进一步予以厘清。另一个对象则是国家权力体系。行政法赋予了行政系统行使行政职权的资格和范围,而行政主体在行政推诿中使这些职权处于懈怠和停滞状态。由于这些职权是由国家政权体系予以设计的,因此国家政权体系就成为行政推诿中的又一个对象。推诿对象的特定性是行政推诿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行政推诿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二则,行为理由的特定性。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常常都会有诸多的理由,包括行政主体在作为的行政行为中,也包括行政主体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中。应当说行政主体作出或者不作出行政行为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这种理由通常都由行政主体自己提供和做出解释。在行政推诿中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理由则是相对单一的,而且这种理由在行政法实践中也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行政主体认为行政相对人的诉求或者某一行政管理事项不是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其也许认为行政相对人的诉求是合法的,行政管理的职责履行也是应当的,但是,这样的合法性和履行职责的正当性与自身是没有关系的。正是行政推诿理由的这种特定性使行政推诿与其他瑕疵行政行为有所不同。我们要强调的是,行政主体推诿理由的特定性以及推诿过程中的具体理由都是由行政主体自己认可和判断的。
三则,行为方式的特定性。行政推诿如果用行政法学理论来衡量,它应当是一种失态的行政行为:“失态具体行政行为又称有瑕疵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欠缺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或法律要素的行为。这类行为徒有行政行为之表,实则并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⑤关保英:《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页。在行政法治实践中,任何失态行政行为都是以一定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瑕疵行为方式便构成了不同的失态行政行为,例如,行政主体对行政职权滥用的行为方式便导致了行政滥用职权这种失态行政行为,即是说行为的特定性是判定某种失态行政行为的一个客观标准。就行政推诿这种失态行政行为而论,它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请求的一种拒绝或者推辞,它是行政主体对行政职权行使的一种懈怠或者不作为。这种推辞、懈怠或者不作为,或以相对柔和的方式为之,或以比较生硬的方式为之,应当说绝大多数的行政推诿的行为方式都是在相对柔和的情况下为之的,但其最终的效果是对行政相对人诉求的拒绝和对行政职权的不作为。
四则,行为后果的特定性。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是行政行为理论中比较重要的构成部分,无论合法的行政行为还是违法的行政行为都必然会产生某种法律后果。那么行政推诿究竟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后果,或者法律后果呢?一方面,行政推诿从行为后果来讲,它使行政权的行使在一定情况下发生了法律上的真空,即行政权本该在某一方面发生作用,但在行政推诿的情况下则没有发生相应的作用。另一方面,行政推诿从法律后果来讲,它应当给行政主体带来法律上的麻烦。进一步讲,行政主体对自己的行政推诿行为是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上列四个方面的切入点对于我们领会行政推诿的概念至关重要,若从上列四个方面切入,行政推诿具有下列本质属性:
第一,行政推诿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在行政法上,我们对相关的主体常常都有一些法理上的称谓。在这些称谓中,有些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而也是法律上的称谓,例如,行政机关、公务员、职能部门等,①这些称谓都有宪法或者行政实在法上的依据,例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处罚法等在对行政主体作出规定时,使用的都是行政机关的概念,而公务员法则专门界定和规定了公务员的概念,诸多部门行政管理法则涉及职能部门的概念等,应当说这些概念被法律规范规定以后,就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和价值,就应当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这些概念在我国宪法和相关的行政法规范中都有相应的规定,这便使它们都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有些则属于学理上的用语,以行政主体的概念为例,它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法教科书中是一个通用性的概念,然而该概念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理上的概念,至少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是如此。我们要强调的是行政主体的概念基本上科学地揭示了我国行政法治中有关行使行政权的组织的状况。从学理上讲,行政主体的概念也是有严格范畴的,它是在与行政相对人概念的对比中形成的。二者是一个相互矛盾着的东西,它们共同存在于行政法关系之中,互为前提条件。应当说我国宪法和相关组织法所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等概念并不是行政法治中的当然的行政主体。只有当法律典则中规定的行政机关等进入到了具体的行政法关系之后,它们才能够享有行政主体资格,它们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主体。行政推诿是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为,因此行政推诿的主体要件是具体化的,是与行政执法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我们将行政推诿的主体泛化到行政系统、行政机关、职能部门等概念之中,我们就有可能使行政推诿从一个严格的行政法问题变成一个行政学或者政治学上的问题。
第二,行政推诿是行政封闭性行为。从理论上讲,行政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相对较大的组织体系。在这个较大的组织体系中,包含着若干分系统、支系统乃至于子系统。行政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相比,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进一步讲行政系统内部的分工无论如何进行,它都应当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社会公众所面对的是行政系统的整体。社会系统尤其广大公众对行政系统的评价是一个整体性的、具有价值倾向的评价。当社会系统和公众对行政系统做出这样的评价时,它并不去考虑行政系统的内部分工,更不会考虑行政系统内部的结构形式。然而,对于行政系统中的各个分系统、支系统和子系统而言,它们都有自己严格的一亩三分地,它们都按照自己的岗位职责和权力行使模式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正因为行政系统内部存在这种复杂的结构和分类方式,才导致在我国前些年形成了行政权行使中的部门保护主义等不当倾向。②行政系统中各个支系统的划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机构名称上将不同的支系统予以区分,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我们难以将有些支系统之间的职权交叉关系完全予以厘清,正是这种职能交叉或者职能相近的情形,常常导致在职权行使中存在部门保护主义等现象,当然部门保护主义形成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驱动。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不当倾向现在仍然处于蔓延状态。行政系统中的推诿便来自于这种结构上的或者职能上的传统划分。当一个行政主体作出行政推诿行为时,它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权利系统中、一个职能范围中,也就是说它认为不是自己圈内的事情就不予受理或者认可。我们要强调的是,行政系统的职能划分虽然是明细的,但是它是相对的,即是说我们无论怎么样对行政系统的职能范围进行划分,都不能够影响行政系统相对于社会系统而言是一个独立的价值系统这个事实。这一理论前提必然使行政推诿作为一种非正当的行政封闭性行为。
第三,行政推诿是行政不配合行为。行政行为依传统行政法的定义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所做的行为。以这个定义,行政行为基本上都是外部性的,就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系统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所实施的。这个定义是非常明了的,也是对行政行为及其相关关系的类型化处理。它将无数复杂的行政行为简化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行政行为从法律形式来讲是外部性的、外在化的,但从一个行政行为作出的具体情况来看,它常常牵扯到诸种内部关系。我们认为,行政相对人在面行政系统时,其认知是比较模糊的,在他们眼里,行政系统内部的复杂分工并不是清晰可见的。这就必然要求在一个行政执法过程中,在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行政系统内部必须有一个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的行为方式。例如,当行政相对人不适当地将产品质量方面的诉求提交给工商行政机关时,就发生了行政相对人认知上的误差。毫无疑问,这样的误差即使存在,也是非常合理的。行政相对人并不应当对这样的误差进行买单,因为他们与行政系统相比,对行政系统内部的职责划分是非常不熟悉的。这就要求无论什么样的行政执法行为,行政主体之间都应当有一个相互配合的意识,都应当有一个相互配合的行为状态。事实上,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系统相互配合的关系作出了相应的规定。①《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19项规定:“加强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点;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在行政推诿的情况下,行政系统内部诸主体发生了配合上的阻滞,即此一行政主体对彼一行政主体所管的事项予以抵制,这种职权行使中的不配合是行政推诿的另一个实质性要件。
第四,行政推诿是行政不法行为。在行政法理论中,有这样一些关于失态行政行为的表述,一是行政违法行为,所谓行政违法行为就是指该行政行为违反了行政实在法的规定,并符合相关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所谓行政违法,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规定义务,侵害受法律保护的行政关系,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②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页。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行政违法行为的概念和行为状态。二是行政不当行为,所谓行政不当行为就是指该行政行为虽然没有严重的行政违法情形,但存在形式上或实质上的不适当状况。在行政法治中,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不适当常常用不当行政行为来表述,对于行政不当行为,《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三是行政瑕疵行为。与上列两个行为相比,行政瑕疵行为在行为失态的程度上可能要相对轻一些,但这样的行政行为仍然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或者对行政合法性构成威胁。我们注意到,在有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中确立了行政瑕疵行为的概念,同时也确立了追究行政瑕疵行为的法律责任。③参见罗传贤著:《行政程序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45页。上列三种行政行为是行政法需要重点规范的行为,也是行政救济制度需要重点解决的行为。从总体上讲,上列三个行为都可以被视为是行政上的不法行为,就是该行为与行政法规范和行政法典则的规定在有些方面来讲是没有保持契合的,甚至是对立的。行政推诿究竟是上列三个不法行为中的一种还是同时具有上列三种不法行为的属性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需要行政实在法予以规定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行政推诿应当分别存在于上列三种不法行为之中,即是说有些行政推诿行为可能就是行政违法行为,有些行政推诿行为则可能是行政不当行为,还有一些行政推诿行为可能与行政瑕疵行为具有同一性质。由于行政行为的不法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时候违法与不当之间、不当与瑕疵之间、违法与瑕疵之间仅仅有非常微小的区别,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通过行政实在法对行政推诿作出定性,对行政推诿的不法类型作出具体规定。
二、行政推诿的弊害
行政推诿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此种不法行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将行政推诿的表现形式用下列标准作出分类。
一是以拟推部门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可以分为行政职能部门之间的推诿和综合管理机关与行政职能部门之间的推诿。我们知道我国行政系统有诸多的职能划分,而且形成了非常复杂的行政职能部门,有工商、税务、物价、环保、土地、民政、公安、交通、产品质量等数十个职能部门的划分。④我国行政系统中的职能划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如果以国务院所设置的部委以上的机构为依据,这种划分有20多个部门,但是国务院还有一个层次的机构就是直属机构,从直属机构的设置上看,实质上每一个直属机构都有特定的职能管理事项,以此来划分的话,我国的行政职能部门则有40多个。正如上述,这些职能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并不一定是泾渭分明的,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常常是诸种职能交织在一起,这既给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诉求带来了不便,也给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使带来了麻烦。正因为如此,职能部门之间的推诿是行政推诿中最容易发生的情形。同时,在我国行政系统中有综合管理机关和职能部门之间职权的划分,并且同时有这样的机构设置。例如,各级人民政府就是一个综合管理机关,而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就是职能管理机关,它们之间的职权划分也常常存在争议。即便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也常常会出现综合管理机关将一些管理权能推给职能部门的情形,也会出现职能部门将一些管理权能推给综合管理机关的情形。上列两个方面的推诿是我们以拟推部门为标准所做的划分。
二是以推诿理由为标准进行的划分。行政职权的行使是以行政行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而依据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行为都应当具有相应的理由。在法治发达国家,行政行为的理由是必须告知于当事人的,这就形成了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制度:“理由原则上也属于行政行为的法律形式。书面发布的或者被确认的行政行为必须有理由。有决定性重要作用的事实和法律的观点,必须在理由中阐明。如果当局有裁量空间,那么也应当说明标准的裁量根据。”①[德]埃贝哈德·施密特-阿斯曼等,《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时,尤其要具有相应的理由。那么,当行政主体推诿当事人的诉求或者推诿自己的职权行为时,它也可以有很多的理由。例如,行政主体可以以自己无权主管某种事项而推诿,可以以当事人首先应当到另一个部门去诉求而推诿,可以以当事人的诉求已经过时而推诿等等。总体上来讲,行政推诿的理由多以行政主体自认为自己无权主管行政相对人的某项诉求或者某种事项为主,这也符合行政推诿的本质特征。
三是以推诿方式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如果我们在行政法上确立了行政推诿的违法行为,那么行政主体推诿的方式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些推诿方式就构成了行政违法行为的具体行为要件。行政推诿在行政法治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下列行为方式:其一是拒绝,就是行政主体将行政相对人的诉求予以拒绝,在拒绝过程中会告知行政相对人某一个行政主体是主管主体。其二是推辞,就是行政主体对当事人的诉求采取了推辞的态度,尽管在推辞的情况下行政主体的行为方式相对要柔和一些,但是它还是没有接受行政相对人的相关诉求。其三是放弃职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行政主体应当行使相应的行政职权,应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能,而行政主体人为地放弃了这样的职权。
上列三种行为方式都是行政推诿的主要行为方式。行政推诿表现形式的分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它也是行政推诿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正是由于大量行政推诿及其行使的存在才给行政法治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法理学和行政法治实践来分析,行政推诿的弊害可以表现为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影响行政一体化的弊害。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是一个中央与地方一体化的国家,这样的国家结构形式和行政权的组织方式使我国行政权的区域划分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而进行的。与联邦制不同,在联邦制之下,地方行政系统是完全独立的,此一地方与彼一地方之间往往不存在行政权的同质性。但是,单一制国家则是另一种情形,地方之间的划分只是从行政权行使方便化的需要而为之的,每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系统的实体,换言之,我国地方之间在行政权的行使中,具有非常强烈的同质性。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论,就地方不同层级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而论,它们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正如上述,它们有系统和结构上的划分,但它们并没有价值体系和目标定位上的差异。行政推诿一个非常明显的弊害就是人为地将行政系统的统一性予以割裂,使行政职权的行使在不同部门有不同的状况,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状况,在不同层级有不同状况。这就使行政权的行使呈现非常大的碎片化和分散化倾向。②行政大系统中的各个支系统和子系统虽然有界限上的划分,但是每一个子系统或者支系统都不应当是绝对封闭的,而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行政推诿的状态下,行政系统中的支系统和子系统都是封闭的,这样的封闭性就必然使行政权的行使显得十分分散。行政的一体化说到底是法治的统一化,因为如果行政权的行使在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情形,那就必然会使行政法的执行因部门差异的变化而变化,因地区差异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一个部门来讲虽然保持了行为的同一性,但是它却没有保持整个法治的同一性。行政的一体化与法治的统一化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学界鲜有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而在笔者看来,行政的一体化与法治的统一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不可分开的。进一步讲,行政一体化一旦失衡,必然会影响法治的统一。为了很好地解决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之中规定了行政执法中的法治统一原则,这实质上为确定行政推诿的不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第二,迟延行政过程的弊害。行政过程是在行政权的运作中得以实现的。在现代法治政府和法治行政的格局之下,行政过程既受到行政程序的制约和规范,①行政程序法与行政过程的关系我国大陆学界鲜有学者进行研究,台湾学者对行政程序与行政过程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行政程序可以深化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原则,可以贯彻依法行政,可以保障人民权益,可以提高行政效能等。参见汤德宗著:《行政程序法论》,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52页。又受到行政权行使中其他内外在因素的制约和规范。现代行政法治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学界已有一些研究,可以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行政法治应当突出程序的价值,应当把程序作为一个与实体相同的指标来看待,并且在行政法治过程中应当实现程序正义。在罗尔斯《正义论》问世以后,这个问题甚至在公法学界形成了共识。另一种主张则认为程序只是行政法中的一个工具性要素,它不具有终极价值或者最高价值,即是说任何程序只有当它能够提高行政效率或者促成效率价值的实现时它才是有意义的:“一般以为,本法之制定所以能够提升行政效能,理论上说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设计得当的行政程序可以协助行政机关,伊始即作成‘正确决定’,因而免除事后救济的种种支出。第二,经由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所形成、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较易于为当事人所接受,可免发生抗争而影响决策之执行。换言之,行政机关虽因采行行政程序,而增加若干行政成本,但设计得当的行政程序所能获致之效益,包括:因决策的正确率提高而节约的事后救济成本,及因决策的正当性增强而节约的政策执行成本等,将胜过(大于)因采行行政程序所需增加之成本,故而能够提升行政效能。”②汤德宗著:《行政程序法论》,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71页。笔者认为,行政法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若干阶段,在20世纪中期,行政法中的程序价值应当是一种最高价值,“红灯理论”的行政法理念就赋予该价值非常高的属性。③参见[英]彼得·莱兰、戈登·安东尼著:《英国行政法教科书》,杨伟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进入21世纪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尤其在给付行政和服务行政的行政法理念之下,程序的相对性就凸显出来,④参见关保英撰:《论行政法中的程序相对主义》,载《江淮论坛》2011年6期。即是说人们更加追求政府行政系统为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哪怕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有一定程度上的程序瑕疵,但只要它能够为社会公众创造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这样的行政行为就应当是合法的。显然在效率理念的支配下,一方面行政过程的运行时间应当短,另一方面行政过程的运行不应当间断,这两者是有机的统一。我们再回头来分析行政推诿,毋庸置疑,行政推诿常常是一个行政决定,或者是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诉求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公文履行,很长时间不能产生实质性后果,这就必然迟延了行政过程。从这个角度讲,行政推诿与现代行政法理念是完全相悖的。
第三,加大行政成本的弊害。在我国行政法制度中有关行政成本的问题还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国行政机构体系的设置并不显得廉价。我们知道,在我国行政机构中长期以来存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状态,行政机构的膨胀便意味着行政系统成本的增大。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通过规范化的行政编织法对行政机构的膨胀进行刚性限制。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依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理论,一个国家行政机构体系的设置应当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正比例关系,即是说在GDP比较发达的国家行政机构体系的规模就应当相对大一些,反之在GDP比较低的国家,行政机构体系的规模也应当相对较小。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问题,除了我国行政机构存在这种成本相对较大的情形之外,我国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也存在投入较大的问题,这包括行政机构每年的消耗,包括行政公职人员每年的消耗:“行政权行使主体的分子消耗是指独立于总消耗之外的行政机构各部分和行政机构各组成人员的消耗。”⑤参见关保英著:《行政法的价值定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我们注意到,法治发达国家已经用相关的成本理论来构建行政法制度,追求行政过程中的最小成本,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推诿必然要加大行政成本。在我国行政法治的历史中,有一个行政许可经过长期部门之间的推诿,历经前后14年,各个部门盖的公章有8000多个,而支撑这个行政许可的部门审批文件可以拉两辆面包车,⑥该行政审批的案件所指的是武汉江汉码头的修建审批的项目,该项目在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项目审核阶段,但到1985年该项目才最终取得了行政审批。我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虽然没有一部完整的行政许可法,但在部门管理法中都有诸多行政许可的规则,当时的行政许可规则都强化了行政系统的审批权,而行政相对人无法通过正常的路径对行政许可请求行为进行救济。这充分反映了部门之间推诿在加大行政成本中的行为状态。推诿所产生的结果既耗费了非常有限的行政资源,也对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①行政推诿必然使行政系统难以做出行政决定,行政相对人则在行政系统的踢皮球中损失了诸多的权益,说到底为行政推诿买单的还是社会公众。
第四,形成行政内部冲突的弊害。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应当有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范畴的关系常常被认为是外部行政法关系,而调整这个范畴的行政法典则被认为是外部行政法;二是行政系统内部诸关系,包括行政系统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包括行政系统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关系,包括行政系统中公务员与行政机关的关系等等,这种关系被认为是行政法中的内部关系,规范这个范畴的行政法也叫内部行政法。从行政法的上列两个范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法治发达国家的行政法不单单要缓和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关系,而且要缓和行政系统内部各种复杂的关系。一定意义上讲,行政系统内部由于存在一定的利益格局,②我国长期以来在行政法理论中否认行政机关独立人格的存在,即是说行政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即是国家拥有行政法上的人格,行政系统没有相应的人格。从这种理论出发,诸多学者也认为行政系统不存在自身的利益,不存在相应的利益关系,但是近年来我国有学者认为行政系统中存在着非常清楚的利益关系,人们用行政系统的“自利性”来描述这种利益关系。因此行政系统内部的冲突也是行政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存在,内部行政法的功能就是要缓和这种冲突。行政推诿从它的行使看所反映的冲突关系是行政主体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冲突。但是由于推诿本身牵扯到另一个行政机关,另一个行政部门,这就使得原来仅仅属于外部冲突的范畴转化到了内部冲突之中。可以说,每一次行政推诿都必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之间形成职权的争议,形成行为方式上的争执,这样的争议对于一国建构理性的行政法治是非常致命的。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踢皮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了非常多的年头。1987年,中共中央决定对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进行改革时就提出了“踢皮球”的问题,而且在中共十三大报告③行政程序法的概念在我国党和政府文件中的出现应当说最早是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制定行政程序法为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使提供规范和程序。中就已经提出了用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解决部门之间互相扯皮的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近三十年来没有对政府组织法进行相应的修改,也没有制定出完整意义的程序法,所以“踢皮球”和扯皮的问题现在仍游离在行政法典则之外。行政系统内部的冲突必然大大降低行政系统的行政公信力。
三、行政推诿的成因分析
行政推诿与行政职权的行使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行政推诿在通常情况下是由下列因素所导致的。第一个因素是行政职权的争议。所谓行政职权的争议是指行政组织法和部门行政管理法所规定的行政职权,或者在部门之间或者在区域之间,或者在层级之间存在相应的争议。以行政处罚为例,案件处理中的管辖就有诸多种,如地域管辖、职能管辖、级别管辖、共同管辖等。④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1条规定:“对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这些不同的管辖常常会导致不同的机关对案件受理中有不同的认识。可以说我国行政系统这种职权的争议是一个普遍存在。以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为例,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前若干个部门都履行着城市管理执法的职能,这就必然使不同的机关在城市管理中存在职权行使中的争议。相对集中处罚权使该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我们必须看到仅就城市管理而论,职权的争议还是普遍存在的。⑤参见关保英主编:《行政处罚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第二个因素是行政职权的不明确。行政实在法是一个相对确定的东西,与之相比,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则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正是由于这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反差,便导致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常常存在管理过程中职权不明的情形。这种情形有时候表现为职权本身无法进行有效的界定,无法寻找出一个明确的管理范围。⑥即便是我们用行政法典则包括行政组织法典则和部门行政法典则对行政职权做出相应的规定,但仍然难以避免行政职权行使中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状态,因为法律本身就是存在模糊性的,而这样的模糊性便导致法律中权利和义务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导致行政主体权利行使中的职权不确定性。参见[英]蒂莫西·A.O.恩迪克特著,《法律中的模糊性》,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有时则是由于行政事态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有些行政事态本身就不必然是非此即彼的明确格局,而往往是相对模糊的。例如,以民政行政管理中的见义勇为为例,究竟什么是见义勇为并不是非常清楚地表现于我们面前的。这种行政事态的模糊性和职权的不明确性也是导致行政推诿的一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行政职权行使中的时间差。我们知道在法律上有一个溯及既往或者不溯及既往的概念或者原理,这实际上所反映的是法律规范与其所规制事项的时间差问题,即是说法律典则制定以后和制定以前是两种状态。制定以后的行政法是否能够调整以前的行政事务,或者已经废止的行政法典则对其生效时所设定的行政法关系还有没有法律上的意义等。这种时间差是行政法典则在调整行政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复杂情形,对这样的情形行政主体并不一定在每一个案件的处理中都会有一个正确的把握,这就为相应推诿行为的产生提供了空间。
第四个因素是行政职权行使中的空间差。在行政法中,地方立法所占的比重比其他任何部门法都要大很多倍,毫无疑问,这样的地方立法使行政法在调整行政事务时有了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同时我国行政系统中的机构设置就是以行政区划为前提条件的,即不同地区的行政主体管理不同地区的行政事务。与之相比,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案件则是一个动态的因素,它们并不必然与行政机构的这种划分予以对应。上列两个方面的空间概念必然使行政执法中存在职权行使中的空间差,而这个空间差与上列行政职权中的时间差一样,也是导致行政推诿的一个因素。
上述四个方面可以被视为是导致行政推诿的直接原因,但如果我们从深层分析,可以发现行政推诿还有下列一些原因。
第一,消极行政的意识原因。人们常常将司法权与行政权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认为司法权是一种相对消极的权利,不告不理就是人们对司法权消极性的描述。行政权则与之不同,它要求行政主体必须主动为之。一些学者在解读依法行政的概念时也认为行政机关积极行使行政权是依法行政的一个基本构成,行政机关适用法律应贯彻法律的目的并妥善运用公权力。①参见张家洋著:《行政法》,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230页。人们关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这种比较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在服务行政的理念之下,行政主体主动作出行政行为,行政主体通过自己的行为为公众积极创造利益是服务行政的必然要求。诸多国家在其行政程序法中甚至将积极行政作为行政程序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行政权的行使从总体上讲应当是积极的,这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在计划经济下行政系统对经济和市场的决定便可以看出。但是,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行政系统中也存在一些消极行政的状况,诸多行政主体在履行行政职权时考虑更多的是在行政过程中不带来较大的麻烦,尤其在《行政诉讼法》颁行以后一些行政主体担心由于积极行使行政行为而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便在可为与不可为的选择中选择后者而不是选择前者。这种行政上的消极情形便导致了我国行政法治中大量行政不作为的存在。对行政系统中的这种不作为,我国学界已普遍关注。行政上的不作为是行政主体消极对待行政职权的表现,不作为的泛滥必然与行政推诿的大量存在联系在一起。消极行政是行政主体对行政职权的放弃,对一个主体而论,它可以表现为不作为,而对于整个行政系统而论,就是对行政职权的一种放弃。可以说,在行政主体相互推诿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的诉求是无法引起重视的,当然也不能够作出正当化的处理。
第二,行政职权划分欠科学的体制原因。我国的行政机构体系是在推翻了旧的政权体系和行政体系之后建立起来的,即是说我国行政系统建立时,既没有相应的历史传统,也没有继承的行政法制度。具体讲,1949年我国建立行政体系并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职能划分时,我们是以苏联的宪法和行政法制为蓝本的,有些方面的行政法制度直接照搬和套用了苏联的行政法,②参见关保英著:《比较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尤其在行政机构体系的设置中,这种借鉴更加明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借鉴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也许它为我国迅速建立起新的行政系统提供了现成的参考答案。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采取“拿来主义”的行政机构体系建构模式,使得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从一开始就缺乏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分类,这一点对于行政机构的建构而言是非常致命的。因为我们知道科学的行政机构体系的建构必须建立在目标分解与综合的原理之上。所谓目标分解与综合是指在建构行政机构时首先必须对行政机构体系赖以存在的行政事态进行科学分类,把这些行政事态作类型化的处理,使不同类型的行政事态归到不同的行政目标之下。通过这样的分类确立行政事态的总目标、次目标、分目标、子目标等。①政府行政系统中的目标分解与综合原理应当说是来自于企业管理理论的。20世纪初,美国学者泰罗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在该著作中,泰罗将目标分解与综合原理作为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运用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而改革的理论前提就是目标的分解与综合。在法治发达国家,其行政机构的建立和改革都是以对行政事态目标分解与综合为前提条件的。行政机构的建立与已经分解好的目标有机统一,根据行政事态设置行政机构,这样的设计模式使任何一个行政机构都存在于一定的行政目标之下,使一个行政机构管目标相同的事。进一步讲,在这种科学的目标分解与机构设置的逻辑之下,行政过程中的推诿就不会发生或者较少发生。上面已经指出,由于我国行政机构在设置过程中没有采取这种科学化的路径,这便导致行政过程中同一个机构常常面对不同的行政目标,而同一个行政目标又常常在若干个行政机构的管理之下,这是造成行政推诿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行政系统自利的法文化原因。利益关系无疑是现代公法制度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行政系统既是由相应的机构实体构成的,同时也有存在于行政系统中的社会个体,这些社会个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务员,这样便使得行政系统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从理论上讲,行政系统是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因此,行政系统可以被视为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可以被视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可以被视为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者,还可以被视为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等。②从我国的传统行政法理论来看,通常认为行政系统所代表的是国家利益,但是近年来我国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有关利益代表的论点,如有人认为行政系统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有人认为是代表公共利益的,等等。在笔者看来,这是分析问题和观察问题的角度所使然,即站在不同的角度就可以得出行政系统代表不同利益的论点。上列利益关系和利益代表问题学界似乎都有相应的研究,但是行政系统自身是不是一个利益群体,尤其行政系统中的不同职能机构乃至于不同的行政机关是不是一个利益群体,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却很少有人关注并进行系统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经济学家曾有论断,就是政府行政系统及其公职人员不是经济的阉人,③这个论断在美国是相当流行的,它的基本意思是说政府行政系统在做行政决定时,乃至于在行政执法时,都必然会将自身的利益考虑进去,因为行政主体自身就是一个利益群体,显然这个论断有着充分的市场经济的渊源。即是说政府行政系统及其公职人员在行政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利益群体,本身就追逐着经济利益和其他社会利益。布坎南的这个论点在我国学界已经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尤其在行政管理学界有学者提出了行政系统的自利问题,④参见张颖举撰:《浅析政府自利性》,载《理论学习》2006年03期。就是说行政系统在行使公权力的同时也是一个自利性的群体,也不同程度地追逐着自己的利益。上列论断和观点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整个行政系统就是一个利益群体,就追逐相应的利益。每一个行政部门也是一个利益群体,也追逐着相应的利益。每一个行政机关也是一个利益群体,也追逐着相应的利益。行政主体对利益的这种追逐表明了行政过程中的一种非正常现象,那就是行政权的行使与经济利益常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我国实行双轨制的管理体制之下显得更加突出。在这样的格局下,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作出的一个重要权衡标准就是利益关系,换言之,如果某种行政行为有利可图行政主体就会积极主动地去做,反之,如果一个行政行为不会带来行政系统自身的利益,那么它就有可能对这样的行政行为予以排斥。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行政推诿存在的相对较深层次的原因。
第四,行政程序法缺位的法治原因。行政程序法与当代行政法治文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诞生,西方主要法治发达国家掀起了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热潮,例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国等都相继制定了自己的行政程序法:“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业于1946年公布施行,继而,西班牙于1958年、瑞士于1968年也已公布施行了行政程序法;日本于1964年、西德于1966年草拟了行政程序法草案。”⑤参见罗传贤著:《行政程序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9页。这些行政程序法在当时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形成了行政法治中的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线。肯定地讲,正是这些国家行政程序法典的大量制定,才奠定了20世纪中期以后的行政法治文明。我们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法治发达国家的这些程序法通过一套严密的行政程序制度使现代行政过程成了严格意义上的法治过程。我们知道,行政程序法确立了诸多新的行政法治原则,例如比例原则、听证原则、行政公开原则、不单方接触原则、救济原则等等。⑥参见罗传贤著:《行政程序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86页。这些原则使当代行政法有了一种新的具有时代精神的气质,在这些原则的作用下,形成了诸多非常好的行政法制度。笔者认为,这些行政法原则和行政法制度一方面使行政系统的组织机构有了确定的活动范围和严密的组织体系,尤其是行政系统的行政行为有了确定的程序规则;另一方面行政系统与公众的关系有了新的行为范式,例如公众诉求什么行政主体承诺什么等等都受严格的行为规则的制约。毫无疑问,在上列行政法治文明的格局之下,行政过程中的行政推诿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与之相比,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则显得较为滞后。众所周知,我国到现在为止还在就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究竟该走统一化的道路还是分散化的道路而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而其他国家的事实是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经对行政过程调整了近百年的时间。就我国现在的行政程序立法而论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白,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行政行为有相互对应的行政程序法典,即行政处罚行为、行政许可行为和行政强制行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缺位是行政推诿产生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四、行政推诿的法治对策
我国在《行政处罚法》第16条中有一个职权整合的法律条文,该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该条是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也是一个行政职权整合规则。就是通过该条,可以将分散于不同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统一在一个行政机构之下。该条颁布以后,国务院便发布了第63号文件,2002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决定》,这些行政法典则在当时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诸多相对比较混乱的现象。因为在这些规定出台之前,至少有四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履行城市行政管理的职能,这便出现了人们常说的“四个大盖帽管一个小草帽”的状况,也出现了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常常留有“真空地带”的状况。在当时对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进行相对集中时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行政执法中的推诿问题,但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立法经验为我们解决行政执法中的相互推诿问题提供了蓝本。我们可以将原来分散的行政职能进行整合,这非常接近于行政体制改革中目标分解与综合的原理。但是,在笔者看来,行政执法中的推诿不能仅仅通过一个机制来解决,而应当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予以进行。笔者试提出下列若干法治对策:
第一,以宪法精神统摄行政法治。法治国家的建设有诸多方面的含义,有诸多层次的法治体系需要进行相应的构建。这些不同层次的法治体系可以作出下列若干区分。其一,宪政层面上的法治建设。现代法治国家都有一部完整的宪法,而宪法作为根本法基本上形成了一国的宪政格局。我们知道,宪政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的含义是指通过宪法典则处理国家政权体系与公民的关系,既是说公民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关系是宪政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应当说它是一个核心内容;另一个层面的含义是指通过宪法典则使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有一个合理的职权划分。例如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职权划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划分。①参见[捷]维克托·纳普主编:《各国法律制度概况》,高绍先、夏登峻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其二,法律层面上的法治建设。就是用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建立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机制,这种社会治理机制首先是一种法律机制,是通过法律体系和法律典则强化了的机制。我国在1999年宪法第13条修正案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该规定实质上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做了定位和定性。其三,行政法治层面上的法治建设。行政法被认为是小宪法,即是说宪法规定一国政治体制和政权体系的基本轮廓,而行政法则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从这个角度讲,行政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它是仅次于宪法的部门法。它的这种特殊地位就使得行政法治是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另一个单独的内容。其四,其他层面上的法治建设。这包括行政法之外的其他部门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上列四个范畴应当是一个体系化的东西,应当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治理国家的法治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宪法处于指导地位。就我国而论,行政法治的建设必须严格受制于宪法,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笔者注意到我国近年来在行政法治建设中相关的制度设计并没有与宪法保持最大限度的契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宪法来统摄行政法治建设,就必然能够理顺在行政法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原则,必然能够理顺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处理关系的原则,而这便能够使行政推诿在行政执法中减到最低限度。
第二,以体制行政法完善职权归属。所谓体制行政法是指相对行政系统的宏观构成和微观构成以及相关权利分配作出规定的行政法规范的总称。体制行政法与政府行政体制有关,它不是政府行政系统某个单一方面行为的规范,而是将行政系统作为一个事物来看待所涉及的所有行为规则。①体制行政法应当包括下列方面的内容:一是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关于国务院职权的规定;二是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例如我国1982年制定了《国务院组织法》;三是国务院部门组织法,例如我国1949年制定了《国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1955年制定了《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等;四是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五是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组织法,如我国解放初期制定的《省市劳动局暂行组织通则》、《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等;六是民族自治区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组织法;七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行政组织法等。②应当说,上列体制行政法在我国都或多或少地规范了行政系统的职权及其分配。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笔者上述所列举的有关行政体制法诸多已经成为历史,诸多都是在我国解放初期制定的,而它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而就目前我国有关体制行政法的立法状况来看,其关于行政系统职权的设计和分配还存在着非常大的缺陷。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来看,它们仅仅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范围,而且采取了概括规定的方式,③即是说在这个规范地方行政组织权力的系统性行政法典则中竟然没有行政系统中职能部门权限的规定。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正是由于行政系统中职权规范上的缺陷才导致了行政过程中的推诿。基于此,应当在我国建构完整的行政体制法体系,使规范行政组织的法律典则成为一个整体,并使每一个这样的法律典则中都有具体的部门职权的划分和规定,这就可以从源头上解决行政推诿问题。
第三,以行政程序法规范执法模式。我国1996年制定了《行政处罚法》,2003年制定了《行政许可法》,2011年制定了《行政强制法》,这三部行政法典被认为是三个针对具体行政行为制度的相对完整的行政程序法典。《行政处罚法》对有关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则作了详细的规定,而《行政许可法》则对行政许可的程序作了规定,《行政强制法》更是把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予以统一。从行政程序法立法道路上来讲,我国走的是分散立法的道路,但不争的事实是上列三部行政程序法典使相关的行政行为有了完整的程序规则。毫无疑问,在这些行政行为具有程序规范的前提下,行政推诿发生的几率就会相对少一些,因为行政主体一旦在实施这种行政行为中有所推诿,就有可能构成程序上的违法。这一点在行政处罚管辖的规定中非常明显。④进一步讲,行政行为程序规则的严谨性与该行政行为在执法过程中发生推诿的概率是成反比例的,即是说某一个行政行为的程序越严谨该行政行为在作出时发生推诿的概率就越低,反之某一行政行为越是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则就越容易发生行政推诿。这应当是一个非常好的立法经验,而这个立法经验提醒我们,应当在我国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通过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使所有行政行为都有可以遵循的程序规则。如果我们能够在立法上达到这一点,那么每一个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就必然被关进了程序的笼子,而这种程序上的约束力则会大大减少行政推诿的发生。
(责任编辑:陈 仪)
A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Prevarication
Guan Baοying
Administrative prevarication is a defective administrative act which commonly exists in practice. It influences the administration integration,delays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creates internal conflicts. Its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and its harmfulness is not less than ultra vires. However,both the theory and legislation of China pay close attention to ultra vires,but ignore the administrative prevarication. It is an unavoidable question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to put the administrative prevaricationinto the regulation of category. The administrative prevarication cannot be resolved only by one mechanism,it needs a series of mechanisms. The spirit of Constitution shall govern the rule of administrative law,administrative organic law shall be improved to clarify the functions of respective administrative agency,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shall be enacted to regulate the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of law.
Administrative prevarication;Negative administration;Standardize law enforcement
D912.1
A
2095-7076(2014)01-0078-12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上海市一流学科(行政法)”、“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专项(行政法)”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