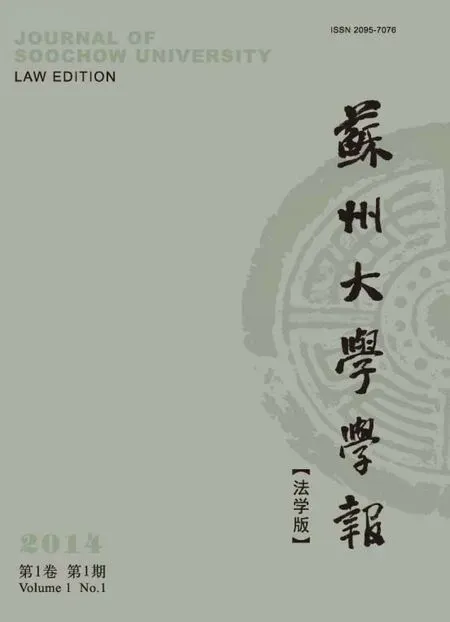中西刑法思想史中的共同犯罪问题探源
赵晓耕孙 倩
中西刑法思想史中的共同犯罪问题探源
赵晓耕*孙 倩**
对于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关于中国共犯体系属于正犯、共犯区分制,单一制,还是双层区分制的争论,不能仅仅局限于类比我国刑法与欧洲大陆各国刑法条文,而应该从各自的传统出发寻求根源。中国共犯体系源于中国传统律例“共犯罪分首从”的罪刑均衡价值,而欧洲大陆各国刑法共犯体系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逻辑前提下推演出来的,这背后是秩序性思维与规范性思维的不同。可见,中国刑法学界关于中国共犯体系归属的争论正是秩序性思维与规范性思维碰撞的结果。
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规范性思维;秩序性思维
在萨维尼对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批评中,有两段精彩的评论:对于法典第6条包含的这个规则:“私人协议不得变更公法”(jus publicum privatorum pactis mutari non potest),有学者称“‘公法’(jus publicum)并非意味着关涉国家的法律,而是指每一部法律,每一部关乎公序良俗(jus publice stabilitum)的法律。”有学者称:“如果说公法就是与私法相反的立法规定的话,那么公法就是关注社会甚于关注个体的法律。”对此萨维尼评论道:“我却欲置一问,究竟这一一般规则(私人协议不得变更公法)与上述问题(学者的讨论)何涉,罗马人是如何理解这同一规则的?接着,如果这一规则与上述问题具有一定的关联,如何可能证明从(古罗马人)巴托洛斯(Bartolus)的一段话(《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者之一波塔利斯将这段话概括为“私人协议不得变更公法”)中而来的、罗马人使用的语言结构,他(巴托洛斯)和罗马法学家乃得归为一类吗?的确,这才叫Tanquam e vinculis sermocinari(确无任何沟通之交谈呢!)。”对于法典引证罗马法关于离婚的规定“婚姻不可能仅由一方即可解除,而必须经由双方同意始可”,萨维尼批评道,法国的立法者们将古罗马的离婚史弃置不顾,“在罗马人中,经由双方同意的离婚不过是过错原则的结果”,因上述引证,法国的立法者们“误解了整个罗马的离婚史,对法典草案的讨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每个人反感”。①[德]弗里德尼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9页。
在此,萨维尼向我们展示了历史性思维的独到之处,对每一种制度,我们只有把它放入到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与创造它运用它的人联系起来,将与此相关的整个制度体系联系起来,进行体系化的观察,才不至于产生谬误。本文正是试图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于刑法学界争论的区分制共犯体系与单一正犯体系及中国共犯体系的归属,进行一番梳理。
一、共犯体系之争:中国共犯体系之归属
根据学界通说,在刑法中,应受刑罚的犯罪行为,有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两种形态。刑法分则正是针对单独犯罪这种典型犯罪形态而设定的。①[日]高则桥夫:《共犯体系与共犯理论》,东京成文堂1988年版。而对于共同犯罪,即多人共同参与实施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从构成要件这一犯罪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基石出发,就必然有的共同犯罪人实施了法定构成要件的行为,而有的共同犯罪人实施的是法定构成要件以外的行为。这便是大陆法系刑法学者所称的犯罪参与形态的不同。②本文大陆法系是指欧洲大陆法系,因日韩等国法律体系最初均移植自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根据犯罪参与形态的不同,将共同犯罪行为区分为实行犯、帮助犯和教唆犯。③参见钱叶六:《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所谓区分制共犯体系是指将参与共同犯罪的人区分为正犯和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分别规定不同的刑罚,共犯刑罚轻于正犯,以《德国刑法典》、《日本刑法典》为代表。而单一制共犯体系,是指对于正犯、共犯不加区分,均视为正犯,规定同一刑罚,以《意大利刑法典》和《奥地利刑法典》为代表。④参见江朔:《单一正犯体系研究》,载《刑事法评论》2009年第1期。同时,单一正犯体系又可分为形式的单一正犯体系、⑤即刑法明确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外,“当多人实施同一犯罪时,每人按该罪的刑罚处罚”(《意大利刑法典》第110条),适用统一的法定刑,并不意味着对各犯罪参与人适用统一的刑罚,由法官来具体决定各犯罪参与者应适用的刑罚。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功能性单一正犯体系。⑥指虽然区分正犯与共犯,但各犯罪参与者量刑上均适用正犯之刑罚,由法官根据具体情节裁量刑罚,并不必然导致共犯刑罚轻于正犯,即奥地利刑法学者Kienapfel所言“单一正犯体系并不是要在构成要件的层面实现个别化,而是通过富有弹性和精炼的量刑规定来实现刑罚个别化。”参见江朔《关于单一正犯体系的若干辩驳》,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5期。从大陆法系共犯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单一制共犯制度模式是为解决区分制共犯模式所面临的量刑不均衡困境而产生的。⑦参见蔡墩铭:《现代刑法思潮与刑事立法》,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295-298页。
(一)中国共犯体系之归属:区分制、双层区分制抑或单一制
根据中国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人有主犯、从犯、胁从犯及教唆犯。很明显,这不是按同一逻辑进行的区分。主犯、从犯、胁从犯的区分是按共同犯罪参与程度进行的划分,我国学界统称之为作用分类法;而教唆犯是按共同犯罪参与人类型进行的划分,学界统称为分工分类法。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我国共犯制度模式为区分制,⑧王志远:《共犯制度的根基与拓展:从“主体间”到“单方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的分工分类法,我国共犯区分制是作用分类法。⑨参见马克昌:《有关共同犯罪的几个争议问题》,载《现代法学》1990年第5期;张明楷:《关于共犯人分类的再思考》,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共犯体系属于单一制共犯体系,不从构成要件的立场来区分正犯与共犯,将所有共同参与犯罪的人都视为正犯,量刑时再对各共同犯罪人分别予以考虑。⑩参见刘明祥:《“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之解释》,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江朔:《区分制共犯体系的整体性批判》,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6期;江朔:《单一正犯体系研究》,载《刑事法评论》2009年第1期。还有学者将德日等大陆法系仅按参与人类型(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划分的区分制称之为“单层次区分制”,而将中国刑法共犯体系称之为“双层区分制”,即分别对参与人类型(教唆犯)与参与程度(主犯、从犯、胁从犯)进行区分,或称在定罪层面采分工分类法、在量刑层面采作用分类法的双层次区分制。⑪参见钱叶六:《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赵志轩:《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标准与立法完善》,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二)争论的背后:中西共同犯罪人分类方法迥异
谈到正犯共犯区分制或是单一制,或是双层区分体制,就不得不先理清区分或不区分共犯制背后所依凭的共同犯罪人分类。
1.明确概念:正犯即实行犯
根据学者考证,“正犯”一词在《大清律例·刑律篇》已有,近代中国刑法理论“正犯”一词源自日本,日本学者将德国刑法中主要共同犯罪人译为“正犯”。⑫杨兴培:《共同犯罪的正犯、帮助犯理论的反思与批评》,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8期。在《钦定大清刑律(草案)》、⑬[清]沈家本等撰:《大清刑律总则草案(17章)》,法律馆1907年铅印本,第40-42页。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暂行新刑律》、①[日]冈田朝太郎:《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民国大学、中华大学1913年版,第40-42页。以及国民党政府1928年刑法②张季忻:《刑法总则概要》,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88页。、1935年刑法都沿用这个词。③《中华民国刑法修正案》,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5年版,第7-8页。这与晚晴沈家本主持修订刑律,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有关,而民国刑法基本继承晚清刑法。④参见赵晓耕:《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460页。从《德国刑法典》(1975)、《日本刑法典》(1974)的规定来看,正犯是指自己亲自实施犯罪的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也认为正犯即实行犯。⑤参见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页;陈兴良:《论我国刑法中的共同正犯》,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4期。英文中的主犯(principal offender),确切含义是指在现场亲自实施犯罪的人,⑥参见江朔:《论美国刑法上的共犯》,载《刑事法评论》2007年第2期。与德日的实行犯含义相同,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主犯(起主要作用)含义完全不同。革命根据地时期的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区分为藏匿者、帮助犯、实行者、附和被胁迫者;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区分为实行犯、教唆犯、从犯(帮助犯或协助犯);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区分为主犯、正犯、从犯。从上述几个文件对正犯的表述可知,正犯即实行犯,而实行犯是主犯的一种形式。⑦参见杨兴培:《共同犯罪的正犯、帮助犯理论的反思与批评》,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8期。
2.西方共犯制度的发展:从严格区分实行犯与非实行犯到模糊二者的界限
从共犯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将共同犯罪区分为正犯与共犯的思想根源在于实行犯与非实行犯的区分,在欧洲大陆中世纪世俗政权只关心犯罪行为有无及其结果,因此实行行为要比非实行行为处罚重,⑧参见陈兴良:《罪刑均衡的立法确认》,载《检察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法]博里康著:《法国二元论体系的形成和演变:犯罪——刑事责任人》,朱琳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欧洲大陆的共犯理论;而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的区分,根据学者研究,源于中世纪意大利法学注释罗马法的成果,将共同犯罪人区分为亲自实行犯罪的实行犯和除此之外的教唆犯和帮助犯。⑨参见蔡墩铭:《现代刑法思潮与刑事立法》,台湾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295-298页。
从学说史上观之,德日刑法学界的正犯、共犯区分理论最初采用的是严格的以构成要件为中心的形式客观说,认为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的为实行犯,不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的为共犯。这一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贝林的构成要件理论。⑩贝林构成要件理论关于犯罪形态与犯罪类型的划分指出,符合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的行为为独立的犯罪类型,而未遂犯、教唆犯、帮助犯虽与法定构成要件存在联系,但不符合法定构成要件,为“不独立犯罪类型即犯罪形态”,有自己的“指导形象”,即“实行行为的开始”、“唆使他人”、“通过建议或行动提供帮助”,“但是,这些指导形象是不独立的”,“自身也是空洞的,只有与法定构成要件联系时才具有刑法含义”。贝林进一步将犯罪形态区分为未遂形态、共犯形态(帮助犯、教唆犯)。在这里,贝林认为犯罪形态属于因其形态而具有可罚性的行为,其可罚性是相对的,只有与行为内容(法定构成要件)联系起来,才能发现其可罚性。参见[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1页。遵循贝林以构成要件理论为犯罪论基石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就不得不采用这种区分制的共犯体系。
经实践检验,贯彻形式客观说所区分的,处刑重的犯罪类型之正犯与处刑轻的犯罪类型之共犯,往往导致罪刑失衡。因为实践中往往出现帮助犯、教唆犯的行为比实行犯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大的情况。故而,现在德日区分理论逐渐转向实质客观说,其中的通说为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即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不应限制于法律规定的形式,而应根据行为的实质,对构成要件行为起支配作用或重大影响的为正犯,其他为共犯。实质上已经放弃了构成要件理论,走向了正犯“主犯化”。⑪参见张红艳:《论德日刑法的犯罪支配理论与共谋共同正犯》,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9期;郝守才:《共同犯罪人分类模式的比较与优化》,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钱叶六:《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3.中国共犯制度的发展:共犯罪分首从从埋葬到复活
共犯罪分首从自唐律定型后,至宋元明清律相沿未改。清末沈家本修订刑律,在共同犯罪上,放弃传统首从犯的区分,而采用德日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的分类方法,民国刑法予以继承。但共犯罪分首从的区分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复活,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人民政府颁布的法律中出现了首要、从犯、胁从犯或主犯、正犯、从犯等模糊的分类;建国初期颁布的几部单行刑事法律将共同犯罪分为首要分子与其他参加者,及被胁迫诱骗参见犯罪的。①参见马克昌:《刑事立法中共同犯罪的历史考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1979年刑法“参考了外国和我国古代共同犯罪的立法例”,②马克昌:《刑事立法中共同犯罪的历史考察》,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将共同犯罪人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及教唆犯。1997年刑法未更改。
顺着萨维尼提供给我们的思考方法,我们不禁要问:到底大陆法系国家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共犯体系的,这一共犯体系在大陆法系国家是怎样的发展起来的?区分制共犯体系与单一制共犯体系都是本着怎样的逻辑思路推演出来的,是为解决什么问题而出现的?可否不顾历史,将我国共犯体系简单归入大陆法系的区分制或单一制共犯体系?
二、大陆法系共犯体系贯彻的罪刑法定原则:使命的变迁,悖论的产生
从上文对于大陆法系共犯体系发展脉络的梳理中,我们知道,谈到共犯问题,就不得不谈符不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问题。③即使是二十世纪大陆法系共犯理论针对区分制量刑不均衡问题分化出的单一制共犯体系及区分制共犯体系内的新秀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也是在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上下功夫,即扩张正犯概念、对符合构成要件行为起支配作用的为正犯不起支配作用的为共犯。参见郝守才:《共同犯罪人分类模式的比较与优化》,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而构成要件符合性行为的核心是构成要件,即刑法分则类型化的行为,“法定构成要件是刑法的根源概念,其他概念无一例外地发源于这个概念”。④[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贝林的构成要件理论使罪刑法定从立法转向了司法,使犯罪论与罪刑法定原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⑤侯国云:《德日犯罪构成理论批判》,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67页。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而大陆法系的另一个分支俄中犯罪构成理论,据我国学者考证是源于斯鸠贝尔和费尔巴哈的犯罪构成理论⑥侯国云:《德日犯罪构成理论批判》,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64页。。另据我国学者对构成要件理论从诉讼概念转化为实体概念的考证,“罪刑法定原则是构成要件的存在前提,离开罪刑法定的构成要件是没有意义的”,⑦王充:《构成要件的历史考察——从诉讼概念到实质概念的嬗变》,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5期。这也是贝林所要表达的“法定构成要件的内容是空洞的,它不能确定自己的内容,具备构成要件功能的千百个具体内容——简称‘构成要件’——不是由概念探讨出来的,而是从独立的犯罪类型中推导出来的”,而犯罪类型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的类型性行为。⑧[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所以,贯穿整个大陆法系共犯理论的原则即是罪刑法定原则。⑨罪刑法定原则经历了绝对罪刑法定到相对罪刑法定的发展,随着英美法系有无罪刑法定的讨论,通过英美学者的努力,正当程序原则也纳入到广义的罪刑法定的概念内。本文的罪刑法定原则限于最初意义上的绝对罪刑法定原则,不包括后来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及英美法系的正当程序原则。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详见彭凤莲:《中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百年变迁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7页。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由刑罚到犯罪,以刑统罪
1.刑法学理论上,通过刑罚厘定犯罪
刑罚是一种易感知的力量,⑩[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第47章版)》,黄凤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18世纪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开篇前三章论述的均是刑罚权的问题,被后世学者称为明确提出罪刑法定原则的贝卡里亚名言的原文是“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⑪[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第47章版)》,黄凤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又没办法落实的口号!在这里犯罪是先验地存在的,而不是由法律规定的,法律需要规定的是刑罚。接着在第六章“刑罚与犯罪相对称”中,贝卡里亚提出制定一个有明确刑罚尺度的刑罚阶梯,⑫即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由高到低排列的阶梯,其中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称之为犯罪的行为,与此对应,也要有一个由强到弱的刑罚阶梯,明智的立法者要标出刑罚尺度的基本点,使一定的越轨行为与刑罚相对应。“任何不包括在上述限度之内的行为,都不能被称为是犯罪,或者以犯罪论处。”⑬[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第47章版)》,黄凤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在这里贝卡里亚是以刑罚来厘定犯罪的,从法律处罚的行为是犯罪的层面界定犯罪,使得犯罪摆脱了中世纪宗教意义上的罪孽的意味,犯罪概念中性化,并开始向世俗法律靠拢。①[法]博里康:《法国二元论体系的形成和演变:犯罪——刑事责任人》,朱琳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3页。受这一观点的影响,18世纪末欧洲大陆的刑法立法已经意识到“消除刑法中的严厉刑罚,给法官提供尽可能详细的规定,应当对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作出规定”。②[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C·J·A·米特迈尔:《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犯罪论发展的端倪。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那么也必须同时规定与刑罚相称的犯罪,为保证刑罚的适用依法,那么就要为法官规定具体可操作的指标——犯罪构成。
贝卡里亚的思想被19世纪的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吸收,发展成“无法无刑”(Keine Strafe ohne Gesetz;Nulla poena sine lege)、“无刑无罪(”Keine Strafe ohne Verbrechen;Nulla poena sine crimine)、“有罪必罚(”Kein Verbrechen darf straflos bleiben,nullum crimen sine poena),从这一原则出发,费尔巴哈提出犯罪的成立要求行为符合一定的类型,即犯罪类型,“犯罪是一个刑法中规定的违法或者说由刑法加以威慑的与他人权利相违背的行为。”与此相关的还有,犯罪构成(构成事实)相关的不清晰的概念:犯罪的可能的主体、犯罪的必要条件、违反刑法的不同表现形式。③[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C·J·A·米特迈尔:《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4页。
明确提出作为犯罪论概念基石的构成要件理论,并使犯罪论实现体系化发展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刑法学家贝林。贝林对犯罪概念的定义:“行为符合了刑法规定才是犯罪”。④[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只有具有法定刑的可罚性行为类型才属犯罪,而只有处于刑罚威慑范围内的类型性行为才是可罚的。”⑤[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在这里贝林通过类型性行为使得贝卡里亚的“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具备了可操作性。贝林提出“新的刑法学思考方法基于实证法进行规范评价”。⑥[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因此,“就法律强制我们进入犯罪类型并因而引入构成要件中而言,法律本身就是‘形式的’,在此方面,构成要件肯定无可非议”。⑦[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在犯罪类型化的基础上,贝林将模糊不清的“犯罪事实”改造为“客观记述的构成要件”,“用以指导刑法中的类型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推动了犯罪论的进一步发展,⑧“此后的刑法理论上,无论是迈尔的法定构成要件体系,还是梅茨格尔的不法构成要件体系,均以构成要件符合性为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参见[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自贝林的构成要件理论取得支配性地位,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段论成为指导德国甚至整个大陆法系犯罪论的基石。结合着前辈费尔巴哈将刑法总论哲学化的努力,⑨[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C·J·A·米特迈尔:《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犯罪论产生并脱离了刑罚,进而取得了支配刑罚的地位。从此定罪,即对犯罪定性的问题,即某一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构成要件的问题,成为困扰着一代又一代大陆法系刑法学者与法官的梦魇。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通过以刑统罪,欧洲大陆刑法学家从刑罚的意义上界定犯罪,进而抽象出犯罪类型、构成要件,发展了犯罪论。这都是19世纪才发生的事,故而定罪问题也只是19世纪才出现。
2.实在法上,以刑统罪
不仅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大陆法系各国法典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751年德国《巴伐利亚刑法典》最先规定的是刑罚。⑩陈惠馨:《1751年德国〈巴伐利亚刑法典〉——德国当代刑法的起源》,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1期。1791年《法国刑法典(草案)》首创刑法总则、分则的体系,在总则部分规定的是刑罚的一般原则,包括刑罚的种类、累犯加重、犯罪年龄对刑罚的影响,并为以后的1810年《法国刑法典》所继承。⑪陈兴良:《罪刑均衡的立法确认》,载《检察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周少元:《从〈大清新刑律〉看中西法律的冲突与融合》,载《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这与中国传统律例以刑统罪的原理是一样的。《唐律》中名例律是关于刑罚的种类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的规定,①王志远:《共犯制度的根基与拓展:从“主体间”到“单方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页。自唐律疏议以来的中国历代律典名例律规定的均是刑罚的一般原则,这里沈家本《钦定大清刑律》奏疏中的概括极为准确“刑律总则为全篇之纲领,分则为各项之事例”。②[清]沈家本:《钦定大清刑律》,1911年刻本。费尔巴哈关于成文刑法的定义是“成文刑法是特定国家(德国)的实在的关于刑罚权的科学”。成文刑法由总论、分论两部分组成,总论是“关于违法行为的处罚的一般原则”。③[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C·J·A·米特迈尔:《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刑法总论部分在费尔巴哈这里开始有了新的变化,费尔巴哈将其哲学观贯穿于总论之中,成文刑法成为关于刑罚权的科学之后,在刑法总论中派生的法律原则开始关注犯罪的本质(包括犯罪的主体、犯罪的必要要件、犯罪的法律后果)、刑法的特征及适用、刑罚的本质及种类。而不再仅仅是关于刑罚的一般原则了。④[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C·J·A·米特迈尔:《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费尔巴哈所做的上述努力则是为了“给法官提供尽可能详细的规定”,“谨小慎微地致力于排除法官擅断的危险”。⑤[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C·J·A·米特迈尔:《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二)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必然性:西欧大陆中世纪封建制度下刑罚权的不统一
在理清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脉络后,顺着萨维尼提供给我们的思路,我们不得不关注罪刑法定原则在西欧大陆产生的社会原因。而罪刑法定的发展导致犯罪论大行其道的背后又预示着什么,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发展脉络,或许关注一下这些理论、概念背后的人,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思考。
正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惠馨教授所指出的,德国刑法理论强调罪刑法定主义,主要是在回应18世纪以前德国各邦刑法为习惯法的本质。⑥参见陈惠馨:《德国法制史——从日耳曼到近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就是说德国罪刑法定主义背后是法律统一、国家统一的呼声。其实这不仅仅是18世纪德国民众的呼声,更是整个中世纪欧洲大陆民众的呼声。身处18世纪意大利的贝卡里亚便是明证。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欧洲中世纪让民众那么渴望罪刑法定呢?
1.欧洲大陆中世纪封建制下司法权的不统一:各封建领主掌握绝对的司法权
欧洲大陆中世纪的社会秩序被西方学者概括为封建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国王的附庸的附庸不是国王的附庸”。⑦即通过授予土地而建构起阶层关系,国王将土地封邑给诸侯、诸侯将采邑封邑给伯爵或自由人,伯爵或自由人将采邑封邑给骑士。与英国中世纪封建制完全不同,在英国,“国王的附庸的附庸仍是国王的附庸”,所有的封臣均需向国王宣誓效忠,而后英国通过颁布司法令状、建立民事诉讼高等法院受理全英格兰民事案件初审,建立王室法院统一刑事管辖权,从而实现了司法权的统一,形成了适用于全英格兰的普通法。参见程汉大:《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49页;[英]爱德华·甄克斯:《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屈文生、任海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在德国,整个中世纪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存在着很多邦或地方的法律,在帝国、区域领主、城市或乡村,均有各种法庭存在,这些法庭适用的法律是各自的习惯法,⑧参见陈惠馨:《德国法制史——从日耳曼到近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165、247页。各个封建领主都有自己的“督察”和“管事”,掌握绝对司法权。⑨参见[英]爱德华·甄克斯:《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屈文生、任海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7-90页。
在法国,司法权由各封建领主行使。13世纪晚期的法国著作《王室法令集》很好地诠释了封建领主的司法权:在采邑界限内,只有领主的禁令(ban)有效,其余一律无效。“国王不可以在男爵领域内颁布任何禁令,男爵也不可以在封臣的领域内发布禁令”。1315年的法国卡贝先王朝的第12个国王路易十世明确承认“封建领主在各类案件中享有绝对的刑事管辖权”,众多的封建领主通过设立“八柱绞刑台”(eight-pillare gallows),处置重罪,甚至连“不可赎之罪”(欧洲中世纪各国将侵犯国王利益的犯罪称为“不可赎之罪”)也脱离了国王的管辖。封建法庭几乎不给“国家”法院留任何空间。⑩参见[英]爱德华·甄克斯:《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屈文生、任海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7-97页。虽然在十六世纪后,随着法国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司法权由国王行使,①参见[法]博里康:《法国二元论体系的形成和演变:犯罪——刑事责任人》,朱琳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英]爱德华·甄克斯:《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屈文生、任海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并建立起了巴黎高等法院,受理部分全国境内的上诉案件,但是王室司法权可以转让和世袭,王室财政署通过出卖官职敛财,而王室法官仅热衷于扩大王室司法权的管辖范围。所以,中世纪晚期法国王室法院的世袭制与贪赃枉法,使得国家司法权仅仅是昙花一现。②参见[英]爱德华·甄克斯:《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屈文生、任海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而在南欧,自11世纪后半期以来,王室斗争在意大利就没有停止过,北意大利被分成若干城市共和国,后来发展成公国;与德国中世纪晚期一样,进入19世纪以来,地方割据愈演愈烈:南部是一个个封建王国、中部是教皇国,北部的意大利王国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③参见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页。王室法律不仅认可王室统领及管事的司法权,还认可封建领主以及经选举产生的司法官的司法权;封建贵族对其封臣拥有审判的绝对权,死刑案件也不例外;在这里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司法权。④参见[英]爱德华·甄克斯:《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屈文生、任海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3页。
统一适用于全国的法律始终没有在欧洲各国出现。在德法,13至16世纪,主要的法律有市镇法、地方法、封建法、王室法,但没有国家法,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保持着相似的情况。⑤参见[英]爱德华·甄克斯:《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屈文生、任海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2.司法权的不统一下的刑罚权不统一的恶果
欧洲大陆中世纪各国分裂割据与其封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重建王国后,日耳曼人的习俗与罗马人的习俗相互影响而形成了封建制这种君主与贵族并存的社会秩序,在这里,法律形态是一种约定,法律的特征是约定,“约定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比强制命令更好得多的模式”。⑥[英]H. L. A. 哈特 :《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 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这已是西方学者的共识。在此模式中,司法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形态”。⑦[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芳,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这一“司法统治”模式与封建制本身所隐含的互惠式契约直接相关,封建本身即是一个“庇护——效忠”契约,领主为附庸提供庇护,以换取附庸的臣服和效忠。⑧参见陈颐:《立法主权与近代国家的建构:以近代早期法国法律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国王“整体而言,与人民没有直接的政治接触,因为对他们的司法是通过无数层的分封制而归附施行的”。⑨[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芳,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5页。这一分散的统治模式直接导致的是司法权不统一,司法权不统一也就意味着刑罚权不统一,刑罚权不统一也就意味着每个封建领主均掌握着生杀大权。
这里仅以德国中世纪关于叛国罪的刑罚为例做一说明。与罗马法意义上的国家内的臣民消灭、危害国家的行为不同,在日耳曼法中,叛国的内涵要宽泛得多,不仅包括“针对国家和统治者的行为”,还包括“针对人们应当给予特别忠诚之人的行为”。在中世纪,罗马法观点与日耳曼法观点相融合,叛国学说涉及领地法及摄政者的内容逐渐丰富,并且“尝试通过严厉的刑罚法规来寻求保护其人身不受攻讦”,从而“那些从针对国家的攻讦中被分离出来的最为严重的情况就越多”。而在叛国的学说中,没有一部通用全德的法律对其做出全面的规定,所以各封建领地法庭不得不以罗马法及当地习惯法为渊源,通过古老罗马法的法律拟制,使得一些没有可比性的犯罪也置于其中,如后来视为职务犯罪的行为、军事犯罪行为、违警罪、蔑视法庭、侵害国家权力的尊严、形象和名誉等等。而当时各封建领地的法律均没有意识到将叛国行为进行详细描述,没有就“叛国罪提出其构成要件”。⑩[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C·J·A·米特迈尔:《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61页。
如果没有统一的法律、没有统一的标准使人们不能明确知道什么是叛国罪,还不能令我们心惊胆战的话,那么看一下费尔巴哈时代各封建领地的刑法规定,我们就会明白,那个时代罪刑法定是多么的必要。根据德意志境内各王国法律规定,①《普鲁士刑法典》第97条规定,“从暴力上根本改变国家宪法,或者行为是针对国家元首的生命或自由。”第100条规定背叛州的行为,“企图将隶属于国家的州、军队、主要要塞处于敌国的暴力之下(对该行为的处罚是车磔之刑);旨在有利于国家之敌人的背叛行为(尚未实施或国家没有遭受损害的,处6年以上10年以下监禁)。”《奥地利刑法典》第52条规定构成叛国罪的行为有,“危害国家元首人身安全;实施旨在暴力改变国家宪法、引入或者增加针对国家的外来危险行为——行为的实施既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秘密的,既可以与具体个人一起实施,也可以表现为教唆、招募和侦查行为。”第53条规定,叛国罪的刑罚(即使行为未遂)是死刑。《巴伐利亚刑法典》叛国罪具体行为:“对国家元首人身安全的攻击;对国家独立性的攻击。”详见[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C·J·A·米特迈尔:《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62页。叛国罪包括背叛国家与背叛州的行为,刑罚是五马分尸,将女性犯罪人溺死,财产收归国库,儿童应当承担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刑事责任。而在德意志帝国解体后,“每一个Hochverrat(背叛国家)现在都是Landeshochverrat(背叛国家)”。1836年8月18日的德意志联邦决议宣布:“针对联邦或者针对联邦宪法的攻击行为,同时也是针对每一个具体邦国的攻击行为。”普鲁士早在1834年就宣布,“旨在暴力改变德意志联邦的宪法的行为,应当视为针对普鲁士的叛国行为。”《萨克森刑法典》第82条规定,“针对德意志联邦的独立性和宪法的攻击行为,视同针对萨克森的叛国行为”,等等。②[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C·J·A·米特迈尔:《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62页。这里我们要知道的是,费尔巴哈时代“所有新颁布的刑法典都承认,如果刑法未事先加以规定以刑罚处罚,任何行为不得被科处刑罚”,③[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C·J·A·米特迈尔:《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已经比十八世纪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让我们回到十八世纪以前,在没有统一国家的情况下,德意志境内有多少个拥有绝对司法权的王国,每个王国领地内又有多少拥有绝对司法权的州,每个州领地内又有多少拥有绝对司法权的封邑。进而扩大至整个欧洲大陆的中世纪,在那个每个封建领主都拥有绝对司法权的时代,在那个没有对叛国罪进行“详细描述”的时代,在那个诸侯割据战争频仍的年代,会有多少人因为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而更为可怕的是罗马教廷也来分一杯羹,在欧洲中世纪,罗马教会与世俗政权分别统治着欧洲中世纪人们的灵与肉,世俗政权只关心犯罪行为及其结果,④参见陈兴良:《罪刑均衡的立法确认》,载《检察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罗马教会只关心犯罪意志,罪孽本身即是犯罪。⑤参见[美]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杨宁、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法]博里康著:《法国二元论体系的形成和演变:犯罪——刑事责任人》,朱琳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因此在教会法庭的判决下,“欧洲土地上洒满了人的鲜血;他把活生生的人体投入火中”。⑥[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第47章版)》,黄凤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这才是贝卡里亚“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这声呐喊的社会背景,这句话寓意是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刑罚权。⑦[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第47章版)》,黄凤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三)罪刑法定的使命:由统一刑罚权到统一定罪
结合上文的社会背景,通过贝卡里亚、费尔巴哈、贝林从刑法理论到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努力,我们看到的是学者为统一法律适用背后的统一刑罚权的努力,他们不是凯撒大帝,他们不能金戈铁马,一统欧洲,而拿破仑帝国的昙花一现,也使他们认识到武力统一的无望。在各级封建领主掌握生杀大权、天主教会意志论罪的封建时代,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也只有借助于那美好的哲学理论与自古罗马流传下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ius”和“lex”来为自由民免遭屠戮尽一点绵薄之力。⑧经学者考证,Ius主旨是权利,lex是指将各种权利明确化的契约。在罗马法,以致整个西方法律文化中,ius、lex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参见费安玲:《罗马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他们无力直接抨击法官背后的各级封建领主,所以他们喊出了防止法官擅断的口号。贝卡里亚提出的“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法律由君主制定”,“多数人专制比一人专制更有害”,⑨[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第47章版)》,黄凤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3页。即是用隐晦的语言表达了统一法律、统一刑罚权、统一国家的反封建主张。而事实是,没有哪一个欧洲中世纪的君主有这样的实力。所以,19世纪的费尔巴哈,将统一刑罚权、统一法律的愿望诉诸于法律内容的统一(在这一点上,现在的德国学者大有其先辈的遗风),既然每个公国、每个州、每个封建领主均掌握刑罚权,那么就将刑罚权所指向的行为类型化、确定化,他抽象出犯罪构成,为规定什么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提出指导原则,明确刑法分则行为为类型化行为,只有刑法规定予以处罚的行为才是犯罪行为。若干年后的贝林,从各种概念不统一的犯罪构成中抽象出了毫无主观因素的纯记述性要件,即构成要件理论,自此,罪刑法定原则得到了具体的贯彻。①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主张法律统一、刑罚权统一、国家统一的愿望得到了各国君主的赞同,因为君主也希望一扫封建制、建立统一的大帝国,拿破仑帝国建立后的刑法典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即是明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学者们主张法律至上,而法律由立法者制定,即拿破仑制定,那么不就是拿破仑皇帝至上吗?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上的天才们用国家一词置换了国王一词,君主主权论即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主权论,大行其道(详见[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正是欧洲大陆各民族渴望国家统一与封建制度内在的契约本性,催生了社会契约论,催生了罪刑法定主义,既不同意各封建领主均握有刑罚权,又不同意将刑罚权交予君主一人之手,于是他们找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lex”,于是罪刑由人民(包括自由民与封建领主)与君主达成的契约(法律)来定,便成了共识。
随着19世纪开始的欧洲大陆主权国家的建立,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邮政系统、铁路交通以及照明系统等等使得地域之间的依赖性加强,服务国家理念的产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的统一,欧洲大陆各国中央权力不断增强,地方自治权的范围在不断缩小。严密的权力监督体系,如检察制度、法院系统内部监督、立法监督逐步完善。②参见[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在这一大背景下,又有哪个法官敢擅断?因此,罪刑法定原则就演变成了法学家与法官争夺法律控制权的斗争(即谁的法律是法律的问题),③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这一点就充分体现在关于共犯理论的争论中,法学家固守着构成要件理论层面定罪个别化的阵地,因为在立法层面实现了罪刑法定以后,具体犯罪类型已经由刑法规定,相应的刑罚也是一目了然,唯一能够留给法官自由裁量(法官控制法律可能性)的便是定罪问题,为了使法官的定罪行为变成纯粹技术性活动,甚至是机械性活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学者便在定罪问题上发展出了各种学说。④彭凤莲:《中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百年变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四)使命的变迁,悖论的产生
为了防止法官“擅断”,即为了减少法官在定罪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在共同犯罪方面,实现每个参与共同犯罪的人定性上的个别化,寻找一个区分实行犯重罚与共犯轻罚的永恒的标准。在共同犯罪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就必须贯彻构成要件理论,而费尔巴哈到贝林创造的构成要件理论是针对刑法分则类型化的行为,而刑法分则类型化行为是针对单独犯罪而设的,故而共犯要贯彻构成要件理论,就必须区分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在构成要件层面实现个别化。但问题是既然非实行行为不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就不应认定为犯罪,那么为什么还要为共犯定罪量刑?自贝林以来的刑法学家们似乎一直在为这一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适用刑罚寻找合适的理由,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味,请问罪刑法定主义精神何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第二个问题是区分制共犯体系将共同犯罪行为区分为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因非实行行为未符合法定构成要件,故对其规定了比实行行为较轻的刑罚(以1871年《德国刑法典》为例,教唆犯之刑以正犯之刑而决定,帮助犯采取得减主义),⑤参见郝守才:《共同犯罪人分类模式的比较与优化》,载《现代法学》2007第5期。但司法实践中,贯彻这个原则却往往导致量刑不均衡,又走入了量刑的悖论。
三、中国共犯体系所蕴含的价值理念:罪刑均衡
罪刑法定原则有其重要的意义,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任重而道远。罪刑法定原则及其构成要件,虽然明确指出了立法者对某一非行的不法评价,如果仅止于此,刑法也就不成其为刑法,刑法的本质是刑罚法,⑥[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C·J·A·米特迈尔:《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立法者必须在此基础上配置不等的刑罚以体现对相应行为的不法评价。⑦参见裘霞、李佑喜:《以刑制罪:一种定罪的司法逻辑》,载《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在此,罪刑均衡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国共犯体系之成型与罪刑法定原则不相干:历史地看待
上文关于欧洲大陆中世纪的历史,告诉给我们罪刑法定原则在欧洲大陆产生的必然性,“有什么样的政府,才会造就什么样的民族”。①[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一群为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苦苦追求了四五个世纪的国家,一群为诸侯割据饱经战乱的国家,一群深受罗马法影响的国家,很难想象他们不会奉行罪刑法定原则,不会将一部法典奉为圭臬,进而展开法律研究,并以此为基石,去发展法典化的法律体系,这背后是法律统一的重任。②[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1页。但我们要知道的是,欧洲大陆中世纪史不是世界各民族的中世纪史,更不是中华民族的中世纪史。
1.帝制中国的统一法律与中央司法权使罪刑法定原则没有生长的土壤
正如我国学者瞿同祖所指出的:中国自秦代开始即实行帝制,战国末期,秦帝国消灭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各自为政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并用统一的法典代替了各诸侯国原有的法律。“这部法典是国家的或者皇帝的,是主权者之于全国所有臣民的命令。”③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7-208页。自秦帝国着手统一文字、统一法律,到后来的汉律、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一脉相承。
(1)罪刑由严格的程序来确定,以罚当其罪、被告人服判为目标。
国家的统一、法律的统一,意味着司法权的统一。根据我国学者的考证,至唐帝国,已发展出完备的中央司法制度:在案件管辖权上,县级只能决断笞杖罪案件,徒以上,县断定,送州,州只能决断徒罪及流应决杖或应决配征赎的案件,流罪案件及死罪案件则送交中央刑部决断。死刑需向皇帝覆奏,“在京者五覆奏,在外者三覆奏”。④参见赵晓耕:《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4页。至明清,死刑案件程序非常复杂,先由督抚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提出,再上报刑部复核拟定,经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会签,最后报皇帝批准。对于死刑监侯案件(自唐以来,死刑案件的执行均分为立决与监侯两种),还需交押等候例行的秋审复核。在案件审查制度上,自秦帝国的“乞鞫”、“奏谳”,到清末的“上控”与“审转”制度,建立了完备的司法监督制度。上控可以向府、道、按察司、督察院甚至皇帝本人上控(即“控府、控道、控司、控院、京控”),并且没有次数、期限的限制,无论是否结案,也无论结案后的时间长短,只要当事人对于裁判结果不满即可“上控”。适用于全部民间细故、轻微的笞杖刑案件及重大的命盗类案件等州县审理的案件。“审转”即“案件自动逐级复审的制度”,适用于可能判处徒、流、死的重大刑事案件。⑤于明:《司法审级中的信息、组织与治理——从中国传统司法的“上控”与“审转”切入》,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在如此严密的“上控”与“审转”制度下,试问有哪个审案的官员敢擅断?更何况还有“出人人罪”这把大刀在头顶悬着。
而完备的中央监察制度的确立也杜绝了司法擅断的可能性,自秦在中央设御史大夫“掌监察百官、诏令及群臣奏章”,在各郡派出监御史,以后历代帝国均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专门针对官吏的监察制度。⑥参见赵晓耕:《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比附援引与司法擅断无关,与限制皇权有关。
根据学者的考证,中国古代律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在规定“断罪无正条”得比附援引的同时,也规定了“断罪引律令”。“断罪无正条”规定在律首《名例律》中,而“断罪引律令”规定于断狱篇中(唐宋是第十二篇,明清律则作为律典第六篇《刑律》下的一个子目录),进而提出疑问“为何传统法中要将比附作为通则性的规则呢?”而“断罪引律令仅仅是司法者需要恪守的规则?”⑦参见陈新宇:《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以规则的分析与案例的论证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学者的考证,审案官员即使在律有正文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罪刑相符、罪情相符,也会抛开正文,直接比附援引,对此,“皇帝采取了一种‘暧昧’的保留比附的态度”。⑧参见陈新宇:《法有正条与罪刑不符——〈大清律例〉“审拟罪名不得擅拟加等”条例考论》,载《清华法治论衡》2009年第2期。这不就是董仲舒春秋决狱“遇到义关伦常而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虽有明文规定但有碍伦常时便用儒家经典及其体现的道德原则判案”的翻版吗?⑨参见赵晓耕:《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作为一名法律学者,我们不禁要问律文是否“义关伦常”、“有碍伦常”,某行为是不是有明文规定,谁说了算?因为法律文本与对文本的解释是两回事,立法者原意解释与文义解释会有很大差别,根据文义解释得出的结果可能会与立法者的初衷相违背,这是一个法学界与法律实务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欧洲大陆国家及我国的法学家们主张立法者原意解释;而英美国家的法官们主张文义解释。①参见赵秉志:《当代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页。很明显对一个文本,奉行文义解释,也就意味着以解释者(法官)对文本的理解为准。回到春秋决狱,我们就可以得出答案,律文是否义关伦常,对某一行为律文是否明文规定,董仲舒说了算,审理案件的官员说了算,饱读四书五经的儒生说了算。更何况,在中国传统官方文本中是没有句逗的(从《唐律疏议》到《钦定大清律例》的原始文本即可看出),如何领会完全依赖于读书人——儒生的解释。通过春秋决狱,儒生获得了对律文的“排他性解释权”——文义解释。②[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页。这无异于宣布:我(儒生)奉行你(皇帝)的文本,但文本的解释权归我(儒生),我(儒生)承认并保障你皇权的至高无上,但皇权要在我(儒生)设计的规矩里运行。中国历代帝王祭拜孔庙便是明证。这个智慧被人类运用了无数次,公元11世纪英王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时宣布保留当地的郡法庭、百户法庭等地方法庭,但它们必须根据国王的令状,并以国王的名义审判。③参见林荣年:《外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确立了议会主权原则,英国的法官们却掌握着对议会制定的法律的排他性解释权,“要理解法律的真正含义,最不应该去垂问的人,就是立法者本身!”④参见[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页。在中国历史上,随着传统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在儒家设定的规矩里成型,春秋决狱也以“断罪无正条”得“比附援引”这一条文固定化。
如果这还不能使我们得出文本与文本解释由不同人掌握背后所蕴含的制衡原理,那么我们看一下大陆法系国家法典革新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律至上大行其道时,纳粹政权的依法种族灭绝、依法实行暴政,给各国浇了一盆冷水,纽伦堡审判确立了“恶法非法”的原则。人们逐渐认识到成文的法律也会侵犯人权,也会导致暴政,任何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导致暴政,立法权也要受到制约,因此,欧洲各国仿效美国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在这里,违宪审查制度判断法律文本是否违宪,所用的肯定不能是立法者原意解释。
早在17世纪英国的爱德华·柯克爵士就提出“与理性和普通法根本原则相违背的制定法是无效的”,⑤[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这一呐喊与春秋决狱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的秦帝国、近代的欧洲大陆国家用血的教训一次次证明其真理性。在中国历史上,正是通过为官的儒生的“比附援引”,合理解释了皇帝发布的各种命令(律、令、制、诏、敕等等),有效制约了皇权,才确保了皇权在既定的规矩内运行,也确保了帝制中国两千余年的稳定。⑥写到这里,也许会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与英国法律历史有相似之处,传统中国属于判例法系,其实纵观世界法律发展史,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会像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那样,从对另一个国家法律典籍(《国法大全》)的注释与评论中产生,有哪一个国家会像中世纪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就那么幸运地有一部《国法大全》摆在面前。罗马人也没有如此发展罗马法。事实是,大多数文明国家会像罗马人与英格兰人那样,不断在原有法律中融入新观念,一代代积累着法律。参见[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2.继承于中国传统的主从犯共犯体系也没有与罪刑法定原则发生过联系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中国共犯体系发端于解放战争时候的解放区政府法制,其根源是中国传统律例上的共犯罪分首从原则。1979年刑法经过一番讨论,才最终采用了主从犯的共犯体系,而1979年刑法不仅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还规定了类推。我国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是1997年刑法。而大陆法系国家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工具——犯罪构成理论(以苏俄为代表的另一分支,不同于以德日为代表的构成要件理论),⑦侯国云:《德日犯罪构成理论批判》,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在我国作为学理上的一种观点存在了很长时间(自20世纪50年代自苏联引入犯罪构成理论始),但与主从犯的区分没有发生过关联。
中国的共犯体系的成型与西方大陆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没有关系,那么真的如学者所说,它是一个简单但充满逻辑挑战的实践集合体吗?①参见杨兴培:《共同犯罪的正犯、帮助犯理论的反思与批评》,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8期;马荣春:《罪刑关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二)罪刑均衡在中国共犯体系中的贯彻:从传统到现代
瞿同祖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每一个具体个案中关注罪刑相当。②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载《霍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美国学者布迪在概括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时指出,其重心在于为一种人民所公认的恶行为确定合适的刑罚,历代帝国每一部律典都注重刑罚与犯罪相当,正是该原则保证了帝制中国刑事制度的长期稳定。③参见[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442页。中国古代立法、司法层面上贯彻罪刑均衡原则的思想基础便是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就指出:“凡爵列官职赏就刑罚,皆报也,以类相比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称功,罚不当罪,不详莫大矣。”(《荀子·正论》)“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荀子·君子》)④荀子:《荀子》,孙安邦、马银华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思想贯穿在共犯体系中,就是根据共同犯罪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大小,将其区分为首犯、从犯,首犯处罚重于从犯。
继承于传统共犯罪分首从的中国主从犯共犯体系内在地贯彻着罪刑均衡原则。大陆法系对共同犯罪人的分工分类法利于解决定罪问题;而中国的共犯人分类法很好地解决了量刑问题。⑤参见张明楷:《关于共犯人分类刑事立法的再思考》,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对此,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有学者提出“首从犯所表现出的罪刑相适应,无区分制的完美逻辑,但表现了事务的本质”。⑥马荣春:《罪刑关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5页。有学者提出“对主犯从重,从犯比照主犯从轻处罚,暗含着罪刑相适应的思想”。⑦郝守才:《共同犯罪人分类模式的比较与优化》,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严格区分主从、从犯必减”的制度性思路,最大程度贯彻了罪刑均衡。⑧王志远:《共犯制度的根基与拓展:从“主体间”到“单方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在中国,罪刑均衡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学界已达成共识。⑨参见陈兴良:《罪刑均衡的中国命运》,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罪当其罚,罚当其罪”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罪刑均衡,其核心在于“追求罪刑之间的价值(质与量)上的对称关系”。⑩陈兴良:《罪刑均衡的价值蕴涵》,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中国的罪刑均衡不仅仅存在于历代帝国的律例里,还贯穿于司法实践中。
(三)罪刑均衡在中国传统律例中的具体落实
1.设计罪刑梯度
在司法实践中落实罪刑相适应,便是设计罪刑均衡的犯罪梯度即罪刑梯度。⑪参见黄伟明:《犯罪梯度设计——罪刑相适应的基础方案》,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3期。设计罪刑梯度,不仅在于体现罪刑均衡,更能够合理地预防犯罪。孟德斯鸠在论述罪刑均衡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中国,抢劫又杀人的处凌迟,其他抢劫刑罚相对要轻。所以,在中国抢劫者不常杀人,而在俄罗斯,因为抢劫和杀人的刑罚是一样的,所以抢劫者经常杀人。”⑫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2页。至唐律时中国传统律例即设立了完美的罪刑梯度,笞杖徒流均分为五等,死刑分绞斩,当然对于死刑这一极刑,人道地考虑,不能够再以各种残酷的杀人方式来体现刑罚的轻重。但其蕴含的道理却是可以借鉴的,即现代我国有些刑法学者所建议的,建立量刑格,对有期徒刑而言,就是划分有期徒刑等级,根据学者考证,有期徒刑等级,在中国刑法史上首创于北魏,将徒刑作为五刑之一,分五等,刑期一至五年,此后相沿未改。以资借鉴,在法定刑的刑罚种类及刑罚幅度内划分出一定数量的等级。在原来跨度过大的刑罚种类及刑罚幅度内划分若干刑格。有了明确的刑格,法官便可根据犯罪的危害程度逐格选择适当的宣告刑,就不至于出现量刑畸重畸轻的情形。⑬参见陈兴良:《罪刑均衡的中国命运》,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黄伟明:《犯罪梯度设计——罪刑相适应的基础方案》,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3期。其实我国现今的刑法已经在不自觉地贯彻着这种理念:
(1)对于死刑。
对于死刑,我国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分为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种。死缓制度为中国独创,其渊源是1930年11月的《关于苏区惩办帝国主义的办法的决议》“对外国人可适用死刑缓刑”的规定,①张希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被1979年刑法确立后,逐步发展成一个完备的刑罚执行制度。这里面就贯彻了罪刑均衡理论,体现了对死刑区分刑格的精神。
(2)对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情况,以及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情况,我国刑法通过规定详细的减刑年数及限制,体现了罪刑均衡。而对于刑期跨度较大的有期徒刑,却没有很好地贯彻罪行均衡,使得有期徒刑实际服刑期限过长,而死缓、无期徒刑实际服刑期限相对于有期徒刑显得较短。对此,刑法理论界及实务界仅注意到了从死缓、无期徒刑本身着手进行调整(刑法修正案八提高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25年即是明证),却忽视了有期徒刑的改革。在幅度较大的有期徒刑内部设定若干刑格,也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方法。而且建立量刑格的建议,我国刑法学者已提了若干年。这里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唐律有关徒刑的规定,“徒刑五等:徒一年、徒一年半、徒二年、徒二年半、徒三年”(当然,在唐律里笞杖徒流死每一种刑罚都分为五等)。②参见赵晓耕:《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4页。在有期徒刑6个月至15年的幅度内划分若干刑格,同时在刑法分则每个具体罪名适用相应的刑格。
2.划分罪过层级
西方国家罪刑关系演进的历史,经历了形式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片面实质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到实质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历程。形式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仅是在罪刑关系之外确立相适应性,立足于社会场景与观念(社会危害性),故而常因社会形势与统治者倾向的改变而变动,随之而来的是适用刑罚的极不公正。17、18世纪产生的片面实质罪刑相适应原则,以犯罪的影响(等害报应、等价报应)作为确立相适应的标准,使罪刑关系具有了逻辑生命力,因其寻找相适应性的根基单一,仅考虑犯罪后果或者刑罚的作用,导致刑罚的不公正。进入现代,实质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才最终找到了“罪过”这一“犯罪和刑罚两者共通的决定性因素”,并以此为根基确立罪刑关系。③参见高艳东、蒋尉:《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探析》,载《学术论坛》2006年第1期。这说明只有通过罪过,才能真正实现罪刑均衡。
从唐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严密的罪过层级:
(1)谋,二人以上共谋与单人独谋,指提前谋划的故意。依《唐律·贼盗律》疏议:“谋杀人者”,谓二人以上(又细分为:同谋共杀,杀时加功,绞;同谋,从而不加功力者,流三千里;“造意者”,谓元谋屠杀,其计已成,身虽不行,仍为首罪,合斩);“若事已彰露,欲杀不虚,虽独一人,亦同二人谋法。”④参见钱大群:《唐律疏议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即特定情况下,一人独谋。
(2)故,第一级,没有预谋的故意,但有明确(杀伤)等目的,被害人没有任何过错。《唐律·斗讼》疏议曰:“非因争斗,无事(指争斗之事)而杀,是名故杀”。依《唐律·贼盗》疏议曰:“若恐迫人者,谓恐动逼迫,使人畏惧,而有死伤者。若履危险,临水岸,故相恐迫,使人坠陷而致死伤者,依故杀伤法。”④明清律斗殴及故杀人条节注:“临时有意欲杀,非人所知,曰故。”⑤参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级,临时起意,犯罪行为的发生,被害人有一定过错。如《唐律·贼盗》疏议曰:“若因斗,恐迫而致死伤者,依斗杀伤法”。④被害人与人争斗,故有一定过错。
(3)误,犯罪人没有明显故意,且犯罪行为发生,被害人没有任何过错。如《唐律·贼盗》“斗殴时误杀旁人身死”。④
(4)过失,第一级,犯罪人有明显过错的过失,如《唐律·贼盗》疏议曰:“因戏恐迫,使人畏惧致死伤者,以戏杀伤论。”④
第二级,犯罪人没有明显过错的过失。汉律“过失杀人不坐死”,过失系“不意误犯”之谓;唐律“诸过失杀人者,各依状以赎论”,宋刑统赋解斗讼律“过失杀人以收赎”;明清律“过失伤人者,各准斗杀伤罪减二等依律收赎,给付其家”,其小注云:“过失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如弹射禽兽,因事投掷砖瓦,不期而杀人者;或因升高险,足有蹉跌,累及同伴;或驾船使风、乘马惊走、驰车下坡,势不能止;或共举重物,力所不致,损及同举物者。凡初无害人之意,而偶致杀伤人者,皆准斗杀伤罪减二等依律收赎,给付被杀被伤之家,以为营葬及医药之资。”①参见赵琛:《刑法学原理》,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02页。民国时刑法学家赵琛将古代过失归纳为三种“为不意误犯;为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初无害人之意”。②同上注①,赵琛文。对此,有学者通过对清代与民国法律责任的比较得出,清代“过失”概念包含完全无意的无过错行为,而民国法律责任在大陆法“negligence”概念影响下,只包含有一定过错的行为。③胡宗绮:《过失杀人:划分犯罪意图的谱系》,载[美]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2-16、165-166页。
(四)对当代的借鉴:取消胁从犯、帮助犯,回归“共犯罪分首从”
首先,承认共同犯罪,证明定罪不成问题,因为它以“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这一有机整体来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共同犯罪的定罪不是只取决于实行犯,而是取决于共同犯罪行为这一整体”。④张明楷:《关于共犯人分类的再思考》,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大陆法系国家是不承认共同犯罪为犯罪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在他们看来共犯是实行犯的共犯,属于犯罪形态而非犯罪的独立类型。因为承认数人共同犯罪为一种独立的犯罪类型,即意味着承认团体责任。
其次,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从逻辑上与主犯、从犯的划分,不属于同一逻辑范畴,同时,教唆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还是要以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区分为主从犯处罚,单纯教唆犯鉴于其有意志论罪的嫌疑应排除在共犯体系之外。⑤参见王志远:《共犯制度的根基与拓展:从“主体间”到“单方化”》,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而胁从犯最终也是要根据其实际参加犯罪的程度、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大小,区分为胁从主犯或胁从从犯处罚。⑥参见赵志轩:《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标准与立法完善》,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并且胁从犯与我国解放战争以来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刑事政策直接相关,只不过是当时社会条件下采取的权宜之计。⑦参见任海涛:《共同犯罪立法模式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有完备的罪刑梯度,再配以细致的罪过层次,共犯罪分首从完全可以解决共同犯罪人的问题,教唆犯、胁从犯能否作为独立的共同犯罪人种类,学界争议颇大,并且,保留教唆犯使得中国共犯体系逻辑混乱,无法自圆其说。因此,二者均有取消的必要。
结论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数学理性,⑧“所谓数学理性就是在对自然界的研究中,采用客观的、定量的、超验的、简单的思维趋向;追求确定性的知识;注重演绎推理”。参见何柏生:《法律文化的数学解读》,载《法制资讯》2013年第4期。古希腊人将包括于数理逻辑中的原理发展为演绎逻辑。这一逻辑也成为构建西方哲学的基石,它所包含的公理精神、科学性、证明方法、确定性也成为以哲学为根基的自然法理论的核心。⑨参见何柏生:《法律与作为西方理性精神核心的数学理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4期。规范法学派承其余绪,发展了成文法,确立了罪刑法定主义,这便是规范性思维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运用。⑩参见[德]卡尔·施密特:《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苏慧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演绎逻辑的缺陷在于,“其存在的大前提可能出现错误”,而“整个推理过程只是在思想内部进行无法实现与客观世界的衔接”。⑪樊百乐:《普通法视野中的刑事类推与罪刑法定》,载《理论月刊》2010年第1期。贝卡里亚罪刑法定原则是以社会契约理论为大前提的,而社会契约论已经在现代国家理论中受到质疑。⑫参见[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如何证明有公民将权利让渡给君主?社会契约论又渊源于自然权利思想,但已有西方学者指出:“从虚构理论来看,自然权利是一种错误的虚构。”⑬[英]弗利登:《权利》,孙嘉明、袁建华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3页。其实,只要我们回到现实,都能够明白从自然权利到社会契约都是虚构的理论。这正是在国家政治制度构建中运用演绎逻辑的弊病。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规范是大前提,案件情况是小前提,案件决定是结论”的三段论演绎逻辑,虽然是定罪过程的完美指针,但这种逻辑推理的前提是完美无缺的刑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绝对真理性,现实是,法官判案不是在做数学题,定罪的目的是为了公正的量刑。在量刑层面上,无法运用演绎推理。
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中国传统律例通过设计罪刑梯度与划分罪过层级,将罪刑均衡完美地呈现了出来,这背后始终贯穿着一致的逻辑,即将任何事物均进行排序,划分刑格、划分不同的罪过层级、划分首从犯就是排序,《唐律疏议》十二篇的完美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排序。除此以外,有关座次的排序(尊位、卑位)、方位的排序(东西南北谁尊谁卑),亲属间的名称本身也是个序列,这种排序逻辑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西方演绎逻辑的基础是数理逻辑这一永恒的逻辑,而中国这种排序逻辑的基础便是人伦这一永恒的逻辑。排序逻辑的运用使得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无一不传递着型塑、说教、守规矩的信息,中国传统的“刑”字通“型”(模型),①据考证,刑字有型范、典范、以典范教化、守规矩的含义。参见赵晓耕、孙倩:《小议先秦社会的史官与法律——从刑字说起》,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本身就蕴含着秩序的含义,运用这种逻辑的思维是一种秩序性思维或称型塑性思维。②20世纪初的德国学者卡尔·施密特在其《政治的神学》中提出了决断论(即命令式)与规范论(规则式)两种对立的思维类型,在《论法学的三种思维模式》中演化为三种思维模式,规则、决定与具体的秩序,即规范论思维、决断论思维、秩序性思维。他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称为具体的秩序思维模式即型塑性思维,将17、18世纪盛行规范法学派思想称为规范论思维模式,将规范实证法学派思维称之为规范论与决断论两种思维的综合体。针对规则思维模式的不足,提出建立新的秩序性思维的口号,他将萨维尼等历史法学派的思考方式归入秩序性思维。本文在惯于进行历史性、体系化思考、着重教化、型塑的层面借用该理论。参见[德]卡尔·施密特:《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苏慧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中国共犯理论之争背后正是西方规范论思维与中国传统固有的秩序性思维的较量。基于规范论思维,必然要贯彻演绎逻辑,从社会契约论推导出罪刑法定再推导出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的区分,从而必然贯彻正犯、共犯区分制,或者采用扩张正犯概念,将共犯(狭义,仅指教唆犯、帮助犯)纳入正犯之中(具体刑罚轻重由法官裁量),即单一正犯体系;而基于中国传统固有思维,却又无法割舍首从犯——这种能够很好地解决量刑问题,但却无法运用演绎逻辑从罪刑法定原则推演出来的共同犯罪人分类方法,所以我国的刑法学者们就一直在这两种思维模式之间游离。
(责任编辑:汪雄涛)
Joint Crim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West
Zhaο Xiaο-geng Sun Qian
For China’s complicity system,academic circles have three opinion:distinguish principal offender and accomplice system,double distinguish system and only principaloffender system. Chinese complicity system cannot match with western country’s accomplice system,because the joint-crime classification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ounty. Civil law theory of accomplice is reasoning strictly follow Nulla poena sine lege,with the rigorous logic,and the paradox cannot be solved,which generated in continental Europe countries for some reasons,the feudalism,without Unified penalty power are the reasons. At the background of unification in our country,the value of legal system is to pursue matching of crime and penalty. Behind this difference are collision of two kinds of logic,two modes of thinking,the deductive logic and sorting logic,standardization thinking collisions with order thinking.
Nulla poena sine lege;Matching of crime and penalty;Standardization thinking;Order thinking
D924.11
A
2095-7076(2014)01-0063-15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