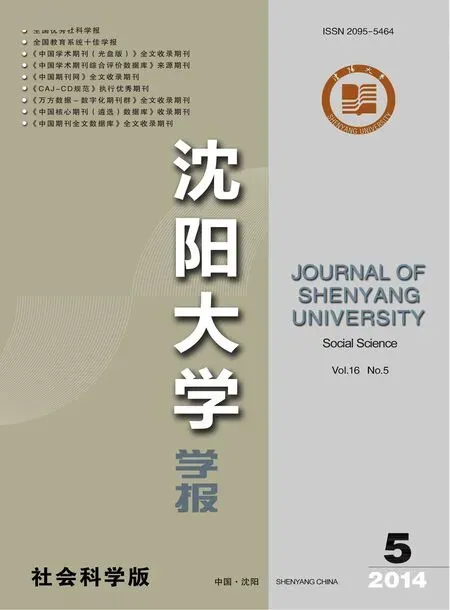中国近二十年来文学道德批评述评
贺 根 民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中国近二十年来文学道德批评述评
贺 根 民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就文学道德批评的方法与效用、地位与取向、角度与模式进行学理的梳理和评析,为即将建构的文学道德学体系提供一个合适的话语平台,在多元并存和跨学科的基础上催生新的批评方法。认为文学道德批评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传统文学与道德文化相互发明,共同夯实了具有东方神韵的文学道德宝库。文学道德批评贴近古代文学生态、文学道德的审美呈现,有效地避免了昔日文学研究中的误读和臆测。
文学道德批评; 方法; 角度; 取向
文学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文学与道德伦理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话题。尽管它曾一度被视为陈腐的话题而备受排斥和冷落,但是道德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从未停歇。文学不单是现实生活的纯客观反映,作为一项复杂的精神劳动,文学活动中或显或潜地存在着道德尺度的色彩,离开伦理道德,文学研究几乎无法展开。早在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言说中,就肇始了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之流,儒家诗教打造了厚重的文学价值大厦,任何作品都带有一定的功利指向,文学消费过程中所展示的道德感召或训诫力量显示传统文学的道德指引,文学的审美功能成为实现教诲目的的途径,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道德伦理规范形成、解构的历史,无论是作品的道德预设、还是叙事话语中的道德干预,传统文学与道德文化相互发明,共同夯实了具有东方神韵的文学道德宝库。
一、 文学道德批评的方法与效用
传统道德与中国文学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就认为,“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做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1]。道德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被提出和强调,归功于聂珍钊先生的大力鼓吹。2004年,在江西南昌市召开的“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聂珍钊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该方法因为其独特的批评视角旋即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鉴于聂珍钊的学术背景,其研究主要就外国文学而论,如伦理禁忌与俄狄浦斯情结、古希腊的复仇模式等主题的探讨,而未能以比较诗学的眼光来透视中国文学,但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学术视野。
如前所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聂珍钊的发明。2004年10月,聂珍钊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一文,该文就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基础、批评对象与内容、思想和渊源探究分析,首次明确亮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论。他又于当年的12月,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刊登《剑桥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从利维斯谈起》,以利维斯为个案探讨文学伦理学批评。聂先生认为文学伦理学不是一种新的学科,只是一种批评方法,它主要侧重从伦理的立场来解读、阐释文学作品,“即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2]35在聂先生的鼓动下,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掀起一股文学伦理学的研究热潮。刘茂生的《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援引文学伦理学方法,披览王尔德的作品,就童话、小说、戏剧进行分类分析,揭示其塑造唯美人物形象的道德前提,挖掘小说文本所承载的道德主题。朱卫红《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基于文学伦理学的批评立场,视理查生小说的道德主题、人物情感为一个有机整体,运用伦理放大镜来考察小说的事件与人物,揭示小说如何通过主题、事件、人物、情感和书信体叙事实现道德说教的目的。刘、朱二位学者均为聂先生的博士,上述二作亦为各自的博士论文,如此,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开出一片鲜艳的花朵。
文学道德批评方法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它跟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法结合,显示出广阔的适用范围。王德清在个案分析王维、苏轼、陆游、元好问、王渔洋等诗歌特色的基础上,阐释中国诗学德本意识的整体思维方法:“诗学德本精神的研究,或者是文学的德本批评,即在于十分珍视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辩证思维,看重‘内省’和‘顿悟’的直觉思维,考察有机整体观对古代文学批评的范畴体系的影响,注重宇宙人生一体观的整合思维方法对批评方法与批评风格的有机渗透,吸纳西方文学批评逻辑分析的严整思维,创造性地张扬和落实批评中的德本精神。”[3]9吸纳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和西方严整思维化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学道德批判方法。文学道德批评作为一种方法,势必以具体的文本为依托,文本所承载的知识涵盖往往是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生态的形象折射。张文浩《宋代儒家道德诗学的研究路径》(《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一文以文学道德批评去梳理宋代诗学,凸显民族融合和文化转型的背景,以历史变迁和中心人物分析为经纬,展示了伦理美学、价值哲学和文化诗学的统一。戴峰《宋元戏曲家伦理观念的民俗学阐释》(《四川戏剧》,2011年第3期)就文学、道德、民俗学的交叉来深挖宋元戏曲的伦理特点,披览文学观念变迁与民俗文化的内在联系,可谓正得其宜。
如果说文学道德批评援引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有效地体现了学科交叉特征,那么诸如依经立义、据诗言志、隐喻取譬、人物品藻等方法的梳理,则展示了文学道德批评的本位方法。美国汉学家艾兰采用隐喻理论来诠释中国早期的哲学观念,她指出中国哲学中最有意义的概念都源于水和植物的本喻,客观道出道德批判方法论体系中的隐喻因子。她认为孔子观水、老子以“水”作为“道”的概念原型,是因为先秦诸子假定“同样的宇宙原则也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础,他们通过体察水与其他自然现象以求提取自然界的原则,这将使之了解人类及其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4]传统文化的取譬思维展示了中国诗学的即兴体悟特点,也侧面阐释了古代文学中山水之想的思维路径。贺根民归纳文学道德批评方法,费力颇多,他的系列论文,如《论先秦比德观念的生成》《文学教育:诗言志说的一个文化侧面》等有效还原古代文学生态,全力爬梳古代文学道德批判的方法原则。其《欲理之辨与中国文学的道德思维》整体统摄古代文学的欲理纠葛,指出:“沉郁深厚的欲理之辨,品砸出捉摸不定的人生况味;激昂酣畅的欲望宣泄,飞扬着豪情万丈的文人情愫,既要求廉洁自律、恪守人性本位,又不隔绝对基本的生存环境与生命情趣的眷恋。”[5]侧重生命本位的救赎行为形成的悖论结构,既真实地反映了尚生贵行的传统文化脉络,也体现了道德批判的生命之喻特征,欲理之辨展示品文论人的叙事文学传统。
文学道德批评是一种贴近古代文学生态的批评方式,文学道德的审美呈现,有效地避免了以往文学研究中的误读和臆测,致使那些全然不顾传统文化生态而打出女权主义旗帜,各种为女性翻案的文章正呈下降之势,这在叙事文学领域表现尤著,譬如视潘金莲为明代中后期追求自由爱情的代言人、过高体认杜十娘追求美满婚姻的举动。这些研究误区的存在,除了研究者各自鼓荡的满腔热情外,不无主题先行的色彩,有意或无意地漠视传统文化生态往往是其症结之所在。天命人受、家国一体的宗法伦理模式,铸造成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传统文学承载的道德意识,往往是社会文化系统本身所赋予的一种文化指向,并由此形成具有东方色彩的文化艺术语境。李劼就明代文学思潮的新变来把捉西门庆形象的时代意义:“正如诗歌在明代有了性灵风貌,《金瓶梅》开始说出了为道德说教长期掩盖的历史真相。男人的造型不再按照男人的道德要求诉诸关公武松孙悟空那样的英雄,而是按照生活的本身的模样写成西门庆式的新兴商人和情欲顽主。这位主人公一面像夏洛克那样按照中国社会所规定的方式经商,一面将中国男人在庭院中的食色本性公之于众。”[6]西门庆完全抛弃了修、齐、治、平的传统信条,无所留恋地走上了奋斗与享乐的道路,花天酒地,最后葬身欲海。他的纵欲折射了明代好货好色的世情本色,道出古典小说塑造人物观念的时代进步。运用文学道德批评方法,凸显了还原文化场景的人物形象分析理路。
文学道德批评带有知人论世的社会历史批评色彩,它在推源溯流的基础上强化了文本细读的力度。陈立人《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及其典型意义》(《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就人物的社会存在、生活道路来挖掘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展示作品的社会批判色彩,该文认为刘兰芝“淑女—贤妻—烈女”的道德实践,足以概括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由特定社会的典型形象推及传统妇女的道德生态,该文较好地尊重了传统文化的结构特质,体现了客观求真的治学理念。笔者爬梳近20年的有关文学道德论文,发现运用此法来研讨人物形象者,在数量上至少占据已发论文的大半江山,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属意于人物形象的道德承载,亦即仍未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人物形象的道德指向充其量只是其具体的研究对象而已。若将此现象推及对某一特定社会的研究,道德意识大多也定格于某一社会的意识形态。孙海莉《论元杂剧中的伦理道德的新变》(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古代文学专业硕士论文)侧重元杂剧的伦理道德剧目,就元代文人、女性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来挖掘元杂剧文体内部诸如情节安排、人物塑造、风格特点方面的新变,较好地体现了文本细读色彩。作为一篇晚出的学位论文,纯粹停留在以往的经验模式之中而自说自话,本无可厚非,但全然不顾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势必影响到论文的研究视域,造成一定面积的学术重复。历史是过去的现在,文学道德批评理应展示现代效能:“德本诗学也是一种以传统实用精神为底蕴而解决当下批评中‘德、美二难’的文学批评,意在精辟地阐释那些建构在伦理与道德基础上的诗歌现象,破译含蕴于诗歌文本中的伦理与道德因素,讨论给予当下的启示。”[3]15文学道德批评实现了文本道德指向的审美呈现,刘义军《审美与道德的天然合一:杜甫诗歌的现代阐释》(《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认为杜诗让审美意识和道德批判得到了完美凸显,其诗不仅给予世人以全身心的美感享受,也寄予其对时代的无情鞭挞和严厉的道德批判。一代诗圣的诗歌高境,道德文章是其诗歌彪炳千秋的最好注脚。刘文侧重文学道德的交叉,盘活杜诗的现代价值,也凸显了文学经典的穿越时代的文化魅力。
二、 文学道德批评的地位与取向
文学道德批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几乎同时产生于文学诞生之初。黄帝与蚩尤之战、颛顼与共工争锋的上古神话,正义与邪恶的定位已显露出先民的道德批评色彩。《诗经》文本中美刺和政教功能的展示,虽不排除孔子变风变雅的可能,但大抵道出当下社会的道德文化取向。一旦宗法伦理逐步固定,文学就很难割断同它的文化脐带。袁济喜高度体认道德精神的化合之力:“所谓中庸与诚都是指一种至上的精神信仰,是神圣而不可逾越的道德精神。西方人将这种精神境域归结为宗教精神,而中国人则将宗教精神与审美精神融入世间的中庸至诚精神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创造。”[7]美善结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主要向度,文艺作品侧重情感和教化两个维度来增强其影响力,几成千古文脉的集体意识。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涉及文艺的审美、教化等注重功能,但仍归结于“事父事君”的礼教图式。汉儒进一步将此功能具象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完整纲领,规设后世文学书写的基本理路,无论是出自何种考虑,文人大多操持道德话语来提升自己作品影响,谋求文体的独立地位,这在所谓的“小道文学”的小说、戏曲中表现尤为显著。文学史上如李贽、金圣叹一般的叛逆者不在多数,文学思潮中的缘情说、性灵说虽具有彰显文学本位的趋向,但仍无法消解文以载道的整体影响。
传统文学的杂文化生态,决定了其诞生之时的杂纂色彩,文学诞生的历史原点就带有一定的道德功利性,文学往往是范围人伦、社会教化的工具,这种工具理性一直延续到当下。黄曼君属意勾勒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在梳理之初先从传统文论的核心问题入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虽因强调美与善统一中的世俗人伦情感而具有主情、重情的传统,但其核心不过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世俗化,所谓‘主情’、‘重情’,也包含着强烈的伦理功利要求,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是在以理(主要是封建伦理)节情的调控下发挥着弘扬名教、以‘善’惩‘恶’的作用。”[8]弘扬名教的道德规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核心和基础,它规设了传统文论的发展轨辙。在传统文化的构成中,道德伦理思想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苏桂宁《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认为:“伦理精神是中国社会的核心精神,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带上了浓厚的伦理色彩。”[9]苏著就天人合一、道、气来分析中国诗学伦理本体,从家国一体的宗法基础、艺术审美精神、生命情结、宗教伦理诸方面考察了宗法伦理影响下的中国诗学的生产过程,全面体现了东方诗学的系统特质。道德——超脱情结允符传统士人寻觅安身立命的生存空间,大量感时抒怀的诗歌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审美与道德的矛盾,又彰显承天地之德的个体生命的修炼和精神意向。
道德批评具有人文关怀的色彩,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客观体认道德意识在民族文化精神中的地位:“在趋向于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目标时,我们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以人伦为本位(或者叫伦理型)的结构体制,道德关系和道德观念成为整个文化体系的纽结点。”[10]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学的逻辑起点,人本和文本的关系脉络凸显人生信仰的感召效能,建筑在人本基础之上的文本维度是文学道德批评的重要取向。黄霖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中认为,儒家伦理思想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的血缘关系和入世精神,“确切地说,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就是建立在这种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思维模式,便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一个相互关联、递进贯通的自足系统。这个系统,体现的是一种融个人伦理、宗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宇宙伦理于一体的伦理精神,最终要达到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11]伦理精神绾合了个体心性修养和家国文化指向,铺设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基本向度。王德清以审美精神与德本精神来厘定中国诗学精神,认为:“德本精神一直就是中国诗学的内核,是中国传统批评话语建构的基础,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追求的一种永恒范式。”[3]1生生不息的中国诗学演进之河,正因为道德精神的观照,才没有过度泛滥或干涸断流。
外国文学领域正式发起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刷新了人们的认知谱系,聂珍钊认为:“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伦理价值是第一位的,审美价值是第二位的,只有建立在伦理价值上的文学的审美价值才有意义。”[2]101道德与审美的崭新定位,解决了文学道德学领域缠夹日久的学术问题。职是之故,秉持道德价值维度来打量文学作品,人们更有可能深层次把捉作品蕴含的悲剧精神和文人悲剧人格的范式意义。高小康认为:“如果从传统的理性观念来看,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道德精神总体说是乐天的、世俗的。而在更高的精神层次上,在穿透世俗的乐天观念而更深刻地观察、领悟世界和人生的艺术追求中,却又潜藏着一种寂寞、悲悯的超越性的精神。”[12]20悲剧的高位体验特质,刷新了昔日就大团圆模式来探究叙事文学形态的积习,深度展示文本的文化取向。悲剧精神的观照,部分改变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叙事传统,以人生的缺陷和不可抗争的宿命来展示高愉悦与低和谐的冲突之美。以此为度,“《桃花扇》和《红楼梦》所表现出的深刻的悲剧审美意识,表明中国近古叙事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脱离了传统的对叙事意义的道德阐释方式,而代之以具有个人体验性质的深刻的意蕴表达。”[12]21民国文人梁启超、王国维分别给予《桃花扇》《红楼梦》以很高的评价,恰从侧面道出二作的悲剧况味。宋铮《〈水浒传〉忠义伦理的悲剧精神》(《东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高度体认《水浒传》忠义伦理的悲剧色彩,认为梁山好汉践行忠义伦理及其失败的历史宿命,已构成对封建忠义伦理规范的反思与批判,底蕴着忠义伦理观的逻辑悖论。文学道德批评走出了以往文学研究讳论道德的认识误区,它以开放、多元的文化向度引领文学研究向深层拓进。
三、 文学道德批评的角度与模式
厚重的道德文化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它不但呈现了丰富而严密的道德规范谱系,还影响到传统文人品人论文的基本视角,古代文人就很少脱离道德视角去考察社会人生。郭英德就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阐述古代文人的道德意识:“就文学家的创作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可以说是文学家的伦理意识与现实感受的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产物,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深层的人生底蕴。”[13]136古代文人力图以伦理意识去衡量生活,引导现实感受,并往往借用伦理意识来支配自我的内心体验。以致他们在感受生活、进行具体的文学评价时亦展示浓郁的道德情结:“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位文学家,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在他们进行社会观察、艺术构思和审美活动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戴上了伦理意识的有色眼镜。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大都充满浓厚的道德色彩,中国古代的文学形象大都是一种道德人格”[13]134。只要是文学作品,几乎所有文类均会包孕一定的道德意识,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情结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人们可以反对视文学为道德训诫副本的观念,却不能放弃文学实践中的道德责任。承认文学实践中的道德责任,并不意味着政治禁锢或精神扼杀,道德与审美并非对立之物,它们彼此可以兼容相长。
文学道德批评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吴士余就传统文化本位来考察道德至上的思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本位的文化意识为其内核的。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魂’。在这一文化模式中,‘知行合一’的知识论上的功利主义和‘重义轻利’、以道制欲的价值论上的反功利主义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侧面。二者从认识自然与人格的自我实现的不同文化视角表示了对人伦道德至善的思维认同。”[14]感受自然和实现自我人格延伸了文学道德批评的文化触角。闵虹的《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士文学》,系统地梳理了古代文士文学的德治思想,考察了德治思想对古代社会结构、古代文人的思维方式及精神建构的影响。该作认为:“中国文学却一直强调文学必须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唯美主义的吟风弄月、无关政治类作品一直没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提倡民本精神和关注社会现实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良的传统。因此,发掘文士文学中的德本精神,借以探讨其在文士文学中的发展流变,对研究中国德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5这是贴近传统文化生态的务实之论,政教中心论一直是中国诗学的核心价值追求,侧重民本精神、挖掘文学反映现实中所展现的道德意识,确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角度。如是,“爬梳整理历代文人构建德治理论的各种表现形式和经验智慧,勾勒一部德治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并由此折射出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人生理想等多层面的精神世界。”[15]317照实看来,若欲展示古代文人浩繁而深邃的精神世界,爬梳德治思想的表现形式和经验智慧,倒不失为比较便利的途径。
苏桂宁的《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从家国精神、人性关怀切入道德观念,发掘宗法伦理精神对中国诗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王德清《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认为德本批评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这种德本批评,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主体,成为中国美学活动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内核。”[3]37道德批评的文化价值地位得以有效体认,其模式的引领色彩亦予以肯定。王先生该作细细梳理了中国诗学的德本意识,认为道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德本精神的基本要素与底蕴,“应该说,中国古代诗学的德本精神是一种超稳定的传统,是一种以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政治观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形态。”[3]16根基于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政治观维度来挖掘中国诗学的德本意识,确实指明了归纳和运用道德批判的主要角度。家庭是社会的窗口,明清家庭文学包孕着浓郁的道德指向。段江丽侧重礼法与人情维度,剖析明清家庭小说的主题。她认为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家庭小说,以家庭来辐射广阔的社会和倾轧纷争的朝廷,家庭、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意义模式,“不仅可以提供自由驰骋的艺术想象空间,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家国同构、伦理道德与政治法规不分的本质特征,从而在艺术和思想两个方面都为创作者和阐释者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16]世情小说杰作《金瓶梅》构筑一片财色迷茫的末世景象,文本中欲望男女的财色争逐抒写了放纵与死亡的主题,作者为转眼成空的财色幻影下一剂猛醒良药,恰好寄予其守礼远害的劝惩苦衷。
张大为《诗歌道德承担的四个层次》(《南都学坛》,2007年第1期)从观念内容层次、心灵作用层次、意义机制层次和语言伦理层次四个角度来显示诗歌的承担色彩,亦可谓为一家之言。秦川《明清小说的伦理观与和谐文化》(《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3期)就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等角度探究其与和谐文化的关系,在归纳了明清小说伦理观的现代意义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文学道德批评的三个维度。傅希亮《道德史观与〈左传〉文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4年博士论文)梳理了左丘明道德史观产生的社会基础、道德史观对《左传》叙事及人物刻画的关系,指出道德史观的思维方式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就其学位论文而言,道德批评只是其论文研究的切入角度,虽不乏一定的方法论色彩,却未能涉及文学道德批评本身所固有的研究模式。贺根民的系列论文较为系统地研讨了文学道德批评的本位模式,譬如在依经立义、据诗言志、比德见物、人物品藻、以情设教诸方面进行了整体打量,他认为依经立义与据诗言志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在伦理旗帜的挥舞下,往往以一副温情脉脉的面纱指引着世人的道德践履,掩盖了事实意义上的阶级矛盾,而展现文人个人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社会诉求的同谋共构。比德见物和人物品藻所推动的山水之思,张扬了士人独立人格的建构幅度,推动中国诗学思维的自然化和人格化。
四、 结 论
中国古代文学的道德情结源远流长,诸如文学与道德的言说资料汗牛充栋,前贤时彦的著书立说已初步涉及古代文学道德批评的话语建构,对文学与道德的发生学意义、演变途径、阐述模式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是,对于中国诗学的道德文化生态的挖掘,还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实践需求,其研究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选择那些曾经影响较大,内涵变化较多,在当下仍具有一定生命力的范畴、主题、模式、思维原则来推源溯流,勾勒其嬗变的文化轨迹,试图为当下的文坛病态提供可资疗救的方案。古代文学道学的各个逻辑组成均是一个个富有生机的路标,在学理上,本文紧扣其所依托的文学文本,进行历史还原,同时辅以政治的、文化的、社会心理的多向考察,发掘古代文学道德批评因子的恒定意义和演变图像,揭示古代文学与道德文化夹杂的文化生态,展示不同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的道德情结的演变规律。本文的研究,不给人以扬中抑西的感觉,对古代文学道德批评进行学理的梳理和评析,为即将建构的古代文学道德学体系提供一个合适的话语平台,在多元并存和跨学科的基础上催生新的批评方法,从而在多元复色的文学批评时代找准文化坐标,提倡一种新的批评方法。
[ 1 ] 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M]. 孙俍工,译. 北京:北新书局, 1928:47.
[ 2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3 ] 王德清. 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 2007.
[ 4 ] 艾兰. 水之道与德之端[M]. 张海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36.
[ 5 ] 贺根民. 欲理之辨与中国文学的道德思维[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8(2):131-133
[ 6 ] 李劼.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5:296.
[ 7 ] 袁济喜. 中国古代文论精神[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57.
[ 8 ] 黄曼君.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13.
[ 9 ] 苏桂宁. 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M]. 上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3-4.
[10] 陈伯海. 文学史与文学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26.
[11] 黄霖.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314.
[12] 高小康. 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3] 郭英德. 中国四大名著讲演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4] 吴士余. 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M]. 上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5.
[15] 闵虹.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士文学[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16] 段江丽. 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 2006:41.
【责任编辑王立欣】
CriticismonLiteratureandEthicsinRecent20YearsofChina
HeGenm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The methods and effectiveness, 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and angle and mode of criticism on literature and ethics are described and analyzed, to provide a suitable discourse platform for the upcoming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system of literature and ethics, and stimulate new critical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criticism on literary and ethics is an important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which consolidated the literature and ethics treasure with oriental charm by the mutual invention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and moral culture. The criticism on literature and ethics is close to the ecology of ancient literature,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aesthetic of literary morality effectively avoids the misreading and speculation in former literary studies.
criticism on literature and ethics; methods; point of view; orientation
2014-05-02
广西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K13YB059)。
贺根民(1971-),男,湖南邵东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博士。
2095-5464(2014)05-0681-06
I 06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