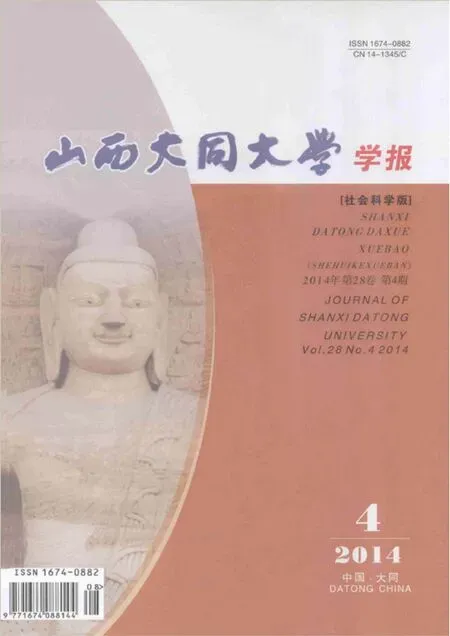论新历史主义的新型文本观
钟观凤,董希文
(鲁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20世纪80年代,后结构主义走向衰落,此时正是新历史主义登上英美文化和文学界的舞台之际。确切地说,于70年代末,新历史主义已经初露端倪,而其最终确立的标志可追溯到1982年,当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以美国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路易·蒙特罗斯、海登·怀特、玛乔里·勒维森和英国的乔纳森·多利莫尔、凯瑟琳·贝尔西等人为主要代表,这批理论批评家在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研究领域中形成新的文本观,关于文学、历史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有其独特的见解。当然,新历史主义文论不可能无根成荫,它也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孕育脱胎而成,尤其是对旧历史主义、形式主义、接受史或解释学、解构主义等文学流派提出的文学观进行一番反思与清算,从中获得启发。
一、“清算”以往的文本观
首先,新历史主义的“新”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的“旧”而言的。在20世纪40年代新批评出现以前,历史主义批评一直主宰着文学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包括思想文化史、文学史在内的历史及其历史哲学方法。该派代表人物包括卢梭、维柯、黑格尔、克罗齐等人,他们推崇历史的客观决定论,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认为“历史”能够决定一切,“坚持对任何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类历史的深思熟虑之上;强调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进程并容许做长期的社会预测和预见”。[1](P393)新历史主义对此不敢苟同,虽然它也肯定历史的“真实性”,但此“真实性”并非旧历史主义的历史的“事实性”,故新历史主义者反对传统历史主义简单地把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视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新历史主义对其进行反驳之前,旧历史主义的观点在20世纪初业已遭到过攻击,卡·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曾批判它的极端,“历史宿命论全然是一种迷信;用科学手段也好,或用任何其他理性手段也好,人类历史的进程都是不能预言的。”[2]波普尔主张非中心论,认为历史决定论由于赋予历史集中的权力必然走向极权主义,终将会被学术界剔除。
其次,对20世纪以来的形式主义的文本观进行学术纠偏。从广义的角度来看,20年代出现的俄国形式主义、40年代兴起的英美新批评以及60年代盛行的结构主义可合称为形式主义批评,因为三者均指向文学的内部 (语言、功能或结构),悬置了“存在”、“历史”、作者、现实和心理等外在因素,而专注于分析文本内的文学性、陌生化语言、形式技巧或结构,将文学禁锢在封闭的的文本藩篱中,与旧历史主义相反,它们推崇的是文本中心论,即文本决定一切,历史被驱逐或遗忘了。然而,新历史主义不满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仅停留在对文本结构和语言技巧的分析上,“也不满结构主义诗学所热衷的‘从一颗蚕豆里见出世界,以单一结构概括天下作品’的做法”,[1](P396)而是将注意力置于形式主义文论所忽略的历史语境上,“将文学批评策略拓展到尚未注意的文化文本的讨论中”。[3](P222)
再次,接受美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历史主义的消解。20世纪60年代末,接受美学(亦称“接受史”)在欧洲文学界崛起,一扫19世纪浪漫主义诗学的作者中心论和20世纪以来的形式主义文论的文本中心论,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研究领域,其代表有德国的“康斯坦学派”的干将尧斯、伊瑟尔,法国的利法代尔以及美国的费什、布莱奇等。该派受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影响,认为“文学史应是以读者为中心在期待视界融合中透视文学效果史研究”,[4](P249)即主张在过去视界(即文本出现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与现代视界(即历史理解主体当下的视界)汇合中把握文本的历史意义。接受史的“视界融合”把“文学的历史性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交叉点呈现出来,”[5](P46)既不囿于一味考据史实的实证主义,又避免陷入读者自身的主观阐释,似乎天衣无缝、不偏不倚。哈贝马斯却不以为然,批判这种做法“事实上是要达到某种关于意义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则完全可能是被系统地歪曲的,它放弃了意识形态的说明”,[4](P256)新历史主义者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反驳,如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文学家或读者由于自己的解释者地位、所处时代的政治关切,致使他必然具有某种政治立场,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约束,不可能完整地重建和进入16世纪的文化并达到超然客观的历史理解。[6]
最后,也是最“暧昧”的清算——对后结构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浮躁的文本游戏观的纠偏。始于60年代末的解构主义以破坏者的姿态出现,其代表有德里达、巴尔特、德曼、福柯等等,他们主要反对逻各斯中心论和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种种形而上学,质疑并解构二元对立和事物的统一性,力图发现哲学中的“他者”。如果说,之前提到的文本观中论及的历史仍具真实性或统一性,作者或文本或读者仍具权威的话,到了解构主义这里,一切都面目皆非了:文本不再具有确定的意义,它成为能指游戏的场地,在德里达看来,语言的能指所指涉的“在场”永远不“在场”,文本只是一张意义不断延宕的踪迹之网;德曼追随尼采,认为语言本质上是隐喻的,而不是指涉的,并且指出由于有修辞格的插入,批评和文学一样,本质上是一种寓言(以此言它),故一切阅读都是误读;不存在所谓的真理,在福柯看来,一切话语和知识不过是权力意志的表达,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无可否认的是,解构主义的文学观,尤其是它解构非文学话语并把它们视为修辞性文本,给予新历史主义很大启发,二者藕断丝连,甚至有学者(如拉曼·塞尔登)把新历史主义纳入后结构主义的框架中。无疑,解构主义理论具有偏激之处,塞尔登指出,“后结构主义者正是那些突然发现自己错误的结构主义者”、“他们总是承认,他们抵制做结论的愿望注定要失败,因为只有什么都不说,他们才能阻止我们认为他们说了什么。即使总结他们的观点本身也暗示他们在这点上的失败。”[3](P228)新历史主义认为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文本观,恢复作品中的被解构主义消解掉的历史意识,以达纠偏去弊之效。
二、建构新型的历史文本观
在文艺界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时代语境下,新历史主义对以往盛行过或仍在发展的文本观进行一一纠正和反思,它在纠偏的过程中抑或得到启发和灵感,抑或收集合理的理论资源来为己所用,因此,“清算”并非完全地否定,它只是纠正其不当之处,而对其中的合理成分适当加以承继与转化。总而言之,“清算”以往的文本观,为新历史主义者重新将历史的维度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有一定的理论说服力。概括地说,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本观包括三大方面: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文本间的互文流通性。
(一)历史的文本性 在后结构主义出现之前,大多数人认为历史是过往发生过的客观而真实的事件和活动,它永远高于文本,因为文本具有想象虚构的诗性。后结构主义思想兴起后,人们认识到历史都是经过“叙述”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家们深受其影响,重新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不再认为“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
“历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是新历史主义文论的重要特征或要旨之一,最初是由美国加州大学的路易·蒙特罗斯所提出,它包括两层意思:“一指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文本,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真正的、完整的过去;二是指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的时候,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7](P156)即是说,人们现在了解到的历史都是以文本的形式呈现的,变成一种“历史叙事”,具有“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这两大特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关于过去的事情”,为此,他将历史上升到所谓“元历史”(metahistory)的层面,探讨历史话语的本质以及它是如何与文学话语互转等问题。可见,海登·怀特和蒙特罗斯一样认为,“历史”应包括“历史事实”(具有真实客观性)与“历史修辞文本”(具有文学虚构性),前者以文本方式记录下来,后者是人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合力”产物。相对而言,怀特更重视后者,主张从文本的写作和阐释的角度审视历史。在《话语转喻论》中,他甚至指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并无区别,这显然揭露了历史的文本性。
(二)文本的历史性 在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看来,历史不纯是记录事件在转化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而且还对之进行描述,与诗人想象的虚构性并无二致,因而具有文本性。同理,新历史主义学者也不难发现文学的历史性,试想一个文学文本一方面记录了人们过去的生活 (当然也包括往昔的情感),另一方面它经过生产、出版、发行等一连串操作之后,其本身也成为一个历史事件。
“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是蒙特劳斯对新历史主义所总结的另一要旨,主要是指“一切文本 (包括文字的文本和广义的社会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7](P156)从强调文学文本的历史性这点看来,新历史主义没有完全抛弃旧历史主义,二者仍有一丝血脉联系。所不同的是,传统历史主义文论更关注宏观的历史事件,强调重大的历史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如法国文论家泰纳将一切(包括文学在内)都视为“种族”、“传统”、“时代”三因素作用下的产物。而新历史主义者受到福柯的解构哲学的影响,认为历史不是整一的,所谓的“和谐统一”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强加给历史的“幻觉”,不存在梯尔雅德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中所论述的没有缝隙的、具有统一意义体系的伊丽莎白历史,相反,由于经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统治时期叙述,历史变得多元化,具有不连续性、矛盾性和断层性。因此,新历史主义者转向研究被主流压抑和边缘化的民间传说、稗官野史等“小写”叙事。
(三)互文流通性 新历史主义把文本从文学文本的小圈子扩张到文化领域,认为文化体系是由文学和其他非文学文本所构成的泛文本之网。文本之间不是孤立的关系,而是具有一种文本间性。“文本间性”这个概念是由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首先提出,又称为“互文性”,指的是任何文本不可能全然脱离其他文本,强调文本之间的互补、互渗、互通的对话关系,即“互文性”,发展到新历史主义这里,它换了一个称呼——“流通”。
“流通”是新历史主义文本观的另一核心概念,是由新历史主义者仔细研究文本间的关系并借助经济学领域的“流通”、“协商”、“交换”等概念的理解而界定的。它很好地解释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作用,还反映了文化形成的动态过程。新历史主义致力于探寻文本间的社会能量流通性,即揭示“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文本,文本又如何转化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共识,亦即一般意识形态,而一般意识形态又如何转化为文学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8]这种认识遍布新历史主义文论中,如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商讨》中论述了作者是如何实现其文本过程的,其中“商讨”(Negotiations)一词透露了“流通”的性质,具有协商、沟通等意义。由于发现了文本间的这种流通性,批评家不再孤立地对单个作品进行分析,而是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学文本实行互文解读,认为文本形象或文学意义是一种“自我形塑”,即对阐释者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关系反复地进行阐述的产物。
三、存在的局限与反思
相对于西方以往的文学理论,新历史主义发展的时间并不算长,也“不是一种严格的学派或理论体系,而是一组学者群,或用格林布拉特的话说,是一种实践而非一种教义。”[4](P255)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历史主义的实践仍在持续,其文本观也在不断完善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用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德曼的话来说,它可能陷入自身理论的“盲点”而不自知,亟待人们反思以发现被其忽视的“洞见”。
(一)反思历史纪实与历史虚构 新历史主义用“文本性”填平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从某种意义上把二者等同了起来,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之前论述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观时已经提及。历史被视为一种文本话语,就是说人们赋予了它以某种思想的地位,和文学一样具有人的意识形态性、主观虚构性。然而,文本经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变成一个意义无限延宕的能指链,文本以外一无所有,也就是说历史文本所指向的真实事件也会被消解掉,不复存在。如果说历史的最终所指消失了,就是说历史从来不曾存在。无疑,这种观点马上会被质疑:人们的“现在”终将成为过去,即历史,如果说历史从来都是虚幻的,那么难道“现在”也是幻觉吗?显然,新历史主义有陷入历史不可知论的嫌疑。但无论如何,人们都不能放弃追求历史本真面目的初衷,而向历史不可知论妥协。这里需要反思的是,历史到底是客观真实的事件(纪实性)?还是新历史主义所说的经过史学家用文本虚构的方式所加工的历史修饰性文本?笔者认为,“历史”应该有三层意思:一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非“叙述”的、非“再现”的);二是流传下来的历史文本(文献),即前人对他们的时代所作的记录与描述,以文本的方式呈现;三是当代的历史文本,即现时的解释主体对前人的历史文本进行再阐述,以往的历史文本只是其解读的素材之一,他还结合当代的意识形态、历时和共时的文本进行互文解读。后两种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以达到第一种对历史本真的认识为目的,相较之下,当代的历史视野要比前人的视界广阔,尽管它们都加入了自身的主观色彩。可以说,新历史主义者若能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对其文本观的完善会有很大帮助。
(二)反思文学的研究对象——宏观与微观 新历史主义所建构的新型历史文本观,不仅打破了文史之间牢不可破的传统藩篱,而且架构了一个赋予动态性的互文本的文化世界。新历史主义如同一个行李箱,其研究几乎囊括了文学、艺术史、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由于打破了学科间经纬分明的研究领域,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的范围扩大了,使该派的批评家能够尽情地施展其批评才情。有趣的是,新历史主义者并不是面面俱到之辈,它也有所偏好,喜欢从民间传说、稗官野史、历史资料、档案记录、医学报告、法律文件等历史碎片中汲取资源,甚至将其视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即新历史主义有把文学文本与这些非文学文本混同之嫌。此外,与“西马”理论、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一样,新历史主义也是一种边缘批评,它迷恋边缘文化,常常质疑经典或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叙事。然而,一些论者批评说新历史主义 (尤其是美国的新历史主义)陷入了一种宏观与微观的悖论中:“在许多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对经典的挑战‘大多局限于人们熟悉的权威文本,而对‘他者’的探索则远远不足,而且它们多满足于提出新观点,对经典文本却触及甚少。”[3](P227)换言之,当面对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时,新历史主义者常常从后者汲取资料;当分析一部权威的文学作品时,面对经典传统的批评,新历史主义常常质疑,并注重挖掘文本中被主流所压抑的边缘阐释;而当面对正统文学与边缘文学 (如草根文学、网络穿越小说等)时,新历史主义往往选取前者作为批评的对象,即使这样,它也只是专注于己见而忽视“经典”的声音。因此,在“宏观”与“微观”上,很难界定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对象,至于二者应如何取舍仍需该派深思。
(三)反思文学的性质——意识形态与审美 新历史主义在文学批评中成功地进行了历史——文化的转型,将被旧历史主义、形式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所颠倒的传统再次颠倒过来,关注文化历史语境,甚至将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轶事趣闻引进权力的历史关系中,怀疑现存的社会秩序。新历史主义以一种政治解读的模式对文本进行文化批评,认为文学不可避免反映当代人的政治态度或政治立场,指出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手段,具有巩固、颠覆、包容社会秩序或权威的作用。由于过于注重文本的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者便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正如格林布拉特一味提倡“文化诗学”,注重社会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协商对话性,而“抛弃了一些神话:譬如审美自治的作品,形式上完整的文学形象,原创性的艺术才能……转而提出,批评应该关注的是形成一部作品的多样的信念、社会的实践和文化的话语”。[9]童庆炳曾在《文学理论教程》中论述过文本的性质问题,认为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可推知,单凭意识形态是不能充分形容文学的。因此,在对文学进行互文阐释时,不可忽视审美批评。
结语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冷静而又颇为大胆激进的文学理论,冷静在于其理论主张不是冒然提出,而是建立在深入考察以往文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对过去文本观存在的“盲点”进行清除;而大胆激进之处在于,新历史主义为被20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解构得千疮百孔的“历史”重新注入生命力,将“历史”与“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的批评视域。在这里,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得到重新审视,形成了新的“文化诗学”。文学与非文学文本在历时与共时中不断“流通”、互动。当然,这种历史文本观仍然存在一些局限,从中引发的一系列文学问题,不仅是新历史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更需每一个文论者深刻探究。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7.
[2](英)卡·波普尔著,何 林,赵 平译.历史主义的贫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3](英)拉曼·塞尔登著,刘象愚译.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周 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德)尧 斯著,金元浦,周宁译.走向接受美学[A].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6]Greenblatt.S.,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7]盛 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思潮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8]盛 宁.新历史主义[M].台北:台湾杨智文化公司,1996.
[9](美)迈克尔·莱恩著,赵炎秋译.文学作品的多种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