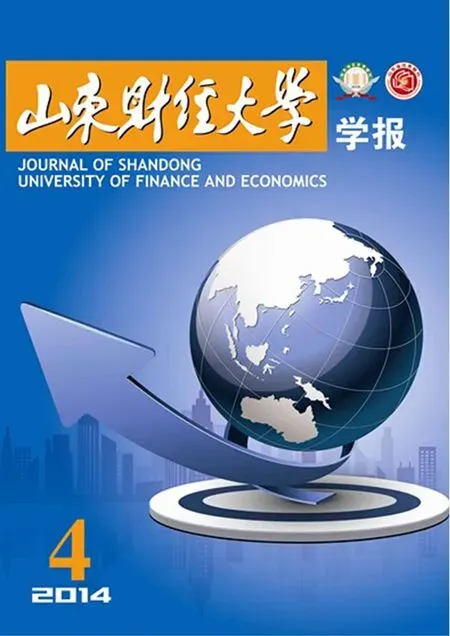《新经济》与抗战时期后方学人的经济研究
赵桂平,崔 丹
(1.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基础部,山东 烟台 265500;2.中山大学 国际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9082)
《新经济》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配合当时形势、关怀抗战民生、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期刊,凝聚了大后方众多知识分子的力量,对经济形势、经济政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抗战和建设国家的对策,保留了经济研究的各种资料。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份期刊重视不够,专题研究极少。本文试图以《新经济》上所反映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言,对其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作一初步探讨。
一、《新经济》的创办和基本情况
《新经济》半月刊创刊于重庆,1938年11月16日正式出版第1卷第1期,每半年编为一卷,至1945年第12卷停刊。期间因敌机空袭重庆,多次短暂中断。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新经济》始终坚持采纳多家之言、共同商榷抗战时期的国计民生问题,关心抗战及战后经济和建立新国家等事宜。正如编者在创刊号中所言:“《新经济》是讨论经济问题的刊物,并诚意的欢迎大家利用这个刊物,来考虑与促进经济政策,以及一切建国的方案”[1]。《新经济》所关注和讨论的“经济”问题,不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其他与建国有关的经济原则和方法,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经济建设固是重要,其它有关大计的内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检讨,亦一律欢迎。实行各种方针的方法,都需要详细的商讨,许多新意见新材料都应该评介质证。因此我们凭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为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媒介,甚盼热心建国的朋友,忠言建论,随时见赐,共策进行”[1]。
《新经济》初创时,“论文”主要登载投稿人的文章,“书评”介绍和评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著作,“现代经济档”是登载战时的经济法规及各机关的重要经济报告,“编辑后记”是编者对刊发论文的简单介绍和评价。从第1卷第6期开始,《新经济》内容稍作了调整,因战时的经济法规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载,如选择其中一二进行登载又难免造成挂一漏万,故取消了“现代经济档”,集中发表投稿者的文章和书评。
《新经济》自创刊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多方关注,从“编辑后记”中可知,由于投稿者众多,刊物编者多次因排版时间问题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大后方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对国家前途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的关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此外,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参与到国家各项事务的讨论中,其中比较积极的经济机关有经济部、交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四联总处、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总行、农本局、农业管理局、农林部垦务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汤鹤逸,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的沈宗濂,广西教育厅长邱昌渭,卫生署的王尔乐、刘行骥,外交部的袁道丰、杨云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吴紱征,都先后在《新经济》上发表文章[2-4]。
《新经济》编者在《新经济的使命》中说:“我们此刻不但须从政权和军权统一之中去追求国力,我们更须进一步的谋经济的统一。以往经济的割据也是国力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举凡一切货币的、税收的、交通的、资源的把持,我们应火速的调整”[1]。正是基于这一使命,《新经济》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为战时及战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内政外交事宜建言献策。
二、《新经济》与“经济战”、“经济建国”
《新经济》半月刊是关注国家经济建设、讨论经济事务的刊物,讨论的经济问题上至国家经济大政方针,下到百姓柴米油盐,面面俱到。学者们通过对战时国家经济现状和面临问题的剖析,指出抗日战争亦是“经济战”,提出“经济建国”的思想。
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经济》,表达“经济是诱发战争最重要的原因,经济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有力的因素”的观点,他通过分析古今内外战争爆发的原因,指出“经济既为诱导战争最重大的原因,经济也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具体到中日战争,他分析道,我们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及敌人,敌人是工业国家,我们还是农业国家,因之,我们军队的装备也不如敌人;然而现在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的精疲力竭了,丧失再战的勇气,不过敌人现在要‘开发华北’,‘振兴中华’,劫略华南,以消化它的战果,我们要彻底打击敌人,使其对华侵略战争根本的失败,今后唯一要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凡是中华民国的人民都有这种责任;须使人人都能尽对敌经济作战的责任”。他强调“加强对敌经济作战,这是决定中日战争最大的关键”。其后李树青、庐郁文、徐日坤也纷纷就“经济战”一题发表看法。李树青[6]在《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一文中分析了都市与内地经济现状,提出了经济作战的对策,认为“我们亟应认清各战区与后方物资的供需实况,然后切实的订下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的策略。……我们的目的,只在设法使敌人的经济力量逐渐减损,我们的日益增强。一切合乎这个原则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庐郁文[7]、徐日琨[8]分别就游击区的经济战、浙西的敌我特产经济战等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对国内特定区域经济作战的思考。
学者们对战时国内经济的讨论引起多方关注,“经济建国”的思想得到认同,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经济建国”思想的重要性、经济建设的原则和要旨的理解。毕敏[9]在《经济建设要旨》一文中认为,“经济建设为建国的基本工作,经济建设需向新的方向发展、经济建设宜注重国防”;宋则行[10]对经济建设的远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认为“今后经济建设的理想是计划经济制度的树立,它是一副远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尽全力去推进国营事业,以期逐渐造成其在全经济领域内的支配作用,这是接近远景的阶梯”,并提出了经济建设远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在这过程中,我们最须注意的是:怎样使全国生产资源在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怎样使外来的经济实力不致成为国营事业扩展的扰乱因素,而反为扩展的重大助力”,给战时和未来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建议。另有不少学者从经济与各方的关系、经济政策和方针措施以及与经济相关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水电政策等发表见解。吴景超[11]分别就经济建设与中国资源、人才训练的关系作,列举了44种与国家经济关系密切的资源,并将它们区分为“不能自足资源”与“可以自足资源”做了说明,认为我国将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资源方面并不存在问题。吴景超[12]还分析了我国农业和工业所需人才的比例和各类职业所需求的人才类型,提醒政府加强对各行业人才的训练。再如,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会1944年12月29日通过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提出了中国实业开发的原则性问题,对此,学者们就经建原则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并就第一期经建原则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经济体制、水电政策等,提出了全面的意见。[13-17]
《新经济》针对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还设立专栏或专号进行研究和探讨,如学者们关注的“利用外资问题”、“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经济地理问题”、“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工业建设问题”、“战后建都问题”、“经济统制问题”、“战后经济制度问题”、“土壤、机构及市区问题”、“区域经济问题”、“森林问题”、“工业化问题”、“粮食问题”、“交通问题”等设有专栏,出版了“农业特辑”、“货币金融特辑”、“金融专号”、“经济建设原则专号”、“物价专号”。在各类针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文章中,学者们或深入剖析出现某类问题的原因所在,或开门见山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有的文章是调查报告,有的是详细的数据统计推论,有的是对现行经济制度、经济机构的评论。内容涵盖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希望政府当局能重视战时社会的经济问题,并采取措施扶持其发展,以经济为后盾支持战争的胜利,并为战后的国家经济建设奠基。“经济建国”的意识可以说是《新经济》中得到反复强调的观念,也是大后方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业学识贡献于民族自救战争的重要体现。
三、《新经济》与战时经济政策建言
《新经济》半月刊是大后方知识分子对战时国家经济领域建言献策的言论阵地,他们关心的问题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方针、经济政策,也有中观层面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经济领域的具体建设措施,更有大量微观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的调查和统计,还有与经济相关的交通建设、人才训练、劳工素质等的观察分析。
战时的政府财政、税收、货币和金融政策,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重点,李卓敏[18]认为战时国家预算对战后经济的影响极大,不在战时平衡国家预算,则“不仅作战期中我们的经济问题将愈趋严重,战后经济建设也将更加不容易”,并提出通过增加税收平衡预算的方法,玄伯[19]专门针对平衡收支的方法进行诠释。张纯明[20]在《三十年度预算的展望》一文中,对战时国内的开支做了分析,并提出三十年度预算的意见,特别提出“我们希望政府能切实的节约。在提倡简约建国的时候,政府要先为国民梳理一个节约的好榜样”,主张政府通过裁撤不需要的机关等措施来力行节约。对战时国家税收政策、保护关税措施,崔敬伯[21]认为政府应采取强制手段征收直接税,抑制战时个别企业和个人的奢靡,他说:“吾人常见长袖善舞一掷万金之辈,其消费能力,至足惊人。违背抗战之国策,助长物价之暴涨,流弊何堪设想。于此再不以课税之方式,节制其消费,并转移一部分购买力于国家,则前方无量之牺牲,适足造成后方分配至不平,当非社会正义之所许。”高平叔[22]亦就开源与增税的关系做出说明,李锐[23]对“统一征课行政”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关系,朱伯康[24]和宋则行[25]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太落后于人,为了保障民族的独立生存及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工业化及现代化,实为刻不容缓的工作,政府应在特殊时期采取保护国内经济的措施。
日本的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生态,战时的中国市场是一种萎靡、消极的氛围,各种经济问题伴随着战争的进行愈发突出。战争带来的高物价,是最为明显的后果,因而对战时物价高涨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新经济》讨论的热点。赵晚屏[26,27]描述了战时物价高涨的情形,田地、农作物种植、农民收入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并从战争造成人们的危机心理,加剧物价上涨的角度,阐述了“我们与其说物价是物资和货币的关系之表示,不如说物价是持有物资和货币的两个人的心理交互作用而决定的一种统一的条件,心理的变异显然比物资和货币的变异程度更大”。就当时一般认识而言,这是一种颇为新颖的思考。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战时物价问题的讨论,孙拯[28]在《建设与物价》一文中说:“物价问题影响国民的生计,抗战的效能,力谋解决,势所当然”。杨蔚和伍启元也对物价问题进行探讨,杨蔚[29]在《吾国最近之物价问题》一文中首先总结了“学者对于最近物价问题的见解与批评”,继而探究了物价问题的表现,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政府管制价格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伍启元[30]分析了当前物价问题的性质,认为“当前物价问题包括物价加速率猛涨、价格失衡、生产失衡、分配不平均、战费负担违反正义和社会解组等严重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问题,物价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这些观点,不仅仅看到了物价高涨的问题,还看到了其背后的根源。对如何稳定当前物价,大多数学者认为平衡和稳定物价的主要手段是实行“物价管制”。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对于高物价水平带来的货币问题,学者们也非常关注,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庄智焕[31]认为,“我国现在要稳定物价,避免危机,则统一全国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实为首要工作”,“苟使人民对关金券确切信仰,则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即可统一,而促成物价高涨之心理因素亦可消除。同时,政府对法币之发行,应竭力避免增加,再提高银行利率,使人民乐于储蓄,而不重囤货居奇或囤货备用,则促成物价高涨之经济因素,亦可减少”。另有学者对“如何稳定法币信用”、“法币回笼的条件”等相关的应对货币问题的方法展开讨论[32]。战时国内的高物价水平导致外汇涨价等汇率问题,采取何种内外汇政策,很多学者做了调查研究,彭学沛[33]对于当时社会上因法币汇价大跌导致的误解,做了澄清,他认为:“第一,虽然中国尚处于战时状态、法币大跌,但是并不代表法币在战后会跌到不值钱的地步;第二,我国外汇平定基金虽日渐减少,但是并不一定说明法币价格会跌的没有底止;第三,我国币值跌落,日本能维持的久,并非意味着中日战争日胜中败”。这种分析澄清了对外汇涨价的误解,稳定了部分人因币值大跌导致的恐慌心理。宋则行[34]在《战后吾国对外汇率厘定标准的商榷》一文中,站在还处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43年,就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引导人们思考战后我国外汇政策的问题。
战时国内的金融事业受到打击,学者们通过主张“金融动员”,对金融政策、金融机构的管理等发表见解,不少人引用美国、德国、英国等国的金融理论,以为国人参考[35];在金融机构的管理上,杨荫溥[36]认为应加强对银行的管理,李卓敏[18]认为加强信用管理尤其重要。在政府的经济措施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处于非正常状态,日本的军事、经济侵略已经使得市场失去了自动调节的功能,政府需对战时经济采取“管制(统制)措施”,从而使得“经济统制”的讨论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和更直接的现实支持,有的学者从战时的现状谈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经济上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以最小的耗费,聚集最大量的经济利源,以供应作战时的必须消耗”[37],有的学者分别就物资管制、外销物资统制、粮价统制等分别说明[38]。
战时的交通运输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新经济》专门对此出了一期交通专号。张嘉璈[39]在《抗战以来之交通设施》一文中,从铁路、公路、航政、电政、邮政各方面讨论了交通与战时军事的关系。薛光前[40]就交通行政管理问题,在《论交通行政管理》一文中痛陈“运输机关之事权过于分散,力量无法集中,效能无法增进,补救之道,应将全国公路运输机关,部分军用民用,一律由军事机关统一管理,以应战时需要”。另有不少学者从战时我国的驿运事业状况,如何增进公路、铁路、水路的运输效率等方面发表看法,给当时的交通运输业提供大量的参考。
对于战时国家工业建设和区域工业现状,经济学家方显廷[41]在《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之没落及其复兴途径》一文中,分析了战争导致工业区域的沦陷,复兴工业应从发展国防工业、统制工业建设、兼重大小工业、发展内地工业、利用民族资本、联系农工生产、统一工业行政等方面进行。方显廷[42]还指出,战时加强西南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对于抗战十分必要,“自军兴以来,我国最高当局,采取以空间战胜时间之抗战政策,西南各省,遂一跃而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及交通之重心,开发西南各运动,遂为朝野上下所瞩目。”彭信威[43]也发表了西南经济建设的意见。抗战期内,东部和沿海省区经济受到重创,相比之下,四川、云南等省区列强势力并未完全入侵,不少学者充分考虑和西南各省物产丰富、地势优越等优势,建议大力发展西南各省的经济,以作为全面抗战的经济支柱。高叔康对四川经济现状和未来的思考,郭恒对云南省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对重点发展西南省区经济重要性的阐释。不少学者就当时工业的现状和存在的弊端,如工业材料供应管理问题、技工的管理问题、民营工业组织动向、工厂联合会的运作等,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44]。虽战时工业受到了极度的损害,但是学者们坚信抗战必胜,对战后国家“工业化”、工业建设区位等问题提前作了建言献策。壳士[45]就战后工业政策建议,“经济建设为战后唯一重要的任务。经济事业中头绪甚繁,又以工业建设为其中最有关系的工作”,并制定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有关战后工业区位问题的讨论,陈振汉[46]指出,战时轻工业和重工业区位分布中有不合理之处,区位不当会造运费剧增、管理成本高等弊端,战后工业区位分布不得不考虑区位问题。任美锷[47]分别就“实业计划中的工业区位思想、战后中国工业的区位以及钢铁工业的位置问题”发表意见。关于战时国家重工业的建设,钱昌照[48,49]认为在利用外资、矿产勘探、工业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的惨痛教训,需要当局去反思;还针对我国重工业的现状,思考未来的发展,提出重工业建设需要考虑“人”和“物(资源)”的条件,负责重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使命,协助国家走向独立富强,重工业建设还不能缺少“公、诚、拼”的“精神”要素,如此,才可以振兴重工业。在重工业建设中,矿产资源的利用尤为重要,李树青[50]倡导“保存我们的天然富源”;学者们针对国内的矿产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如对西南煤田、宁属资源、甘青矿产、陕甘矿产的调研[51]。吴景超[52]、徐梗生[53]、青水[54]对国内重要煤、铁、金、铜矿山,如龙烟铁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本溪湖煤矿、凤凰山铁矿的调研,为更加清晰的了解战时的矿产资源状况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提醒政府对矿产资源的保护、重视和利用。轻工业建设同样关系着国计民生,后方学者们发表大量针对战时制革工业、棉纺织业、制盐业、制茶业、蔗糖业、紫胶业、植桐业和制酒业的文章,倡导加强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建设[55-58]。
在农业经济领域,学者们对战时国家农业政策和农业经济相关理论、制度进行解析,吴景超[59]和董时进[60]对农业政策的讨论,都主张农业不仅仅要满足自己自足,还需要扩大生产、农产品输出,农业管理需要加强农业合作事业。农业管理和农业机构的运作,关系着农业建设的重要方面,学者们主张健全农业管理机构、管制制度,完善农田土地金融机构的设立,提高农本局、农业合作社等组织的作用[61]。有的学者主张对全国土地利用进行调查,指出“土地是农业的基础,一国农业进步与否,必须视其土地利用是否合理化而为断。土地利用是世界经济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尤为立国的基础问题”,并针对“中国土地利用的详细情形,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智识”,主张绘制“土地利用图”,以明了全国土地利用情形的基本工作[62]。有学者对我国西部土地耕作情形进行关注,对红土区、黄土区、棕钙土区、黑钙土区、紫色土区的土质进行详细分析,给各土区的农业产生提供借鉴[63]。另有学者从“土壤保存”问题进行阐述,主张保护土壤[64]。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资源,学者们对土地资源的研究、倡导利用和保护,为了解战时土地状况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提醒了政府对土地的保护和利用。对于战时我国森林资源的状况,有学者对日寇掠夺我国森林资源进行清算,对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台湾省、朝鲜、库页岛及我国内地森林的面积、树种资源进行统计,并希望收复失地之后各区应设置经营管理机构,合理整理利用[65];学者们对土地、农产、森林资源的统计,给政府提供了大量借鉴参考,同时,也为后来学者对战时资源的研究提供史料价值。
结 语
《新经济》刊载了大量的战时经济资料,当时国家经济各领域的调查和研究,学者们对战时国家经济的思考和建言献策,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大后方学者们所关注的不仅是国家的经济事业和经济建设,也从经济抗战的视角,表达了他们对于政治、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关怀和讨论。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大后方知识分子自觉地将自身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合在一起,将自己的专业学识与抗战时期经济建设的现实结合起来,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推动了经济学的本土化发展,不仅为抗战现实提供了智力上的贡献,同时也为学术和学者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新经济编辑部.新经济的使命[J].新经济,1938,1(1).
[2]新经济编辑部.编辑后记[J].新经济,1938,1(1).
[3]新经济编辑部.编辑后记[J].新经济,1940,4(8).
[4]新经济编辑部.编辑后记[J].新经济,1941,3(13).
[5]高叔康.经济战[J].新经济,1940,4(8).
[6]李树青.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J].新经济,1940,3(9).
[7]庐郁文.论游击区经济战[J].新经济,1939,2(9).
[8]徐日琨.浙西敌我特产的经济战[J].新经济,1940,3(7).
[9]毕敏.经济建设要旨[J].新经济,1940,3(5).
[10]宋则行.经济建设的远景和近路[J].新经济,1942,7(10).
[11]吴景超.中国资源与经济建设[J].新经济,1942,8(5).
[12]吴景超.经济建设与人才训练[J].新经济,1942,8(2).
[13]曹立瀛.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平议[J].新经济1945,11(12).
[14]简贯三.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的工业政策[J].新经济,1945,11(12).
[15]王祥春.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的外交政策[J].新经济,1945,11(12).
[16]齐植璐.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的经济体制[J].新经济,1945,11(12).
[17]吴承洛.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的水电政策[J].新经济,1945,11(12).
[18]李卓敏.我国财政政策之商榷[J].新经济,1940,4(8).
[19]玄伯.论平衡收支[J].新经济,1941,6(1).
[20]张纯明.三十年度预算的展望[J].新经济,1940,4(6).
[21]崔敬伯.直接税与中国财政[J].新经济,1941,6(1).
[22]高平叔.开源与增税[J].新经济,1942,8(4).
[23]李锐.论统一征课行政[J].新经济,1941,6(1).
[24]朱伯康,宋则行.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J].新经济,1942,8(7).
[25]宋则行.关税政策、进口限额、外汇统制[J].新经济,1943,9(11).
[26]赵晚屏.物价腾涨下的广西农村[J].新经济,1940,4(6).
[27]赵晚屏.危机心理和战时物价上涨[J].新经济,1941,6(5).
[28]孙拯.建设与物价[J].新经济,1941,6(9).
[29]杨蔚.吾国最近之物价问题[J].新经济,1938,1(6).
[30]伍启元.当前物价问题的性质[J].新经济,1942,8(1).
[31]庄智焕.如何稳定我国币值的一个建议[J].新经济,1942,7(11).
[32]孙丹忱.如何维持法币信用[J].新经济,1931,1(12).
[33]彭学沛.论外汇涨价[J].新经济,1939,2(5).
[34]宋则行.战后吾国对外汇率厘定标准的商榷[J].新经济,1943,9(8).
[35]邓传诗.德国金融政策与物价问题的一斑[J].新经济,1940,4(2).
[36]杨荫溥.加强银行管理[J].新经济,1941,6(6).
[38]陈振汉.战时经济的统制与放任[J].新经济,1940,4(12).
[38]杨桂和.物资管制的正当途径[J].新经济,1942,8(1).
[39]张嘉璈.抗战以来之交通设施[J].新经济,1939,1(8).
[40]薛光前.论交通行政管理[J].新经济,1941,5(9).
[41]方显廷.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之没落及其复兴途径[J].新经济,1938,1(4).
[42]方显廷.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J].新经济,1938,1(2).
[43]彭信威.四川西南区工业化现在及将来[J].新经济,1938,1(5).
[44]傅安华.工业建设中之工业管理问题[J].新经济,1941,5(9).
[45]壳士.战后工业政策的建议[J].新经济,1943,9(7).
[46]陈振汉.战前工业区位的评价[J].新经济,1941,5(9).
[47]任美锷.实业计划中的工业区位思想[J].新经济,1942,7(1).
[48]钱昌照.两年半创办重工业之经过及感想[J].新经济,1939,2(1).
[49]钱昌照.重工业建设之现在及将来[J].新经济,1942,7(6).
[50]李树青.保存我们天然的富源[J].新经济,1941,5(1).
[51]黄汲清.西南煤田之分布与工业中心[J].新经济,19391(7).
[52]吴景超.龙烟铁矿的故事[J].新经济,1938,1(6).
[53]徐梗生.本溪湖之炼铁[J].新经济,1942,7(1).
[54]青水.如何加紧开采我国至金矿[J].新经济,1939,2(12).
[55]王祥麟.我国之制革工业[J].新经济,1939,2(9).
[56]邢苏华.抗战期内的四川盐水[J].新经济,1932,1(9).
[57]刘宗乐.云南紫胶在国家经济上之重要[J].新经济,1940,3(4).
[58]董新堂.国内之橡胶植物[J].新经济,1945,11(10).
[59]吴景超.我国农业政策的检讨[J].新经济,1939,2(10).
[60]董时进.我国对于农业政策的主张[J].新经济,1940,4(2).
[61]郭垣.农业经济建设与合作金库制度[J].新经济,1940,3(3).
[62]任美锷.举办全国土地利用调查刍议[J].新经济,1943,9(9).
[63]周昌芸.吾国西部各土区之耕作情形[J].新经济,194310(2).
[64]吴士雄.土壤保存之学说[J].新经济,1943,9(9).
[65]董新堂.日寇掠夺我国森林资源之清算[J].新经济,1943,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