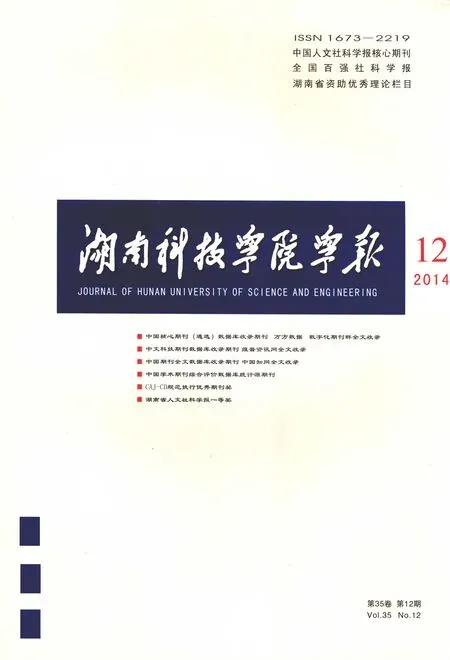田人诗作的文化解读
周甲辰
(湖南科技学院 办公室,湖南 永州425199)
讨论永州及湖南近年来的诗歌创作,不能不提及《永州日报》编辑田人。田人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曾在《诗刊》、《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刊发作品,结集为《虚饰》、《三十年后·大湾村》等。田人的诗作没有宏大的叙事,也鲜见酣畅淋漓的抒情,但却诗味醇厚,风格独具,具有经久的艺术魅力。
一 驮着故乡上路
大湾村是田人生命的出发地。那是南方丘陵地区极普通的一个小村庄,地处荒僻,即便在永州,也鲜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田人没有隐晦它的贫穷:“饥饿的光在它的上空盘旋”(《萤火虫》);没有隐晦它的落寞:“天井中漏进的光照着那只木桶”(《旧屋》);没有隐晦它的忧伤:“低矮的山在舞蹈/被低矮的大湾村撕裂的忧郁/排列,涌起、埋怨、摇晃”(《印象》)。与当今中国许多小村庄一样,在席卷而来的城市化大潮冲击下,大湾村也一天天走向破败:“一棵树,在大湾村四十年/它吃过山菜的嘴唇隐现了裂痕/曾经绿得很茂盛的叶子现在很寂寥”(《我不想再说了》);一天天被人遗忘:“用土垒成的屋前坐着的老人,孤零零而毫无欢乐”(《来世今生》。但是,大湾村“在诗人田人心里的高度是无与伦比的”。[1]他深爱着那个地方,将其视为“出淤泥的莲花”和“唯一的精神空间”。在他看来,大湾村那“宽阔的石头和倒悬的青碧的水”,就是他自己的骨头和血液。只有在大湾村,他才拥有快乐(《梦》)。他说:“我不要金钱/我也不要虚假的荣誉/我要与大湾村同浴在星月的银辉下/把性灵埋在高的峰峦”(《诗章》)。
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现代都市越来越强大的诱惑,一辈又一辈农村人从世世代代生活里土壤里拔根而起,移居城镇,乡愁也就成了当今时代最普遍的精神症候。田人很早就走出了他的大湾村,先后投身多个城镇打拼。不一样的是,对于离乡田人显然是痛苦的。他说:“离开家乡的感受如同生活在地狱”。(《说一下萝卜湾》)而且田人的心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湾村。无论走到哪里,他的灵魂总是“被曾有的家时时包围”(《怀念枣红的马匹》)。他认为,自己就如同一只风筝,一生的岁月都已被故乡的荠菜花“用红红绿绿的丝线牵住”(《乡村的荠菜花》)。他把自己喻为一辆马车的轮子,要始终“驮着故乡走向未来”(《故乡若要厌弃我》)。由于身上总驮着故乡,所以,在田人眼里,无论多么高的云端,“也没有高过大湾村的翅膀”(《七天》);即便是与故乡远隔数千公里的廊坊,菖蒲那多年生的叶子,也“被大湾村的风吹着”(《廊坊菖蒲》)。围绕故乡,田人展开了他一系列温馨而美好的想象,他梦想着能“把影子长成丝瓜花,爬在大湾村的房前和屋后”(《风俗》);梦想着能将一盏马灯挂在故乡静谧的夜空(《一盏马灯》);梦想着死后,能在大湾村长睡,身边“长出一些稚嫩的青草”(《姐妹兄弟》)。返乡本是诗人的天职,但像田人这样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境都不肯舍弃故乡的诗人确实还不多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故乡不仅是指个人出生成长之地以及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还意指精神的家园与灵魂的故土,意指生命价值的最终归依。因此,田人坚持驮着故乡上路,不仅是源于他对过往乡村生活的留恋与回忆,更是源自于他对灵魂故土的顽强坚守,对精神生活的不懈追求。这种坚守与追求在一个高度物质化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因为那不仅仅需要情感与勇气,更需要思想与毅力。始终没有从身上卸下故乡的人,无法真正融入多元喧嚣的现代文化;对于繁杂混乱的都市生活而言,他只能是一个外来者,而且永远是一个外来者,孤独是其难以跳脱的宿命。田人的孤独感似乎无所不在。他不时咀嚼并呈现自己的孤独,他说:“我的故乡,我的声名的马车/把我的孤独一件一件,/放在我的灰烬安放的地方”(《归途》)。他感叹:“在这条孤零零的路上/没有一个车夫/我走着,/没有人看得见”(《在这条路上》)。
二 置身底层叙说
草根出身的田人“根茎又细又软”,但却有着异常坚定的信仰。他如飞蛾扑火般,“苦苦地向着太阳”(《向太阳》)。他一直梦想拥有一双漂亮的翅膀,能够忽左忽右自在地翻飞,有时能飞得“比所有鹰飞还猛烈”(《十几亩油菜花》)。他还梦想化身为苦难的骆驼,“在广大的沙漠渴死自己/美丽的驼铃飘扬在天空”(《完成》)。梦想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田人过人之处在于,他在仰望星空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脚下社会底层坚实的土壤。他明知,在当今这个时代,“诗歌和稻谷是低廉的/因此生产诗歌的诗人/与生产稻谷的农民很清贫”,但他“还是愿意做一名生产诗歌的诗人”(《诗人之歌》)。他说:“我不会选择一条寻找金子的道路”(《我不会选择一条寻找金子的道路》)。他酷爱创作,创作也曾给予他无限的精神满足,他说:“说到写诗,好比一个生命一生坐在光明之中/它茁壮成长的样子令世界心痛”。(《我追求的是我所不知的东西》)由于潜心于诗歌创作,他淡化了对金钱、权位等诸多现实价值的追求,坚守着清贫。即便是住在保洁车旁一间低矮的平房里,与蚊虫作伴,“用身体的血做蚊虫的粮食”,内心仍然充满了浪漫的遐想。
基于脚下的位置,田人曾说:“星空高远/生命多么卑微啊。”(《一年又一年》)在创作中,他始终“以弱者的身份出现”[2],身姿放得很低很低。他以故乡大湾村为主要对象,写低低的山岗,写矮矮的土坡,写挂满旧物的篱笆,写湘江式的青石板路。他说:“虽然我仅代表一个村庄,但是我无边的低矮是你最初的忧郁”(《器皿》)。与此同时,他热情洋溢地咏唱了一系列卑微的生命,包括麻雀、蚂蚱、蜻蜓、萤火虫等。他自喻为卑贱的蚂蚁,从一个村庄出发,走得很辛苦,终于来到了镇上。但是它还要承受一路的危险与孤独,经过县城和省城,走到它的首都去(《蚂蚁》)。他写的稗子,明知“自己是一株害草,生命也不会长久”,但却有了一次爱情,“它深深爱着一株稻子”(《一株稗子的爱情故事》);他写的菜青虫,在辰河边歌唱着爱情,“她的歌唱多么动人”(《菜青虫》);他写的田鼠夫妇,相依为命,养儿育女,有过“许多浪漫而历险的经历”(《一只田鼠》)。而在田野里庄稼所剩无几的时候,他则称野猪为“兄弟”并向其发出诚挚的邀请:“坐到大湾村来吧/坐到它的火边来,吃酒和取暖”。(《梦呓》)田鼠、野猪这些形象不仅卑微渺小,而且还一直被视为对人类生产、生活有害的对象,但田人却从中发掘出了最美好的品质和最温馨的情感。他的诗句往往能拨响读者心灵深处最温柔的那根弦,让人留下经久难忘的印象。
在社会急剧转型发展的历史时期,在弱肉强食法则依然盛行的商品经济时代,底层百姓最有可能遭受到无法抵御的变故和残酷无情的碾压,也最容易被忽视和遗忘。田人坚守社会底层的位置,执着地咏唱卑微者的生存与情感,这既离不开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与普通人的身份,同时也体现他对生命意义的肯定和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因此,田人的创作不仅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体现了他博大、包容的人文情怀。他写“乱坟遍布的山冈”与路边那些“仍在蓬勃生长”的花草树木”(《山冈》);写“一只牛犊带着它父亲母亲的血液/一边走一边茁壮地成长”(《一只牛犊的诞生》);写大湾村那颗稀松平常的老树,“人们对它视若无睹了/乃至它的枝上发出的那几片新芽”(《花儿渐渐远去》),所有这些也都源于他对生命的喜爱与敬重。
三 静对自然感悟
田人曾把自己比作“一粒纯粹的泥土”(《青铜村庄》),完全属于乡野,尤其是自己的故乡。他不喜欢城市,也极少写到城市。他说,在城市里他“不能自由地漫步”(《废墟》)。他还说,城市里“没有鸟,没有葱茏土地和瓦蓝天空”,所以他“不会把死去的亲人埋在它的地下”(《回乡》)。但是,他却一直无奈地生活在城市中,乡野的景致“只能在记忆中重温”(《我不知道我所痴迷的路是对还是不对》)。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赋予了乡野以童话般的色彩,使得那里的一切都显得格外美好。在那里,蚂蚱拥有“薄亮的翅膀”(《珍藏》);“狗在秋天的叫声是金黄的”(《秋天的声音》);油菜花在爱情的季节“撒下这些散碎的金子”(《一片黄》);“茅屋经历了忧郁之夏,便展开了希望的翅膀”(《私语的秋日》);大白菜发自内心地感叹:“世界多美好啊”(《一颗大白菜》)。可以说,田人笔下的乡村总那么令人神往。
寄情乡野的田人,就像梦中之人“坐在那里静静观看一只黑山羊”一样(《一首诗》),习惯于置身自然的对面独自静静地观赏对象。一个人一生中反复写到的词虽然很多,但是,田人说自己“只是反复写到了春天”(《反复写到了春天》)。在他的笔下,以大湾村为代表的江南乡村生长着槐树、桃树、石榴树,盛开着油菜花、荠菜花、金银花,还有“梨花似的女子/沐浴在诗歌里(《驶向城连墟》)。在他的笔下,乡野的一切显得特别纯净:那里“见不到一颗尘粒”(《我们的菊花》),“那些花,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它们都是这样,干净”(《一盏马灯》);特别自在:“另外几只麻雀/则在散淡的天上盘飞/年老的那只麻雀在打盹/草垛想着心事/地球自在地转着”(《深秋》);特别安宁:“星空下,豆安睡的时候/月亮也在安睡/万物展开了想象”(《豆》);特别浪漫:“浅浅的溪水中/她在洗着大湾村的心跳/接着便听见了鸟的鸣叫”。(《我的村庄》)翻阅田人的诗,读者还可以见到贞洁的秋日、飘悠的白云、迷蒙的晨露、徐徐的清风等,所有这些景致均能使人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体验到难得的宁静与悠闲,心灵因此而变得更加纯净。
在文艺作品中,纯美的自然景象均是诗人纯美内心世界的形象展示。诗人田人以其未惹尘埃的自由的灵魂静观那远离尘嚣的乡野世界,便留下了这些能净化人心灵的纯美诗章。作为敏锐而多情的诗人,田人在静观和表现自然景象过程中,常伴随着自我独特的生命感悟。值得注意的是,田人在表现生命的感悟时,往往轻触即止,给鉴赏者留出了广阔的艺术空白。
从艺术表现看,田人的诗作“都表现出了适度的节制。既节制感情的泛滥,也节制文字的泛滥”[3]。他淡淡地介绍铁树的命运:“铁树是那个很老的老人栽的/一百年之后铁树开花了/开完花之后铁树就死了。”(《大湾村》)他缓缓地叙述鱼虾的故事:“鱼虾从清澈的溪水里走上岸/坐火车来到市区的集市/他们虽有些不情愿/但是他们没有太多的话说。”他慢慢地告诉自己的爱人:“我们的爱之路是曲长的/要经过一片荒地,那里是一些长者的坟/它们以前爱过,它们的爱化作坟头的花”。(《再到南郊》)在这些诗句中,我们找不到华丽别致的辞藻,感受不到慷慨激昂的声调,也听不到动人心魄的故事。但在反复阅读之后,却能慢慢领悟到诗人关于生命、关于人生、关于历史与宇宙等形而上问题的个人感悟,从而激发出无限的审美想象。所以说,田人的诗作词句虽然很简单,但内涵却很丰富;外表虽然很朴实,但滋味却很醇厚。它带给人的印象,往往就像是诗人笔下的玫瑰花,被珍藏了十四年,始终没能送出去,但“它的颜色仍然像一团火焰”(《一朵玫瑰的命运》)。对于广大读者而言,田人的诗作迥异于时下流行的文化快餐,欣赏它需要静下心来,斟上一杯清茶,细细品味。
田人“不是旁观者,而是一个亲历者,一个在自己故事里不停走动的人,一个可以与自己灵魂对话的人,一个透明的人,一个真情的人,一个执着的人”[4]。在高度物质化的社会固守灵魂的家园,在社会急剧转型发展的时代关注卑弱者的生存,在流光溢彩的现代都市品味大自然的纯美,在众语喧嚣、个性张扬的语境中保持平静与节制,田人的诗作显示了独特的风格,体现了对诗歌艺术的执着坚守。通过田人,人们知道了永州有个地方叫大湾村;大湾村也必将随着田人一步步走向更广阔、更精彩的外面世界。
[1]凌鹰.琐谈田人和他的大湾村[A].田人.三十年后·大湾村[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2]李小雨.大湾村:一个人的诗意故事及灵魂[A].田人.三十年后·大湾村[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3]罗譞.清贫的守望——评当代青年诗人田人的诗集《虚饰》[A].田人.永州这个地方[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
[4]大卫.比金子更深远[A].田人.虚饰[C].北京:华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