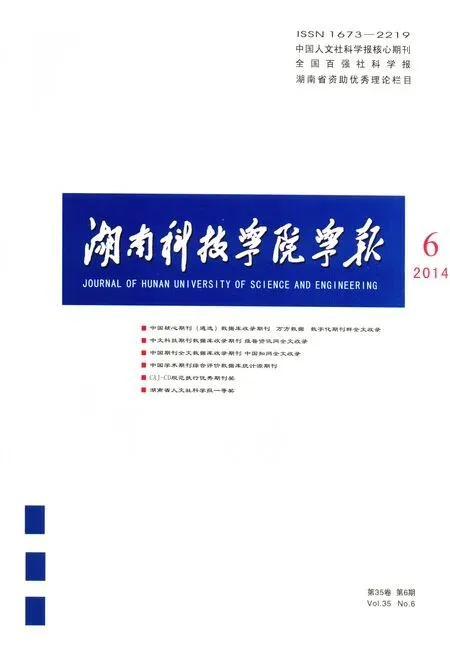阿马蒂亚·森与罗尔斯全球正义思想比较
王 芳 邹海贵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阿马蒂亚·森与罗尔斯全球正义思想比较
王 芳 邹海贵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罗尔斯的全球正义思想主要强调基本人权,关注“承受负担的社会”。阿马蒂亚·森认为,需要超越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评价一国内部的公正,为了解决全球利益分配的不平等需要变革全球性的制度安排。阿马蒂亚·森批判罗尔斯的全球正义具有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在评价标准方面放弃了公正原则,采用的是“封闭的”中立性,没有将他的差别原则应用到全球领域。阿马蒂亚·森的全球正义思想具有更大的实践性和优越性,对解决当今全球普遍存在的正义问题,给出了较为可行的策略和方案,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问题提供实质性的指导。
阿马蒂亚·森;罗尔斯;全球正义;比较
当前,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下,人类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日渐走向一体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空前加强,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存在秩序和生存方式。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也在不断扩大,贫困、不平等、恐怖活动、战争和自然灾害等不仅影响一国之民生,也威胁着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实现全球正义?以及实现何种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难题。
一 罗尔斯的国际正义①严格说来,国际正义与全球正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际正义以国家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是道德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而全球正义本质上是“以人为关注中心”的,是一种类正义,是道德普遍主义的,其价值取向上是世界主义的,而不是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是对国际正义的超越。参见邹海贵《社会救助制度的伦理考量》[M].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0页。思想
人们关于正义的探讨大多都预设了一个政治边界,即民族国家。古代社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即是城邦正义,正义的原则仅局限于国家或民族范围内。罗尔斯把正义分为三个层次,即局部正义、国内正义和全球正义。作为公平的正义是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是“应用于国内正义的――基本结构的正义”,而局部正义的问题和全球正义的问题“需要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分别加以考虑。”[1]罗尔斯的全球正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万民法》中。
大致来说,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思想:第一,人类个体享有生存的基本权利,而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对它进行干预可能就是有辩护的。罗尔斯指出,人权不应被当做特殊的西方传统观念而被拒绝,人权为国内政治与社会机构的合宜性建立必要的标准,“它们是人民中多元主义的界限”[2],同时,人权也是人民间强行干涉乃至武装干涉的界限。也就是说,罗尔斯把普遍人权作为一种底线伦理和普世伦理。所以罗尔斯充分肯定人权在万民法中的作用,把人权作为国际正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在《万民法》提出了三种基本的人权,一是生命权,即维持生存和安全;二是自由权,即摆脱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三是财产权。第二,关于如何解决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罗尔斯的思路是:组织良好的人民有义务援助“承受负担的社会”。罗尔斯全球正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和平问题,也就是战争正义的问题,对于全球分配正义整体上持否定态度。罗尔斯把世界上的国家(罗尔斯所谓的“人民”)分为“组织良好的社会(良序社会)”和“承受负担的社会”。罗尔斯把“良序社会”描述为由某个公共的(政治)正义观来有效地调节的一个社会。而“承受负担的社会”则是指承受不利条件的社会,这种社会缺乏政治及文化传统,缺乏基本的人力资源和技能,且缺乏良序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和技术资源等。罗尔斯认为组织良好的社会有责任和义务援助“承受负担的社会”,使其成为组织良好的社会。“此一目标实现之后,便无须进一步援助,即便如今组织良好的社会依然相对贫穷也是如此。”[2]罗尔斯并不认为援助“承受负担的社会”的理由是分配正义的理由,他也没有把这种理由看作是慈善的理由,他认为援助的基本准则是帮助他们改变政治和社会文化,因为人民财富的目标与其社会的政治文化、政治德性和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由此可见,罗尔斯并没有把他的差别原则应用到全球领域,他对世界主义的分配正义持否定态度。对罗尔斯来说,要把人民之间的平等尊重和促进基本人权在全世界的实现设想为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通过实施某种全球的分配正义,以此来调节不同社会或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可能是不必要的。
由此可见,对罗尔斯来说,全球正义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秩序,或者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革目前的国际秩序,以保证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基本需要都能有保障地得到满足。罗尔斯并不否认援助的责任可能要求资源、财富的国际转让,但他强调国际或者政府必须把实现其人民的基本人权视为首要职责。罗尔斯的学生涛慕思·博格(Thomas W. Pogge)认为,罗尔斯在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上应用不同的道德原则意味着一种任意的歧视,这种歧视支持富裕社会而反对全球的贫穷社会[3]。博格论证说,在罗尔斯的国内正义理论和国际正义理论之间有一种不融贯性:罗尔斯在前一情形中认同了规范的个体主义(normative individualism),但在后一情形中却拒斥了这个思想基础。
二 阿马蒂亚·森全球正义思想及其与罗尔斯的比较
(一)森的全球正义思想
阿马蒂亚·森的全球正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全球正义的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关于全球正义的本质问题的认识;三是关于实现全球正义的路径是改革不平等的全球制度。
首先,森认为全球性正义成为可能是解决诸如全球变暖、全球性经济危机等问题,或者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等全球性流利疾病的关键。他指出,2009年哥本哈根环境峰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之前全球性的相关的公开讨论很少,所以在处理世界事务时,忽略全球性对话是行不通的。森认为,“我们需要超越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评价一国内部的公正。首先,一国发生的事情及其制度运行的方式,势必会影响他国,有时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想起恐怖主义或反恐行动,甚或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拉克等事件时,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超越国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其次,每个国家或社会都可能持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而对此需要从全球视角进行审思,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拓展所思考的问题范围与种类,并且唯有如此才能通过其他国家或社会的经验,对潜藏于特定的道德与政治评判之后的事实性假设加以思考。例如,对与妇女不平等相关的事实和价值观,酷刑或与此相关的死刑的可接受性进行全面的评价,全球性的思考会比局部的讨论更加重要”[4]。
其次,关于全球正义主题的思想。森指出,“不平等是全球化的核心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全球化利益的分配问题”[5]。全球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涉及潜在财富的分配,在穷国和富国之间以及在一国内不同集团之间的分配。在全球化条件下,在世界范围内,世界各国的穷人能否获得什么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的份额和获得的机会是否是公平的。所以森认为,全球正义的中心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是对制度安排的总体格局的不平等进行改革,这种不平等产生了对全球化利益的极为不公平的分享。收入不平等是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越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国家政治越不稳定,同时政治的不稳定也反过来对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应该共同面对全球范围内的贫困、不平等和灾难等各种问题。
第三,森指出,“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也带来安全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制度因素引起的,解决这些不平等不可能完全依靠经济增长,而需要依靠非市场制度和国际机构改革。森分析了引起不平等的6种非市场制度因素,如全球性的民主和参与管理制度、跨国公司制度、多样性的全球制度安排、专利制度、对军事和种族冲突、地方战争以及全球军事支出的全球化进行管理的制度问题以及国际机构的管理制度和全球金融制度结构的制度漏洞等。所以,森指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剥夺和分配不平等问题应该进行非市场制度的改革,在国际方面应改革旧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的制度结构,或者设立新的国际专门机构来解决全球性的不平等问题。森的思路显示了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强烈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也暗示了发达国家应该在实现全球分配正义的任务中承担主要责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6]。森在批判罗尔斯的基础上肯定全球化存在的必要,也承认全球化带来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森认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特别重视非市场制度改革和国际机构的作用。森认为,制度改革不仅包括国内制度的改革,也包括世界制度的改革,不同制度之间需要相互补充和相互依赖。与此同时,制度不仅包括市场制度也包括非市场制度,非市场制度譬如民主制度、社会机会以及政治自由方面的制度。国家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可以通过制定新规则、改革旧规则或者设立新的国际机构来解决。国际规则的改革譬如国际贸易协定、教育交流、技术传播、环境保护等等。
(二)森对罗尔斯全球正义思想的批判
森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批判了罗尔斯契约主义方法的局限性。森指出,罗尔斯将正义理论视为一套“理想的社会制度”,对于主权国家的依赖使得研究正义问题的社会契约方法被局限在单个国家的范围内,而全球性的正义则无实现的可能。森指出:罗尔斯所采用的社会契约方法,无可避免地将追求公正的参与者限定在某个既定的政体,或“民族”(罗尔斯称之为“集体”(collectivity),与标准政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具有广泛的相似性)之内。初始状态的机制使人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除非寻求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契约。而正义要求无偏颇的中立与客观,因此,罗尔斯所采用的是“封闭的”中立性,即将观点与关注所涉及的范围圈定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成员之中,由某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作出中立的判断。相反,“开放的中立性”指的是,由于彼此之间无论远近所负有的相互义务、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的相互依赖,以及为了避免地域性的偏见,中立的评价应该包括来自所关注的群体之外的判断。因此,我们需要超越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评价一国内部的公正。
其次,森批判罗尔斯在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中采取了不同的评价标准。森指出,当涉及如何评价全球正义的时候,罗尔斯放弃了自己的公正原则,也没有要求造就一个所谓的全球政权。在《万民法》中,罗尔斯对其由单个国家追求“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论,进行了某种“补充”。但这一“补充”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不同国家的代表之间就礼仪和人道的基本问题进行协商,这可被视为正义的非常有限的特征。事实上,罗尔斯并未致力于从这些协商中推演出“公正的原则”(实际上也无法推演出“公正的原则”),只是关注人道主义行为的某些一般性原则而已。罗尔斯的全球正义思想是有局限的、保守的,并且把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完全归结为内部的政治经济制度,带有政治偏见之嫌。罗尔斯并没有把他的差别原则应用到全球领域,他对世界主义的分配正义持否定态度。
三 阿马蒂亚·森全球正义思想的优越性
无疑,罗尔斯和森的正义理论,包括全球正义理论都具有强烈的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人员利益的道德倾向。森的正义理论在很多方面继承了罗尔斯的思想,但是在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的相互关系上,罗尔斯的两种正义思想是分割的,其全球正义思想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保守性,甚至歧视性,其价值取向是现实主义的。森的两种正义思想具有更大的融贯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其全球正义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世界主义的,对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和优越性。
森的全球正义理论对解决当今全球普遍存在的正义问题给出了可行的策略和方案,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森的全球正义理论与国内正义理论是沟通的、融贯的,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罗尔斯的全球正义是形式正义,而森的全球正义是实质正义。“森多次谈到,基于能力的正义理论具有普适性,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分享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并赞同某些共同的承诺,这是实现全球正义的首要条件之一,因为若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和国家就不可能就何谓正义的问题达成相对一致的看法,更不用说实质性的正义了”[7]。所以,全球正义问题的解决需要以全球普适性价值观的形成为基础。森的这一思想具有明显的前瞻性,为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正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照。在世界范围内,森认为全球化带来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特别重视非市场制度改革和国际机构的作用。因此,对中国来讲,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改革,主动应对全球化。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积极贯彻和谐世界的理念,在国家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各种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的作用,同时增强制度意识,推动制度改革和创新以及国际游戏规则的平等合理,这是我国应对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森的全球正义理论为各国、各地区实现各自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多样的标准和现实途径。比如,同样是贫困地区,中国贫困地区和印度贫困地区的成因以及各种外在条件不同,那么就可以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中国贫困地区卫生条件比印度好,并且中国政府比较重视中小学教育,而印度精英更看重中高等教育,并忽视基本医疗保障[8]。在不同的发展背景下,制定政策时就可以权衡不同的变量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而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应该说,这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现实性,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认为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的原因。
四 阿马蒂亚·森全球正义思想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及不安全呢?毫无疑问,我国国内公平正义的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要在全球正义的框架下来思考国内正义的实现。根据森的观点,就是要给弱势群体以充分的机会,提高他们的各种能力。我国有必要设计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包括完善民主制度和政治参与制度;制定普遍受益的贸易、外资政策;构建弱者扶持体系;建立完善的义务教育支持体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限制并消除种族和性别歧视以提供给不同人群以相同的机会使用自己拥有的要素等等。
[1][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 2002:19.
[2][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85,119.
[3][美]涛慕思·博格.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189-191.
[4][印]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印]阿马蒂亚·森,[阿根廷]贝纳多·科利克斯伯格.以人为本——全球化世界的发展伦理学[M].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2:9.
[6]邹海贵.社会救助制度的伦理考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王旭凤,阿马蒂亚·森.“平等的正义理论”初探[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8][印]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34.
D09
A
1673-2219(2014)06-0121-03
2014-03-06
王芳,女,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邹海贵(1970-),男,湖南新化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校:何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