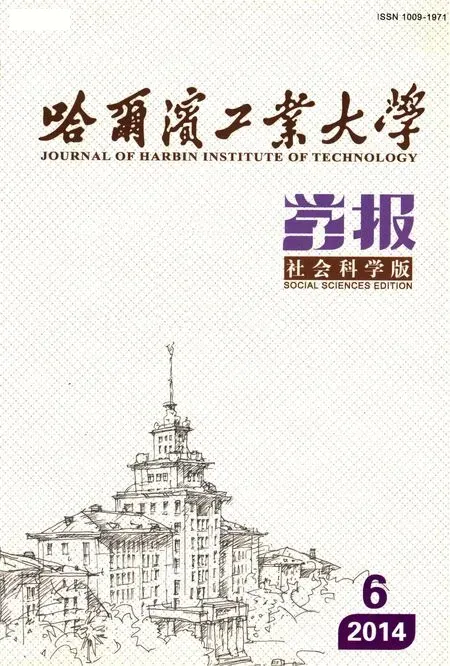论生态良心
周 苏 娅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40)
引 言
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由于人类行为所导致的生态恶化甚至生态灾难的出现,使百年前恩格斯关于“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预言成为现实。自1996年以来,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其中2005年以来,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共927 起,其中重特大事件72起,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1]。面对困境,人类开始审视自身灵魂。正如贝塔朗菲的宣告:“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的西方文明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的伟大创造同时已告结束。新的文明,将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生态意义上的文明。”[2]我们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理念?人类的生态道德如何建设?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涉及到生态道德意识和习惯内化的生态良心,因为生态良心正在道德主体内心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着生态道德观念,操纵着生态道德实践。
一、生态良心缺失原因追问
生态良心是以人的自觉悟性为前提条件形成的自觉生态道德意识、生态道德习惯和生态行为规范的总和。于是,人们开始反思生态良心缺失原因,想从生态伦理道德层面寻求生态转变之道,以观念的转变来突破现实人类困境。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导向
当人类开始反思人与自然关系时,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是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检省。虽然二者之争的意义已远超出是非的定论,但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对峙中败下阵来,使人们确信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是导致生态困境的理论深层根源。
人类中心主义植根于西方传统文化所秉承的机械世界观、主客体分离的二元哲学,理性被视为人类优于所有生物的本质属性,因而人是具有最高内在价值的唯一伦理主体和道德代理人,自然则是“为我而生”的非理性存在物。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理性的张扬,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日益高涨并获空前成功,迅速集聚并确立起了人对自然的中心地位。
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达到顶峰是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命题。这一命题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永远的主体,自然则是客体,人类掌握着价值评价的标准而且是价值评判的主体,人类活动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利益驱使下,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作为最根本的目标和归宿,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极端地认为,大自然本身就是为人类而创造的。康德从理性优越的角度认为,人类具有的理性特质决定了只有人才能获得道德关怀,动物不是理性存在物,因而将它们当作工具来使用是恰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坚持的生态伦理,本质上只是作为价值主体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认为自然界并不是价值主体,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和手段,自然界处于为人类服务的被动地位,即“人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环境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是人的利益,因此,人只对人类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大自然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3]。
虽然人类中心主义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积累物质财富、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过度强调人类伦理主体地位,崇尚人类利己主义原理,人类丢失了约束自我的生态行为和衡量自我价值的尺度——自己的生态良心,无所忌惮地凌驾于自然之上,征服、竭取自然万物。这种人性的堕落和生态良心的缺失显然是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那种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物欲膨胀与精神空虚等现象的存在,使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及其内部的平衡机制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以至于自然把人类施加于其上的破坏后果返还给人类,人类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后果的最终承担者。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消除了。”[4]困境之下人们开始反思,其路向之一,就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念发动攻击,从而也使环境伦理(即生态伦理)兴起。
(二)道德相对主义的行为羁绊
我们承认道德具有相对性,因为它是特定民族或国家的人们的道德,是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道德。但我们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因为良好的社会秩序、生态环境只能依赖于多数人的道德自律,建立在公共道德和法制的基础上。
道德相对主义又称伦理相对主义:它既是人类道德认识中存在的一种独特现象,又是现实的人类道德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方式或实践。道德相对主义主张,当不同文化或个人的根本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我们没有客观的标准去评判它们的优劣。
斯坎伦认为通常有三条抵制道德相对主义的理由,即道德是约束人们遵守秩序和保护我们不受不道德者伤害的重要力量,而道德相对主义者有可能破坏这种力量,就像洛克对无神论者的担心一样;道德相对主义会剥夺我们进行道德批评或道德谴责的权利;即使它不要求我们撤销我们的判断或批评,但它似乎也可能减弱或取消我们道德判断或道德批评的重要性。斯坎伦认为第二条理由更为重要。这种观点说明在生态良心丧失时,道德相对主义者必然会剥夺我们进行道德谴责的权利,或者削弱道德谴责的力度。阿兰·布鲁姆在批评与反思美国文化的书中,曾就道德相对主义问题这样说道,它(指道德相对主义)构成了我们对道德和政治观察的视角变化,从此,本体论问题和传统价值观就大受疑问,其变化之巨,堪与基督教取代希腊罗马世俗文化相比。道德相对主义的要害在于否认存在判断善恶是非的合理标准。在道德相对主义影响下,世界性的生态伦理道德观无法建立,使生态与利益、政治、经济等因素交织在一起,遭遇无法突破的现实瓶颈。生态伦理道德永远无法超越国家、地域、个体的界限,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很难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来达成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共识。没有共同遵守的道德观,就不可能在行为中体现良心,就不可能赢得多数人的忠诚。
正如斯坎伦担心的那样,道德相对主义无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二者彼此是独立存在系统。事实上,生态文明建设中法律与道德在规范方面有很多重合部分。因为任何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必定有普遍有效的法律,这普遍有效的法律就有内在的道德维度,为法律的正义性辩护的观念就是一套道德观念,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普遍有效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同时我们也要清醒意识到,人类如果没有自觉形成生态良心,即使在道德引导和法律强制下,还有多少自信摆脱道德相对主义呢?只有形成生态良心,才可以突破道德相对主义的窠臼,只有当我们的道德共同体中有较多的像缪尔、利奥波德和梭罗那样的肯虚心倾听自然言说的人,我们的社会秩序(包含道德规范)才会与自然秩序协调一致。
如何能让人们在反思生态环境危机时伦理觉醒,重新厘定人与自然关系时良心再现,生态良心内涵的外在表现提供了指向性选择。
二、生态良心问题理论考辨
在道德规范和道德良知延展过程中,生态良心的本质特征要求人们自觉自律,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共融,追求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和谐,体现出对自然界的生态关爱。
(一)伦理上提供着道德标准
良心是内化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感,生态良心是人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内心表达,具有内在性的特征。黑格尔说:“良心于是就是自身确信的精神,而自身确信的精神本身就包含着它自己的真理性。”[5]生态良心是随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厘定,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事实在人们心理上产生强烈冲撞后在内心形成的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它奉行着保护环境的生态思维,主张通过理性判断和善恶评价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们发自肺腑的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精神呐喊,是检测人们生态行为最为隐蔽的内心“监督器”。
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生态良心不是精英们“小资”情绪的呻吟,而是生态危机严峻现实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体现意识特征的生态良心,同样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特征。表现为主体的“生态自觉”、“生态自律”和“生态自责”,它要求实践主体从生态学的维度对生态环境的状况和人们的生态实践做出“绿色”的判断和评价,它可以匡正人们的生产行为,倡导生态实践论,推行生态生产,杜绝无视生态规律、破坏环境的所谓“政绩”,唤醒人们内在生态良心,从思想上彻底根除破坏生态环境的意识与观念。
生态良心也体现了个人对生态环境危机责任感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态环境危机事实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生态良心问题的提出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历史性。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催生了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同时也氤氲着生态良心。社会通过政府倡导、法律监督、学者呼吁、舆论引导等方式,在社会上形成提倡生态良心的强大的“社会场”,这为倡导生态良心的价值取向奠定了很好的社会基础。生态良心是生态文明时代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在人们伦理思想领域的产物,是萦绕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关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反思意识,它倡导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尊重生命的良心觉悟和道德情感。
(二)价值观上体现着生态文明理念
从生态危机和生态道德层面上说,生态良心作为一个道德衡量尺度,可以对人们自身行为是否符合生态规律做出道义上的评价。体现在人们依据心中的道德和良心尺度对生态行为的评估与考量,是判断生态行为的“心灵判官”或“心灵法庭”。康德说:“我清楚地意识到,永远也不能失去良心,它是我心中的神圣法官。”[6]符合生态良心的行为,在人们的良心上产生对大自然的善良之情和怜悯之感,可以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不符合生态良心的行为会受到人们在生态良心上的谴责和质问。生态良心的评价功能是生态道德准则在人的生态行为上的外化,更多的是作为生态评价的手段。
生态良心可以通过人们的伦理尺度自觉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这种调节是内在的,能把主体的生态良心与客观的社会要求,把现实的条件与未来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并成为更为正确的道德选择。它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水平,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保持生态平衡、保护动植物、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作为一种责任和义务。生态良心能够善待万物,展示人们尊重生命、爱护自然的良知。同时,能调节人们的生活方式,教化人们养育“民胞物与”的生态情怀。通过调节功能,人们开始对生态平衡关心、对大自然保护,反映出人类对后代利益的责任心,也体现出当代道德观念的根本变革和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
生态良心可成为人们实践活动的“调节器”和“监控器”,即使没有监督、没有法律制裁,人们也不能违背生态良心,用良心来约束自己对自然的行为。在人们自觉遵守生态道德的前提下,培养人们对自身行为自觉、自愿和自省的生态意识,在人们内心形成和确立养育万物的观念,从而规范和约束人们的生态行为。人们在与大自然打交道时要经常对自身行为“扪心自问”,应当“吾日三省吾身”,这就是对生态良心的追问。这种约束功能增强人们对生态环境行为的自律,积极投身到维护和营造生态平衡的社会实践中去,自觉履行作为生态道德主体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人人都渴望提升自己的生态良心素质,整个社会都倡导生态良心,那么这股强大的道德力量,将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只有在生态良心的感召下,人类才能把分散的、孤立的价值信仰整合起来形成生态道德合力。体现在人们通过生态良心这种“黏合剂”,把一些零碎的、片断的生态蒙醒、生态自觉和生态意识聚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具有强大力量和同一作用方向的群体生态意识。人们凝聚在生态良心的理念下,自觉地在自己的位置上与他人、与社会同侪共舞,即自觉地、内在性地把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控制在制度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生态、敬畏自然的强大合力。
正是因生态良心的外在表现,奥尔多·利奥波德在阐发“大地伦理”思想时,号召人们培养一种“生态的良心”(ecological conscience)素质,主张人类应该把良心的关怀和道德权利从人伦关系延伸到人与大地万物的整个自然界。那么,在人类困境视角下,生态良心要向何处寻路?
三、生态良心素质路径构建
实践中人们认识到,必须在道德领域开展一场“道德革命”,把道德关怀、良心关爱扩大到整个自然界,在人们心中树立对自然万物的道德义务感和良心责任感。
(一)培育生态意识
生态良心属于生态意识范畴,本质上是对人的生态意识进行养育。生态意识是人们在处理人类活动与周围自然环境间相互关系时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哲学意义上来看,生态意识是生态存在的观念反映,它反映了人类主体对自己生存发展于其中的生态存在即社会—生态系统的深层把握,强调从生态环境整体优化角度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指出:“没有生态意识,私利以外的义务就是一种空话。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大地(自然界)。”[7]所以,生态意识在本质上是社会意识在自然界的延伸。
海德格尔用“烦”、尼采用“空虚”、舍勒用“怨恨”指称现代人,足可见现代人的内在精神紧张。紧张的精神状态反过来说明必备东西的遗失,因为“紧张”、“麻烦”简单说就是“有问题”。杜威认为,“所谓‘有问题’来自下面这个事实: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缺少某种东西和需要某种东西。”[8]究竟缺少什么、需要什么而陷入如此麻烦的窘境呢?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场景中的每个人,都是核心问题。”[9]毋庸置疑,人类在生态困境中缺少的某种东西和需要的某种东西就是生态意识。其中,缺少对生态危机的理性察觉和正确认识,缺少重视运用科学技术去调节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及发挥科学技术保护社会生产力的生态科学意识,更缺少国家、企业、个人对生态保护的责任意识以及判断人类行为善恶的道德意识。
提高生态道德意识是生态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形成生态良心的精神依托和动力来源。但意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教育引导的过程。要通过各种培养意识的方法和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人们施加影响,使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并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自觉地养成尊重和保护生态的行为习惯,从而能动地协调人与生态的关系,形成生态良心,实现人与生态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学校、社会、个人要多方协调,共同努力,让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其中,以政府为主导,加强生态文明思想的普及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条件保证和政策支持力度。以学校为主体,将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国民教育和再教育的体系,逐步把生态教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程。以社会为阵地,形成以生态文化意识为主导的社会潮流。
(二)汲取文化智慧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等生态思想,符合现代生态世界观的理论与思想原则,可为当今生态道德、生态良心素质的培养和体现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
“顺天应物、天人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传统。充分肯定了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强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协调、人与自然的统一、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统一。在处理和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不同的思想家和哲学流派的理解和追求也不甚相同,如儒墨突出人道原则,道家则把关注重点放在自然(天)之上,尽管各家学说的态度略有差异,但在相对互补、融合与发展中所呈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与演进的主导倾向是清晰的。体现出传统文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博大深邃的生态智慧。
人类与自然一体,这是生态道德的哲学基础。孔子在《说卦传》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柔刚;立人之道,曰仁义。”《易》以天、地、人三才之理作为自然法则,建立有条理的世界体系。汉代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三者处于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作用,但是它们是“合而为一”,即“事物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道家哲学还有儒家哲学,都把“道”和“德”联系起来,而且认为“生”(包括人和其他生命)与“德”(人类行为)两者是统一的,万物生生不息是人类最崇高的德行,即“至德”或“大德”。孔子以“仁学”为其全部思想的核心,主要是关于人际道德的理论。儒学发展到汉代董仲舒,就其生命哲学而言,可以说是完成了“仁”从“爱人”发展到“爱物”的转变,并把“和合”提到天地生成的本能,万物生成发展的机制,并首次把“和”与“德”联系起来,又把“和”与“中”联系起来,即“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因而“德莫大于和”。道家的“无以人灭天”、“法自然”包含着尊重自然的呼声,强调人为过程不能偏离或违背自然的法则,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人为要循乎天理、合乎天道。
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当人类遵从了生态良心,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自我身心平衡与外在自然的平衡,天道与人道的平衡等都是可能的。
(三)践行生态道德
生态良心究竟能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主要取决于生态道德教育的广度和深度。生态道德教育不同于以往的道德教育,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生存论教育,生存论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类自身的批判与思考,确立人们的普遍信念和基本道德规范,涉及内心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利奥波德曾清醒地意识到,要把道德引入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来,还有许多障碍。他在《沙乡年鉴》中写道:“如果没有一种知识重心、忠诚、情感和信念方面的内在变化,我们的道德观上的重大变化永远不会完成。”马克思则指出:“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10]所以,生态道德教育内容及途径将决定教育的有效性。首先,通过内容的激励养育生态良心,包括树立可持续发展观、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公正、尊重生命、善待自然、适度消费等方面的内容。体现在生态环境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性原则;以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命运为出发点的普遍性原则;激励民众广泛参与的实践性原则;从长远利益出发,贯穿每一个人全部实践过程的持久性原则。其次,营造生态道德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用舆论引导、监督行为,把生态道德教育潜移默化地寓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使他们意识到:“自然界的利益与人类自己的最重要的利益是一致的。”[11]企业自觉承担其环境责任和义务,各级政府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起到示范作用,还要积极主动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和良心教育的调控、监督、赏罚、反馈等机制。再次,发挥道德制度的约束强制作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协调发展,单凭道德的社会调试功能作用有限,必须发挥法律的强制功能,成为生态良心素质形成过程的“他律”。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将社会生态道德内容统一化、规范化,成为道德教育的保障和纲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人人懂法、遵法、守法,当法律和道德相结合、人类生态良心重铸时,人类生态危机问题必然会得以解决。
由此可见,生态良心是生态道德内化的集中标志,表现出了道德主体生态意识的自我确认和形成。生态良心的养育,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呼唤人们的生态良知,把人伦社会的良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存在。
[1]近年来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年均递增29%[N].新京报,2012-10-27.
[2][美]贝塔朗菲.开放系统论与人类社会、人文科学系统[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7,(2).
[3]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33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5][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56.
[6][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27.
[7][美]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2.
[8][美]杜威.评价理论[M].冯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39.
[9][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52.
[11][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