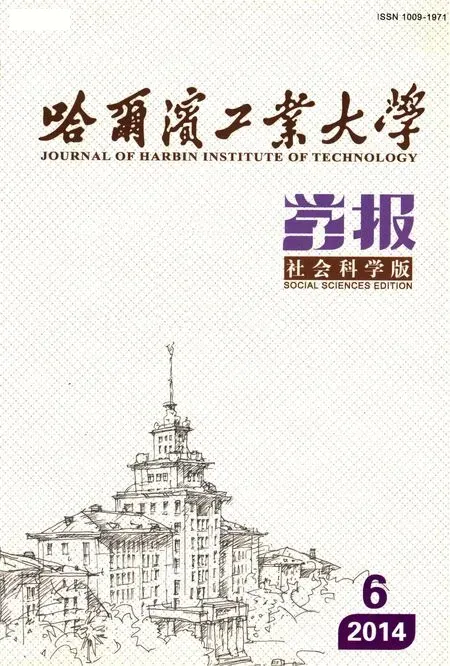论马克思生态哲学的自然生态原理
苗启明,兰文华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a.哲学研究所;b.马列主义研究所,昆明650034)
引 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最初是要以生态学补充马克思主义。但是通过研究,人们发现马克思本身就有深刻的生态思想。比较早的,是德国哲学家施密特,他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指出了马克思自然观的两大特色:一是社会历史性,二是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的确,马克思所关心的自然界,从来不是孤立在人之外的自然界,他看重的是"自然界的人类性",因而,他眼中的自然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这种自然与人类的相互渗透的思想是一切生态思想可能产生的哲学前提,因而应当说,马克思最早奠定了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美国学者豪沃德·帕森斯通过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研究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生态唯物主义,这种生态唯物主义注入到了他后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研究之中,因而他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符合生态原理的。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具体的生态思想的研究,如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其《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指出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大城市的人口集中,使人从自然界中吸取的自然物质不能再回到自然界,从而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交流。中国青年学者杜秀娟,在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研究》一书中,具体研究了马克思的生态经济观、生态社会观、生态伦理观等等。但是,总的来说,学术界既没有从生态学高度研究马克思一般哲学思想的生态意义,也没有从人类学的深度理解马克思在自然界和人类两方面之间所构建的自然生态原理和社会生态原理。能不能从具体原理方面概括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关键。这里,我们拟从生态原理方面,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做一点初步的考察。
通过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开拓,人们公认,马克思在“生态”一词出现之前,就有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并从生态上批判了资本主义。那么,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人类学的理论活动中,究竟构建了怎样的生态原理呢?这里,我们主要从马克思的自然生态思想方面加以归纳,而把他的更重要的社会生态思想另外成文。
一、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生态整体原理
马克思是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思想家,他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来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问题,他把人与自然界视为一种辩证的生态整体,这从以下递进的思想环节可以看出。
(一)人是“自然界的人”和自然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
马克思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首先把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来看待:“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不论人怎样发展,人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与自然界的最基本的关系,首先是自然界内部的互生关系,马克思直接表明了这一思想:“所谓人的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49
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自然界也是“人类学的自然界”。这是马克思从人类学上对自然界的特有理解。换句话说,人所面对的自然界,不是本来意义的“与人无关的自然界”,而是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人化了的自然界”,即通过人的作用而打上了人的烙印的、成了与人血肉相连的生存环境的自然界;是生成人、养育人的自然界;是与“人的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健全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界。人正是在这种人类化了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样一种人化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不是由人任意摆布的自然界,而是有着“自在生活”和自身规律的自然界,是“走着自己道路的”自然界,人既依存于它,服从于它,它不会迎合于人;人又必须认识它的整体联系和它与人的生存关系,协调这种关系,把它人化为自己生命的生存环境,这是人作为有生命、有智慧的存在物,必然要产生的对象性的生态前提。
(二)人与自然界:互为对象的生态整体
“作为自然界的人”与“人类学的自然界”的统一,就是人与自然界互为对象的生态一体性存在,即成为一种生态整体。马克思是以“人的无机的身体”来表达这一点的:“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的人的身体。”[1]49恩格斯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2]
这种把“有机的身体”与“无机的身体”视为“不断地交互作用”而成为一体的思想,是一种把人与自然界视为血肉一体的生态整体的生态思想。它站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一元论这一高度上来了。而当代西方的生态整体思想,即所谓“生态整体主义”,其核心思想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而不把人包含在内。有的虽然包含了人,但人只是其中的一个普通物种。因而,它的哲学基础逃不出人与自然界的二元对立。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超出了这种人与自然界的二元论,上升到人与自然界的生态一元论即生态整体性的立场上来了。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在起点上就高于当代西方生态主义的单纯自然界的起点。
(三)人在生态整体中的能动作用:辩证生态整体论
上面二层意思表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界的生态整体论,包含这样几层规定性:其一,人和自然界在物质和生命基础上是一样的,同一的;其二,自然界是人化的即社会化的自然界,与人类的生存要求是同一的;其三,人与自然界是共同的生存体,是生态一体性的生态共同体、共存体;其四,在这个人—天共同体中,人加入的是能动性、智慧、自由、形式、创造性因素,他成为这个人天共同体中的理性的调控者和主导者,使他成了有灵性的东西;其五,人在这种人天生态共同体中是能动作用与主动构建的因素,使这种生态共同体成为有自身内在矛盾和发展方向的辩证生态整体。
所以,马克思并没有像当代生态主义者那样把人湮没于自然界之中,视为自然界里的“一个物种”,从而得出自然主义的“生物界平等”,而是充分认识到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不同于自然物,因为人有他作为人的精神性、能动性赋予他的自由创造性。马克思表明:一方面,人有“意识和意志”,是“自由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存在物”,即通过社会实现他的意识、意志和自由,实现他的秉赋、能力和情欲,并积极通过智慧和工具(科技等等)反作用于自然存在物,从而人在自然的与人的双重规定之下创造了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世界。
人可以“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既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又“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1]50-51,借以实现人自己的人类学的生存。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强调人是生命化、智力化、情欲化、主体化的存在物。人的自由和能动性在于他在自己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能够自由地借助于工具、技术等作用于自然界,因而他既可以按照自然的尺度改造自然界,又可以按照人的尺度创造一个美的世界,借以实现自己的“秉赋、能力和情欲”,实现自己的“自由自觉”的人的生活。这样,马克思就指出了人既与自然界相同一,又高于自然界,从而指出人与自然界的生态整体是既由自然界的实体所规定,又因人的能动作用而有其发展方向的辩证生态整体。从这种辩证生态整体论出发,就为理解人既能违背自然生态规律而破坏生态世界,又能按照自然生态规律而遵从和改善自然生态系统的巨大能动性提供了理论根据。人的能动性(意识意志等等)和工具的非自然性(对自然的改造性),在人与自然界之间既划下一条分离的界线,又拉起了一条结合的扭带,这就为辩证地、能动地理解人与自然界的生态整体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换句话说,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生态整体论,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理论支点。一切生态考虑,都应当从这一支点出发。
根据马克思的这种辩证生态整体论,在今天应当引申出这样的生态原理:人一方面要平等地对待一切自然存在物,把自己主动降到一个自然物种而遵守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切生态规律,并把自己的自私的类群伦理,转化为一种全面地适应于整个生物圈的生态伦理,尊重一切自然物,无权任意践踏任何自然物;另一方面,人又有责任既按照“物种的尺度”,又按照人的尺度重整自然界和重整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循环。用中国哲学的话说,这里构建了这样一种人天一体的人天观:第一,它是一种人天一体论;第二,这种人天一体论是一种人天统一论,即人与自然界由于人的智慧的加入在生态上可以主动走向统一;第三,马克思的这种人天统一论是人天和谐论,因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73,这种解决就是和谐。马克思看到现实世界不可能实现这种人天和谐,他把这种统一与和谐的希望,寄托于消除了生态对立的共产主义,他强调: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所谓“完成”,应当理解为充分实现。它表明:马克思追求的是人(人本主义)与自然界(自然主义)在生态生存上的统一与和谐。但是,生态危机把这一“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任务提到了当前。
(四)辩证生态整体论:一切生态思考的理论基点
辩证生态整体论作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第一原理,不仅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界的生态世界观,更是马克思一切生态问题的理论支点。从辩证生态整体论出发,既注意到人与自然界的生态同一性,又注意到人类高于自然界的能动性、自由性和创造性。这是马克思创立的一种人—境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哲学立场,坚持马克思的这一生态哲学立场,既可以超越传统的蔑视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又可以超越当前的崇拜自然的自然中心主义,从而超越了这种目前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困境。
确认人与自然界的这样一种辩证生态整体关系,确立人—境生态整体的哲学立场,是马克思直接确立他的生态哲学思想的第一原理。这一原理对今天思考和解决生态危机有重要意义。这一原理要求,人应当主动适应这种生态整体的生态要求,既要直接大力进行生态保护,又要在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上进行根本性的改变。这就要克服资本逻辑对世界的统治,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人与人的生态和谐与健康生存。要做到这一层,需要权力的生态觉醒和资本的生态觉醒,使原来的权力为资本扩张服务和资本为权力扩张服务,都转化到为人类的生态化发展服务上来,走一条“生态—生产—生活”的合理生存与健康发展的道路。当然,这不是一两个国家的事,而是要促进和伴随全世界走向和平、合作、生态的人类学时代的世界历史大事。正是这一原理,可以成为破解当代生态危机、倡导生态文明的理论根据。在面对今天的世界性生态危机中,人应当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的智慧,由征服自然向顺从自然,由放任自己对自然的掠夺态度向约束自己的“生态化发展”方向转变,全力以赴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
总之,如果说维尔纳茨基发现了地球上的生物圈的话,那么,由于人和其智慧与意志的渗入,出现了一个人化的“人—境”关系圈,这个圈就是由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辩证生态整体圈,生态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圈层之中,因而人是可以主导这个圈层的生态运动的。
二、自然界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循环、生态平衡原理
正由于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界视为一种相互内在的存在,即一种生态整体,所以,他能够把握——或者说感受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性的生态生存关系,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以及自然界内部的生态循环、生态平衡原理,并在他的理论批判活动中表现出来。
生态社会主义者最有力的代表人物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哲学原理的最重要的阐发,就是指出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这的确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最有力的批判理论。但是,福斯特的理解是否正确呢?他所依据的马克思的最有代表性的几段文字如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551
“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的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也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552-553
“大土地所有者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和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4]
福斯特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物质变换概念,也就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新陈代谢概念(不同翻译)。因此,在这几段话中,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指的就是新陈代谢在城乡之间的“断裂”。把“裂缝”发展为“断裂”,这当然是对马克思生态批判的一种深刻理解和进一步概括。福斯特还对这一理解做了扩展:从直接的意义上说,新陈代谢断裂既是指“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使地力枯竭,又是指这些东西汇集于大城市,造成普遍的污染。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新陈代谢断裂还可指城乡之间、资本主义的工业与农业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他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代谢断裂,也是全球层面上新陈代谢断裂的一个证据。”[5]因而,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但是,这一理解是否准确揭示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了呢?我们认为,还可以加以更深入的理解。
如果说,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造成的城乡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这种事实上的不合理性,那么,在他的思想深处,“土地的组成部分”与土地的肥力之间、人口与地力之间、城乡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物质循环,这种物质循环得到满足,土地就能恢复和保持地力的持久平衡,反之就会因断裂而受到破坏。这就是说,马克思之所以能提出“裂缝”即断裂理论,应当基于一种更根本的原理,即人与土地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物质性的生态循环和生态平衡这样一种更加根本的原理。没有这一原理做底蕴,无法在逻辑上产生“裂缝”观念,无法提出土地的组成部分因不能回到土地而破坏土地肥力,并且把这视为对“永恒的自然条件”的破坏。当然,马克思没有直接说出生态循环或物质循环一词,但是,“无法弥补的裂缝”指的正是生态循环受到破坏。至少,这是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潜在原理,没有这一原理在胸,不可能做出上述批判。因为,福斯特所谓的“新陈代谢断裂”、“物质变换断裂”,本质上只能是生态循环断裂。由于当时还没有“生态”、“物质循环”、生态“平衡”这些词,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没有产生这些观念,所以,马克思经常扩大地使用“物质变换”或“新陈代谢”一词,用它表示物质循环、生态循环这一潜在理念。比如:使“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明显就是指人与土地之间的生态循环受到破坏。作为“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明显就是指人与土地之间的生态平衡。只是当时没有这些概念,马克思不得不用“土地肥力的持久源泉”、“永恒的自然条件”这种繁复的修饰词,来表达生态循环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这种思想。所以,福斯特所说的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论,是建立在马克思没有直接说出的但已潜在于心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循环和生态平衡这种先在原理之存在的前提之上的。事实上,这些概念产生得很晩。“平衡”作为哲学概念,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才得到研究。而生态意义的“循环”和“生态循环”这些概念,是在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1926年在苏联出版之后,才得到广泛重视。正像在没有“生态”一词出现时,马克思就产生了生态哲学一样,在自然界的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循环、生态平衡这些概念出现之前,马克思通过“人与土地的物质变换”、“土地肥力的持久源泉”受到破坏、“永恒的自然条件”受到破坏、在“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等等词句,把握住了自然界的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生态平衡、生态循环原理,表明了这些原理在自然界、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的客观存在。所以可以认为,马克思的“裂缝”概念、福斯特的“断裂”概念,指的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了自然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循环、生态平衡这样一种生态原理。马克思的上述批判,就是以这种客观原理为根据的。福斯特所发挥出来的“断裂”概念,其意义也只能建立在人与土地之间、城乡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循环和物质平衡关系受到破坏这一层上,才更显得有生态力量。但是,遗憾的是,福斯特却没有指出这一深层实质,而仅仅止于新陈代谢断裂说。
如果以上讨论是符合事实的,那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循环、生态平衡原理,是马克思生态思想预先设定的并以“物质变换”、“新陈代谢”、“永恒的自然条件”受到破坏、“裂缝”等概念加以论证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现代工业文明,是建立在违背人与土地、社会与自然、人与自然界以及自然界内部的生态循环、生态平衡这种根本生态规律之上的,它造成了这些方面的生态循环的断裂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因而是不能持久、不可延续的。而从马克思的更深入的思想来说,正是资本主义对生态循环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才使人与人的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走向异化,导致了今天的生态危机。今天公认,生态循环、生态平衡,正是生物圈以及人与生物圈之间的最根本的物质性的生态原理。马克思已经潜在地表明了这一原理的存在,并以此批判资本主义。因而,应当视之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奠基原理。
不过,马克思的上述原理,重点不在于研究自然界本身的生态循环和生态平衡,这是自然科学即生态学的事(1860年海克尔构建了生态学,实现了这一科学要求)。马克思的理论批判的指向,正如上面所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违背了这种原理。那么,人为什么会违背这一原理呢?这是由于人类社会内部的不合理关系所决定的,马克思希望,通过人类内部不合理关系的解决,来解决人与自然界的不合理关系,这就产生了马克思的伟大的对今天更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生态原理。
三、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双重实现原理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包括他的生态哲学思想、他的奋斗,其根本性质、根本目标,正像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样,不外是:“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6]的理论。
这是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概括,他准确地抓住了他们所推动的那个时代的变革方向。而马克思自己,也在较早的《巴黎手稿》中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强调:他的理论目的,就是为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73。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提出了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途径,即人与自然界的和人与人的“合理的物质变换”。可以认为:马克思要通过人与自然界的合理物质变换,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而通过人与人的合理物质变换,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如果说,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解是一种自然生态原理,而人与人的和解是一种社会生态原理的话,那么,马克思的理论目标,就在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双重实现,这是马克思为生态哲学所确立的人与自然界的和人与人的双重生态原理。正是这一原理,高过了后来西方一切生态主义的生态思想。只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才继承了马克思的这种自然的与社会的双重生态立场。所以,这应当是马克思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所确立的最重要的双重生态原理,是解决今日生态问题的最重要的原理。
[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16-918.
[5][美]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8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