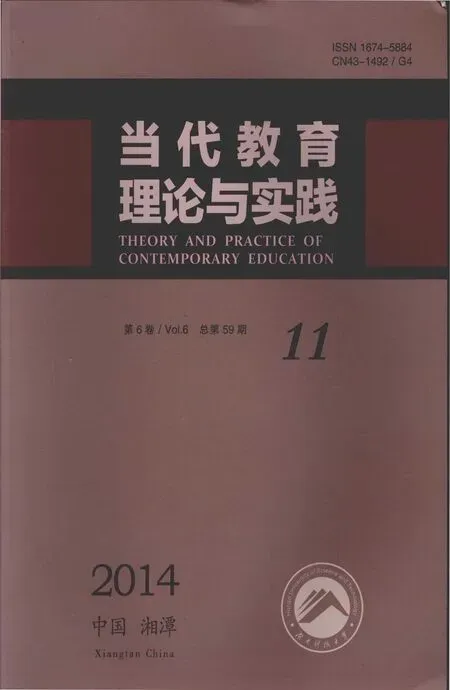《泰比》中的土著文化观照
胡 鑫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泰比》(Typee,1846)是赫尔曼·麦尔维尔创作生涯的首部小说。这部作品讲述了叙述者托莫在泰比山谷中的冒险故事,展现了南海群岛的异域风光。在小说中,麦尔维尔对土著文化进行了描述和评论。本文通过分析《泰比》中的土著人形象、南海岛屿的自然风光以及土著人的异教信仰,揭示麦尔维尔对于土著文化的书写是出于白人优于他者的心理写就的。
1 土著人形象
赛义德认为,传统的19世纪帝国主义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诸如“劣等或臣属种族、臣民、依赖、扩张和权威之类的字词和概念。关于文化的概念都是根据帝国主义的历史而得到澄清、加强、批评或摈弃的[1]。以往的旅行文学中,被塑造为他者的土著人与白人相异的丑陋外貌是白人作家乐于描述的一个方面。在这类作品中,几乎所有的白人作家都是根据白人的审美观念来刻画土著人。因此,麦尔维尔在描述土著人的外貌时,着重突出了土著人这一他者形象与白人的差异:
“四个面相可怕的老人让我们记忆犹新,他们苍老的面孔和满身的刺青让人感觉他们定是饱经了人世的风霜。[……]他们个个身上刺有绿色花纹—颜色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变化。他们的皮肤粗糙异常,再加上统一的色调,看起来十分像某种绿色的植物标本。他们的肌肉呈块状分布全身,像交叠在犀牛身体两侧的毛辫。他们的头全部光着,脸上爬满皱纹,却不见一根胡须。然而最特别的还要数他们的双脚,脚趾像海员指南针上四散的刻度线,指向不同的方向”(105-106)①书中所有《泰比》的引文,均引自赫尔曼·麦尔维尔《泰比》.马惠琴,舒程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随文只注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显而易见,麦尔维尔对土著人没有任何好感。他不仅使用了“面相可怕”这类充满偏见的字眼,还把土著人比作“植物标本”和“交叠在犀牛身体两侧的毛辫”。麦尔维尔笔下的土著老人不仅苍老、丑陋,连他们的脚趾都异于常人。正如美斯特勒指出,“欧洲人[……]在哥伦布的时代拒绝承认新大陆上的那些落魄的居民为自己的同类[……]看着那些野人而不诅咒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这样说不仅仅指他们的灵魂,还包括他们的身体外在形式”[2]。麦尔维尔对土著人的脚趾为何会如此难看做出了解释。由于“他们的脚有生以来从未受到过任何人为的局限,故而不肯相亲相近,最终还是各行其是,互不干涉”(106)。麦尔维尔以这种看似幽默的笔调道出原因,实际上在嘲讽土著人的丑陋外貌。麦尔维尔还在小说中描绘了土著人抓猪的情景:“[……]几个土著人试图将一只硕肥的大猪按倒在地,而一个身材结实的家伙正手持大头棒笨拙地向着猪头砸去。他一次次地错过目标,虽气喘吁吁但仍旧锲而不舍,经过一番足以击倒一群牛的捶打,那头猪终于在受到最后一击后倒在他的脚下”(181)。小说中,麦尔维尔对土著人的刻画凸显了土著人的笨拙,有意将土著人塑造为笨拙、无能的劣等形象。
此外,土著人的纹身也是麦尔维尔进行着重描述的一个方面。土著岛民从国王、王后到普通人,所有人都有纹身。国王的脸上“有个小小的缺陷”,他的面部有一条很宽的刺青,与双眼成为一线,“看上去像是戴了一副巨大的护目镜”(7)。麦尔维尔认为,让国王戴上护目镜“显然是一个滑稽的想法”(7),流露出其对纹身的偏见态度。小说中,叙述者托莫的土著朋友科里克里的脸上也有3条刺青横穿面部,像是“要改善天生的容貌或是想增加面部的表情”(249)。他脸上的刺青“犹如山间小道越过重重障碍向前延伸,穿过鼻梁和眼窝甚至到嘴角,[……]总让我想起监牢里隔着铁窗向外张望的囚犯”(249)。且不说在白人观念中,纹身代表了异教和邪恶。在白人看来,纹身看上去不具有任何美感,反而让土著人变得更加丑陋和不正常。土著人会为自己背上的巨大的长方形纹身而洋洋得意,但在托莫眼中,土著人颇为得意的纹身“像是沾满了斑蜇素的气泡”(249)。在土著人的观念里,纹身是他们独特的文化。土著人身上布满形状各异的花纹线条,惊人的繁复程度不亚于一些“价格昂贵的织物上才得一见的花样”(92)。同白人理解的相反,纹身花样复杂,是土著人身上最纯朴也是最气派的饰品。不仅如此,纹身还兼有区分等级等多种作用,并不是丑陋、邪恶的代名词。
2 南海群岛的自然风光
在《泰比》中,麦尔维尔笔下的南海群岛风景优美,与美国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充满了异域风情。由于自然景观对外来者而言是最容易观察、感受到的体验,读者对于这些有别于本土的景物也充满了新鲜感。因此,描述旅行故事的作品多以椰树、棕榈林、大海等富有热带特征的景物描写增加小说的异域色彩。
可以发现,同麦尔维尔对土著人的形象塑造相一致,他对南海群岛的风光也有一种前见式的认识:“从描写它们美景的书中可以看出,很多人把它们想象成如漆般美丽和轻柔的高原,绿树成荫,小溪潺涓,整个岛屿只略微高于环绕四周的海水”(13)。麦尔维尔在《泰比》开篇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南海岛屿的美丽画卷:“幽深的峡谷,飞流而下的瀑布和起伏延绵的小树林,它们在阳光和海岬的作用下时隐时现,一时一景,令人惊叹不已”(13)。此外,在小说中麦尔维尔反复强调南海岛屿的美丽景色:“第一次到达南海的人肯定会为这里岛上的美景所折服”,“努库赫瓦湾的美景实在难于述诸笔端”(13),“第一次进入那美丽山谷时的情景将会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之中。面对这青翠的山谷,我不知如何才能描绘得出它的景色!”(32)。
然而实际上,麦尔维尔在小说中提到“真实的情况却与之相去甚远”(13)。海岸上“尽是光秃的岩石,海浪击打着巨大的岩壁激起高耸的水花,散落到深处的水湾”(13)。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指出,“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3]。从某种程度上说,《泰比》中呈现的南海岛屿的风景并非完全是客观的描绘,而是经过麦尔维尔美化后的东方。
3 土著人的异教信仰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4]。当白人文化面对土著文化时,白人总是以基督教的概念或范畴对土著人的宗教信仰进行解读。于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土著人的非基督教信仰被白人认为邪恶的“他者”,并由此对土著文化做出否定的评价。麦尔维尔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因而其在创作中不经意地流露出强烈的白人优越心理。
在《泰比》中,麦尔维尔对土著人的异教信仰的书写就是源于白人文化优越的心理。白人叙述者托莫不仅对土著人的外貌带有强烈的偏见,在对其宗教信仰的描述中更是着重突出了异教的“可怕”与“邪恶”。泰比山谷中的禁忌果林是土著人“举行盛宴”和“各种可怕仪式”的地方(104),这里“异教崇拜的气氛静静地笼罩四周,向其中的一切物体都发出咒语”(105)。林地中央专门用以举行宗教仪式场地的巨大祭坛上站着“面目狰狞的偶像”,祭坛空地的中间的参天大树“向下投出阴森的阴影,粗壮的树枝节节上升,高出地面数英尺,上面藤条缠绕”(105)。麦尔维尔对禁忌果林的描绘正是白人观念中异教活动场所的环境,阴森而恐怖。
土著人根据个人喜好,信奉“面目狰狞、鼻大如瓶、臃臂怀胸的神像”,亦或崇拜“天上人间都难得一见的古怪偶像”(194)。麦尔维尔对土著人崇拜的木质偶像嗤之以鼻,对他们的宗教仪式也充满蔑视。麦尔维尔评价道,“整个仪式仿佛是一群小孩子在玩过家家游戏”(199)。由于“游记作家总是把所见的‘异域’文化视为‘他者’文化,并盘踞在权力核心位置,有意识地塑形异类文化,并使其边缘化”[5]。在白人看来,土著人不信仰基督教、崇拜偶像,从而土著文化与白人文化的相异性便首先表现为异教色彩的邪恶与愚昧。因此,信仰基督教、高度文明的白人在描述土著文化时,以一种俯视的文化心态看待土著人及其信仰,渲染他者的野蛮、愚昧。“邪恶”的异教作为“文化他者”成为白人优越性的最佳参照,确认了西方进步秩序、自由秩序与文明秩序的优越性。
虽然麦尔维尔与同时代的白人作家对土著人的异教信仰的描述相类似,但麦尔维尔并不是完全认同这类殖民话语。在小说中,麦尔维尔对于在白人中普遍流传的关于异教的错误观念表现出一定的不满。麦尔维尔在小说中提到,葫芦节“作为一种庄严的宗教仪式,它与一些关于波里尼西亚宗教仪式的恐怖描述根本不吻合,与传教士们所宣讲的更是大相径庭”(192)。麦尔维尔进一步指出,如果传教士们“这些从事神圣职业的人的确不是出于单纯的动机,我猜他们为了宣传自己作为无私奉献者的功德才有意夸大了异教的邪恶”(192)。在一些提及北马克萨斯群岛的作品中,有多处关于土著居民用焚烧活人来祭奠众神的场面描写。麦尔维尔承认,“这些描述给读者的感觉是他们的祭坛上每天都有人肉祭品,书中异教徒的残忍仍在继续上演,这些无知的异教徒在迷信的巨大力量作用下处于极度的不幸之中”(193)。麦尔维尔认为,“科学人士无意中对波里尼西亚宗教法律的描述存在着巨大的虚假性”。由于这些学者的众多信息来自于一些曾在南海和太平洋诸岛上漂泊或在野蛮部落居住过的人,这些人了解读者想听什么故事,便“毫无节制地大肆渲染”以吸引、迎合读者(193)。学者们带着“各种神奇故事”回到家中(193),不加分辨就将他们搜集来的信息向大众展示。于是,土著人由此成为自己都闻所未闻的各种迷信和宗教活动的参与者。
由此可见,19世纪白人作家的作品中描述的土著文化大多都不是建立在切实接触和研究的基础上的,这些书写几乎都带有白人的想象或者具有目的性。正如萨义德所言,“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东方也有助于欧洲(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3]。可以说,白人作家笔下的土著文化缺乏真实性,土著文化作为白人文明的对照,突出了白人文明的优越性。
即使麦尔维尔意识到白人对土著文化存在错误的理解,其在《泰比》中仍然以白人固有的观念为基调,描述土著人的异教信仰。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谈到,西方的东方主义是各类文本共同创造的具有一定霸权意义的话语,不同领域的人通过不同的文本,对东方进行描述,从而建立起一整套言说东方的词汇、意象、观念,一整套有关东方的思考、书写、教育、传播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提供给人们想象、思考东方的框架,任何个别表述都受制于这一整体,任何一个个人,哪怕再有想象力、个性与独特的思考,都无法摆脱这种话语的控制,只能作为一个侧面重新安排已有素材,参与东方主义话语的生产[3]。处于白人对土著人及其文化充满偏见的背景下,麦尔维尔也参与到迎合读者的写作行列中。
诺贝特·埃利亚斯指出,“文明尽管意义复杂,但归根结底是西方现代自我认同意识的表现”。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6]小说中的叙述者托莫在南海群岛上生活之后发现,土著人的纹身体制与他们的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小说中,土著国王向托莫表达了3次托莫应该纹身的要求,托莫都表示厌恶和拒绝。在托莫看来,土著人显然是执意要改变他的信仰。托莫对于土著人提出让他纹身的盛情邀请十分害怕,因为一旦让这个“疯狂的邀请”得逞,他将“终身带上一副丑陋的面孔”(249)。亨廷顿认为,“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认同文明,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7]托莫无法认同土著文化,因此拒绝纹身,从而“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之中”。土著人多次热情地邀请托莫纹身也让他“意识到了一个新的危险”,他担心某天“不幸降临,我就会被这样强行施虐,然后再也无颜面对国人”(248)。托莫不愿改变自己“神圣的面孔”,更是把纹身看做是不幸。自从他偶然与纹身艺术家相遇,他的生活“简直难过极了”。每天都有土著人缠着他去纹身,“他们的纠缠几乎令我发疯,我觉得他们要我做这做那的愿望实在来得太过容易”(262)。因此,托莫坚持要回归文明,出逃的念头又强烈起来。最终,托莫由于害怕被土著人强行纹身,选择乘船逃跑。托莫面对前来追赶的土著朋友茅茅,来不及同情和内疚,只顾瞄准目标,用尽所有的力气将手中的钩镐掷向了茅茅。托莫不顾一切逃跑的行为是他做出的文化身份选择,反映出强烈的白人文化意识。
4 结语
在《泰比》中,麦尔维尔将土著人、南海岛屿以及土著文化描述为与白人和白人文化对立的他者。在很大程度上,这类描写迎合了白人的优越心理,流露出对土著人及其文化偏见甚至否定的态度。小说中,麦尔维尔虽然对白人观念中对土著文化的错误认识予以了一定纠正,可是白人叙述者托莫不愿接受土著文化,最终逃回白人社会的结局反映出作者麦尔维尔思想观念中强烈的白人优越意识。由于深受白人优越的种族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泰比》中麦尔维尔对于土著文化的书写是出于白人优于“他者”的心理写就的。
[1]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M].杨乃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Braudel,Fernand.On Histor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5]杨金才.英美旅行文学与东方主义[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1):79-83.
[6]Elias,Norbert.The Civilizing Process[M].New York:Blackwell Publishing,2000.
[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评《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