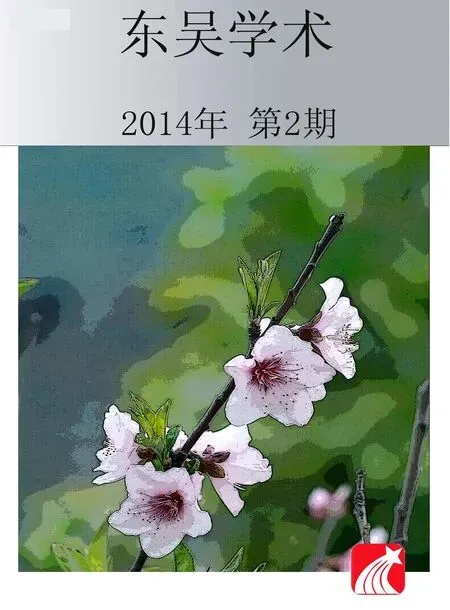一说再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张新颖
一说:与谁说这么多话
一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①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1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本文引用据此版本,文中只标出页码,并简写为《无愁河》。八十万字,才写到十二岁,少小离家。怎么有这么多话要说?这么多话怎么说?和谁说?
第一部写的是故乡和童年,这个叫朱雀城的地方,这个叫序子的孩子。写法是,从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从心所欲的前提是,心里得有;黄永玉一九四五年就起意写这小说,没有写下去,这也好,心里有了这么多年,酝酿发酵了这么多年。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似乎很简单,不就是自由嘛;但要获得这种自由的能力,却是很难,难到没有多少写作的人能达到的程度。二十五年前黄永玉写《这一些忧郁的碎屑》,谈起过沈从文的《长河》,说表叔的这部作品“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这才是真知灼见。写小说的人,对“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孜孜以求尚且不及,哪里还想到、并且还敢于“排除”?不仅是人物和情节,还有诸多的文学要素,既是要追求的东西,又是要超越的东西,否则,斤斤于金科玉律,哪来的自由?怎么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样不在乎文学“行规”自由地写,习惯了文学“行规”的读者,会接受吗?其实,这只不过是“外人”才会提出来的问题,对黄永玉来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还是在谈《长河》时,他说表叔,“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②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孙冰编:《沈从文印象》,第20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这才是知心的话,知心,所以有分量;这些话用在黄永玉自己身上,用在《无愁河》上,也同样恰当,恰当得有分量。
所以,在黄永玉的心里,与其说这部作品写出来要面对“读者”,不如说是要和故乡人说说故乡。甚至,在现实中,在现在的湘西,有或没有、有多么多或有多么少的故乡人要听他漫长的叙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心目中,存在这样知心的故乡父老子弟。
还有一个说话的对象,是自己。一个老人,他回溯生命的来路,他打量着自己是怎么一点儿一点儿长成的。起笔是两岁多,坐在窗台上,“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醒悟’,他没想过要从窗台上下来自己各处走走”;(第4页)结束是他离开朱雀,到了长沙,见到父亲,“原本是想笑的,一下子大哭起来”。(第1187页)黄永玉用第三人称来写自己,显见得是拉开了打量的距离;但奇妙的是,这样拉开距离打量自己,反倒和自己更亲近了。
生命不能重新再过一遍,可是写作能够让生命重返起点,让生命从起点开始再走一遍,一直走到现在,走成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写作中重现的生命历程,与生命第一次在世界中展开的过程不一样:写的是一个孩子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的情形,可这是一个老人在写他的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童稚时候懵懂的,现在明白了;当时没有意识的,现在意识到了。所以不能说这部作品写的就只是记忆:确实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呈现过去的情形和状态,然而同时也在在隐现着现在的情形,写书人现在的生命状态。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老人与两岁、四岁、七岁、十二岁的自己的对话和交流。这种对话和交流,在字面上通常是隐蔽的,偶尔也显现一下,不管是显还是隐,从始至终都是存在的。感受到这种存在,才算对得起这部书。
与故乡父老子弟说话,与自己说话,还与几个特殊的人说话。《无愁河》的写作不面对抽象的读者,却面对具体的几个人,几个作者生命中特殊的人。黄永玉说:“我感到周围有朋友在等着看我,有沈从文、有萧乾在盯着我,我们仿佛要对对口径,我每写一章,就在想,要是他们看的时候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在的话,哪怕只有一个人在。比如如果萧乾还活着,我估计他看了肯定开心得不得了。表叔如果看到了,他会在旁边写注,注的内容可能比我写的还要多。”①黄永玉的话见王悦阳的采访《黄永玉:流不尽的无愁河》,《新民周刊》2013年11月11日。这几个想象中的读者,伴随着写作过程,以特别的方式“参与”到了写作之中。其实还不仅是写作过程,黄永玉写这部书的冲动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素,就是和这些已经逝去的老人谈谈话,让他们“开心”,或者“写注”——没有多少人知道,沈从文一九四四年给自己和父老乡亲谈心的《长河》,十分细致地加了大量批注;倘若他读到《无愁河》,兴起写注,一写起来就没完没了,那简直是一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愁河》也是一部献给几位逝者的书,他们是无可替代的重要读者,他们有不少东西融入了作者的生命。
那么,你会明白,在九十岁老人身上活着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
一个生命里,“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一个生命 “融合了许多的生命,在融合后开了花,结了果”——这是冯至在《十四行集》里写到的句子。②冯至:《十四行集》第20首,王圣思编:《昨日之歌》,第89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黄永玉和沈从文的合影里有一张特别好,书报刊上多次刊出,那是一九五〇年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在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前照的,摄影者就是冯至,顺便提一下,是因为刊登这张照片时很少注明摄影者,沈从文那时候的邻居。
黄永玉万分惋惜和感慨《长河》没有写完,他说那应该是像《战争与和平》那样厚的大书。长长的《无愁河》,会弥补这个巨大的遗憾,为表叔,为自己。
二
《无愁河》一经面世,就会遇到四面八方的读者。《收获》从二〇〇九年开始连载这部作品,连载了五年,“浪荡汉子”才走出故乡闯荡世界。据说非议不断,有读者宣布,一天不停止连载,一天不订《收获》。但我认识的人里面,有人盼着新的一期《收获》,就是盼着《无愁河》,几年下来,已经成了习惯,成了阅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无愁河》有它的“超级读者”,除开黄永玉的故乡人之外。我熟悉的人里就有。
北京的李辉和应红自不必说,他们催促老人每天做日课,见证和护生了这部作品。我的师叔李辉,写黄永玉传,搜集黄永玉七十年的文学创作编出《黄永玉全集》文学编,策划黄永玉《我的文学行当》巡展——说他是黄永玉的“超粉”,那是轻薄了。他从研究巴金,写萧乾传,与晚年的沈从文相交,到发掘整理黄永玉的文学作品,自然一脉相承。他是太知道《无愁河》的价值了。
我的同学和朋友周毅,生活在上海的四川人,她写了一篇《无愁河》札记,几万字长,怎么写得出这么长的文章?过了两年,她又写札记之二,又是几万字;再过了些日子,札记之三出来了,还是几万字。①我要把周毅这三篇札记的题目和发表的地方写在这里:《高高朱雀城》,《上海文学》2010年第2期;《“无愁河”内外的玉公》,《上海文化》2012年第3、4期;《身在万物中》,《上海文化》2013年第9期。她和《无愁河》之间,究竟建立起了什么样的关系?
有一次她告诉我,《无愁河》对她来说,是一部“养生”的书。
“养生”,很重的词。庶几近乎庄子讲的“养生”。怎么个“养生”法?身在万物中,息息相通。这样的话现在的人读起来已经没有什么感受了,当然也不怎么明白什么叫身在万物中,生机、生气如何从天地万物中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吹也。”息是自心,生命万物的呼吸,息息相通才能生生。生的大气象,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以”字,就是建立起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体会到这个“以”,就能体会到息息相通,就是“养生”。
就是单纯从字面讲,当代文学中又有多少作品能“养生”——“养”生命之“生”?《无愁河》担得起,这就是《无愁河》文学上的大价值。
说起价值来,人是这样的,小价值容易认得出,算得清;大价值——不认识,超出了感知范围。
一部书有它的“超级读者”,是幸福的。这幸福不是幸运,是它应得的,它自身有魅力和能量。说到能量,我们不难想到,有些作品,是消耗作者的能量而写成的,但消耗了作者能量的作品,却并不一定能够把能量再传给读者;《无愁河》的写作依赖于作者过往的全部生命经验,但它的写作却不是消耗型的,而是生产型的,从过往的经验中再生了源源不断的能量。由此而言,写作这部作品,对黄永玉来说,也是“养生”的。序子的爷爷境民,有一次随口谈起一个人的文章,说“写出文章,自己顺着文章走起来——人格,有时候是自己的文章培养出来的”(第24页)。作品能不断产生出能量支持作者,这是幸福的写作。
作品还能不断把能量传递给读者,读者吸收变成自身的养分,这样的读者也是幸福的。
三
序子生长的朱雀城,有片地方叫赤塘坪,“是个行刑砍脑壳的地方”。杀人的时候人拥到这里看杀人,平常野狗在这里吃尸体,顽童放学后经过这里“东摸摸,西踢踢”。“其实杀不杀人也没有影响热闹事。六七月天,唱辰河大戏就在这里。人山人海,足足万多看客。扎了大戏台,夜间点松明火把铁网子照明,台底下放口棺材,一旦演《刘氏四娘》、《目连救母》叉死人随手装进去。”清明前后,“这地方也好放风筝”。(第185-186页)我们以为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事情,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生命经验,却能够在这么小小的同一片地方轮番上阵,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我想说的是生命经验的宽度、幅度的问题。一个生命从小就在这样的地方、在这么大幅度的日常转换中历练,倘若这个生命善于发展自己,没有辜负这样的历练,那么它能够撑开的格局、能够忍受的遭遇、能够吸收的养分、能够看开的世事,就不会同于一般了。序子三岁多的时候城里“砍共产党”,父母仓促出逃异地,他被保姆王伯带往苗乡荒僻的山间。这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又带来另外的养分,在不知不觉中培育性格和性灵。
大幅度的经验往往会诱惑人们集中专注于经验的不平常性,关注大而忽略小,关注极端而忽略日常;《无愁河》却是细密、结实的,在经验的极端之间,充实着的还是日常的人、事、物。黄永玉写朱雀城,譬如写一条街道,他要一家铺子挨着一家铺子写过来,生怕漏掉什么;写完这条街道接着又写另一条街道。再譬如说他写吃,写了一次又一次,从准备材料写起,写制作,写吃的过程、感觉,写吃的环境和氛围,当然还有吃的人——这其实很难,写一次还不难,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写,七次八次都写出特别来,真难。谁不相信可以试试。乡愁这东西,说抽象可以无限抽象,说具体就可以具体到极其细微的地方,譬如味蕾——味觉的乡愁。他写苗人地里栽的、圈里养的、山上长的、山里头有的、窑里有的,名称一列就是好几行,“请不要嫌我啰唆,不能不写。这不是账单,是诗;像诗那样读下去好了”(第249页)。他还写“空东西”:序子在苗乡,好天气的日子,王伯问他:“狗狗!你咬哪样?”
“我咬空东西。”
“哪样空东西?”王伯问。
“我咬空东西,你不懂!我喜欢这里的空东西。 ”(第229页)
黄永玉写得满,他巨细靡遗,万一哪里忘了点什么,他后来想起还会补上。
难道写作不应该经过“选择”吗?“选择”,甚至是“精挑细选”——这个词又出现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这是许多作家的态度和写作必须的步骤;但对黄永玉来说,生命经验的任何一事一物,都能写,都不必拒绝,用吃的比喻来说,他不“挑食忌口”。因为这些事事物物都融进了生命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道理。你以为这样的事物、这样的经验对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那样的事物、那样的经验对你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你要区分,你要选择;其实是所有的经验,包括你没有明确意识到的经验,共同造就你的生命。序子在苗乡的时候,有一个常来帮助王伯的猎人隆庆,隆庆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小说是这样写的:
狗狗挨隆庆坐,闻着隆庆身上的味道。这味道真好闻,他从来没有闻过,这味道配方十分复杂,也花功夫。要喂过马,喂过猪,喂过养,喂过牛,喂过狗,喂过鸡和鸭子;要熏过腊肉,煮过猪食,挑粪浇菜,种过谷子苞谷,硝过牛皮,割过新鲜马草;要能喝一点酒,吃很多苕和饭,青菜酸汤,很多肉、辣子、油、盐;要会上山打猎,从好多刺丛、野花、长草、大树小树中间穿过;要抽草烟,屋里长年燃着火炉膛的柴烟,灶里的灶烟熏过……
自由自在单身汉的味道,老辣经验的味道。闻过这种味道或跟这种味道一起,你会感到受庇护的安全,受到好人的信赖。
这种味道,“具有隆重的大地根源”。(第238-239页)
你要是从隆庆的经验中排除掉一部分,那这味道就不是隆庆的味道了。
《无愁河》是条宽阔的大河,有源头,“具有隆重的大地根源”;有流程,蜿蜒漫长的流程。大河不会小心眼,斤斤计较,挑挑拣拣。大河流经之处,遇到泥沙要冲刷,遇到汊港湾区要灌注萦回,遇到岩石要披拂,遇到水草要爱惜地飘荡几下。
《无愁河》的丰富,得力于作者感知和经验的丰富,他过去经历时没有“挑食忌口”,现在写作时没有“精挑细选”。他身受得多,触发得多,心能容下得多。容得多,心就大了。山川形胜、日月光辉、人物事体、活动遭遇,都是养人的东西,生命就是在其中生长、长大、长成,长出精神和力量,长出智慧,长出不断扩大的生机。
再说:这些话里的意思
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题目叫《与谁说这么多话》;文章结束的时候,我自己怎么感觉像说话才开了个头?没有写完一篇文章之后期待的轻松,反而是没说出来的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折腾。
我得把它们写出来,否则,“我会病!”——这是借了蓝师傅的话。蓝师傅是朱雀城有名的厨师,他曾经为人办席,天气把东西热坏了,大家都说过得去,可是蓝师傅硬是补了一桌席,“不补我会病!”(第35页)——我的短文章,哪里有蓝师傅一桌席重要,只是把翻腾的话写出来,自己就轻松了。
一
序子和小伙伴们去果园偷李子,路上有开着白花带刺的“刺梨”。学堂里,先生要大家相信它学名“野蔷薇”,小孩子的反应是:
这是卵话,太阳底下的花,哪里有野不野的问题? (第817页)
《无愁河》里随随便便写下的这么一个句子,给我强烈的震惊感。人类早就习惯了区分“野”与“不野”,这样区分的意识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从人类文明的视野看出去,确实有“野”与“不野”的问题,人驯服了一些动物,驯化了一些植物,改造了部分自然,把“野”的变成“不野”的。但是,单从人的角度看问题是偏私的,狭隘的。古人讲天、地、人,现代人的观念里人把天、地都挤出去了,格局、气象自然不同。换一个格局,“太阳底下”,就看出小格局里面的斤斤计较来了。
小孩子还没有那么多“文化”,脑子还没有被人事占满,身心还混沌,混沌中能感受天地气息,所以懵懵懂懂中还有这样大的气象,不经意就显了出来。
小说家阿来写 《格萨尔王》,开篇第一句:“那时家马与野马刚刚分开。”①阿来:《格萨尔王》,第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一句话,气象全开。序子离“家马与野马刚刚分开”的时代已经隔得非常遥远,他却能从“太阳底下”的感受,本能地否认“野与不野的问题”,真是心“大”得很,也“古”得很。小孩子的世界很小,一般可以这样说吧;但其实也很难这样说。小孩子的心,比起大人来,或许就是与“古民白心”近得多。
《无愁河》说到“野”的地方很多,我再挑出一句来。说“挑”也不合适,因为这也只是作品里面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作者也没有刻意强调突出。是序子的奶奶说的:“伢崽家野点好,跟山水合适。”(第1127页)这个话,前半句好多人能说出来,不过我们无非是说,小孩子野,聪明,对身体好之类;婆说的这后半句,就很少有人能说出来了,“跟山水合适”,是把人放在天地间,放在万物之中,与天地万物形成一种息息相通的“合适”关系——我们说不出后半句,是因为我们的意识里面没有。
二
我们说到小孩,很容易就联想到天真烂漫的生命状态。其实呢,在“天真”之前,恐怕还有一段状态,常常被忽略了。序子也有些特别,他的这种状态算得上长,到了七八岁该“天真”了,他还很“老成”——其实是童蒙。黄永玉写出了这种“蒙”,并且尊重它。
序子小,“谈不上感动反应”;(第141页)再大点,大人期望他对事对物有反应,可是常发现他“有点麻木,对哪样事都不在乎”;(第183页)他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像个木头,不会喜形于色;他似乎迟迟不开窍,让人着急。
不开窍,就是“蒙”。周易有蒙卦,“蒙”是花的罩,包在外面保护里面的元。“发蒙”就是去掉这个罩,让花长出来,开出来。但是在花开出来之前,是要有“蒙”来保护里面的元的,而且要等到那个元充实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去掉这个“蒙”。所以这里就有个时间的问题,去得过早,那个元就长不成花。
“发蒙”不是越早越好。世上确有神童,那是特例;再说,天才儿童的天才能维持多长时间,也是个问题。现在儿童教育赶早再赶早,那是不懂得“蒙”的作用,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尊重“蒙”。等不及“蒙”所必需的时间长度,让生命的元慢慢充实起来,就慌慌张张地“启蒙”,那是比拔苗助长更可怕的事情。
序子在生命该“蒙”的阶段“蒙”,其实是大好的事情。
尊重“蒙”,是很不容易的。
序子后来上学读书,在他那一帮同伴中间,“有一种不知所以然的吸引力”(第809页)。这个“不知所以然”好。
要去掉“蒙”,也不是一下子的事情,是要一点儿一点儿去掉的。光靠外力也不成,得有机缘,更得有从内而外的“萌发”。序子四岁的时候,跟玩伴岩弄在谷仓里忽然爆发了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打闹,对此王伯“一点不烦,她喜欢狗狗第一次萌发出来的这种难得的野性。狗狗缺的就是这种抒发,这种狂热的投入”——王伯懂得“萌发”;序子“得这么个培养性灵的师傅”,是机缘。(第273页)
话再说多一点,“蒙”也不只是“童蒙”,比如说我活到了中年,有些事才明白,还有些事得将来才能明白,或者将来也未必明白;明白之前,就是“蒙”。尊重“蒙”,说大一点,就是尊重生命本身。
三
但人活着,就得朝着明白的方向活。岁月确实能教人懂得越来越多的东西。《无愁河》第一部,是一位老人写童年,是“明白”写“童蒙”,“懂”写“不懂”,两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奇妙的关系。所以《无愁河》第一部展现的世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童年世界,它同时还是一个历经千难万险的生命回首来路重新看待的世界。我们讨论一部作品,喜欢说它的视角,其中童年视角常被提出来说;《无愁河》呢,既是一双童稚的眼睛初次打量的世界——随着作品的延续,视角还将自然变换为少年视角、青年视角……——又是一双饱含沧桑的眼睛看过了一遍又一遍的世界。
而不同眼光的转换,从黄永玉笔下出来,既自由,又自然。
老人借给我们一双眼睛,让我们从这个童稚的世界看明白一些事情。所以读这部书,如果不注意老人的“明白”,这阅读也是很大的浪费。
“明白”啥?无法一概而论,因为大千世界,时时处处都可能有需要我们明白的东西。说起来会没完没了,举例讲几点。
(一)“道理”和“学问”
序子的妈妈柳惠是女子小学的校长,她“讲起道理来轻言细语,生怕道理上吓了人家”。(第181页)你看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人是生怕道理吓不着人。政界就不去谈了,就说学界,有人就是靠着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道理而成为学术明星的,这只是一面;另一面是,还真奇怪了,有些人还就崇拜能把他吓住的道理,吓不住他的他还瞧不起呢。
“胃先生上课,学生最是开怀,都觉得学问这东西离身边好近。”(第642页)学问、道理,都是一样,好的学问与人亲近,不是冷冰冰的,更不是压迫人的东西。胃先生还讲过一句话,“儿童扯谎可以荡漾智慧!”(第795页)“荡漾”这个词,用的真是“妩媚”。“妩媚”是沈从文喜欢用的一个词,用法特别。
(二)风俗节庆
中秋节到道门口“摸狮子”,不知哪一代传下来的习俗。人山人海,虔诚,热闹。小孩子里面有胡闹的,摸了自己的“鸡公”,又摸狮子的“鸡公”;摸摸自己的“奶奶”,再摸摸母狮子的“奶奶”。苗族妇女无奈,但也“默认某种灵验力量是包括城里佻皮孩子的淘气行为在内的”——“你必须承认历来生活中的严峻礼数总是跟笑谑混合一起,在不断营养着一个怀有希望的民族的”。(第69页)
过年,战争期间是双方“息怒”的“暂停”;太平年月,“老百姓把破坏了的民族庄严性质用过年的形式重新捡拾回来。”
所以,过年是一种分量沉重的历史情感教育。
文化上的分寸板眼,表面上看仿佛一种特殊“行规”,实际上它是修补历史裂痕和绝情的有效的黏合物,有如被折断的树木在春天经过绑扎护理重获生命一样。(第160页)
现代人又无知又自大,才会把人类在漫长的生活中形成的一些习俗当成“迷信”;又懈怠马虎怕麻烦,就把“文化上的分寸板眼”当成“繁文缛节”;还现代得浅薄,所以无从感受什么叫“历史情感教育”。那么,怎么可能在季节轮换、年岁更迭中,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恭敬、虔诚,一身的感怀和新鲜”?(第161页)
(三)自己和别人
序子上学后,以前的玩伴表哥表姐来得少了。黄永玉顺笔讨论了一下这个“某人某人以前来得多,现在来得少”的问题:
只顾自己怨尤,不考虑别人也有人生。
以前提携过的部下、学生……现在都来得少了。你没想到人人各有各的衣禄前程,各有各的悲欢。有的人的确把你忘了;可能是得意的混蛋,也可能惭愧于自己的沦落无脸见人。大部分人却是肩负着沉重担子顾不上细致的感情。
你要想得开;你要原谅世人万般无奈和委屈……(第408-411页)
能明白到大部分世人的重担、无奈和委屈,才能克服个人的怨尤,才可以产生怜悯人生的心吧。“爱·怜悯·感恩”,是黄永玉写在这本书前的三个词,每个词都是沉甸甸的。
不仅要原谅别人的万般无奈和委屈,自己也难免不陷入这种境地,要担得起这些东西:“人之所以活在世上就是要懂得千万不要去讨公道。好好地挺下去,讨公道既费时间也自我作践。”(第999-1000页)——看上去是 “消极”、“负面”的经验和智慧,其实是要“积极”地去做值得做的事,“正面”地做自己。
(四)命运这东西
《无愁河》里有一段写一群孩子做“鬼脑壳粑粑”,这一帮幼小的艺术家们认认真真地施展他们造型能手的才华,快快活活地享受创造的过程和其间的满足,完成之后累得卧地即睡。在写到这一群小艺术家好梦正酣的时刻,黄永玉换了笔墨:“这里我要提前说一说他们的 ‘未来’。我忍不住,不说睡不着,继续不了底下的文章。”“他们没有一个人活过八年抗战,没有端端正正地浅尝哪怕是一点点的、希望的青年时代……往时的朱雀城死点人算不了什么大事,偏偏序子周围的表兄弟除柏茂老表兄之外都死得失去所以然,死得没有章法。八年抗战初期,嘉善一役,一二八师全是朱雀子弟,算来算去整师剩下不到百八十人。全城的孤儿寡妇,伟大的悲苦之下,我那几个表兄弟就没人想得起来了……”(第532页)——活到了后来的人才知道后来的事;但是活到了后来的人,看着他们当时对于“未来”的无知无觉,会是怎样无可比拟的沉痛。命运这东西,常常“没有章法”(!)得让人痛切失语。
为什么我要强调《无愁河》展现的不仅仅是童稚的眼睛第一次看到的世界,同时也是沧桑之眼看了一遍又一遍的世界?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只有通过漫长的人生经历之后才会明白的人情和世事、文化和智慧,还有曲折沉重的历史。
四
起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打算谈谈这部作品的用字、用词和造句,既有“花开得也实在放肆”(第8页)这样的乡野之言——我想起我的祖父和父母也这样用“放肆”;也有“酲”这样看上去很文雅的字眼,《无愁河》里出现却是在方言里,“酲酲家”。(第201页)我会注意到这个字是因为一直很喜欢“五斗解酲”这样的“任诞”——喝五斗酒来解酒病:《世说新语》里这样描写刘伶;还有一些“跨学科”的句子,如序子的父亲幼麟做菜,“一个菜一个菜地轮着研究其中节奏变化,他觉得很像自己本行的音乐关系”。(第19页)蓝师傅做菜,“他在迷神,在构思,在盘算时间、火候、味道、刀法、配料之间的平仄关系”。(第34页)
还打算谈谈这部作品里的引述,从《圣经》到《约翰逊博士传》到《尤利西斯》到《管锥编》,从古典诗词到朋友著作到电视相亲节目 “非诚勿扰”孟非总是要来那么一句的“爱琴海之旅”。
我更想谈谈这部作品整体气质上的“野”和“文”。光看到“野”是太不够了,它还“文”得很。既“野”又“文”,“野”和“文”非但不冲突,还和谐得很,互相映衬,互相呼应,互相突出,合而为一。这不是一般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的吧?
为了这些打算,反反复复看了三厚册书中我画的道道、写的旁注、折的页码,真是犯了愁。太多地方了,怎么说得完,说得清?——干脆放弃吧。
末了给自己找个理由:要是一部作品的好,你能说得完,说得清,也就算不上特别丰富的那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