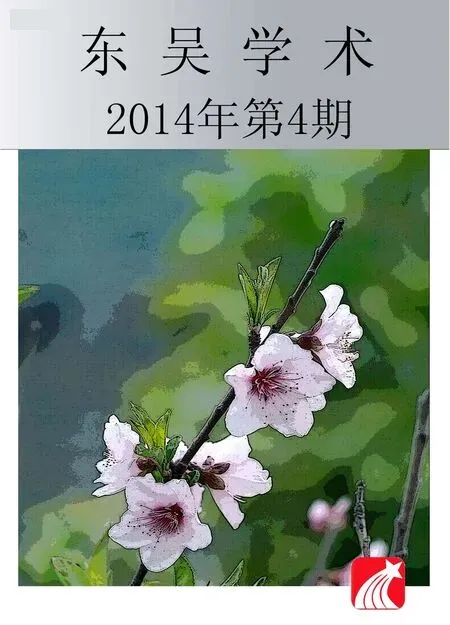卡夫卡的《判决》:传统与背叛*
〔美〕罗素·伯曼著赵山奎译
世界文学
卡夫卡的《判决》:传统与背叛*
〔美〕罗素·伯曼著赵山奎译
《判决》是卡夫卡写作事业的一个突破,也是他关于正义和罪行之思考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学叙事,而正义和罪行,正是他其后作品的伟大主题。这个故事同时展现了进行判决的必须性和罪疚感的普遍共存性。《判决》的最后问题并非父亲判词的不可靠品质,而是格奥尔格的沉默与顺从。作品中的格奥尔格是一个避世独居、思前想后而又心神涣散的作家形象。通过自身所包含的批判视角及对文学成规的抵制,《判决》表达了另一种文学选择:向社会和传统开放,向过去和经典开放。这种文学有能力赢得一种公共和群体的生活。
卡夫卡;《判决》;文学传统
卡夫卡的《判决》(Das Urteil)短小精悍,却在文学原野上赫然耸立,此种情形并不多见。这个不乏欺骗性、布满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的简短故事对卡夫卡来说是个突破,对解读者来说是个诱惑——解读者被其同时具有的松散和致密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品质所吸引。卡夫卡记述了他是如何在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与二十三日之间的那个令他精疲力竭的晚上一鼓作气地写出了整个故事的。这是一个将他之前的文学试笔和其成熟之作分离开来的关键时刻:接下来的十一月到十二月他写出了《变形记》,长篇小说(布罗德后来命名为《美国》)的写作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①HartmutBinder,Kafka-Kommentarzu säm tlichen Erzählungen(Munich:Winkler Verlag,1975),pp.123-125.《判决》的写作无疑把卡夫卡的创作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是其一系列现在已占据现代文学核心地带作品的先导。我们知道卡夫卡要布罗德毁掉大部分写出来的东西,但《判决》不在其列。相反,该作是卡夫卡持续性地表示好感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②J.P.Stern,“Guiltand the Feeling ofGuilt,”in The Problem of The Judgment:Eleven Approaches to Kafka’s Story,ed.Angel Flores(New York:Gordian Press,1977),p.114.无论对于理解卡夫卡的主要成就,还是对于理解更为宽泛的二十世纪文学之敏感性来说,它都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③Walter H.Sokel,“Kafka and Modernism,”in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afka’s Short Fiction,ed.Richard T.Gray(New York:MLA,1995),p.34.《判决》代表了一个突破,重新界定了文学经典的传统,这种重新界定是通过精确的文本逻辑展现出来的。
这一创造力为何会突然爆发,又为何采取了“判决/决断”这一形式?当然这里有一个传记性背景;许多评论着力于此,试图参照卡夫卡的生活来解释这个烦人的故事。一九一二年他遇到了后来成为其未婚妻的菲丽丝·鲍尔(Felice Bauer),这个故事就是题献给她的;很清楚,她成为作品里格奥尔格未婚妻弗丽达·布兰登菲尔德(Frieda Brandenfeld)的原型(两者的首字母一样),在与菲丽丝的通信中,他称《判决》为“她的故事”。结婚的愿景向卡夫卡提出了问题:他要献身于作家生活,离弃安全的布尔乔亚生活,但传统的婚姻生活和不那么传统的作家生活都将激活卡夫卡与他的父亲之间的麻烦关系。因此把这个故事非常明显的那些主题——比如说父子冲突、与一个远方朋友的关系以及迫近的婚姻——与卡夫卡的生活处境联系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的确有批评家把卡夫卡在一九一九年写给父亲的信作为家庭关系紧张的证据,以此来解释《判决》,尤其是格奥尔格与父亲之间的争执。①HartmutBinder,Kafka-Kommentarzu sämtlichen Erzählungen,p.132;Gerhard Neumann,“‘The Judgment,’‘Letter to His Father,’and the Bourgeois Family,”in Reading Kafka:Prague,Politics,and the Fin de siècle,ed.Mark Anderson,New York:Schocken,1989,p.217.
还有种做法是把注意力转向其文学来源,以此来解释该故事的复杂性。这种努力与探讨作品的传记性联系没有根本性差别:两者都试图通过外部的客观材料来解释——这并非是说:“通过解释来消除”——文学作品里的现象。在这方面,《判决》被与布拉格的一则童话故事联系起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尤其是其《罪与罚》联系起来,与布罗德的小说《阿诺德·比尔》联系起来。②比较起来,卡夫卡与意地绪语剧团的相遇经历似乎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写作《判决》之前的那段日子他常常去看戏。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非现实主义姿势的运用,以及形势的突转直下都可以看作来自卡夫卡所观看的戏剧表演。③还有一个更为纵深的相关来源是犹太教最为隆重的仪式——悔罪日,举行这个仪式的日子就是卡夫卡写作《判决》的那个夜晚的前一天。我们知道他在犹太教堂参加了这次活动,因此可以推测与仪式相关的比喻必定萦绕在他的脑际,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可能即将发生的神圣判决与悔罪。
这些传记性的和互文性的参照尽管可能有其重要性——它们能阐明文本中的某个方面,它们却并不能提供对于这个作品本身的富有穿透力的说明。卡夫卡与未婚妻或父亲的关系,或与这个作品相联系的阅读习惯或宗教信仰,都是非常私人化的东西。把这个故事与这类私人信息绑得太紧的解释因此就难以解释这个文本从专业批评家和公众读者那里都能引发出来的那种迷恋。罗纳德·格雷这样评论说:
卡夫卡是否不仅仅是自娱自乐呢?这里有没有为读者——一个“普通的读者”,某个为了阅读的快乐和获得启迪的读者而不是为了研究的读者——而准备的东西呢?为理解这个故事所需要的传记信息的数量首先表明,这个故事本质上是神秘的和隐微的,其次还表明,这个故事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于它在卡夫卡作品中的位置——它作为一个起点和入口具有价值,但其自身还算不上成功的艺术品。④
把这个文本主要作为私人事务的表达其实是在暗示:这个文本作为文学价值不大,卡夫卡对这个文本的评价是错误的,还暗示它只应该被症候性地阅读,或在最好的情况下被当作研究以《变形记》为起点的成熟作品所要经过的一个环节。最终,这一方法把格奥尔格孤零零地留在了故事开头所呈现的他自己的房间里:格奥尔格或许是卡夫卡走向文学生活的一个人格道具,但其自身却并非一个具有想象力的成就。我们不能低估这种批评策略的诱惑力,因为这将把文本对读者提出的挑战减至最小。读者必须与文本中关于人际关系的让人苦恼的叙述纠缠:父亲与儿子之间争执的非逻辑特点,那个朋友不稳定的立场,我们所了解的格奥尔格与其所受惩罚之严重性之间那让人诧异的不协调,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格奥尔格在执行对自己的死刑时所表现出的顺服。
我们不应贸然做出假定:作品中这些难以解决的困难会削弱其文学地位。相反,这种几乎难以穿透的网络系统,这种层层叠叠的意义区间,正是该作品的实质性成就。《判决》成为卡夫卡写作事业的一个突破,也是他关于正义和罪行之思考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学叙事,而正义和罪行,正是他其后作品的伟大主题。更重要的是,通过重新解释文学成就、文学判断/判决和文学经典的本性,此文本之错综复杂和布满问题的品质也为文学写作的可能性设定了新的标准。这个文本的主题是加于儿子身上的判决——我们将看到这个判决的可能性会变得如何费解,但它更是对文学的判决,对制度化的文学,以及对文学潜在能量的判决。《判决》召唤对于文学生活的再度判决/判断。
《判决》的魅力首先源于故事开头和结尾之间令人窒息的对比——从沾沾自喜下降到自杀,叙述的简洁和快速更强化了这种艺术效果。本德曼在自己的世界里本来好好的,但在没有充分解释的情况下,突然间一切显得都错了,这一突转把读者拖入了一个没有尽头的反思线圈,陷入了对于判决及其执行之解释的无穷寻找。然而,更切近来看,最初的稳定和最后的惊跳都不具有单一的确定性意义,作品的叙述比初看上去要更复杂。叙述一开始采取了看似熟悉和俗套的现实主义文学修辞:所引入的青年商人是一个“标准”人物,毫无疑问,牢固地占据了中心视角。我们发现他在自己的私人房间里,坐在他的桌子旁,或更准确地说,坐在写字台(Schreibtisch,writing table)旁,他刚在那里写好了一封信;同时他可往窗外看,远处有桥、有河、有山。此类主人公及其将私人和公共领域(私人书信和外部景观)连接与整合起来的认知方式至少是自一八四八年以来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必备品——此类文学在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之间进行协调和平衡。①Peter Uwe Hohendahl,Literarische Kultur im Zeitalter des Liberalismus:1830-1870(Munich:Beck,1985),pp. 376-419.其实早在一九一二年之前,也不止在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此类模式已经被商业化的娱乐文学所挪用,它们已经成为流行小说的标准模式。在《判决》的开头,卡夫卡炫耀性地展示了这些现实主义的标志,这种夸张的姿态反而破坏了这些标志的根基。故事开头被高调宣布的时间——某个春天周日上午——传达了某种童话氛围,这种氛围被故事所用的过去时态(Eswar,Itwas)进一步强化。现实主义修辞和童话故事标志之间的文类张力应该会让读者保持警惕。格奥尔格在书桌旁的沾沾自喜其实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因为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由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其商业化和流俗化了的变体)所承诺的认识方式之封闭结构将成为一个问题,将通过经受文学真实性期待视野的再次界定而成为一个问题。
严格意义上说,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就是在文学文本中突出感官细节(也就是日常生活模拟物),再把它们按照从假设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顺序加以编排。因此,正如约翰·伊利斯所指出的,第一段的描写显得焦点没有调好。屋子有很多排,格奥尔格在其中一排的房间里,而这些排和这些屋只在颜色和高度上有所区别。但这些被叙述者轻描淡写的“颜色”和“高度”恰也正是文学现实主义所要强调的有关文学事物最具标志性的特点。此外,在河对岸的原野的“绿色”被修饰为“弱的”(schwach),在德语中也是个奇怪的用法,在这里本应用另一个词。②Ellis,John M.“The Bizarre Texture of‘The Judgment’,”in The Problem of The Judgment:Eleven Approaches to Kafka’s Story,pp.76-77.现实主义者进行客观描述的目标眼看着就这样塌陷了,这一印象被格奥尔格所扮演的观察者所体现出观察视野进一步加强了。他似乎是一个寓言式形象,是作家审视展现在他面前的世界的寓言式形象。但我们发现他心不在焉、漫不经心。他以一种游戏般的态度把信装进信封,就好像它没什么特殊重要性;他对窗外的世界显然也兴趣甚小。这里暗含着从格奥尔格的职业身份出发而来的解释:与世界的疏远关系,漠不关心,以及随着叙述的展开被归于他的罪过,都可以看作主人公置身其中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私人财产所有制的必然结果。至少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说是个可能的起点。但这些和阶级相关的标示同时也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显见标示,上述提及的第一段之异常微妙处,其实就已经为更进一步审视这种已经文学化了的文化做好了准备。现实主义期待同时被强化和弱化。J.P.斯特恩说:“在卡夫卡的故事中,煽情性的东西被避免了,因为从现实性的东西到超现实性的或幻想性的东西的转换是悄无声息的。”①J.P.Stern,“Guiltand the Feeling of Guilt,”in The Problem of The Judgment:Eleven Approaches to Kafka’s Story,p.119.现实主义认识框架的塌陷最终会在父亲对格奥尔格的死刑判决中被实现,但其实在看似平静的开头处的字里行间已经被预示了。
除了对于文学现实主义描写的颠覆外,文本从一开始还在叙述视角方面引入了麻烦。从“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的开头,读者便期待会有一个全知的叙述者谈谈主人公格奥尔格的个人感受和社会地位。第一段从叙述者的排屋视角很快地转到格奥尔格的视角:看到的是河对岸的原野。此后的视角持续在客观性描述和主观性视野之间交替;特别是通过一些指示词的使用,叙述者与读者似乎就和格奥尔格的主观性站在一起了。于是就有这样的建议:在彼得堡的朋友应把生意搬到“这里”;稍后又说格奥尔格的生意“现在”好了很多——就好像叙述者和读者共享着格奥尔格的“这里”和“现在”。就格奥尔格来说,在全知叙述者和被限定认识的人物之间进行清楚区分这一文学现实主义惯例失效了,尽管在其他人物那里这一区分还保留着:父亲仍是客观“报道”的对象。父亲的思考没有像格奥尔格的那样被揭示,其结果就是读者被要求接受一个关于格奥尔格的故事,从外部来说是这样,从内部来说则直接参与了格奥尔格的思考。私密房间的主观内部性与客观外部视野之间的区分,无论如何都难以成立了,而叙述自身的形式结构以相似的方式进一步破坏了这一区分。由书桌旁的格奥尔格所体现的那种个体性的或布尔乔亚式的独立自主,正在失去其根基。
故事的结局同样复杂。起初,格奥尔格的失败似乎是开头场景的全然颠倒,那时他为自己的独立感到飘飘然;开头和结尾对应的分别就是私人空间的自由与公开的自裁,开头处的自我满足的世界观崩溃了。但正如开头不是单一维度的——开头已经暗示了将要爆发的问题,结尾部分也不能简单地被解读为对主人公的弃绝。下达“判决”之后,父亲也垮了,这一描写标示出他和儿子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错综斑驳的关系,非简单的“父子冲突”模式所能涵盖。格奥尔格在楼梯与女仆的相遇(包括后者对耶稣的呼唤及遮盖脸部的动作)暗示的恰是一个错过的机会,(这个机会)与格奥尔格有着奇怪的对立关系——“但是他已经走了”,尽管转折词“但是”所表达转折的意思并没有得到解释。更令人困惑的还有那段被拖延的时间:格奥尔格跳过栏杆之后,还在桥那里吊了一会儿;格奥尔格用这段时间表达了他对父母的爱,还等来了一辆公交车;这后一个东西大概是为了盖住他落下去的声音而出现的,同时也使得他的死悖论性地具有了某种公共的匿名性。
如果现实主义认识原则的解体已经颠覆了《判决》开头对于独处之安全性的立场,那么对于结尾的推论就是:格奥尔格跳河举动亦即他的自杀行为的最后性质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不那么确定的。结尾与情节自身对结尾的要求比起来,少了一些绝对性。如前所述,父亲垮台了,父亲与儿子、法官和罪犯之间的清楚界限随之也成了问题。两者不是对立面,而是同一个机制或机构的参与者,这个机构的统治者可能就是某种罪疚(但愿这点能够确定)。如是这样,它就是一种集体性的责任而非个体的罪过。《判决》不是格奥尔格个人命运的叙述,作品中复杂的“爱”的意象说明了这一点:女仆呼唤的“耶稣”、格奥尔格对父母的呼唤以及正开过来的“自我公车”(Autoomnibus)——该用语从构词方式上就挑明了独立自主的个体与更广泛的集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符号网络中,或许还可提及圣彼得堡、俄国教士以及父亲宣称自己朋友的代表: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基督教符号或象征。如果落入河中暗示了一种再生的洗礼,作品最后部分的用词“unendlicher Verkehr”(无尽的交通)也可以说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作为集体的人类的生命与生活正在进行,而无尽的交通也特别地包含着性意味。斯坦利·康格德曾就此说起“结尾处的句子具有爱欲高涨及无尽‘交通’所带来的兴奋和力量”。①Stanley Corngold,“The Hermeneutic of‘The Judgment’,”in The Problem of The Judgment:Eleven Approaches to Kafka’sStory,p.40.至此,考虑到父亲的最后结局、对公共生活的诉求以及重生的可能,格奥尔格在父亲宣判之后的死亡就是作品的结局,这个最初印象就不太准确。以此来看,格奥尔格让自己从桥掉落并非叙述其死亡。相反,我们发现有着多重含义的无限交通取代了死亡,结尾远非确定的最终的结论。车流之下的格奥尔格死了还是活着,文本并未定论。
故事最基本的框架于是走入了一个解释的漩涡。首次接近情节的读者不难发现,从在一个春天周日美好的早晨处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保护性环境中的格奥尔格,到跳进河里很可能已经毁了自己的格奥尔格之间,存在着一个弧形轨迹。开头和结尾之间的对比必定诱发弄清楚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努力:对那个在美好周日早晨给自己朋友写信的美好的年轻人的裁决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呢?但《判决》令人费解之处在于:比起故事的那个具有欺骗性的弧线所暗示的,开头和结尾之间的关系靠得要更近些,并非像表面看来难以兼容。如果另有一条进入《判决》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就是要认识到书桌前的格奥尔格和挂在桥下的格奥尔格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并非像最初看上去那样紧张。以此来看,叙述所要展开的,并非一个走了霉运的故事,也无关一个个体不幸,毋宁说是关于一般意义上判决的本性以及这一本性与偶然或机运及世界的运行方式的故事。对这一可能的路径进行更深入探索,就需要更切近考察故事中间也就是开头和结尾之间的那个部分的构造机理和言辞特点。
如果说开头和结尾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将两者连在一起的东西也已经说过了,也就是在对于法庭审议式言辞的常规期待与个体话语持续滑脱这一轨道并具有某种神秘性的特点之间的对立。一方面,格奥尔格和他的父亲(当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了理性的论证中,直接地或间接地(格奥尔格的思想流程有时是被叙述者“报告”的)。这种深思熟虑的言辞姿态诱惑读者将他们之间的争论当作严格意义上的争论,也就是说,是逻辑的,近似于法庭辩论所使用的语言;这构成了衡量、评价和判断各种决定的一个尺度和背景,格奥尔格选择向朋友宣布订婚的决定,或者父亲的判决,都是在这样一个语言背景中被理解的。卡夫卡对于法律语言的反复征用实际上构造了他所处理的素材,这种语言暗示,“判决”最终一定要有意义。但(另一方面)文本也一再地表明,在其所用的语言和用于其中的话题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对此线索进行追索将导向这一理解:该文本至关重要的判决与其说是关于格奥尔格的,毋宁说是对于判决自身之可能性的。
对于判决的批评最清楚地体现在文本对于证据问题的处理上。法庭审理言辞需要证据,证据就是此种言辞的话题。要做出判决,必须参照事实以及事实被认定必然具有的意义。卡夫卡对其笔下的格奥尔格及其父亲的宣称进行了蜿蜒曲折的司法式语言包装,这给读者带来了相应的期待。但这些对于读者来说都不是陌生的东西,因为这已经构成了对于法律程序的现代理解:恰当的判绝不是任意的,必须有充分的证据以及对证据的恰当评价,评价必须根据论证的规则进行。
然而,《判决》尽管激起了对于深思熟虑之言辞品质的期待,其中的大多证词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显示出是充满漏洞和不确定的——它们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对于手头的案件来说没有什么用处。这种颠覆性证词中可举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比如格里高尔在家族企业中的崛起。关于此事的评论显然出自叙述者角度,因此读者会期望得到一个确定的描述。但读者面对的却只是三个独立的叙述,每个前面都有个“也许”,其中最后一个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解释,只是将其看作意外的好运气。②Martin Swales,“Why Read Kafka?”Modern Language Review 76(1981),p.360.这样,在对格奥尔格与其朋友之间的通信的性质以及更为具体地对格奥尔格商业成功之性质进行假定性的沉思的语境中,论证的基础,也就是证据性的基础,就成为推测性的。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父亲后面将谴责儿子在商业上暗算他。
形式上是在进行理性论证,但支撑性证据不足或不兼容,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屡屡发生。相关的事实要么不具有决定性,要么对于所宣称的东西不恰当。为证明格奥尔格对父亲的爱,叙述者举的例子是他们在同一个食堂吃午饭,但文本却没说他们是不是在一起吃的;而他们在夜晚各自读各自的报纸的景象所显示出的更多的是疏离而非礼让。相似地,文本说格奥尔格的朋友没能对格奥尔格母亲的去世表达足够的哀悼之情,这点还被当作他在社会关系方面有问题的一个症状。但我们还了解到这个朋友事实上要极力促成他去俄国,这是一种情感表示,与格奥尔格自己摇摆于是否邀请他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格奥尔格对其朋友的判断,亦即他所认为自己的朋友在社会关系中是孤独的,其实并不能从这个事实获得支持;这个事实倒可以用来证明相反的东西,无情的不是他的朋友,而是格奥尔格自己。
论证性宣称和所宣称的事实之间的不协调甚至也表现在那些看起来无争议的话语中。格奥尔格注意到父亲关着窗户,父亲说这是他的爱好。格奥尔格接着说外面暖和,“就好像在他前面那句评论加了一句”。①“Wie in Anhang zu dem früheren”;“asif continuing his previous remark.”在这里并不清楚这句对于天气的随意评论放在这里什么意思:是对窗户没开这件事进行批评的延续呢,还是对父亲愿意让它关着的习惯表示肯定呢?似乎理性的交谈在这里被模拟了,但在每一点上都缺乏实质性,甚至在对天气的谈论上。文本标示出了这种滑向解体的论证,也就是说,文本缺乏强有力的逻辑,其后的评论只是“像是”之前事情的“延续”。
最后应当提及,不只是格奥尔格,父亲那些看似精审的宣称也在经受着靠不住的事实的颠覆。他开始时对格奥尔格的批评伴随着一系列的陈述,这些陈述恰好取消了所暗含的某些指控。起先他抱怨说格奥尔格没有告诉他全部真相,而后又限定自己的说法,承诺说不谈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也就是说,不谈那些可能与那位朋友无关的事。他批评格奥尔格不透露详情,而自己其实正在宣称自己不会讨论某些话题。而他很快突然转向,谈起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一些发生在他妻子去世之后的事情,但又没指明到底是哪些事。他两次强调说“或许”是到了他们之间摊牌的时候了。这样指控就同时被暗示和掏空。以相似的方式,他又说自己可能忽略生意上的一些事,暗示格奥尔格或许欺骗了他,但他对此并不明说。对这些交错起来而显得不那么清楚的指控,格奥尔格其实根本无法进行理性的反驳,因为父亲承认自己的记忆力正在衰退。这段文本因此就以理性判断修辞的方式向格奥尔格暗示了一个有关于他罪行的宽广范围,与此同时又避免与任何具体的事实以及具体的指控扯上关系。任何想要以一种恰当的思考方式解释这种指控的努力都必定会受挫,理性形式与最终不可触摸也难以确定的经验事实之间的鸿沟难以填补。
因此在《判决》中,法庭审议言辞已经失去了相对可靠的事实性证据本来能够提供的支撑。不仅如此,在总结性判断的层面上,法庭审议言辞还遭到了第二种意义上的失败,也就是说,正如对于那些飘忽不定的要点的评价并不充分一样,总体性的判断也站不住脚。格奥尔格对朋友的判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判决),父亲对格奥尔格的判断(第二个判决),在细查之下,都没有一个能说服人的逻辑。相反,论证和经验在这两个情形中都显得不一致,尽管两种情形的矛盾特点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文本把格奥尔格对朋友夸大其词的关心放在前台,然而接下来反而更加泄露了他根本不愿让其来参加自己婚礼的实情。他一再声称为朋友的好处考虑,看起来倒更像是将其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借口。这样,格奥尔格对朋友及其在俄罗斯情形的判断背后就有一个复杂的心理动机,这一点许多批评家都谈到了。隐蔽的忧虑埋藏在表层之下,迫使格里高尔对自己不愿邀请朋友的事实寻找理性的借口。在这里显示出卡夫卡对弗洛伊德与尼采的兴趣,包含着对秘而不宣的和无意识的动机的认识。如格哈德·库尔茨所说:“考古的冲动,在城市之下寻找城市的冲动,把尼采、弗洛伊德和卡夫卡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人类灵魂的现代发掘者。”①Gerhard Kurz,“Nietzsche,Freud,and Kafka,”in Reading Kafka:Prague,Politics,and the Fin de siècle,p.128-48.格奥尔格对父亲坚称他最初只是考虑到朋友的好处才犹豫是否要把结婚的事情告诉他:“这是唯一的原因”②“aus keinem anderen Grunde sonst”;“thatwas the only reason.”——这一点被如此强调,读者不免会看出这个宣称其实是个借口。
相比格奥尔格对朋友的判决的公然欺骗,父亲对格奥尔格的评价所依据的法庭审议言辞要含混得多。在后一种情形下,判断的脆弱之处清楚地表现在父亲言辞在许多方面的自我矛盾。他对儿子的痛切攻击一再地被其自我否定的言辞弱化。于是他最初对彼得堡的那个朋友的是否存在的质疑似乎只是为了反对自己:他坚称和这个朋友有一种隐秘的联系,并且还是这个朋友在此地的一个代表。在另一个例子中,他似乎一方面责备格奥尔格耽误婚姻太久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却又批评他如此心血来潮地要结婚。最终格奥尔格被置于此境地:他与弗丽达的订婚既太早也太迟。最后,父亲对格奥尔格性格的判断也同样是矛盾的。格奥尔格因急于独立和成熟(表现在商业和婚姻领域)而受到批评,同时他也因孩子气而受到攻击:一个“小丑”,父亲的“小丸子”。对格奥尔格指控是互相排斥的。在父亲的谴责中不可能辨认出清晰的逻辑,他的谴责包括了诸多难以兼容的因素。换句话说,确有判决,判决也很严厉,但这判决却不符合此前由法庭审议话语所设定的规范。在格奥尔格对其朋友进行评判的情况中,文本显示出深层动机扭曲了判断,论证和结论并不契合。在父亲对儿子判决的情况中,我们只是得到了几个站不住脚的大胆断言。在两种情形中,《判决》都指向了内在于判断的结构性缺陷——进行判断是如何地难以避免则是另外一回事。
判断的缺陷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涉及语言的使用:尽管卡夫卡个人的语言是精确的,格奥尔格却常常难以控制自己的言辞。语言胜过他,或者超越了他的掌控,有时飘忽,有时顽固,但从未完全受其控制。没有对语言的有效控制,他就没有为自己的情况进行辩护的位置。显然,论证性判断的逻辑没有能力依赖语言,后者倒是有取胜的需要。其结果是,语言能产生本不想要的结果,就如同与朋友的通信:格奥尔格本想随便聊聊,却由于提到一个陌生人的婚姻(本来这恰是为了避免谈论更为实质性的话题)而引发了朋友的好奇心。或者,在父亲愤怒的爆发中他的几次插话本来都是为了避开攻击的,却悲惨地表明并不顶用。他缺乏完成一个强有力的反向论证的修辞力量。此外,另一个缺陷也把判断弄得不那么稳定——格奥尔格的主体性逐渐解体了。面对父亲,他被描述为越来越健忘,失去了为自己辩护所必需的连续性意识。这与开头处的自信满满、顾盼自得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那时的格奥尔格也已经滑向某种失神状态。在与父亲的对话中,他持续性地失去记忆,这正支持了父亲的指控:儿子忘记了他死去的母亲。格奥尔格的即刻性逐渐引发了对于过去的抑制;如果从对他的判决中找出一种关于判断的伦理的话,不妨说:失去过去意味着失去未来。
作品非凡之处在于,在展示了任何一个判断过程都具有的缺陷之后,它仍然把读者无情地拖入到一个必须做出判断的境况中。然而,任何对于《判决》的判断/判决,都不可能逃脱作品的叙事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判断”的命运。可能之一,确认判决必须要赋予父亲的指控以一种逻辑上的连贯性,但这种连贯性在文本中是缺乏的。可能之二,试图回应指控来为格奥尔格辩护,需要一个现代主义的立场或女性主义立场的支持——它们反对父权和父亲的权威,这种立场如果贯彻到底的话,会主张颠倒一切判决。③Gerhard Neumann,“‘The Judgment,’‘Letter to His Father,’and the Bourgeois Family,”in Reading Kafka:Prague,Politics,and the Fin de siècle,pp.220-221.最后,认为这个作品是对判断之不可能性的说明的解读则会把解读者卷入到后现代意识的行为矛盾中:一方面坚称在一个绝对不确定的想象性世界里进行判断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却又乐于拥有作为一个判断者的特权和优先权。④Stanley Corngold,“The Hermeneutic of‘The Judgment’,”in The Problem of The Judgment:Eleven Approaches to Kafka’s Story,p.40.
不可能选择支持控告者,也不可能选择支持辩护者,因为双方的论证都有很大的缺陷。一个对文本进行详尽阅读的读者也不可能宣称不可能判断或判断的不可能——这个判断很明显既与这个故事的中心事件相矛盾,也与批评者自己的阅读过程相矛盾。相反,这个故事同时展现了进行判决的必须性和罪疚感的普遍共存性。格奥尔格和父亲都进行判决,也都分有着某种罪疚(这也正是为什么当儿子跑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时,父亲也垮掉了)。还有,在与弗丽达谈话的过程中,格奥尔格把自己的朋友卷进了罪疚,弗丽达坚持要格奥尔格写信给朋友则促成了危机。如果初读起来《判决》像是关于格奥尔格的故事(这一印象因内心独白而得以强化),细查之下则会膨胀拓展起来。从一个单独的私人房间,衍生出父子冲突,进一步卷入了弗丽达、朋友和母亲的角色,而在边缘地带,还有俄罗斯的教士与群众,直到小说最后,出现了“自我-公共汽车”(Autoomnibus)和无尽的交通。叙事过程中的不断扩展为父亲的谴责增加了额外的分量:格奥尔格只想着他自己。罪疚内在于这一个体自我的闭锁过程。另一种可能是对于集体的多重关系的包容。格奥尔格开始的自我关注难以通达真正的独立自主。相反,开头那种孤立状态的自我存在形式不过是通向一种走向终结的软弱个体性的开始,事实上这种孤立状态与普遍性的异化状态沆瀣一气。所以他才会没有为自己做辩护的论证能力,只能顺服于对他的判决。《判决》的最后问题并非父亲判词的不可靠品质——我们知道任何判决的依据在最终的意义上都必然是脆弱的——而是格奥尔格的沉默与顺从。何种文化产生出了如此强烈的服从意愿——哪怕是这种服从导致的是自我毁灭?
这是一种关注自我之孤立状态的文化,也就是自恋文化,个体如此沉迷于自我以至于他变得看不见自我。①在此种文化中对自我的兴趣与背叛相联系:格奥尔格背叛了朋友和对母亲的记忆,也抛弃了自己的父亲。但首要的是,这种文化是由一种退化堕落的写作模式标示出来的——卡夫卡通过这个文本突破了自我,走向了成熟,而这个文本恰是关于写作的。我们在作品的一开始遇到的,就是一个写作者格奥尔格,一个避世独居、思前想后而又心神涣散的作家。我们知道他很想写出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作品;我们还知道他试图利用语言策略来掌控读者;此外这种类型的写作看起来还不需要某种特别的努力——他以游戏般的慢腾腾的动作结束了写信。但这一文学世界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动词的使用:格奥尔格刚刚“结束”(beendet)文本,这一用词以某种变化了的形式在结尾处重复出现了:“无尽(没有结束)的交通”(unendliche Verkehr)。《判决》自身所包含的批判视角及其对文学成规的抵制决定了其结尾的力度:封闭的形式、封闭的心灵以及由之而来的弱化的主体性。格奥尔格的文本遗世独立,也正是这个原因才虚晃不实,其所采用的书信体对应的就是文化工业时代堕落退化的现实主义,这在小说的第一个句子所呈现的老套形象中就已经显示出来了。而作品《判决》表达了另一种选择:这种文学向社会和传统开放,向过去和经典开放,这种文学有能力赢得一种公共和群体的生活。那个在手掌切开十字的俄罗斯教士暗示了一种真正的写作,也预示了《在流刑营》中的身体铭刻。那个在书桌旁的自由个体尽管声称真诚和开明,最终却愿意接受自我毁灭,没有能力作出实质性判断;相反,宗教性群众却能够掀起一场革命。卡夫卡深受一种与传统有深刻共鸣的文学的吸引,这种文学“关乎民众”——他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一则日记中如此写道,以这种方式他也作出了对现代文化最严厉的判决:失忆,原子主义,以及对内在于任何判断的复杂困难的持续逃避。
〔本译文系译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批评视野中的卡夫卡学术”(项目编号:13YJC752042)及浙江省哲社规划项目“卡夫卡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12JCWW01YB)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译者简介】赵山奎,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罗素·伯曼(Russell A. Berman),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沃尔特·海斯(Walter A.Haas)讲座教授,德国研究系、比较文学系教授,曾任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会长(二○一一),现为斯坦福大学德国研究系系主任,新左派权威刊物《泰勒斯》(TELOS)主编。著作有《现代德语小说的兴起》(一九八六)、《现代文化与批评理论》(一九八九)、《启蒙或帝国:德国文化中的殖民话语》(一九九八)、《欧洲的反美主义》(二○○四)与《虚构让你自由:文学、解放与西方文化》(二○○七)等多种。
*原文题为“Tradition and Betrayal in‘Das Urteil’”,原载于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Franz Kafka(James Rolleston ed.,New York:Camden House,2002),第85-99页,特别感谢Camen House的JimWalker授权发表该文中译。作者所引用《判决》原文和英译文据Franz Kafka,Ein Landarztund andereDrucke zu Lebzeiten,ed. Hans-Gerd Koch(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7);“The Judgment,”in The Complete Stories,ed.(Nahum N.Glatzer.New York:Schocken,1971),pp.7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