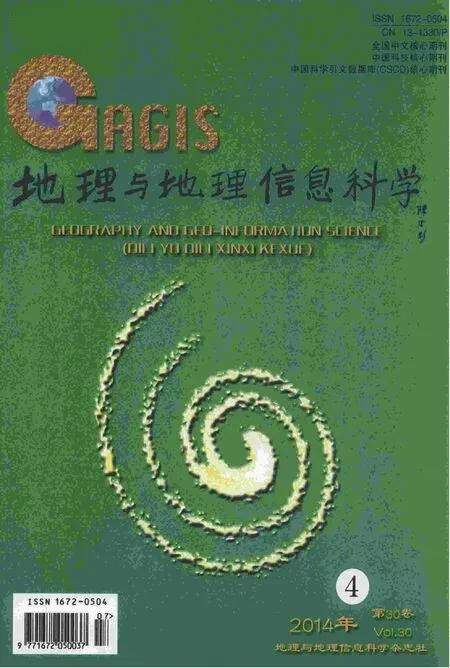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争议再辨析——兼与张立生先生商榷
祁洪玲,刘继生,梅林,3,张振国
(1.大连民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50;2.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3.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7)
0 引言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旅游地演化理论的重要框架,是旅游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1],在旅游学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引为经典的是巴特勒(Butler,1980)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根据该理论,旅游地演化的一般过程可划分为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稳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六大阶段。停滞阶段的旅游地通过再开发可产生5种类型的结果,从剧烈衰退、缓慢衰退、平稳波动、小幅增长到增速强劲的复兴,但旅游地的长期趋势是走向衰退,在这一进程中,旅游地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人地要素会发生规律性变迁,游客特征及客源市场状况随之发生规律性变化[2]。
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提出迄今30多年,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世界最权威的旅游刊物(如旅游研究纪事、旅游管理、旅游研究杂志等)30年来频繁发表以“旅游地生命周期”为篇名的文章,在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验证不同类型、不同尺度旅游地的具体演化形态,分析旅游地演化的影响因子及内在机制,完善模型的内容体系,探索旅游地演化理论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赢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极高的赞誉,被西方人文学界评述为“十分经典的学术模型”[3]。
我国旅游学术界张文(1990)最早讨论了旅游区生命周期问题[4],保继刚(1993)最早引入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内容[1,4],随后旅游学界逐渐开始关注旅游地演化理论的探索。但伴随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的推进,国内学者产生了一些争议,如果不深入追溯这一理论的发展脉络,很难分辨孰是孰非,因此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将这些争议进行剖析、厘清,期望在争论中达成一种共识甚至妥协,对国内旅游学界继续推进这一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来源辨析
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旅游地演化理论体系的重要框架,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理论主要源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实际上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国外地理学者就开始对旅游地演化规律的探讨。19世纪末期,戈德金(Godkin,1883)在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上发表了题为“夏季寄宿者的演化”的文章,认为随着游客的不断到来,旅游地居民改善接待条件,旅游花费不断攀升,低收入者失去租住能力,并称之为“旅游地发展悲剧”。这篇文章曾引起当时各界的激烈争论[5],也是早期探索旅游地演化方面较有影响力的文献。此后,更多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旅游地演化规律的探索,但在一段漫长时期中,关于旅游地演化的相关研究都是处于描述性研究层面或是对具体某个特例的研究(Hobs,1913;Webster,1914;Ogilvie,1933)[6],1939年吉尔伯特(Gilbert)首次关注旅游地一般演变规律的探索,尽管其研究范围仅限于英格兰地区的内陆与滨海度假地,却是探索旅游地演化一般性规律的开端[7]。
二战后,大众旅游逐渐兴起,欧洲旅游业恢复繁荣,但一些传统旅游地却因地中海地区新兴旅游地的冲击等原因,出现了衰退状况。因此旅游地演化规律的探讨逐渐成为西方旅游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许多学者如平洛特(Pimlott,1947)、沃尔夫(Wolfe,1952、1966)、豪斯(House,1954)、吉尔伯特(1954)、巴瑞特(Barrett,1958)、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63)、普洛戈(Plog,1972、1973)、斯坦斯菲尔德、李克特(Stansfield&Rickert,1972、1978)和诺洛尼亚(Noronha,1976)纷纷开始了对旅游地演化的一般路径和发展模式的研究[6]。其中巴瑞特、斯坦斯菲尔德和李克特等先后探索了滨海旅游地空间形态特征的演变规律。著名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则生动地描述了旅游地发展的经典动态演变模式,被探索者发现,逐渐变得流行。随着大批观光客的涌入,旅游地过度商业化导致旅游吸引力逐渐丧失,旅游地发展与环境背离并逐渐走向衰退[8]。克里斯泰勒文中旅游地“发现-兴起-衰退”的演变路径脉络清晰,尽管这一模式被认为最符合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旅游地的发展,且有较大局限性,但它是学术界公认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的开篇之作[4,6,8];此后,诺洛尼亚提出了旅游地开发的三段论,包括发现阶段、当地响应和积极参与阶段、规范化和制度化阶段;普洛戈则描述了旅游地演化不同时期所吸引的游客具有差异显著的性格特征。布鲁厄姆与巴特勒合著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resort cycle”这一称谓,斯坦斯菲尔德则首次将“resort cycle”用在文章题目中[9]。
西方学术界对旅游地演化理论的研究构成了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基石,伦德格伦(Lundgren,1984)评述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时认为,巴特勒只是将学术界普遍已知但却没有系统建构的理论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10]。巴特勒在其1980年发表的文章中大段援引了克里斯泰勒的文章[2],值得强调的是,克里斯泰勒提出旅游地演化理论的时间是1963年,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年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11],所以认为旅游地生命周期论来源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2-14]的观点有失偏颇。不可否认的是,巴特勒提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确是参考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内容[2],所以对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阶段的划分比克里斯泰勒更加细致、生动,可以说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完善是受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启迪,但有关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完全来源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2-14]的说法,则过分夸大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作用,有些言过其实。实际上,忽视旅游地演化规律研究长期的历史积累和酝酿过程,是将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误认为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2 理论内容相关争议的辨析
2.1 有关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核心概念的争议
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概念是争议的焦点之一,但国内外争议的内容略有不同。国外学术界对核心概念的争议主要有两点。第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借鉴了生物学领域的物种进化理论,很多学者探讨借用生物学领域中达尔文的物种演化(evolution)理论表述没有生命的旅游地发展是否恰当[15]。有学者认为旅游地发展比较符合生物进化论奠基人拉马克提出的遗传的“突变”特质,而非达尔文的“渐变”,这种突变理论更符合文化和技术的发展规律[16]。但也有学者(包括巴特勒)认为旅游地的发展过程是渐进的,且必须不断调整才能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所以借用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也无可厚非[15];另外一个曾在概念上引起争议的是巴特勒最初提出的理论中用的是旅游地(tourist area),而非旅游目的地(tourist destination),尽管两者含义相近,但两者在空间范畴和统计意义上都有很大差别。空间上,旅游地不仅包含旅游目的地,而且还有其外围地区(satellite destination);统计上,前者的接待人次只计量过夜游客,而旅游地的接待人次则包括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17]。
中国学者对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基本概念的争论,则是着眼于巴特勒的理论究竟是表述为“旅游地生命周期”还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更为恰当。认为应表述为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有杨森林、许春晓、张立生等,综合起来理由有四:第一,从源头上讲,Butler理论受营销学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启迪,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旅游学中的应用[12,13];第二,旅游产品可以分为旅游地产品、旅游线路产品、旅游节庆活动产品等类型,旅游地生命周期应该是旅游地产品生命周期的分支或者类型,旅游地是旅游产品的空间载体,只有旅游产品才有生命周期,仅因为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研究中实际操作的便捷性,旅游地产品生命周期才以旅游地产品替代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旅游产品[13,18];第三,一些知名学者(如申葆嘉等)也使用旅游产品生命周期一词[18]。认为应表述为旅游地生命周期(如余书炜、阎友兵等)的证据有两个:一是从翻译学的角度,国外包含Butler在内的学者的研究对象都是旅游目的地、旅游度假地或者旅游胜地,并始终以旅游地生命周期为名;二是在旅游地的构成要素中,包含了旅游活动的参与者——当地居民,而旅游产品的研究通常不包含这一要素[19,20]。还有潜在的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种概念都可以,因为旅游地生命周期和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密切相关,没有严格差别或者区分的意义不大。
笔者认为出现激烈争议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属于舶来品,由于文化和发展背景的差异,中英很多词汇在外延与内涵上都无法完全一一对应,一些概念必须经过修正才能适应我国的客观情况,这有待进一步厘清和完善。第二,巴特勒于1980年发表的文章虽然是写旅游地在时间维上的演化,但“S”曲线图模型所能展现的信息较为简单,只直观地描述了旅游者数量在时间维上的变动。很多学者在引入这个理论时只详细介绍了“S”线图,与产品生命周期的销量和利润在时间维上的变动相似,让很多学者误以为是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巴特勒(2010)也认为,模型图吸引了学者过多的关注[5],以至理论的整体内容被曲解或忽视。第三,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也可以用于指导旅游产品演化的研究,这也是很多知名学者基于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研究旅游产品管理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巴特勒的理论还是翻译为旅游地生命周期更恰当。主要原因有:第一,尽管旅游产品依附于地方的特性使其包含了地方特征,但旅游产品与旅游地的概念在内涵及外延上仍有很大差异。旅游产品是旅游地提供给游客的吸引物与服务的总和,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旅游地是提供游客旅游产品的区域或地方,包含与旅游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要素,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再看巴特勒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中,研究对象是包含一定地域内以旅游要素为显性特征的人文、自然等地方综合要素,符合旅游地的概念。第二,尽管巴特勒勾勒的“S”曲线图只用游客量变化这一数量指标作为阶段识别标志,但文中详细阐述了旅游地社会、文化、经济等要素在各个阶段的变迁规律。如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交流程度、当地居民对游客态度、当地居民生活受影响程度、自然人文环境的变化等社会、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变迁,尽管这些要素性质的改变无法或很难量化,也很难以图形的方式展现出来,但可看出文章表述的是旅游地域综合体的演变,且在空间进程上存在核心-外围的地理特征转变[5]。第三,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可用于指导旅游产品演化,更可用于分析如国家、地区、省、市、县、乡、村等不同空间尺度上旅游地域综合体的演化研究[5],而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第四,最重要的依据是,原作者巴特勒认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根植于地理学的土壤,在对概念的补充解释里重点提到了旅游地演化具有核心地区到外围地带的空间扩散的特性[21,22]。所以,综合以上内容,巴特勒的理论表述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更为恰当和严谨。
另外,即使不考虑文章的出处,有三个背景仍然值得关注:第一,巴特勒一直接受的是系统的地理专业教育,长期在大学的地理系任职[23],而旅游地演化也是自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第二,巴特勒文章中的参考文献多来自当时比较著名的地理学家,且研究对象都是旅游地;第三,完善和使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的学者,多将其用来研究旅游地发展的问题[24]。所以从背景上看,巴特勒理论表述为旅游地生命周期也更符合逻辑。
2.2 有关旅游地演化阶段特征的研究
有关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化形态,也是产生争议的热点问题。阶段划分争议的范畴里,各学者认可旅游地的演化呈现相同的起点和终点以及相似的逻辑进程和演化路径,旅游地生命周期呈现开始、兴起、衰退的单一曲线形态,但在阶段划分上有所不同,大致有将旅游地生命周期划分为三、四、五、六、七阶段的说法。
三阶段说主要是早期探索旅游地发展规律时提出的,将旅游地演变分为发现、发展和衰退三阶段[7,25],并且三阶段旅游地主要吸引异我中心型、中间型、自我中心型3种性格的游客[26];也有学者在验证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时发现,尼亚加拉瀑布起步阶段与发展阶段无明显界限,停滞、衰落与复兴阶段并存,即尼亚加拉瀑布发展也呈现了三阶段态势[27]。四、五阶段划分法是各国学者在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个案地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旅游地在发展中呈现出不同于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进特征。旅游地演进呈现四阶段,与产品生命周期基本一致,包括引入、发展、成熟和衰退阶段[28],有的旅游地在经历探索、参与、发展阶段之后,长期呈现稳定阶段[29],或者旅游地直接进入发展阶段,经历短暂的巩固和停滞阶段后进入衰退阶段。当前研究中也有呈现五阶段发展的个案地,如有学者对美国乡村兰卡斯特进行了持续研究后发现,该旅游地的发展呈现了探索、参与、发展、成熟和衰退五阶段[30,31]。六阶段说受到包括巴特勒在内的多位学者的支持,发现很多旅游地的发展支持了经典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尽管各个案例地由于自身特征或外在因素干扰,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间跨度,但历史数据证明旅游地经历了探索、参与、发展、巩固、停滞、不同程度的复兴或者衰退[1,32,33]。七阶段说认为旅游地在经历停滞阶段后,必须对其发展进行重大调整,也就是所谓的“再定位”或者 “重构”这一阶段,如果干预成功,旅游地才能进入复兴阶段,如果干预失败,旅游地则彻底步入衰退阶段[34,35]。由于旅游地衰退后会出现经济凋敝、人口失业严重、社会治安恶化、旅游设施废弃,所以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即如何“退出”旅游发展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所以鲍姆(Baum,1998)等认为应该在旅游地衰退阶段之后加入“退出”阶段,这样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化进程才更加完整[36]。
就其实质而言,早期的三阶段说是学者们为了突出旅游地的动态性,在时间轴线上呈现一定规律性的演进而提出的分法。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正是基于以上研究,对旅游地的演化进程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提出了所谓的六阶段说。至于四阶段、五阶段说,是各国学者依据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结合各个案例地的发展数据,发现旅游地的演化并不是完整的依次呈现六个发展阶段,某些阶段因为旅游地的特殊性而没有出现。所以严格意义上,对三、四、五、六阶段说并没有产生争议,真正产生争议的是旅游地经典演化模型到底应该是六阶段还是七阶段。毫无疑问,巴特勒的六阶段模型提出早、传播广、受众多,现在世界各地的学者以巴特勒的六阶段模型作为旅游地演化进程模型的最多[37]。而七阶段说的阿贾瓦尔 (Agarwal,1994、1997、1999、2002、2006)是持续对巴特勒理论和案例地研究之后提出的[6],认为停滞之后必须加入“再定位”阶段,才能决定旅游地是否走向复兴。这一说法不但有其他学者支持[34,38],巴特勒也对阿贾瓦尔的这一建议给予了高度肯定[6]。
从演进方向上看,这五种阶段划分法都描述了旅游地从初期的发现到最终的衰落,呈现出一致的逻辑进程和演化路径。三阶段说对演化过程的划分比较粗略,而四、五阶段说则是不同个案地的演化实证,是对六阶段说的验证和具体表现。六、七阶段说才是对旅游地演化规律的一般性抽象,虽然六阶段说知名度高,应用最广,但综合考虑巴特勒一再强调其提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主旨是强调只有通过人为的恰当干预,旅游地才有机会重新走向复兴,因此,加入“再定位”阶段,更能体现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服务于旅游地管理实践,追求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价值。因此,不同于张立生先生的说法[13],笔者认为阿贾瓦尔的七阶段说更加经典、完整,也更加体现了生命周期理论服务于旅游地发展管理的价值。另外考虑到旅游地彻底衰退之后可能出现严重的经济、社会等问题,所以如何选择恰当的“退出”路径,也是旅游地开发中的重要课题,因此,在旅游地衰退后考虑如何平稳“退出”旅游业,也是非常合理而有必要的。
2.3 有关理论价值的争议
巴特勒提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模型后,有两处备受争议,即模型的真伪问题和模型的价值问题。
2.3.1 模型的真伪之争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表述的是旅游地长期演进的路径,所以收集完备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实证研究不易。尤其是旅游地处于探索阶段和参与阶段时,各地很少关注和收集旅游发展的一手数据,所以有关游客数量、特征的资料很难找到。巴特勒也承认由于历史数据的缺失,使得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在实践验证时存在较大的困难[2]。旅游地生命周期引进到中国后,杨森林、阎友兵等学者据此相继质疑其理论价值,认为实践中难以找到完全符合理论表述的旅游地[10,17],这是巴特勒理论提出后早期学者们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27]。各国学者用不同案例地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尽管各案例中旅游地发展中呈现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但其演化方向和路径基本符合巴特勒构建的模型[1,5,33,37,39,40]。
后期,借助多学科视角,许多学者用数学等多学科方法对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进行模型拟合,证实了巴特勒理论可以用于旅游地发展的分析与预测。如贡萨尔维斯和阿瓜斯利用三阶多元回归方程,结合葡萄牙的阿尔加维省旅游业的发展数据,证实了巴特勒模型的正确性[41]。伦德托普(Lundtorp,2001)及我国学者吴江等发现作为描述事物生长方程的Logistic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的“S”型曲线[42,43]。张骁明等对Logistic曲线模型和Compertz模型比较后,发现Logistic曲线模型在我国省级旅游地的发展中,能较好地拟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而Compertz模型则比较适合研究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的发展[44]。沈苏彦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发现50年内的时间尺度下,系统稳定发展时旅游地发展规律符合巴特勒模型[45]。
有关理论真伪的争议渐微,但是有一点质疑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即是否如巴特勒最初在文中断定,此后也一直坚持的那样,所有旅游地最终一定会走向衰退[2,6]。至于衰退的原因,有4种观点:第一,旅游地发展超过了其承载力水平,自然、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旅游地走向衰退[2];第二,旅游地衰退是由于对潜在市场开发不利,无法继续保持其吸引力;第三,旅游地技术革新不利,旅游地因老化而退出市场;第四,无法保持良好的竞争力,旅游地被新兴旅游地超越[6]。但无论有关衰退的影响因子为何,有关旅游地是否一定走向衰退的质疑从未消退。笔者认为,尽管现在的确有很多旅游地出现了衰退,也依然无法对“衰退必然论”给出充分的证据。但巴特勒的这一论断有其价值和意义,即使不完全正确,也可以对旅游规划者和管理者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提醒决策者旅游地要追求合理而不是无度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46]。
2.3.2 模型的应用价值 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自提出以来,其应用价值的大小也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6,47]。许多学者指出其不但无法准确判断旅游地所处的具体阶段,更难以精确判断何时出现阶段拐点,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的分析功能不强。“S”型曲线模型是一个描述性模型,所以定量预测功能欠缺也是其一大弱点。而且由于旅游统计的滞后性,模型只能对旅游地演化进程进行一般性描述,分析、预测功能欠缺,对旅游规划与管理的指导价值不强。
因此,对于如何准确判断旅游地所处阶段及转折点,各国学者进行了积极尝试,在发掘模型的判别指标和预测指标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48],有更多学者则提出了预测部分阶段的指标和方法,如利用当地社区对旅游态度转变作为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转折的指标[49],或者利用旅游地利润、游客百分比的变化等[6]。我国学者也试图建立各种指标体系,精确判断旅游地究竟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一阶段。如许春晓提出了旅游地生命力指标法判定旅游地演进阶段[15];杨春宇等提出了旅游地阶段预测模型,即用游客量增长速度的“加速度”变化定量划分旅游地阶段,并利用相应数理统计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游客量预测[50],该方法不但可以判断阶段拐点,而且开发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的预测功能,较之前众多学者采用的数学模型更加符合旅游地发展的实际;杨振之等提出了旅游地发展时间、游客接待人数、年接待量及增长率、外来投资规模、社区居民态度及就业等八方面的因素,综合判断旅游地发展阶段[51];唐代剑提出了旅游地经济力的复合指标判断旅游地是否到达需要复兴的第二曲线拐点[52]。随着各国学者研究的深入,不断产生新的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及拐点的判断方法和手段。
同时,不断有学者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指导旅游地规划和发展。如我国著名旅游地理学者保继刚、吴必虎、陆林等分别探索了旅游地生命周期指导旅游规划实践的方法,唐代剑探索了延长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路径[52]。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提升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应用价值。而且,旅游地的发展空间有限,只有合理的发展,才能避免旅游地走向衰退,这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旅游地生命周期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旅游规划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53]。孙根年利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估危机对旅游影响程度的方法[54],进一步提升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价值。需要提及的是,近年来,欧洲南部一些旅游地出现游客量下滑,旅游收入减少,尽管企业和政府都加大了营销力度,结果仍然差强人意。由于这些地方经济对旅游业依赖较强,所以旅游业的衰退引起了强烈关注,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也受到了当地学者和旅游管理者的重视。
因此,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进,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考虑到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其在旅游地管理和规划实践的应用也会不断推进。当然,要想更加深入地发掘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理论价值,需要进一步探索模型的内部机制,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地理学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都将重点聚焦在研究推进旅游地演化的内在规律和影响机制上,这对提升旅游地演化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有着更积极意义[55]。
3 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系统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在称谓上“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更为严谨,但是可以用于指导旅游产品演化的研究;阶段划分上,巴特勒的六阶段分法推广程度最高,但是阿贾瓦尔的七阶段说更细致、完整,也更能体现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即巴特勒一再强调的,只有通过积极而恰当的人为干预,旅游地才有可能避免走向衰退阶段;在理论价值上,认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描述旅游地演化方向和路径的学说,虽然无法证实所有的旅游地最终必然进入衰退阶段,但是当前越来越多的旅游地步入衰退阶段这一事实,证实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存在的价值。同时,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应用于旅游规划和可持续发展中,而且随着各国学者的深入研究,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逐渐成为定性、定量分析和预测的重要理论,其重要的应用价值不断被发现和证实。因此,引入这一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我国旅游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是我国旅游研究和实践领域不容回避的任务。厘清概念和认识上的误区,对进一步推进理论在我国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旅游地生命周期产生于20世纪初期,成型于20世纪中后叶,而今的旅游发展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旅游业赖以生存的交通技术出现了根本性改变,廉价航空的普及,使得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格局出现了巨大改变。世界各国普遍富裕、文明的深入推进、休假制度和信息技术的革新都对旅游地的演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当前的宏微观背景下,旅游地演化将呈现什么样的新特征,旅游地演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因子发生了哪些改变,新社会、经济、文化、技术要素的影响有哪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会从哪些方面深化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并拓展其应用领域和应用价值?如何才能有效实现旅游目的地的复兴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所以探讨并完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内容,以发展的思路深入发掘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价值,对正确认识不同历史阶段的旅游地发展规律以及指导旅游地的开发和管理都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
[1] 保继刚,楚义芳,彭华.旅游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34.
[2] BUTLER R W.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J].Canadian Geography,1980(1):5-12.
[3] GIERET R N.How models are used to represent reality[J].Philosophy of Science,2004,71(12):742-745.
[4] 杨效忠,陆林.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人文地理,2004,19(5):5-10.
[5] BUTLER R W.The origins of 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A].BUTLER R W.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Vol.1):Applications and Modifications[C].England: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6.1-9.
[6] BUTLER R W.Tourism Area Life Cycle:Contemporary Tourism Review[M].Oxford:Goodfellow Publishers Limited,2011.1-30.
[7] GILBERT E W.The growth of inland and seaside health resorts in England[J].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1939(55):16-35.
[8] CHRISTALLER W.Some considerations of tourism location in Europe:The peripheral regions-underdeveloped countries-recreational areas[J].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Papers,1963,12(4):103-105.
[9] 徐致云,陆林.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进展[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29(6):599-603.
[10] LUNDGREN J O.Geographic concep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earch in Canada[J].Geojournal,1984(9):17-25.
[11] RAYMOND V.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5):190-207.
[12] 杨森林.“旅游产品生命周期论”质疑[J].旅游学刊,1996(1):45-48.
[13] 张立生.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主要争议辨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29(1):96-100.
[14] 覃江华.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综述[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23(3):214-216.
[15] RAVENSCROFT N,HADJIHAMBI I.The implications of Lamarckian theory for the TALC model[A].BUTLER R W.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Vol.2)[C].Bristol: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6.163-250.
[16] BRENT.RITCHIE J R,GEOFFREY I C.The competitive destination:A sustainable tourism perspective[J].Tourism Management,2000(21):1-7.
[17] SAGAR S.The tourism area"life cycle":A clarifica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38):1178-1187.
[18] 许春晓.“旅游产品生命周期论”的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1997,12(5):4-47.
[19] 余书炜.“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综论——兼与杨森林商榷[J].旅游学刊,1997,12(1):32-37.
[20] 阎友兵.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辨析[J].旅游学刊,2001,16(6):31-33.
[21] BUTLER R W.The resort cycle two decades on[A].FAULKNER B,LAWS E,MOSCARDO G.Tourism in the 21﹟Century:Reflections on Experience[M].London:Cassell,2000.284-299.
[22] BUTLER R W.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Vol.1):Applications and Modifications[C].Cleveland: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6.13-26.
[23] ZYGMUNT K,ADAM S.A brief outline of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Richard W.Butler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earch[J].Folia Touristic,2011:62-66.
[24] AGARWAL S,SHAW G.Managing Coastal Tourism Resorts A Global Perspective[M].Clevedon·Buffolo·Toronto: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7.11-12.
[25] NORONHA R.Review of the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on Tourism[R].New York:World Bank,1976.
[26] PLOG S.Why destination areas rise and fall in popularity[J].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2001,6(42):13-24.
[27] GETZ D.Tourism planning and destination life cycl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2,19(4):752-770.
[28] COOPER C,FLETEHER J,GILBERTAND D,et al.Tourism Principles and Practice[M].London:Pitman Publishing,1993.20-48.
[29] 陆林.山岳型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安徽黄山、九华山实证分析[J].地理科学,1997,17(1):63-69.
[30] HOVINEN G R.Visitor cycles:Outlook for tourism in Lancaster County[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2,9(4):565-583.
[31] HOVIVEN G R.Revisiting the destination lifecycle model[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5):209-230.
[32] ANDRIOTIS K.The tourism life cycle:An overview of the Cretan case.http://tour.teipat.gr/Files/Synedrio/Conference%20Articles/Andriotis_paper%5B1%5D.pdf.2013-12-30.
[33] 杨效忠,陆林.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产品结构演变关系初步研究——以普陀山为例[J].地理科学,2004(4):117-122.
[34] AGARWAL S.Coastal resort restructuring and the TALC[A].BUTLER R W.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C].Clevedon.UK: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6.201-218.
[35] PRIESTLEY G,MUNDET L.The post-stagnation phase of the resort cycl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8,25(1):85-111.
[36] BAUM T G.Tasking the exit route:Extending 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model[J].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1998,1(2):167-175.
[37] LEGIEWSKI R M.The application of the TALC model:A lit-erature survey[A].BUTLER R W.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Vol.1):Applications and Modification[C].Clevedon: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6.27-50.
[38] GARY L.Life cycles,stages and tourism history the Catalonia(Spain)experienc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38):651-671.
[39] 丁健,保继刚.特类喀斯特洞穴旅游生命周期探讨——以云南建水燕子洞为例[J].中国岩溶,2000,19(3):294-289.
[40] ZHONG L S,DENG J Y,XIANG B H.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tourism area life-cycle model: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 National Forest Park,China[J].Tourism Management,2007,10(10):841-856.
[41] DA C G,RONQUEÁ.The concept of the life cycle:An application to the tourist product[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97,36(9):12-21.
[42] LUNDTORP S,WANHILL S.The resort lifecycle theory:Generating processes and estima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28(4):947-964.
[43] 吴江,黄震方.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模拟的初步研究——Logistic曲线模型方法的应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5):91-94.
[44] 张骁明,薛丹.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数学模型比较研究[J].旅游科学,2009(4):6-12.
[45] 沈苏彦.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旅游地演化规律探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27(10):195-201.
[46] JARKKO S.Traditions of sustainability in tourism studie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6,6(33):1121-1140.
[47] HAYWOOD K M.Can the tourist-area life cycle be made operational?[J].Tourism Management,1986,9(7):154-167.
[48] BERRY T.The predictive potential of the TALC model[A].BUTLER R W.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Vol.2):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C].Clevedon: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6.254-280.
[49] DIEDRICH A,GARCIA B E.Local perceptions of tourism as indicators of destination decline[J].Tourism Management,2009,30:512-521.
[50] 杨春宇.旅游地阶段预测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J].资源科学,2009,31(6):1015-1021.
[51] 杨振之.试论延长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模式[J].人文地理,2003,18(6):44-47.
[52] 唐代剑.旅游地复兴的第二曲线理论及其路径[J].经济地理,2009,29(5):840-845.
[53] BUTLER R W.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model[A].BUTLER R W.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Vol.1):Applications and Modification[C].Clevedon: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6.1-385.
[54] 孙根年.论旅游危机的生命周期与后评价研究[J].人文地理,2008,99(1):7-12.
[55] 邵晓兰,高峻.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现状和展望[J].旅游学刊,2006,21(6):7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