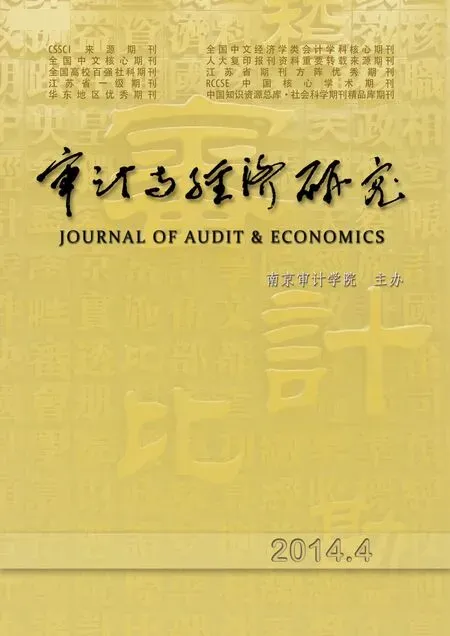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干预与控制权转移绩效
邓可斌,李智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财经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一、 引言
中国式分权改革既有效刺激了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区域间对资本的恶性竞争。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去干预属地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行为,以期使得资本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更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自1993年深宝安收购上海延中的我国第一起控制权转移事件发生以来,控制权转移背后的地方政府之手就经常如影随形。分权改革背景下的地方政府之手是否扭曲了控制权转移绩效?这正是本文关心的主要问题。
理论上而言,在完全竞争经济环境的有效资本市场中,控制权转移能够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实现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但是在我国企业的实际操作中,企业在控制权转移后绩效没有明显提升的现实例子时有发生。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控制权市场仍处于成长阶段,因而控制权转移绩效的体现可能不是太明朗。另一方面原因则可能在于,中国式分权改革引致的地方政府对企业控制权转移干预过度,从而使得控制权转移缺乏绩效。两种因素何者更为重要仍未有充分的经验证据。目前能够直接证实政府干预对控制权转移绩效影响作用的文献仍不多见。尽管有研究证明,不同级别政府控制的企业控制权转移绩效存在显著差别,级别越低政府控制的企业控制权转移绩效越低[1]。但控股企业的政府级别越高,并不必然代表其在具体的企业控制权转移过程中对企业的干预就强[注]就地方政府而言,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和政府业绩考核都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对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行为,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关注。但是,地方政府能否对属地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行为进行有效干预,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水平,而未必是上市公司的股东性质。换言之,在一个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很强的地区,即使是民营企业的控制权转移,也可能受到很强的政府干预;而在一个市场经济机制相对完善的地区,即使是国有控股企业的控制权转移,可能受到的政府干预度也不是太强。。在中国式分权改革的宏观背景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水平实质与其对当地经济的干预水平紧密联系,而不仅仅是与股东性质有关。因此,在考察控制权转移绩效时,加入对中国式分权改革及其引致的地方政府干预行为这一宏观背景因素,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 文献回顾
(一) 控制权转移绩效
Manne认为当企业出现严重的代理问题,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之一的控制权市场则可以弥补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缺陷,有效地减轻代理问题[2]。代理问题严重的企业很有可能面临绩效低下的困境,此时外部潜在竞价者便会受到吸引,从而对代理问题严重的企业进行收购,然后通过调整组织结构、优化管理模式、更换高管等手段减轻代理问题的影响,改善企业绩效。控制权市场的存在是约束管理者行为的有效手段,控制权转移后企业绩效会得到提升,这种绩效提升来源于代理问题的弱化。
在采用经营现金流为主要财务绩效指标的国外文献中,普遍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的长期绩效在控制权转移后得到提升。Kaplan对坎普收购联合百货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控制权转移后2年内企业绩效显著提升[3]。Healy等以1979—1984年美国最大规模的50例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事后资产管理能力的提升是企业绩效显著提高的原因[4]。Smith对1977—1986年发生管理层收购的58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后认为,事后绩效的改善源于管理层得到激励。而采用资产收益率为主要财务绩效指标的国外研究则出现较多相反的结论[5]。Denis和Kruse对并购活跃时期(1985—1988年)和并购非活跃时期(1989—1992年)的研究发现,目标企业绩效在事后3年内显著下降[6]。Ravenscraft和Scherer使用联邦交易委员会数据库的信息,运用变化模型研究了1950—1977年471家公司事后的绩效变化,结果显示事后目标企业的ROA比相同行业其他企业显著低1%至2%[7]。
我国控制权市场形成时间较晚,资本市场制度建设非常缺失,控制权市场的作用非常不稳定,因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常常由于样本不同而得出迥异的结论。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控制权转移能够取得很好的绩效。比如,朱宝宪和王怡凯以1998年发生的67例控股股权转让事件为样本,研究转移前2年到后3年目标企业的绩效变化情况,发现事后目标公司的ROE高出行业平均水平56%[8]。张新以ROA、EPS和CROE为指标,研究企业在控制权转移前后各3年的绩效变化情况,结果显示事后企业绩效显著改善[9]。白云霞和吴联生的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10]。徐向艺和王俊韡以2004—2006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109例事件为样本,研究事前事后各3年的绩效变化情况,结果发现目标公司出现显著的财富效应[11]。陈琳、魏林晚和乔志林对2006—2008年发生控制权转移企业事前1年到事后3年的绩效进行分析,发现绩效改善尽管存在滞后性,但企业绩效会有显著提升[12]。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发现控制权转移后企业长期绩效没有得到显著改善。比如,陆国庆以1999年在上交所发生第一大股东变更的221家公司为样本,以ROE为指标,考察转移前1年至当年企业绩效的变化,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变更后企业ROE降低18%[13]。冯根福和吴林江以1995—1998年发生并购的20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CROA、ROA、EPS、ROE构造综合绩效指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绩效从转移后第2年开始逐渐下降[14]。王会芳以1999—2001年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第一大股东变更没有改善公司绩效,反而使上市公司的平均CROE逐渐降低,甚至低于行业平均值[15]。宋建波和王晓玲研究2003—2005年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事前1年和事后3年的绩效变化,结果发现企业绩效在事后1年上升,但是随后逐渐下降[16]。张媛春和邹东海对2002—2005年的样本进行研究后则认为,控股股东更换不能有效提升企业绩效[17]。高勇强、熊伟和杨斌则发现,控制权转移后企业绩效不仅没有显著改善而是逐渐恶化[18]。
(二) 政府干预与企业绩效
众多文献使用国有股控股股东背景、董事会成员的政治关联度等微观指标研究政府干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得出的结论较为统一,即政府干预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罗党论和唐清泉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大、产权保护制度欠缺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等因素导致我国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且会对民营企业的绩效产生不良影响[19]。陈玉罡等发现政府控制会降低企业价值,且基层政府对于企业价值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20]。宋献中和周昌仕则认为政府“拉郎配”的并购活动不能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21]。田满文的研究发现并购可以促进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是政府干预会对此造成负面影响[22]。由上可知,在微观层面的政府直接干预,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然而,已有研究仍未提供较充分的,关于地方政府经济干预与控制权绩效关系的直接证据。而且,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改革与微观企业控制权转移的政府干预间的关系,亦缺乏实证与逻辑分析。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控制权转移理论
与控制权转移有关的理论成果包括协同效应理论、效率理论、管理主义理论、垄断理论和多元化经营理论等。其中直接关注控制权转移活动如何作用于企业绩效的理论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是控制权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控制权转移活动是企业外部治理的一种手段,能够弱化企业代理问题从而改善企业绩效。第二种是基于体制因素主导下的价值转移与再分配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我国各级政府、资本市场监管机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因素会促使发生本不应发生的控制权转移活动。上述控制权转移活动的本质只是利益的再分配,不会创造额外的价值。以上两种理论的区别实质在于对我国控制权市场成长阶段的判断,如果控制权市场较发达,控制权转移将显著改善企业绩效;如果控制权市场仍有待成长,控制权转移将无助于提升企业绩效。我们根据第一种理论提出研究假设1-1,然后根据第二种理论提出备择假设1-2。
研究假设1-1:相对控制权转移前,控制权转移后目标上市公司的长期绩效得到显著提升。
备择假设1-2:相对控制权转移前,控制权转移后目标上市公司的长期绩效未能得到显著提升。
(二)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干预的关系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财政分权改革极大地改变了我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传统财政分权不同,我国财政分权的本质是经济分权与垂直政治治理体制的结合。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这种“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特殊性在给予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激励的同时,还实现了我国近十几年来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究其微观原因,Qian和Roland认为我国该时期经济增长的原因是财政分权后地区竞争程度加剧,导致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硬化[23]。周黎安则认为原因在于各地地方政府比拼,形成了不断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政治锦标赛”[1]。上述前一种观点强调地方政府干预对于企业的救助是经济无效率的,而后一种观点则强调地方政府干预对于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上述两种说法在解释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财政分权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起到的促进作用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都肯定了财政分权对于各地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
我国财政分权的特点是经济上分权与政治上集权的并存。经济分权使地方政府在管理地方经济上更具独立性,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能够掌握并管理地区的经济剩余的能力也越大。而政治集权的存在则使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考核密切相关。为了获得政治晋升的机会,地方政府官员在追求自身地区经济剩余的同时,也需要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完成各项社会性任务或达成若干政治性目标。虽然与分税制改革实施的初期相比,如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要求包含了GDP以外的更多内容,但围绕GDP而展开的锦标赛式竞争仍是政府的关键任务,因而地方政府有充足的动力在能力范围内进行大量的政府干预活动,以促使政绩项目实现。
(三)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干预与控制权转移绩效
经济个体活动的独立性是控制权市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假设,也是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但中国式分权改革下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有着充足的动力源泉,使得我国企业活动中始终伴随着政府干预,在控制权转移活动中也是如此。回顾我国控制权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是并购活动的低迷时期,政府极力限制控制权转移的发生。直到1997年,我国政府才开始逐步放宽对控制权转移活动的若干限制,使得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事件数量相比20世纪90年代大大增加。由于地方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既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体现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地方政府形象的重要载体。地方政府有动机通过干预当地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从而更好地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完成中央下派的社会性或政治性任务,这一动机或可理解为“地方法团主义”。虽然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成本比非国有企业低,地方政府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更倾向于进行地方国有企业的干预。但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非国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地方非国有企业在地方财政收支中所占的平均比重也逐渐上升。此外,地方非国有制企业在地方政府完成中央下派的社会性或政治性任务时起到的作用远比国有企业大,如就业岗位的提供。因此,地方政府为了谋求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促进地方社会性或政治性任务的达成,事实上对包括非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地方企业都存在着适时干预的动机。
综上所述,财政分权制度及由此引发的地方政府经济干预动机,理论上会对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发生的控制权转移活动,由于当地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较高,其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可能会更难得以发挥。地方政府以满足政策需要和寻求政治晋升为动机,对地方企业的控制权转移活动进行干预。如上文所述,众多文献都支持政府干预会负面影响企业绩效的观点。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2-1和研究假设3-1,并相应提出备择假设2-2和备择假设3-2。
研究假设2-1:控制权转移时企业所属地区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控制权转移绩效提升的程度越小。
备择假设2-2:控制权转移时企业所属地区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控制权转移绩效提升的程度越大。
研究假设3-1:控制权转移时企业所属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控制权转移绩效提升的程度越小。
备择假设3-2:控制权转移时企业所属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控制权转移绩效提升的程度越大。
四、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市场逐步形成于2003年。已有关于企业控制权转移长期绩效变化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选取发生控制权转移的样本是介乎于2002—2006年之间,对于以2006年以后发生控制权转移的样本研究则比较缺乏。因此本文以2005—2011年为研究区间,选取2006—2008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控制权转移(第一大股东变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注]这是因为在计量回归中,有些变量需要滞后一期,且我们要考察控制权转移后三年内的绩效变化。。本文选择这一期间的样本是为了尽量减少因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变更、股权分置改革以及财政收支科目变化产生的额外影响,并且增加样本在研究区间内各年数据的可比性。
本文对初选样本经过以下常规性调整:(1)剔除属于证监会行业分类中金融、保险类行业的样本;(2)剔除同时发行A股以外其他类型股份的样本;(3)剔除研究区间发生过不止一次控制权转移活动的样本;(4)剔除控制权转移活动最终终止实施的样本;(5)剔除研究区间中发生退市的样本;(6)剔除部分信息缺少或异常的样本。本文之所以没有剔除发生控制权转移的目标ST公司,因为在考察企业控制权转移绩效时ST公司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且在所有发生控制权转移目标企业中占据较大的比例。本文最终得到的样本数量为135个。
各项数据中,上市公司财务绩效指标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股权转让数据来源于RESSET数据库,财政分权数据来源于2006—2011年《中国财政年鉴》,政府干预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
(二) 控制权转移绩效的衡量指标
研究控制权转移企业绩效变化的方法包括事件研究法和财务指标法两种。由于我国的股票市场存在着很多噪音信息,因此运用事件研究法容易产生准确性不强的问题。而我国上市公司的报表中具备较强的信息含量,尽管会计信息会受到一定的人为操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真实信息会重新表现在会计报表中。因此,与众多已有文献类似,本文选择以财务指标法进行研究。
财务指标法相较事件研究法,虽然准确性较好,但为克服选择不同财务指标导致研究结论随指标变化而不一致的问题,本文采用多个财务指标构建综合绩效指标体系。已有研究中关于绩效指标的选取差异较大:冯根福和吴林江选择了总资产净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总资产周转率4个指标;而宋建波和王晓玲则将选取的指标增加到8个,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和成长能力共4个方面的绩效水平[14,16]。相对而言,王化成构造的综合指标体系较为全面,共选取了12个指标全面衡量企业[注]包括盈利能力(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主营业务利润率)、成长能力(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偿债能力(现金负债率和债务资产比率)和资产周转能力(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的综合绩效水平[26]。

表1 控制权转移企业绩效综合指标体系
注: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2005—2011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相关数据。
因此,本文主要参考王化成的指标选取方法,但在具体处理时,我们把每个方面的指标处理为不超过两个指标,让各方面的指标数量更为均衡。在选择盈利能力指标时,我们将净利润和营业利润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重要指标,它们分别代表了企业总体的盈利能力和企业持续的盈利能力。此外,我们还加入国外学者经常用到的现金流指标。最终本文选取可衡量企业盈利能力、发展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以及现金流能力5个方面共8个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综合绩效水平。具体如表1所示。
由于不管样本空间多么大,行业差异这一因素必定会影响到企业绩效测量的准确性。因此,本文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一级行业分类对本文所选的135个样本按照所属行业进行划分,并将样本各年相应绩效指标分别减去该样本所属行业该年度的平均绩效指标,从而消除行业差异的影响。
为了便于比较控制权转移前后目标上市公司的绩效变动,本文亦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上述8个经行业调整的绩效指标进行简化,计算出每个因子的得分,以因子方差贡献率与因子得分的乘积构造综合绩效得分模型,最终将8个绩效指标转化成1个综合绩效指标。由于对衡量企业绩效好坏方向不同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的处理会造成一定影响,本文在对所选取的8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前需要保持每个指标在衡量企业绩效的同向性。在这8个指标中,除债务资产率之外的其他指标在衡量企业绩效时都是同向的,即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企业绩效越好。因此,本文有必要对衡量企业偿债能力的债务资产率这一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由于债务资产率的指标数据全部介于0到1之间,本文的正向化处理是用1减去每一个债务资产率的原始数据,从而得到股东权益比率这一替代指标后再进行因子分析。本文以因子总累积贡献率大于90%为标准,按下列函数形式构建综合绩效得分模型:
ZFi=ai1Fi1+ai2Fi2+……+ai8Fi8
上式中,ZFi表示第i个样本的综合绩效得分,aij表示第i个样本第j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Fij表示第i个公司第j个因子的得分。

表2 KMO和Bartlett检验
本文经KMO检验发现,总体样本的KMO值超过0.7,达到0.722。Bartlett球体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如表2所示),说明选取的8个绩效指标的相关性较大,适合运用在因子分析法中。
经因子分析法处理后发现,样本前6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9.39%,接近90%(如表3所示),因此可选择前6个因子作为衡量上市公司综合绩效的因子得分。

表3 解释的总方差
注:提取方法是主成份分析。
第一个因子代表营业利润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第二个因子代表总资产现金回收率和总资产净利润率,第三个因子代表股东权益比率,第四个因子代表应收账款周转率,第五个因子代表净资产增长率,第六个因子代表营业收入增长率(如表4所示)。
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最终得到上市公司综合绩效得分函数为:
ZFi=0.3295F1+0.1517F2+0.1240F3+0.1148F4+0.0923F5+0.0818F6

表4 旋转成份矩阵
注:提取方法是主成份分析法,旋转法是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
(三) 实证模型与变量解释
按照上述综合绩效得分函数可以计算出各年企业的综合绩效得分。本文选择的被解释变量是相应年份的企业综合绩效得分与控制权转移前一年的综合绩效得分之差,以ZF表示。
解释变量包括以下变量。
(1) 财政分权:本文分别参考陈硕和张光关于财政分权的两种不同计算方法得出的指标,符号分别为FD1和FD2[24,25]。FD1是从政府收入的角度衡量财政分权,FD2是从政府支出的角度衡量财政分权,两个指标的数值越大表示财政分权程度越高。
(2) 地方政府干预:地方政府干预是一种较难定量的隐蔽行为,尚未有统一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度量。本文参考了程仲鸣,夏新平和余明桂的做法,在衡量地方政府干预程度时选择采用了《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的“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得分[27]。由于这个得分是政府干预程度的反向指标,为了让该得分的大小与政府干预程度形成正向的关系,与财政分权这一变量的指标描述方向一致,以便更好地描述下文的实证结果,本文对原有得分逐一取其相反数,作为调整后的“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的得分并用于回归检验中,用GOV表示[注]该处理并不改变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只改变了系数的符号,保证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因此,本文用于衡量地方政府干预的指标数值越大表示政府干预企业的程度越高。
在对企业绩效指标进行行业调整以及因子分析简化后,有关行业特征的影响已经排除,而部分企业特征也被包含在综合绩效得分中,这样使得本文的控制变量选择相对简单。我们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盈余管理:目标上市公司不同年份之间线下项目占总资产的比例变化;(2)公司规模:目标上市公司不同年份之间总资产自然对数的变化;(3)转移年度:目标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发生年份的虚拟变化。变量的具体含义和度量方法如表5所示。其中,引入盈余管理变量的原因在于,有研究表明,新控股股东可能会在控制权转移后进行盈余管理活动,从而引起控制权转移绩效度量的偏差。

表5 变量含义
本文进行回归的方程如下所示:
ZF=a0+a1FD+a2EM+a3SIZE+a4Y2006+a5Y2007+ε
(1)
ZF=a0+a1GOV+a2EM+a3SIZE+a4Y2006+a5Y2007+ε
(2)
式(1)和式(2)分别检验研究假设2-1和研究假设2-2。两个假设成立要求a1显著为负。此外,两式中ε代表回归残差项。
五、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控制权转移目标上市公司综合绩效得分变化描述性统计

表6 控制权转移前后目标上市公司平均综合业绩得分
注:“年度”一栏中,数字0表示控制权转移当年,负数和正数分别表示控制权转移前后相应年份。“总体”表示2006年、2007年、2008年三年的所有样本。
根据综合绩效得分函数计算各个样本控制权转移前1年到控制权转移后3年共5年内上市公司的综合绩效得分,得到的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从总体样本上来看,与控制权转移前1年的综合绩效得分相比,控制权转移后第1年的综合绩效得分多数有一定提升,个别有所下降。但随后第2年和第3年综合绩效得分均开始逐渐地改善,初步证明了控制权转移有利于改善目标上市公司的绩效。也即表6的结果基本支持了研究假设1-1,而拒绝了备择假设1-2。这说明,我国控制权市场已经能够对企业绩效的改善,发挥出较为明显的作用。
接着,我们按照样本对应财政分权程度的高低将样本平均划分成3份,然后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法对财政分权程度差异与控制权转移绩效的关系进行描述性统计,具体方法为:考察目标上市公司综合绩效得分在控制权转移后各年与控制权转移前1年的差异,以及控制权转移后各年与前1年的差异,检验结果如下页表7所示。
表7中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控制权转移后第1年、第2年和第3年与控制权转移前1年相比,总体样本的综合绩效得分都得到显著提升,均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控制权转移后第3年与第2年相比,样本的综合绩效得分也得到显著提升,在0.05水平下显著。目标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第2年绩效与第1年相比绩效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而第3年与第2年相比绩效有显著改善,这可能是因为控制权转移后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整合活动,如资产融合、人员设置、管理模式调整等,然后才可以实现企业绩效的提高。总体而言,这一结果同样支持了研究假设1-1。本文将样本按照对应财政分权程度的高低进行划分后再进行检验发现,样本对应财政分权程度越低,其绩效在控制权转移后得到改善的结果越显著,这一结果初步证明财政分权会降低控制权转移后企业绩效的提升幅度,支持了研究假设2-1。

表7 控制权转移对目标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的配对样本T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0.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绩效”一栏中,下标数字0表示控制权转移当年,负数和正数分别表示控制权转移前后相应年份。(下页表8相同)
我们还进一步按地方政府干预指标对样本进行分组,重复表7的描述性检验,结果与表7基本一致。这说明研究假设3-1也成立。为节约篇幅,我们略去这一比较结果。
(二) 地方政府干预与控制权转移绩效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如前文所述,实质上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和地方政府干预密不可分,经Pearson相关性检验发现,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干预指标的确存在极高的关联度,相关性系数高达0.783。
为了避免将财政分权和政府干预同时作为变量进行回归的共线性问题,本文以控制权转移后各年(1—3年)目标上市公司综合绩效得分与控制权转移前1年的综合绩效得分之差为被解释变量,以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干预指标分别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页表8所示。
从表8结果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干预的变量系数均为负,系数符号与符号预期一致。以财政分权为自变量的回归中,系数的t检验至少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测试。而以地方政府干预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中,除了以控制权转移后2年与控制权转移前1年的综合绩效得分为因变量的情况中,系数是在接近0.1水平附近显著外,其余系数至少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水平测试。这说明财政分权或地方政府干预对于目标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各年与控制权转移前1年的综合绩效得分之差有反向的影响,即目标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时对应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干预的程度越高,事后上市公司的综合绩效得分与事前相比得到提升的幅度越小。我们的结果充分支持了研究假设2-1和研究假设3-1,而拒绝了备择假设2-2和3-2。同时,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干预指标在控制权转移后3年内都对目标上市公司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反向影响,表明控制权转移当年的财政分权或地方政府干预降低目标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绩效的作用时间较长[注]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选取另外一种计算财政分权程度的方法(支出法),以FD2作为自变量,再次考察财政分权程度对目标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综合绩效得分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一致。因篇幅有限略去此处结果。。

表8 财政分权、政府干预与目标上市公司综合绩效得分变化回归分析结果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6—200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控制权转移的135个目标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中国式分权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干预因素对企业控制权转移绩效的作用。在控制了行业特征、企业特征、时间及盈余管理等因素后,本文发现:(1)与控制权转移前1年的综合绩效得分相比,目标上市公司的综合绩效得分在控制权转移后3年内都有显著的提高;(2)控制权转移当年的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对于目标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后3年内的综合绩效得分提升均有显著的反向作用。
以上实证结论肯定了我国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即控制权转移后企业绩效能够得到显著的提升,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经过多年的建设,企业已可以通过控制权转移来实现提升经营水平的目的。另外,我们的结论证实了政府之手在控制权转移事件中的扭曲作用。这说明,我国宏观上的分权式改革,与充分发挥微观企业主体的经营能动性并优化资本配置间仍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分权式改革遇到了明显的瓶颈,片面通过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权力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已不可取。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我国控制权转移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但改革的方向不应局限于资本市场相关制度的完善,而应将更多精力放在对地方政府以GDP和财政收入/支出权为核心的考核机制的改革上。政府干预对企业控制权转移绩效存在负面影响,会降低控制权市场效率,因此政府应该积极构建良好的控制权市场环境而非过度干预企业控制权转移活动,从而逐步完善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法律、规章建设,如产权监督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等。
参考文献:
[1]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2]Manne H G. Merger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5,73(2):110-120.
[3]Kaplan S N. Campeau’s acquisition of federated: value destroyed or value added[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1989,25(1):191-212.
[4]Healy P M, Krishna G P, Rchiard S R. Does corporate performance improve after merger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cs,1992,31(2):135-175.
[5]Smith A.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management buyou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1990,27(2):143-164.
[6]David J D, Kruse T A. Managerial disciplines and corporate restructing following performance declin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55(3):391-424.
[7]Ravenscraft D J, Scherer F M. Life after takeover[J].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87,36(2):147-156.
[8]朱宝宪,王怡凯.1998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实践的效应分析[J].经济研究,2002(11):20-26.
[9]张新.并购重组是否创造价值?——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3(6):20-29.
[10]白云霞,吴联生.国有控制权转移、终极控制人变更与公司业绩[J].金融研究,2008(6):130-143.
[11]徐向艺,王俊韡.控制权转移、股权结构与目标公司绩效——来自深、沪上市公司2001—2009的经验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1(8):89-98.
[12]陈琳,魏林晚,乔志林.控制权转移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解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7):10-15.
[13]陆国庆.中国上市公司不同资产重组类型的绩效比较:对1999年度沪市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00(6):20-24.
[14]冯根福,吴林江.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1(1):54-61.
[15]王会芳.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4(2):64-70.
[16]宋建波,王晓玲.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8(6):60-65.
[17]张媛春,邹东海.控股股东更换是否会提高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1):88-93.
[18]高勇强,熊伟,杨斌.控制权转移、资产重组与CEO更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当代经济管理,2013(2):24-31.
[19]罗党论,唐清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9(2):106-118.
[20]陈玉罡,莫夏君.后股权分置时期公司控制权及其私有收益之争[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4):104-112.
[21]宋献中,周昌仕.股权结构、大股东变更与收购公司竞争优势[J].财经科学,2007(5):32-40.
[22]田满文.政府干预、终极控制人变更与并购价值效应平均[J].财经科学,2012(6):18-25.
[23]Qian Yingyi, 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28(5):1143-1162.
[24]陈硕.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J].经济学(季刊),2010(7):1427-1446.
[25]张光.测量中国的财政分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6):48-61.
[26]王化成.企业财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7]程仲鸣,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J].管理世界,2008(9):3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