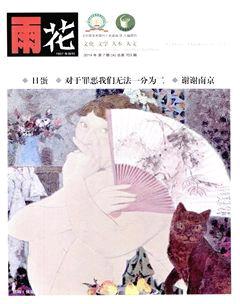纠结于出入仕的苏轼(外一篇)
◎孙青瑜
纠结于出入仕的苏轼(外一篇)
◎孙青瑜
东坡和《东坡易传》是一对矛盾存在,又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东坡虽是在生活中悟道的大哲,可他面对吉凶得丧之变,所提倡的与他的生存实际,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和矛盾。
纵读各家易传,唯有《东坡易传》让我读出了人味、炊烟味和诗味,只觉得东坡老汉不是在注《易》,着实在玩《易》,他不是用思维注《易》,而是在以情牵道,以情释“易”。他借《易经》向我们发泄他满腹的牢骚、不满、哀怨、愤恨……仿佛让我看到他正站在文字的深处“把酒问青天”,用他本真的性情把我带进了雷霆万钧的雨幕,体认乾道神化和坤道莫测。
熙宁九年的中秋之夜,苏轼狂饮达旦,酣然大醉,冲着密州上空的姣月仰脸便问: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
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很多人以为这是苏轼想念弟弟苏辙的亲情诗篇,实际上苏轼只是借弟弟想皇帝。苏轼作为一介儒生,和众多儒生一样,携着文化底色的人格分裂,纠结在“入世”和“归隐”的矛盾中,始终没有实现过来自心灵上的真正超然。身处密州,心念朝廷,乘醉徘徊于天上人间,最后还是舍不了人间的朝廷,不想还没有望到朝廷,一场大祸已于悄然向他伸出了魔掌——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乌台”大祸从天而降。苏轼在他提倡的“不知然而然”婴儿状中,被人诬陷进大狱。在这命悬一线的一百零三天里,苏轼日夜受审,心里肯定是排山倒海,越想越觉得“死生祸福”是命!但又说不明白,“自度会死狱中”,于是他便在绝望中写了一首相当于遗书的诗歌:“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世未了情”。这首诗真是写给弟弟苏辙的,可是在他生死一线之际,救他出囹圄的却不是他的弟弟,而是他的仇人王安石。
当时王安石正处在“众疑群谤”之中,日子也不好过。听说皇帝要斩苏轼,急匆匆地上了一折:“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若不是王安石及时搬出这一老例,各方人士再努力,恐怕也难免苏轼一死。可多年仇敌的王安石,为什么要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将他从鬼门关上捞回来?苏轼觉得这就是“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
由此可见,不管乌台诗案的幕后黑手是不是王安石,他内心深处并没有要害死苏轼的歹毒念头,所有的排斥、诬陷和打压,只是不想让苏轼在朝廷上的叫嚣妨碍自己改革罢了!正是因为有这个本性底子,所以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王安石将平日的芥蒂、隔阂、矛盾统统置于脑后,就像现在逢到大灾之年,国家领导人常说的那句话:“救人要紧”,从而造就了苏轼之后命的延续。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苏轼的入狱并没有给王安石的新法推行带来实际上的益处,因为反对他的保守派远非苏轼一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二程、张载等为首的宋代巨儒全是苏轼的死党,大有“死了我一个,还有后来者”的星星燎原之势。面对保守派的讨伐,再加上改革派内部四分五裂,王安石不得不在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隐退于江宁。
苏轼从监狱里放出来,踏上被贬黄州的羊肠小道,途经江宁时,特地去拜访了他的救命恩人。据说那一日两位“天涯沦落人”还同游了蒋山。游玩归来,二人扛着落日的余晖携手下山,落日将他们的面色映照得有些沉阴,四溢着日落西山的绝望底色。王安石或许想解释什么,突然觉得被握的手“紧”了一下,不由侧目打量,却没有从对方绝望的神情里看到什么,猜不出这用力的一握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感激,还是怀恨?
乌台诗案的余悸一直像不散的阴魂纠结在苏轼心里,在他与王安石携手游玩时,心里可能还在嘀咕:到底是谁在幕后指使?苏轼像是很明白。想到这儿,他向着朝廷靠拢的决心,竟百跌不死地跳动了一下。正是这不死的入世之心,注定着他要与携手之人续写缘性情而起、以气散而命终的战斗篇章。因为在黄州出炉的《东坡易传》,字里行间不见他提倡的“无心”,反倒处处是他“存心”的失落、阴影、余悸,不服、艾怨、激愤,不满、愤闷和无奈“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
也正是这乌台诗案九死一生的遭遇,让苏轼在不知然而然中证悟出的福兮祸兮,对自然本真的“性”和“情”“命”也有了直通“道”的深刻体认。
1085年,哲宗即位,苏轼复归朝廷。
要命的是,回到朝廷,苏轼不但没有念及王安石的救命之恩,反而又连连上了几道奏折攻击新政。等于说和司马光联手反整了王安石一把,成功废除了大多数“为害甚巨”的新法。
王安石看着自己多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于翌年四月,连病带气,于遗恨中忧愤逝去了。
常言说,气死人不偿命。苏轼从九死一生的乌台诗案里挣扎过来,气归气,却依然活得好好的,可王安石为什么就偏偏不经气,被活活气死了?是不是真应了他在《东坡易传》的那句诠释:“贞,正也。方其变化,各之于情,无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于命。此所以为贞也!”细想想,王安石可不就是用他的忠贞之性情与他的忠贞之道,最终达以性道相合,散发为气,返还太虚了吗?
如果时光倒流,王安石还会不会挺身救其出水火?王安石走了,命也没了,我们已无处求解。而没有了王安石,苏轼的个性同样难以立身朝廷,先被贬谪到惠州,随后又被赶到了海南岛。
当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孤独地踏进南国风光的那一瞬,心情一定是凝重的,自知东山再起的政治希望不大了,必须抓紧所剩不多的余生,来重修一下他的《东坡易传》了。
因为他太看重这部书了:“一生得意处,惟在‘三传’”。(三传是:《东坡易传》、《书传》和《论语传》,后两传不知去向,唯有《东坡易传》流转后世。)
可是让苏轼想不到的是,后人皆仰其诗词书画,唯小瞧其得意的“三传”,甚至带着鄙视将《东坡易传》定为杂学和异学。如果在天有灵,苏轼一定在为无人识透《东坡易传》“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的学术价值而着急。因为《东坡易传》读到书人合一处,能让人无心于己。情真处,如海边观潮,恍觉浪潮叠起,又如群龙翻腾,击起水花飞溅、升腾,虚变为“气”,环吾四周,不体而体,东坡之情与读者神会合一之际,文情、人情、人命、天命、人道与天道在诗学层面得以通达,这种通达远非诠释所得,只有深究进情旺质变处,才能神会到什么叫情道合一!而苏轼这种以情牵理、以情达道的写作“至”法,无形中也解决了中国古典文论中情理不通的尴尬。也就是说,读不到东坡的情盛虚变之气,就难说真的读懂了东坡、更难说真的读懂了《东坡易传》和其间至乐,更不会明白为什么苏轼要偏爱他的“三传”。
可实际上,东坡和《东坡易传》是一对矛盾存在,又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东坡虽是在生活中悟道的大哲,可他面对吉凶得丧之变,所提倡的与他的生存实际,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和矛盾。按他的说法,人面对一切吉凶之变,只有全然不放在心上,才能达到无伪之“至情”,才能无往而不乐。
可生活中的苏轼真的很快乐吗?真的做到了他提倡的“无心”和“无意于济”的高境了吗?
再看苏轼在儋州呆到第二年,在他完全料想不到的情况下,朝廷方面突然传来了圣旨,要他火速北归。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召唤,老人家太激动了,在跪拜接旨的那一刻才发现海南竟是这样的明亮和温暖,烈日如火悬在头顶,照得他眩晕又迷糊,想着赵佶稚嫩的脸膛,他必须立即起程辅佐。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他北归路上,竟不幸病逝于常州。而信奉生死轮回之说的苏老汉,在旁人忙着葬其肉体、料理后事时,他心向朝廷靠拢的不死灵魂却等不及了,不得不坚定而倔强地离开肉体,踏着北归之路:迈着苍老的腿脚,一步,两步,三步——向开封进发……用灵魂演绎着他的“不以命废志”的命题。
其实他并不孤独,因为在他身后,还有一帮壮志未酬的儒生正像扫帚星一般尾随着他,在心急火燎地向朝廷方面靠拢、靠拢……
父亲的目光
中国有不少词汇源于哲学术语,比如“变卦”、“说道”、“交错”……当然还有近几年在网络上传开的“八卦”等等,它们的原初义都具有丰富哲学内容,可是当这些理论术语进入日常语言后,就遭遇了所指义的萎缩或变异,“生气”一词就是一例。
荀子认为,水火、草木、禽兽和人都“有气”,《荀子·王制》中曰:“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而在《荀子·礼论》中,他又从供给性命运转的角度谈到了气的问题:“有血气之属必有知。”知就是知觉,也就是说万物体气的基础必须是血气运转着的活物。再如《淮南子·原道训》中的:“夫开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郭象在《庄子注》中所言的:“夫噫气者,岂有物哉?”等等,皆是在说只有活着才能感觉到气的存在,这大概才是“生气”一词根本义。比如滔滔流动着的黄河水,就会给人一种生命感,而池塘里的水,尤其是快要干涸之时,就会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息。
气本是中国古典哲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尤其是经过唐朝的孔颖达,再到宋朝的张载,气从原来的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中国哲学里的一个重要分支——气本论。而实际上,在气概念独立出来之前,中国哲人就一直在“宇宙生成”的阶段上寻绎、阐释气的转化问题,而“气”的性质大体无外乎:自然之气和供给性命运转的血气。而现在我们说生气时,基本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所指义,主要是指不高兴,意指因某件事闹情绪。不久前,父亲猝不及防地离开我和家人,我在极度的悲痛中思考了很多生死问题,比如情绪被“气”化就是其中一例。因为只有活着的人才会闹情绪生气,因为活人有“知”事、“知”物、“知”人的能力。而过世的人却因血断气散,化为太虚,丧失了“知”的能力,何谈生气一说?所以根据所指义萎缩了的日常语言来说,能不能生气,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生与死的差异。
比如我,由于常年坐在家中啃老,从而缺失一种应对社交场上的经验,再加上先天头脑拙笨,常会说些不得体的傻话冒犯别人,所以每逢与父亲一块赴席,若不小心说了不得体的话,我立即就能感觉到父亲斜射过来两道利光。久而久之,在人场里说话,我就养成了说一句话偷看父亲一眼的习惯,神情是怯懦的,像贼一样;如果父亲的目光没有投向我,说明我没说什么冒犯别人的言辞……
那时候父亲还有感知我存在的能力,现在父亲走了,再逢到我说错话的时候,远埋于故土下面的父亲也无力感知了,可我寻找父亲目光的习惯却依然如故。酒场上,我总会习惯于瞄上一位长者,说一句话,偷视他或她一眼,只可惜那人不是我的父亲,我的言语有没有修养、说不说半吊子的傻话与人家毫不相干,而与我血脉相连的父亲,却无法再用着急的目光管束和提醒我,更不会因此而着急和生气。所以父亲去世之后,我将他最严肃的一张照片放在电脑的桌面上,让父亲的一双大眼时时提醒着我注意自己的修养和言行。而每每与屏幕上的父亲对视时,我总是免不了泪如泉涌,因为无论我是上天还是入地,父亲都没有生气的能力了。虽然惹父亲
生气是不对的,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能惹父亲动气的人,多少幸福呀!
父亲的去世让我知道什么叫知死者生也,同时也让我知道了人世间没有人能够直接体悟死亡,历史上所有关于死亡的认识和思考都是活着的人通过他人之死旁悟得来的。如果说有真正的体悟者,如果有灵魂一说,那他一定是位过世者。只能旁悟才能感知的死亡,就像我们感知别人内在化的情绪一样,只能通过目光、表情、举动和言语等一系列被外在化了的内容旁悟得一个大概。比如父亲朝我投来两道利光:“噢,我一定是又说了没教养的话,惹父亲着急并生气了!”因为他的目光正严肃地盯着我——只可惜,那只是一张永远不会再动的相片——两道严肃的利光正从生气状到毫无生气状一点一点地僵化着,一点一点地僵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