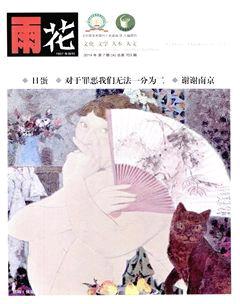卸下自己的枷锁——2013年读书笔记
◎ 杨光祖
台静农《中国文学史》
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乃未完稿,系根据他生前手稿整理出版。迫于高压,此书终于金元两朝。当年台湾白色恐怖,台先生不敢引鲁迅一语,但字里行间皆有鲁迅,论先秦、魏晋多承自先生。不过,台湾有台静农亦台湾一幸,他主持台大中文系多年,培养了大批优秀弟子。我有幸曾聆听其中两位演讲,无论人德,学养,皆令人钦服。一位是林文月,翻译《源氏物语》,谈及先生,几欲泪下。一位已忘却姓名,香港某大学教授,讲唐诗中颜色词,极好。
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极有个性,多有独见,他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谈起文学来,当是本行。书中关于陶渊明、李白两节,甚是喜欢,很有个人见解。我们大陆的文学史很全面,政治正确,但就是缺乏个性,也缺乏文学。读了让学生无法热爱文学。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不错,但相较之下,就有点江湖气了。
尤其谢灵运一节,台静农四页文字,已无人可及矣。刘大杰不如也,王瑶更勿论。不愧为迅翁早期入室弟子。
扬之水《先秦文学史》
购读扬之水《先秦文学史》,其关于《左传》一节文字,极好,读得齿颊生香,余味无穷。真无法想象,一个女工,得缘进入《读书》杂志,十年竟修成如此功夫?除开自己的天赋及勤奋,徐梵澄、金克木诸高人指点恐亦为重要因素。
木心《文学回忆录》
读木心《文学回忆录》,先读中国部分,真的好,我虽然也是中文科班出身,从事文学教研半辈子,但读来依然感觉大开眼界。后读外国部分,发觉人家依然是行家,绝不露怯。喜欢他的一句话:“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罢——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脸红,这不是骂我吗?
今天北京雪后劲风,也别有情趣。窝床上,续读木心《文学回忆录》,真是好,读一段,就舍不得读下去了,怕读完了空虚。人到中年,才体会到读书的乐趣,也不算晚吧?
孔子有颜回,是孔子的福分,颜回早死,却也是孔子的不幸。木心之有陈丹青,既是丹青的造化,也是木心的造化。最可怜的莫如陆九渊,临死之时,手指腹部,慨叹道,某有绝学在此,惜无人能承当耳。那真是一种大寂寞。读木心《文学回忆录》,幸福难以言说,既感慨丹青遇此良师,也羡慕木心能遇陈丹青这样的弟子。不过木心毕竟略有江湖气,胆子也大了点,一涉西方哲学,比如胡塞尔、萨特、海德格尔,皮毛之论太多,但自我感觉却极好。哲学说希腊话,可能有它的道理,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化,真还有难度,就如让一位西方人看王羲之《兰亭序》。
木心《文学回忆录》,厚厚的两大卷,50多万字,一言以蔽之,即:你要走向未来,你得走过现代艺术的洗礼。你再丰富的传统、知识、技巧,不经过现代艺术洗礼,你走不到哪里去。这也是木心的话,是他讲课快结束时的一句话。
《金瓶梅》
重读《金瓶梅》至第五回,真是上等文字,惊心动魄。张竹坡批点也是了得:“此回文字幽惨恶毒,真是一派地狱文字。夜深风雨,鬼火青荧,对之心绝欲死。我不忍批,不耐批,亦且不能批,却不知作者当日何以能细细的做出也。”当今没有如此佳作,也没有如许批评。呜呼。人有生而知之者,不信不行。天才,那是天生就的才,人力岂能奈何?热爱文学四十余年,越来越绝望,自己的才华太有限了。本就是一个泥鳅,你就是放到大海里,也不会养成一条鲸鱼。
读《金瓶梅》至第十回,真是绝佳文字,字字泪来字字血,还有无耻与淫荡。《红楼梦》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果然。想当年粗读过两次《金瓶梅》,未能读出人生二字来,可能更多关注了它的色与欲了。人过四十,进入秋天,心境明澈,再读此书,大师之作也。描写之精细,人情之练达,当今文坛无人能及矣。
《蒋碧薇回忆徐悲鸿》
读蒋碧薇回忆徐悲鸿,感觉到她的那种怨恨,人到晚年了,文字还那么充满戾气,当初何必私奔呢?看张爱玲晚年的《小团圆》,她最终原谅了胡兰成,也就是卸下自己的枷锁。张毕竟是张。
刘再复《双典批判》
读完了刘再复的《双典批判》,略有点失望。总想着去国20多年的他应该有所变化吧,或者进步吧?竟然没有多少,还是1980年代的那种激情,还有东拉西扯的几堆西方理论。有着浓厚的官文化色彩的刘再复,无论对于西方文化传统,还是中国文化传统,其实都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但他胆大,这是当代学人的共性。洋洋洒洒,几十册书都出版了,有学术专著,大多是散文。他的散文,真的让人失望透顶,只那册《师友纪事》,差点就读不完了,怎么那么让人酸倒牙?而红楼四书,《双典批判》,其实都没有任何新意,都是在王国维、鲁迅、胡适等前辈的基础上,敷衍成文而已,多了一些资料,添了一点西方理论,可是读完了,依然觉得没有前辈谈得好,谈得透。说到底,可以作为普及书,但不是严格的学术专著。其中,没有自己的血肉,没有自己的精神。对于《水浒传》的暴力,《三国演义》的权术,所谈只是常识而已,都没有深入研讨。暴力、权术、色情作为人类的文化现象,是没有断绝过的,它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与读者的关系,也是一个中西共有的问题。只是于中为烈而已。到当下的中国作家中不是还传人不断吗?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手稿本》
今日读《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手稿本》,鲁迅的文字峭拔,多冷峻,但在给二萧的书信里却有难得的温暖。我想可能与萧红颇有关系吧?但萧军的注释文字,却废话成堆,缺乏独立人格,鄙吝之气很盛。看来,他是不懂鲁迅的,当然也不懂萧红。此人一生未脱兵气、匪气,可怜。那些注释文字附在鲁迅书信后面,真有续貂之感。而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也极其不负责任,所用的纸张太次,影印的鲁迅书信很不清晰。鲁迅写信是很讲究信纸的,如果影印好一些,是极佳的艺术品。可惜现在弄得黑乎乎,连笔触都看不见,更休谈信笺颜色、图案了。
真正的好文字,都是用生命浇铸出来的,像萧红、张爱玲。
《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手稿本》
读《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手稿本》,感觉很不爽。首先是萧军的注释文字,啰嗦有所减弱,而无赖之相令人生厌。他在文字里一再嘲笑萧红的体弱、敏感,说:“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萧红是一个苦命人,一生没有在自己的丈夫那里得到尊重,还有爱,包括后来的花花公子端木蕻良。她说了:“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1942年,31岁的萧红病死了,她临死前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但又能如何?她遇人不淑,徒唤奈何?据说,她临死还有遗言,希望把她的骨灰带给上海许广平,附葬于鲁迅墓边,“于愿足矣。”但这又怎么可以呢?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把她以杰出作家视之,而给予足够尊重、爱护的人,只有鲁迅一人而已。读完萧红给萧军的书信,你就知道萧红的优秀、温暖、屈辱。萧军不懂萧红,嫉妒萧红之才,最后却还是因为萧红而被人记住,世事白云苍狗,大浪淘沙,由不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