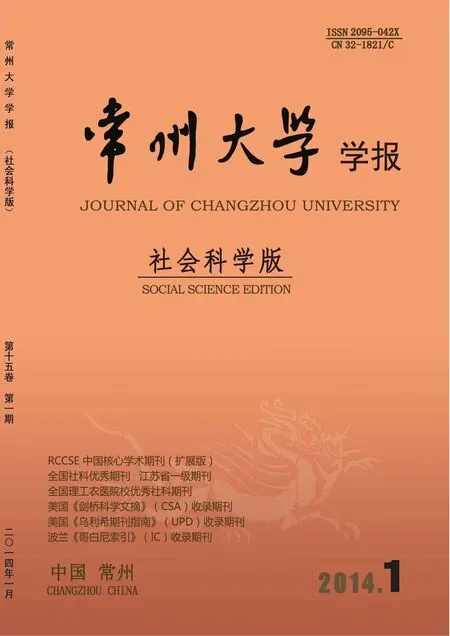试论中国古代的“审出多门”
张春梅,艾永明
(苏州大学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试论中国古代的“审出多门”
张春梅,艾永明
(苏州大学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审判是司法运行中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制度在运行中,由于审判权不能划一行使呈现出“审出多门”的怪状。文章认为中国古代“审出多门”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各不同机关及皇权的审判,并从限制各机关权力、行政兼理司法、加强皇权以及权力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几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反思当今司法需要走出“审出多门”的历史巢臼,汇入“审出一门”的时代潮流。借古鉴今,这对促进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加快现代法治建设有重要意义。
皇权至上;权力一体化;审出多门;司法独立
司法审判是法律运作过程中至为重要的环节,本文所讲司法审判主要是指中央司法机关的审判。中国古代专掌司法事宜的机关和官员,各朝均有史书、典籍记载。西周已有中央司法机关,秦汉魏晋时期中央和地方各司法机构设置从简单到复杂,至唐已颇为完备,到明清时期则发展至极致。各朝主管审判职能的机关从司寇到廷尉再到大理寺直至刑部,一目了然。[1]然而司法运行实践中果真能做到“审出一门”吗?答案是否定的。
一、审出多门之表现
(一)会审机关的审判
会审是中国古代对于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的审理方式之一。广而言之,指群体审议,即主审的司法官员与其他相关机构的非司法官员共同参加审理。“杂治”、“三司推事”、“三司使”、“三司会审”、“九卿圆审”、“热审”、“秋审”、“朝审”等等,皆为不同时期对会审的称呼。
秦汉时期遇有重大案件,廷尉须会同丞相、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共同审理,此即“杂治”。唐代对发生在京师的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司长官会同审理,称为“三司推事”,开创了后世“三法司”联合审判的先河。“三司使”是指对京师以外及地方的重大案件由三司的下属官员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寺评事前往审理的情形。另有清代的“会大法”、“会小法”①大体与唐代类似。会审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不仅种类多样且已成定制②。明代时定制,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机关组成三法司,会审重大案件;遇有特大案件,则由三法司会同各部尚书、通政史进行“九卿圆审”。“秋审”则由中央三法司长官加之九卿、詹事、科道、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中央各部长官共同参与,于每年秋后(八月上旬)定期举行。[2]如此会审之情形不一而足。
不难看出,在中央司法机构参与的审判中,重大案件皆为多机关参与,而不仅仅是赋予专门的司法审判机关和官员。汉代的丞相、唐宋时期的中书门下省长官、明清时期的内阁首辅、秋审中刑部以外的各部尚书及通政使,都在不同程度代行司法审判职能。如此之多的非专职司法机关和官员参与审判,行使司法审判职权,充分反映了审出多门的现象。
(二)特权机关的审判
元朝不同于以往王朝,突出维护蒙古族,特别是蒙古王公贵族的特权。故元朝建立后,撤销大理寺,将管理贵族事务的大宗正府,作为重要的中央司法审判机构。由蒙古贵族把持的大宗正府专门受理蒙古人、色目人,尤其是蒙古上层人士的诉讼案件。“凡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诱掠逃驱、轻重罪囚……悉掌之。”(《元史·百官志三》)宣政院为最高宗教审判机关,负责审理僧侣的狱讼。枢密院为元朝的最高军事机构,“掌处决军府之狱讼”(《元史·刑法志一》),即主管军政大事。
说起“法外”特务司法机关最饱受争议的当属明代的“厂”、“卫”司法。厂,包括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指皇帝亲卫军十二卫中的锦衣卫。厂卫制司法机构可以法外用刑直接行使审判权,并凌驾于三法司之上,不受普通司法机构和法律的约束。这是明代的独特现象。故有“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矣。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明史·刑法志三》特务机关主要处理政治案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成化年间,作为锦衣卫审讯机构之一的南镇抚司“职卑而权日重”。
清王朝设有专门机关理藩院负责对少数民族犯罪案件的审判。此外,还特设理事厅、理事通判、理事同知等特殊司法机构以专门维护旗人利益。内务府中的慎刑司和宗人府专门管理皇室以及皇室宗族事务。
从上可以看出,为了加强皇权,愈是王朝后期,特权机关的司法审判权限愈大,特权机关直接代行皇权凌驾于正常的司法审判机关和司法审判程序之上,令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因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轻罪重判、无罪冤判的案件大量增加。特权机关的审判是审出多门的另一例证。
(三)军事司法机关的审判
我国古代的法律乃是源自“刑起于兵”的军事征战时期,军队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基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把军队的建设放到治理国家的首要位置。对军队有关的诉讼各个朝代都异常重视。两宋之前,军队审判权归于中央司法机关,像唐代的司法体系并未设置专门的中央军事司法机构,而是由三大中央司法机构,分掌司法事务,互相配合、监督,军事司法权也包括在内。宋代开始在中央设枢密院,作为全国最高军政机关,与中书、门下并列为中央最高机关之一,是专门的军事司法机构。“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宋史·职官志二》)
枢密院不仅负责复核审定军人死、流罪案,也主管复审军官的奏案,还可直接开庭审裁军事案件。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诏:“自来将帅行军,诸军于军前犯罪,或违节制不用命,自合于军前处置外,若军马已还行在,诸军犯罪至死,申枢密院取旨断遣。”(《宋会要辑稿·刑法》)宋代的军事司法,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
明代的中央军事司法机构为五军都督府,和兵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机关,二者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明代对军人实行专属管辖,明律明确规定:“凡军官犯罪,从本衙门开具事由,申呈五军都督府,奏闻请旨取问,……”(《大明律·名例》)即使是一般的军人犯罪,也由军事机关处理。五军都督府在都督府中设有断事官,负责所管辖之军人的诉讼事宜以及司法行政事务。一般来说,都督府主管比较重大的军人案件和都督府内部军人的犯罪。
军事司法审判机关对于军事案件的专属管辖,分割了中央司法机关的审判权,因此对于军事案件的审判存在交叉重叠的关系,造成审出多门,司法混乱。
(四)监察机关的审判
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虽属于司法机构的范畴之中,但它却不是名正言顺的审判机关。有籍可查,监察机关“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明史·职官二》)“风宪之任,在肃纪纲,清吏治,非专理刑。”(《国朝典汇·按察司》)可知其职能主要是在“劾”,而非“理刑”和“审”。但两机关的交织存在又不可或缺:对于官吏的违法之事,往往由监察机关发现并纠举,再由审判机关进行审理;监察机关还行使对审判机关所下判决的监督权,以使判决合乎法律之情理。
从法定程序讲,御史台设立之初是专门的监察、弹劾机关。然而监察机关在实际的运行中并没有达到预期设立的期望。唐朝伊始,御史台确不直接受理诉讼,但随着风闻奏事③在唐朝再度兴起,御史台不仅收受诉讼,还在台中自设监狱,与大理寺分庭抗审。御史台受命参与“诏狱”、制狱,《唐会要·御史台》记载“伏以台司推事,多是制狱,其中或有准敕,便须处分,要知法理。”“三司推事”和“三司受事”是御史台参与司法审判的主要方式,以至于御史既是监察官,又是“天子之法官”。御史台由单纯的监督司法到干预司法直至僭越司法,监察机关的司法审判职能日益强化,对后来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职能混淆、僭越的问题在各朝代都不乏实例,造成审出多门。
(五)皇权的审判
秦始皇南征北伐,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中国古代对“君权神授”思想的接受,无形中使得天子的地位处于各种权力的最顶端,皇帝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直接掌控司法大权。《宋史·刑法志》记载“凡御笔断案,不许诣尚书省述,如违,并以违御笔论。”所以,皇帝亲自参与或审判的案件无论是否公正,两造都只能接受,且是最终判决。
皇帝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中央和地方的刑事审判进行监督。对复核、审判、大赦等司法程序的行使,牢牢的将司法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致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出于上”。秦始皇 “专任刑罚,躬耕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东汉光武帝“常临朝听讼,躬决疑事”;(《晋书·刑法志》)明太祖“凡有大狱,当面讯,防构陷锻炼之弊。故其时重案多亲鞠,不委法司”(《明史·刑法二》),而死刑复奏制、大案奏裁制的不断强化都是皇帝至上于司法审判机关的突出表现。所以中国古代皇权大于法律,皇权高于司法审判权。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各时期与明朝大同小异。皇权专断司法使得刑事审判的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
二、审出多门之原因分析
(一)“审出多门”源于各机关权力相互制约
自秦以来,中央集权趋势日益加强,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维护皇权统治,一方面司法机关越来越健全,另一方面皇帝对司法的控制不断强化。各朝统治者将司法职能由几个平行部门分别执掌,以期达到相互配合并制约的目的。
唐朝中央常设的司法机关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唐六典·大理寺鸿胪》),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勾复、关禁之政令”(《唐六典·刑部尚书侍郎》),御史台是中央行政监察和司法监督机关,“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旧唐书·职官三》)。三机关分别行使审判、复核、监督的职责,这样的职能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使各部门、各机构之间权力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相互制衡作用明显。例如,对于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必须由三司会审或者九卿会审等形式进行,多家机关分工负责,共同审理作出判决。这种由多个机关分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设置,既可避免审判的独断擅行,又可集思广益,防止冤滥。
宋朝也是如此,由御史台、刑部、审刑院等司法监察机构对大理寺的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复核。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理寺作为独断审判官员的曲法枉断、拥权过重问题的发生,也加强了司法审判程序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这便与统治者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不谋而合。
中国古代统治者采用“杂治”“三司推事”“九卿会审”“秋审”等多机关共同审理的形式,这种运用精心设计司法机构和有效分配司法权力的做法,使得各个司法机构互相制约和监督,从而结出了审出多门之果。
(二)“审出多门”产于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
司法机关始终无法成为独立的司法体系,还与中国古代行政兼理司法的传统分不开。有学者指出:“我国古代有司法职能而无统一的司法体系。[3]。”这在各地方官府的表现最为典型,地方各州县长官受命于皇权,代表皇帝处理辖区内所有政务,因而司法审判只是众多行政职能之一。大而观之“行政兼理司法”的影子也投射在中央司法机构的审判环节中。“司寇”、“士”在当时即是军事首脑又是司法长官,拥有军事和司法双重权能。而汉代最高行政长官丞相涉足司法干预审判也是常事,及至以后各朝,行政长官决断司法实务都已司空见惯。
中国古代各种类型的会审都能找到行政官员的身影。比如,汉代时廷尉不能解决的疑案,需由丞相等中央高级行政官员讨论定案;唐时三省中的中书省、门下省作为行政部门反而成为审判某些案件的最高审级。明清时期,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对一切案件代行皇帝的终审权力。还有学者认为“古代会审制度是由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决定的,会审制度正是行政官员兼理司法事务的另类表现。[4]”诸如“三司会审”、“九卿会审”、“秋审”、“朝审”、“热审”等实则是包括中央所有机构高级官员的审判仪式。还有学者认为“除了专门的司法机构外,应该说,古代朝廷中主要职能部门的主管官员都可以称为司法官吏,都有参与司法审判的职权。[5]”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司法主体与行政主体身份合一以及行政长官往往成为司法审判的主体就不那么难理解了。
(三)“审出多门”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
中国古代皇帝集权,乾纲独断、大权独揽,皇权是唯一的终极的,它至高无上,不可怀疑,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然而,皇帝又不可能对天下万事亲自操办,这就必须建立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组织体系。不过,除了皇权之外,一切权力都是从皇权派生出来的权力,都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皇权。可是,这些从皇权派生出来的权力又天然地具有离心力。因此,这些权力机关或行使权力的官员既必不可少,又不被信任,必须予以监督制约。这是中国古代审出多门的根本原因。
唐代以后的司法机构设置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为了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有的朝代在普通司法机构之外另设特殊司法机构,还有的朝代另设出负责特殊事务的司法机构。如宋代设立专门机关审刑院及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元代有专管道教案件的道教所;专理宗教事务的宣政院;专审蒙古贵族案件的大宗正府以及掌管军事事务的枢密院等机构,建立了一整套蒙古贵族领衔的司法体系。清朝则有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司法机关和维护旗人利益的特殊司法机构。这些法外特殊司法机构及特权司法机构的出现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所有这些根本上都是为集权政治服务,都是为加强皇权服务。
(四)“审出多门”附于权力一体化制度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设计如此周密为何还会出现“审出多门”的现象?问题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权力一体化制度”④。在这一根本体制之下运行,司法审判必然无法独立行使。
权力一体化的政治体制的核心在于维护最高权力的至上地位,所有权力都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此最高权力。在此体制内,所有机关、部门及其所属具体权力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有了最高权力的皇权,就绝不容许再出现任何独立于它的权力,包括最应独立的审判权。任何权力的独立都被看成对皇权的挑战,都势必消弱甚至瓦解皇权,破坏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一体化制度,就有可能走向分权的道路。故而中国古代审判是皇权之下的多元审判、多门审判,不可能是专门审判机关的独立审判。
在此种体制下,必然会导致共同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其根本指向乃是为皇权服务,觊觎皇权的恩泽。同时,在这种体制之下,各机关及官员之间要达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几乎是不可能。“权力一体化之下的部门分工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权力制约作用,但就其宗旨和性质而言,这种分工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皇权统治的需要,是稳固政权的措施。如果说也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互相猜疑、监视的作用,既不是尊重审判权,也不是维护法律的权威,而是严防一家独大。”[6]因此,它的作用越大,皇权就越强,离审判独立就越远,法律就越没有权威。
在权力一体化制度下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其司法机关也好,行政机关也罢,最终都是隶属于皇帝,受皇权左右,司法审判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各朝代无一不是如此。所以审判独立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审出一门的历史必然
中国古代历经数千年,改朝换代,循环往复,既积累了宝贵的法制经验,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中国古代“审出多门”的问题既是客观存在,又非常值得研究。“审出多门”这一古代司法审判之怪状,是植根于中国古代权力一体化的专制体制,是这种体制的必然产物。所谓中央司法机构的“分权”只是一种职能的分工,一切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不存在司法独立,更无法实现审判的独立性,也无法树立审判的权威性。借古鉴今,这对促进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加快现代法治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只有走出“审出多门”的历史传统,真正做到“审出一门”,才是治愈顽疾的“良药”,才是通向法治的必由之路。
所谓“审出一门”,即是指审判独立,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独立作为一项重大的司法原则已为一切现代文明国家所普遍接受和遵行,已成为评判现代司法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一)“审出一门”有利于树立审判权威
中国古代司法机关相当程度上隶属于行政,并最终隶属于专制皇权,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导致司法不独立、审判出多门,因而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判权威性大打折扣当是意料之中。
现代司法强调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司法独立要求司法与立法、行政分立不受任何其他权力和个人干预。《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审判独立原则。如此良法当道的时代,为何现今仍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笔者认为,这与传统司法的负面影响不无关系。
中国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历史传统,孕育出独特的中国古代法律文明,“像权力本位、集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像特权法、等级法和伦理法等特质[7]。”这可以作为我国的特色引以为傲,也是固疾令我国司法举步维艰。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法律思想作用下,保持司法审判的中立性和裁判性甚为艰巨,故而牵绊到当代司法权威性的实现。
当今中国要树立起司法权威,真正达到司法独立,虽并非易事,但绝对有可能。首要任务是独立的司法审判体系的建立,将司法事务中的审判事务与行政事务进行明确区分,确保司法审判权摆脱行政权的干扰。其次,司法审判权要脱离行政权的“控制”获得解放,只从行动和制度两方面还不够,还需“解冻”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因此破除传统法律文化中消极不适的思想,树立起现代法治的意识,坚定审判独立的理念,为司法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提供思想保证,努力做到“审出一门”,建立公正、公开、民主、高效的审判制度,切实维护司法的权威。
(二)“审出一门”有利于实现审判专业化
古人将专职法司事务的官吏称为法官, “法官”一词最早出现在《商君书·定分》中,从此就多以“法官”作为司法官员的通称。在中国古代的审判中这些“法官”们虽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大案件最终决定权却往往不由他们掌控。从文章上篇的阐述中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不仅仅中央机关的专门司法机构能够行使司法职权,朝廷中主要职能部门的主管官员在当中也拥有不同程度的裁决作用,因而都可以成为司法官吏,拥有参与司法审判的职权。由此不难得出,中国古代法官群体的非专业化。如果无法保证审判人员科班出身、熟谙律条,何以对那些重大复杂案件做出专业和公允的决断?
“审出一门”实行司法独立,要求审判权划一行使,这正是实现审判专业化、法官专职化的前提,而司法部门和人员的专业化、精英化也是现代法制文明发展的普遍趋势。当今中国无论在地方还是中央,各级法院权责分明已然成为司法审判的专门机关,突破了中国古代“审出多门”的藩篱,朝着司法独立的方向迈进。然而在此进程中依然阻碍重重,法官的专业性和职业化群体尚未完全形成。法官这个角色存在一个从非职业化到职业化的发展过程,在现代社会,对于法官专职化的需求比之其他官员更为严格,这是大势所趋,必须予以保证。要使法官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活动成为一种令人尊重的职业,就必须净化法官队伍,提高法官的职业准入资格,确保法官职业的专业性与稳定性。
(三)“审出一门”有利于促进法治社会建设
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君权高于法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集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因而,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不可能产生和形成近代意义的审判独立精神和制度。当今意义上审判独立的概念源自清末的“西学东渐”并由此逐渐付诸实践。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和现代司法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治国理念。毫无疑问,这条道路曲折而漫长,需要积极探索大胆实践,这既需借鉴他山之石,也要汲取历史教训。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有这样精辟的论述:“因为,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情况。[8]”法治强调“法律至上”、“一断于法”法律始终高于权力,而人治则相反。因此法律是否至上,特别是权力的运行是否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是区分法治与人治的标志之一。
“审出一门”正是法治国家的表征之一,它摒弃以往立法、司法、行政、监察等多部门、多职能交叉重叠的混乱状态,明确要求司法权独立划一行使、审判唯法是从,确保审判结果更权威更专业。在已制定的成文法律面前,法律必须得到普遍的遵从,这便是法治的开端,也是建设法治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法治国家呼唤“审出一门”,“审出一门”也是法治国家的最好“招牌”。欲跻身于文明世界之林,就必须“审出一门”。
注释:
①“会小法”由承办的刑部清吏司长官召集,大理寺派寺丞或评事,都察院派御史参加共同审理,参加会审的非各机构的最高长官。于此相对“会大法”即是三法司各机构的最高长官。张晋藩.中国司法制度史[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395-396.
②《明会典》规定:“凡在外五年审录,……差刑部、大理寺官往南北直隶及十三布政司,会同巡按御史、三司官(指各省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审录。”也就是说,会审在明朝正式制度化,发展成为一系列会审制度,形成了九卿圆审、热审、朝审、大审等系列会审。清代会审制度达到顶峰,出现了三司会审、九卿会审、朝审和秋审等制度。
③所谓“风闻奏事”,就是举报人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不必拿出真凭实据,也不署名。
④“首先,就横向而言,国家所有权力(包括政治、经济、司法、军事、文化、教育等等)统统属于一个组织主体。中国古代权力传递以朝代更替为方式,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就是夺取了江山,夺取了天下一切的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然,国家所有的权力也就归为一个组织主体,或刘家、或李家、或赵家等等,其他组织主体不得染指。这种朝代更替下的权力传递是一种“打包”式的继受模式。其次,就纵向而言,实行中央集权,地方没有或几乎很少有自治性的权力。这种中央集权制是为了保证一切权力属于一个组织主体,所以根本上也是由“打包”式权力继受模式决定的。”艾永明.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利弊的理性分析[J].河北学刊,2013(4):154—159.
[1]张晋藩.中国司法制度史[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38.
[2]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史:古代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29.
[3]谢佑平.刑事司法权力的配置与运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18.
[4]谢冬慧.中国古代会审制度考析[J].政法论坛,2010(4):86—97.
[5]陈海光.中国法官制度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2.
[6]艾永明.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利弊的理性分析[J].河北学刊,2013(4):154—159.
[7]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82.
[8][美]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5—36.
An Analysis of the Multi-trial in Ancient China
ZHANG Chun-mei,AI Yong-ming
(School of Law,Suzhou University,Suzhou215006,China)
Judicial trial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hinese ancient lawful institution.Because jurisdiction could not be uniformly performed,the ancient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in operation demonstrated the weird multitrial phenomenon,that is,the trials by the emperors and different agencies.This paper analyzes in-depth the following aspects:limiting the power of each agency,combining administration with judicial func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imperial power and integral power of the political system.The contemporary judicial system could get rid of the“multi-trial”tradition and follow the trend of independent trial by legal agencies.Learning from the past to illuminate today can draw essential lessons to promote today′s judicial system reform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legal system.
the supreme imperial power;integral power;multi-trial;judicial independence
D929
A
2095—042X(2014)01-0062-06
10.3969/j.issn.2095—042X.2014.01.014
(责任编辑:朱世龙)
2013-11-09
张春梅(1988—),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
艾永明(1957—),男,苏州常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行政法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