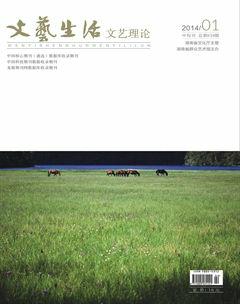谈滕守尧先生的“生态式教育”理论对艺术教育的启示
孙丹青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谈滕守尧先生的“生态式教育”理论对艺术教育的启示
孙丹青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当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处于一种非常态的模式下,体制的刻板单一化,学生只学主课轻视副课的学习模式以及以“分数”论英雄的评判标准,都制约着学生的天性和创造力,因此,学生艺术素养的匮乏和学校艺术教育的不完善就成了当今中国艺术教育的现状。滕守尧先生在《艺术与创生——生态式教育理论》中提出的“生态式教育”理论对中国的艺术教育有所启示。
生态式教育;艺术教育
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之久历史的国家来说,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理因传承至今,并发扬光大,但由于当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处于一种非常态的模式下,体制的刻板单一化,学生只学主课轻视副课的学习模式以及以“分数”论英雄的评判标准,都制约着学生的天性和创造力,因此,学生艺术素养的匮乏和学校艺术教育的不完善就成了当今中国艺术教育的现状。滕守尧先生在《艺术与创生——生态式教育理论》中提出写这些关于艺术教育的书籍和文章其意图在于纠正和改善当今中国艺术教育现状,并给中国的艺术教育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艺术与创生——滕守尧先生生态理论之路》从多角度解释和分析了滕守尧先生提出的“生态式教育”理论。何为生态,为什么要把生态观运用到教育领域中。生态是指人以及其他一切生物存在的状态,我们常说生态系统,教育同样作为一种系统,各环节就是有联系的,如果断了其中一个环节,这个系统就不完整,重则垮塌或毁灭,固然也就不能称之为系统了。因此,滕守尧先生把当今艺术教育的改革理论用“生态”二字诠释,就再好不过了,教育的系统犹如生态的系统,少了某一门课或某一教学环节,都会使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所缺失。
滕守尧先生通过长期对古今中外艺术、美学、教育、哲学、和心理学的潜心研究意识到在原始智慧(野性智慧)、现实人文智慧(圣贤智慧和)和神性智慧(超然智慧)这三种主要人类智慧中,唯有神性智慧可以诠释生态式教育中的“对话”精神。艺术不同门类需要对话、艺术与文化、生活、情感以及科技需要对话、教师与学生需要对话,教学与环境需要对话,学科与学科间需要对话等等。这些对话可以使人回到生命的本源,找到智慧的源泉并重新认识自我的存在价值。
文中归纳总结了八个生态式教育的特征,师生平等、对话精神、开放态度、人的可持续发展、不分主副、主题单元式教学、鼓励活动式教学和融通文理,我想这些生态式教育的方法或许对当今中国的艺术教育有将所启示。
一、师生平等,和谐育人
在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中,课堂方式不外乎是老师说,学生听;老师说一,学生不敢说二;老师是主,学生是宾,诸如此类。教师一直以来都是高高在上的形象,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低位,在被教训、被灌输、被征服的对立关系中学习和成长,这样一来,学生本来的天性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必定被抹杀。因此滕先生提出平等的师生关系是教育者教书育人的最高原则,即“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所谓和谐育人,是要求教师和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平等对待、互促互补、共同发展。和谐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和谐,同时也是知识之间的和谐。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关系中的主要两方,都有权利展示自己的知识观点,知识的获取与分享不分高低,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同样可以同学生身上完善自我的知识体系结构。
二、以“对话”为中心
“对话”作为生态式理论的核心,其真正意义是在两级边缘地带举行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家长、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对话)、人与事物的对话(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教育之间的对话)、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对话(主科与副科、文科与理科、技与理之间的对话)。继而滕先生也指出:“这种对话不是形式上的面对面说话,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相遇,一种灵魂上的沟通。”
课堂上,教师常说:“请同学们互相讨论下这个问题。”“讨论”作为课堂的常态教学模式,已经沿用很多年。在滕先生看来,讨论是有规则的、有主题的,不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也不能碰撞出知识的火花,因此仅仅有“讨论”的教学模式是不够,我们要“讨论”更要“对话”。“对话”与“讨论“的区别之处在于,“对话”是不确定、随意的,是不分身份等级、学位高低的。学生和老师在这样一种不限制的、放松的状态下,通过真诚的“对话”,
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在提出师生平等、要讨论更要对话两点之后,滕先生继而提出生态教育需要开放的态度,对学识、对他人、对自然、对社会的开放态度。人们常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顾名思义,大海的宽广可以容纳众多的河流,就如心胸宽广的人可以包容一切。做人做事需要一颗宽广的心,学知识又何尝不是呢?滕先生认为,以“对话”为核心的生态式教育其目的在于彻底消除以“我”为圆心的封闭意识。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同样学识是有限的,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层面都不一样,每个人感兴趣和擅长的知识面也有所不同,正因如此,我们应通过开放的“对话”方式不断提高自我,完善自我,那些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天下老子最大”的思想都是狭隘的,也是不可取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更何况是在广阔无限的知识海洋里。
四、人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于1987年在《我们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一文中明确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近几十年世界和社会共同倡导的议题,一直广受关注,在自然、社会、以及经济领域都有所建树,而人作为可持续发展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人自身的发展是不是也应该被重视起来,所以,人要发展必然要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将学习转化为智慧,学以致用,完善自我的人生价值和目标。滕先生认为:“一个人的素质高低的标志是看其是否具有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绝不仅仅通过分数来表现”。在这个“以分数论英雄”的时代,分数的高低似乎论定了一个学生的未来发展和潜力,从高考到考研、考公务员等,“无处不是考,无处不见分”,分数的过分重视往往会模糊了人们对教育目的认识,教育的目的是替年轻人的终生自修做准备,而学习知识意在运用智慧指导人的发展。当然,分数是考核一个人所学知识多少、好坏的客观标准,但却非唯一标准。园金斯曾说过:“教育不在于使人知其所未知,而在于按其所未行而行。”另一方面滕先生也明确了“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智慧而非知识”,知识与智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指人类认知的成果,如经验知识、科学成果等;智慧指的是一个人的决断力,两者区别在于智慧可以产生知识,但知识却未必能够产生智慧,有时还可能蒙蔽你的智慧。
五、不分主副,融通文理
滕先生指出,除了教师与学生、孩子与家长之间力求一种生态关系,学校教育在学科、文理之间也应建立一种平等的生态关系。读书多年,我们潜意识里都会对学科的主副有着很明确的概念,语文、数学、英语是主课,我要好好学;美术、音乐、体育是副课,我可学可不可学。循环往复,就形成了大多数中小学的课堂里只见主课未见副课的场面,课堂失衡,学生的发展同样失衡。音体美等课程作为一门课程,必然有他存在的价值,音乐陶冶情操,体育强身健体,美术提高审美,这些都是使一个学生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必备因素。所以不管是主科还是副科都是同样重要的。同样道理,人文学科与理工科之间建立的生态关系也是如此,人文学科具有人文本性,让学生认识自己,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理工科作为自然、科学的统称,意在让人变的睿智和理性,滕先生就认为:“人文与科学的相融合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因此,学科、文理之间无论偏向哪一方,都会使学生的发展失衡,使其得到平衡与统一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由此看来,滕守尧先生的“生态式教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作为一名学者,滕先生对艺术教育的发展一直是亲力亲为的,从其诸多理论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艺术教育正在寻求进步和完善的影子。当然,艺术教育改革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迈出“生态教育”之路实属不易。因此,作为一名即将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我来说,把“生态教育”这一理念付诸于实践,更深层次的挖掘“生态教育”理念的价值,发扬光大,都是将来我们要做且必须做的。
G 42
A
1005-5312(2014)02-022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