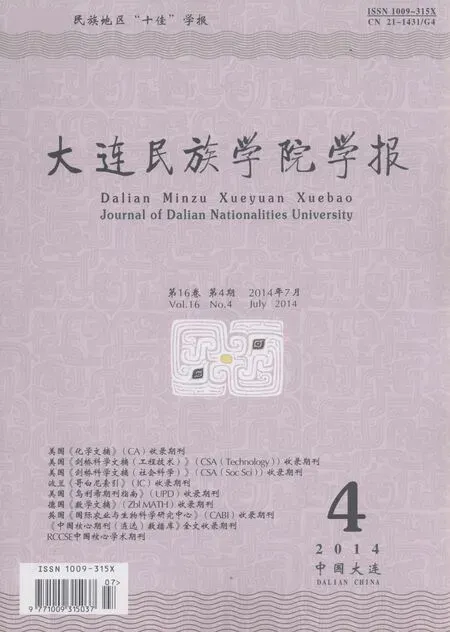东北民族森林生态文化论纲
南文渊
(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大连116605)
一、森林-草原:东北民族生态文化形成的环境基础
东北地区是中国北方诸民族发源地之一。自汉代以来东北地区各民族逐步形成三大族系:东胡蒙古系民族包括东胡、鲜卑、乌桓、契丹、奚、乌洛侯、室韦、蒙古。肃慎靺鞨系民族,包括肃慎、挹娄、匆吉、靺鞨、渤海、女真、满洲。夫余豸岁貊系民族包括夫余、高句丽、新罗、百济及以后的高丽民族。历史上东北少数民族生存于森林生态环境,由此而形成了森林环境下不同的生计方式,如森林采集-渔猎方式,森林-草原猎牧混合方式,疏林-草原游牧方式,森林-平原耕作方式,等等,从中也培育了各民族生态文化。这种生态文化可以称之为森林生态文化[1]。其基本特征是民族对其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适应,并按照森林生态规律的要求,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谨慎利用自然资源,进而所形成的与森林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生计方式、社会规范、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
1.东北的森林-草原生态环境特征
东北区在行政区域上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大部地区是森林环境或者是森林-草原景观。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历史文明的先秦时代,东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森林广泛发育。辽宁南部地区以栎和桤木为主的阔叶林占优势,东北三江平原和长白山区属温带落叶阔叶林,内蒙古东、中部地区发育有温性针叶林和阔叶林,一直到黑龙江省的呼玛县一带也分布落叶阔叶树桤树的优势带。3当时全国森林覆盖率在49.6%,而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地区超过90%[2]。
虽然从14世纪初至19世纪末的元后期至清末,中国东部地区气候转向寒冷,东北地区人口有所增加,但是东北地区大、小兴安岭及周边地区的原始森林植被被保存完好。清代初期辽宁地区森林覆盖率超过40%,黑龙江、吉林地区的大兴安岭与长白山地中部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70%,属温带森林植被。
森林生态系统是东北区域生态环境演进发展到顶峰时期出现的生物资源。该系统有着最复杂的构成,最完美的结构,最旺盛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森林-草原区域中生物多样性得到充分发展,为各民族生存提供了丰富的生存资源;森林生态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御风沙的功能。为各民族的生存质量存发展提供了保障。
同时,东北地区也是我国最寒冷的自然区。在14世纪初至19世纪末期东北地区处于气候寒冷期(所谓小冰期)。《后汉书·东夷传》描述东北地区气候“土气寒”或“土气极寒”。这种气候制约了森林民族对森林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也阻止了外来民族人口的大规模进入林区。
2.森林民族生态文化的演进
从新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森林生态文化中分化出山地森林狩猎-渔猎-农耕民族生态文化、森林边缘区的平原耕作民族生态文化和森林-草原游牧-猎耕民族生态文化等三种类型。
(1)山地森林狩猎-渔猎-农耕民族生态文化。东北地区历史上先后出现有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历史上这些民族生存在森林环境或者森林边缘的草原地带。
肃慎这个名称出现在先秦时期。《山海经·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之国。”肃慎在燕国之北,当时处于森林草原生态环境。
先秦时期的挹娄最初发源于辽西医巫闾山一带。春秋战国之际,从辽西迁至辽东山区,后又向北迁至吉林、黑龙江东部。《后汉书·东夷传》载:挹娄“土地多山险。……有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还说: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这正是对处于山林之间的森林民族生计方式的具体写照。
唐代“黑水靺鞨”居黑龙江下游。元代译作“帖列灭”。明代译作“吉列迷”。吉列迷人夏天至河海边野居,出海捕鱼、捕海兽;冬天进山挖土作穴,衣狗皮、兽皮、乘狗爬犁出入。表明是森林-沼泽-湖泊地区的渔猎民族[3]。
元代,对生活于内外兴安岭的所有游猎民族,统称为“林木中百姓”。明代对东北地区记载较多的是女真各部的分布和迁徙。北部女真各部均以渔猎、畜牧和采集为主。南方近辽东和朝鲜的地区“农猎兼资”、“农牧兼资”;辽东地区的部分女真人,则主要从事农业,兼事狩猎和采集人参,与汉族杂居、通婚,同汉族农民相差无几。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东北地区的鄂伦春、赫哲、鄂温克等民族是典型的森林民族。被称为“树中人”。作为森林民族的鄂伦春居室是用桦木、柳木或是落叶叶松的细木杆搭建的仙仁柱,建立在森林边缘的河川地带或者背靠树林的坡地、山腰、丘陵地。
(2)森林边缘区的山地-平原耕作民族生态文化。这是指东北东部和南部森林边缘地区的生态文化类型。东部森林山区先后出现的沃沮、夫余、高句丽等民族。最初是狩猎民族,以后转向猎耕牧结合的生计方式。例如汉代的夫余,居今吉林农安一带。《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夫余“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纳,……以六畜为官,有马加、牛加、狗加。”是典型的牧、农、猎混合生计方式,农耕为主,但畜牧生计占重要的地位。
早期的满族的先民肃慎、挹娄、勿吉使用“楛矢石砮”射猎,兼营原始农业,并且擅长养猪。这是长白山地区以及小兴安岭自然环境制约的结果。近代以来满族在不断的迁徙中,其主要生产活动逐渐由采猎转变为农业生产。栖息于东北松辽平原及其周边丘陵、河谷地带的满族民众顺应当地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发展了以粟、麦、黍、豆等杂粮栽培为主的农耕生产。当时满族还没有掌握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种地不施肥,仅以烧荒的余烬为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高梁、玉米、大豆在东北满族的农耕发展史上都占据着主粮的地位[4]。
(3)森林-草原游牧-猎耕民族生态文化。这一系统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主要是猃狁、犬戎、赤狄、白狄、长狄、乌桓、鲜卑、柔然、室韦、契丹、奚、蒙古、达斡尔、锡伯诸民族。商周三代笼统地称之为“北狄”。历史学家认为是两个系统:一是猃狁、犬戎、狄、胡和匈奴民族系统;另一是肃慎、貊、貉、山戎、东胡民族系统,是分布在河北北部及其东北地区的狩猎游牧民族[5]。
战国晚期的匈奴来自森林区域,以后游牧于草原。《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乌桓的经济以畜牧、狩猎为主,亦知农业,《后汉书.乌桓传》云:“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为衣。”
鲜卑:《后汉书·鲜卑传》云:“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鲜卑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在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处的大兴安岭北段发现了鲜卑拓跋氏原始地祭祖的嘎仙洞,据此可以肯定鲜卑最初应居住于大兴安岭地区,而历史上这里是典型的森林生态环境。契丹可以说是居于松漠之间的森林-草原民族。公元10-11世纪,额尔古纳河和海拉尔河流域作为森林-草原地带成为“契丹二十部族放牧地”。
室韦属东胡族系,室韦人先秦时曾在辽东一带活动过。唐代主要活动于今天内蒙古呼伦湖和额尔古纳河流域。室韦是典型的森林民族。“室韦”一词的本来含义是“森林中的人”。13世纪的蒙古民族是以大兴安岭森林部落和呼伦贝尔草原部落两大原蒙古人集团为核心,后来融合蒙古高原的突厥游牧部落以及一部分流亡漠北的契丹、女真乃至汉族农牧民,最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其发源地在森林与草原之间。
由此看东北森林-草原民族的生态文化变迁,其在适应森林-草原生态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生计方式。其一是以森林环境为生存场地而创造的狩猎、渔猎生计方式。其二是森林-草原游牧生计方式。其三是森林边缘地区的森林-农耕生计方式,其早期是在森林边缘地带开辟的小块耕地,实施耕、牧、猎混合生计;后期森林退化,农田扩大,农耕成为生存区域中主导产业。
二、东北民族生态文化的环境适应性特征
历史上作为东北森林民族、草原民族的诸民族,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保护自然环境方面,为我们创造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适应自然这一独具特色的森林-草原民族生态文化适应模式。
1.聚落形式与生计方式:森林民族的特性
一般而言,寒冷气候下的森林族群注重生存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森林民族的聚落形式。森林民族聚落地点并不在森林深处,通常选择在森林盆地边缘的山脚下或者半山腰,湖泊周围,江河岸边,等等。东北地区的所谓“窝集”是比较典型的森林居民聚落地方。人们对“窝集”理解不一,凌纯声说:“窝集……并不是指某一部落或某一地域而言,不过是森林民族的通称。”[6]实际上“窝集”便是森林盆地之别称:吴振辰《宁古塔记略》说:“乌稽则为窝集的转音。……意为乌色树枝,即黑森林之意,因原始森林茂密苍老,枝干叶皆带褐色之故,今德国南部也有黑森林。”《宁古塔记略》举例说:“吉林有大小乌稽,大乌稽,名黑松林,树木参天,槎枒突兀,皆数千年之物,绵绵延延,横亘千里,不知纪极。夏有哈汤之险,数百里俱是泥淖,其深不可测。”《柳边纪略》卷二载:“自混同江至宁古塔,窝稽凡二:曰那木窝稽,曰色出窝稽。那木窝稽四十里,色出窝稽六十里;各有领界。其中万木参天,排比联络,间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山通道,乃漏天一线,而树根盘错,乱石坑呀。秋冬冰雪凝结,不受马蹄。春夏高处泥淖数尺,低处汇为波涛;或数日或数十日不得达。蚊蝱白戟之类,攒啮人马,马畏之不前,乃焚青草聚烟以驱之。夜据木石,燎火自卫,山魈野鬼啸呼,隋人心胆。馁则咽干粮,粮尽,又或射禽兽,烧而食之。”《黑龙江外纪》云:黑龙江境内著名窝集四:曰巴延窝集,库穆尔窝集,巴兰窝集,吞窝集。《吉林汇征》云:“吉林省有四十八个窝集,分长白山、小长白山两系。”这些记载表明这实际上是森林民族聚落的森林盆地[7]。
森林民族的生计方式。“窝集”的采集民族和狩猎民族被称为“树中人”、“栖林人”。他们在夏季的居住方式是巢居,即在树上用枝条编成巢状的掩蔽所,可以避潮湿,防止野兽、蚊虫的侵害。其交通工具主要依靠他们所养的驯鹿。同时以桦树皮船、犴皮船、独木舟、滑雪板、雪橇、拖架、曳架等也是森林河流中运输工具;“树中人”实施树葬,肃慎族把死者“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槨,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契丹族用树葬:“其俗,死者不得作家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室韦族也采用“尸则置于林树之上”的葬法。
寒冷森林地带的居民讲究居室的稳固耐用,不随意破坏森林资源。隋唐时期的室韦部落的生活规律是:夏天巢居,冬天穴居。夏天巢居于森林之中的。《隋书·室韦传》载:“每溽夏……山多草木鸟兽,然若飞蚊,则巢居以避”。《新唐书·回鹊传》载:鞠室韦是“聚木作屋,尊卑共居”。聚木作屋可能是桦皮屋:“构木类井干,覆桦为室”。这是以木为支架,上覆桦树皮而成。典型地反映了森林边缘生存的特征。这种记载与14世纪森林蒙古人的生计方式相同。据拉施特记载:11~14世纪构成蒙古族一支的森林兀良哈惕部落“他们从来没有帐篷,也没有天幕;……在迁徙时,他们用白桦和其他树皮筑成敞棚和茅屋,并以此为满足。”[8]
森林边缘民族虽然在森林盆地边缘的山脚下、湖泊周围、江河岸边开辟了小块的农业耕种地,但是长期以来没有扩大,没有大规模地毁林开荒。如早在西周春秋之际肃慎人就已经有了原始农业,但是,他们的农业生产发展极其缓慢,渔猎、采集经济却长期地保持下来。渔猎采集、经济仍然在其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辽、宋时期一直到明代的女真族最初也是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计,主要是以渔猎、采集为生,过着“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经济生活。在农业遭受自然灾害之后有的部落基本放弃农业生产而专以渔猎采集为主,到了冬季,狩猎几乎成了唯一的生产活动。
疏林-草原游牧民族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草原游牧方式是一种较典型的既饲养家畜又保护草原的方式。古人称游牧为“逐水草而居”。随水草射猎。居住无常,实际上“逐”是循自然规律所动,按自然变化而行的行为。依据气候指令而作周期性的游走迁徙,自由游牧是它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
2.社会生态制度:环境的严格保护与社会环境的宽松
(1)稀疏分散的人口和集中的商贸集镇相结合。生态学认为,一个健康协调的生态环境中,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应该达到最佳状态。而在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中,人口数量和密度的控制是关键的因素。就东北地区而言,辽阔的森林草地原野,宽裕的生存场地,稀疏的人口分布是古代森林民族生态文化产生发展的前提。
19世纪以前的历史上东北地区人口增长一直比较缓慢。战国中期辽东辽西属燕国领地,当时整个辽宁地区来说估计不少于40万;今吉林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扶余、肃慎人,大约20万;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估计15万人;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呼伦贝尔高原地区,主要居民是被称为东胡人的民族,人口有六七十万[9]。这一时期整个东北地区人口60~70万人,按1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计算,人均占地2.4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6人/平方千米。
元代东北地区人口约400万~500万左右。因此,新石器时期到18世纪初期清政府大规模移民之前的5000年间,人口增长很慢,东北地区人口一直在500~600万以下,人口密度到19世纪最多时才50人/平方千米。同一时期森林覆盖率一直在稀疏的人口东北的森林资源一直保持得比较好。
历史上进入东北地区的汉族人口大多集中在城镇市区。两汉时期的郡县城址,多分布在河谷平原、交通道路。例如辽东郡治辽宁各县。汉武帝时代在东部区域设置了玄菟、临屯、乐浪、真番四郡。与此同时,东北地方森林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也在当地建立城镇。唐代高句丽山城分布在吉林省的南部和东南部至朝鲜半岛的东北部。渤海建立起以五京制为核心的城市体系包括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市),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中京显德府(今吉林和龙市),西京鸭绿府(今吉林省临江市),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北道)。女真族建立金朝,其都城金上京会宁府位于松嫩平原东部边缘。同时在黑龙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普遍设立了府、路、州、县。16世纪努尔哈赤修筑佛阿拉城、赫图阿拉城和盛京城。到清朝光绪年间,东北地区的城镇已很普遍。而近代东北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域之一。
城市的形成促进了集市的发展,成为民族成员聚居、交流、融合的中心,进而带来了人口的聚集,形成了城市市民和商贸生活方式,而减轻了对广袤森林草原的人口压力和开垦破坏。因此,集中的城镇、稀疏的乡村人口和广袤的森林草原区域是保护东北生态环境的制度性体系。
(2)人口控制协调制度与森林-草原环境保护的形成。受到当地动植物资源储量的限制,当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缓慢增长到一定的规模时,无论是森林民族还是草原民族,都要通过部落分裂、出走、迁徙到别处的方式使得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与当地动植物资源的承受能力保持相对平衡,使原生存区域的生态压力得到缓解。历史上东北诸民族多次发生的大规模向外迁移,比如9-10世纪的东北各民族南下迁徙,12世纪蒙古各部的分裂和迁徙,14世纪北方草原诸族的分裂与争夺草原的斗争,17世纪满族的南迁等。
有关研究表明,在古代森林-草原民族中,妇女生育率是比较低的。许多部族往往通过延长孩子出生后的性生活禁忌等措施来降低生育率。狩猎—采集群体的妇女一般有三四年的生育间隔,使得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从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看,寒冷的气候下婴儿成活率会降低,而在温暖的气候下婴儿成活率会提高。寒冷潮湿的气候使人易发多种疾病,同时森林草原食物资源相对匮乏,传染病的流行(如天花),这些都影响控制了人口的高出生率。
3.社会管理的宽松自由
东北内蒙古地区区域辽阔,生态类型丰富多元,自然资源丰富而人口稀少,同时社会环境宽松自由,各个区域相互流通相互交融,因而培育了文化的多样化和思想流派的多元性。这里是东北亚文化传播走廊,各民族文化交流是建立在随时游动的公地与自由宽容的社会管理之下的,从而鼓励了自由精神的宏扬。森林草原民族是不断迁徙游动的。当一个部落,或一个游牧民族的国家游牧猎耕于一片森林草原时,整个区域便是这一个部落或民族集体的。任何人不可能画地为牢,占一块土地为己有。森林民族随时随地都在迁徙之中。社会的自由交往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对保持森林草原生态环境的繁荣更新生生不息起了决定性作用。
4.精神信仰:森林民族生态文化的核心是萨满教
新石器时期从东起大小兴安岭、西到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广大地区形成了相近的信仰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的核心便是萨满教。萨满教应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曾为东北亚,北美,北欧等众多民族全民信奉。而中国北方地处萨满教分布的核心地域。古代北方森林-草原大地上诸文化系统都有其共同的信仰体系,在文化价值观上是统一的。这就是萨满教的支持,至少,受了萨满教信仰的影响。萨满教源于森林-草原环境,注重于对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适应:
(1)构建了神圣的森林草原区域:森林草原环境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建立有神圣的区域,神圣区域分布着神山、神湖、神泉、神河,神树、神圣动物。鄂伦春人认为认为森林归天神所有,为猎民所使用。猎场是天神“恩都利”赐予的,属大家所共有的;猎物是山神“白那恰”赏给的,人可以享用,但是要珍惜[10]。他们认为有山无林的地方只有山神,但有山有林的地方同时还有林神。凡神圣的都带有禁忌特性。神山、神水的地方都成为神圣自然保护区,任何人都不能触犯神地及其范围内的生物。各民族对周围的环境尽可能地不触动它,维持它的原样。这种心态和行为反映到民族文化上,就是注重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维护,而不是剧烈地毁坏、改造。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森林面积没有出现人为的大规模减退。18世纪以前东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在65%上下。这得益于森林民族的保护行为。
(2)形成了森林民族的标志性生态文化象征:如宇宙树、敖包、龙神,等等。在森林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有一棵贯通上、中、下三界的宇宙树,亦称为神树、萨满树。这神树是天神往来于三界的通路,亦是萨满上天入地的通路。
森林边缘的草原地区一般建立有“敖包”,“敖包”是区域圣山的象征,也是区域天、地、人间三界的象征。祭祀敖包表达人们对自己生存地的崇敬和热爱。
中国人崇拜的龙可能出自森林-草原民族萨满教文化,因为龙的特性约有如下数端:与云相属能升天;与水相依能潜渊;深山森林之中能长吟。这些特征与森林-沼泽、森林-湖泊生态环境的植物与动物相联系。有人认为“龙”是树神,象征贯通上、中、下三界的宇宙树。它的原型是森林中四季常青的“松”、“柏”一类乔木[11]。这种通天神树后来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得到继承,渐渐被赋予诸如保佑庄稼丰收、掌控雨水甚至动植物生殖繁育等多重神性功能。所以中国人对龙的崇拜,是树神崇拜的曲折反映。
(3)萨满教突出的功能是激励人们敬畏森林-草原。草原森林地区的萨满教文化认为,大自然有其生命特性,不仅具有生物生命特性,而且具有精神生命特性。大自然有其自己的生命权利与生存功能,作为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存权。赫哲人最尊敬之神为天神。这天神常供在神树上。鄂温克人在狩猎前,要先敬山神“白纳恰”。狩猎民族忌讳在大雷雨中外出远行、上山打猎、到草场放牧等;严禁在雷雨中到大树下避雨,否则的话将被雷电击死;被雷击死的各种动物肉严禁食用;雷击过的地方严禁牲畜踏入;雷电火引起的森林火灾,不许扑灭[12]。对雷电的畏惧实际是对森林-草原的禁忌。鄂伦春族限制对森林的随意砍伐;出猎和捕鱼的人路经“白纳恰”(在大树的根部用刀斧砍成的人脸形),必须下马撒酒敬烟并磕头,否则认为会倒霉的[13]。
(4)简约、节简是森林-草原生态文化的特点。森林-草原民族生活的特点是顺从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生物、融入自然环境。这种方式限制了家畜数量的增长,使其不超出草原牧草生产力的限度。牧人保护草原一切生物的生命权与生存权,既养家畜又保护野生动物;既要放牧又要保护水草资源,从而维护了生物的多样性。森林草原民族在长期的生存环境中没有筑城建市,没有大面积开垦草地种植;没有砍伐森林盖房做棺;他们没有猎取草原生物去牟利;他们没有专门的官吏、常备军以及机构设施管理牧人——他们只放牧牛羊,但不牧人。
简约、节俭是森林-草原民族的生活习性。14世纪的波斯作家志费尼对草原民族的生活状态描述说:北方尤其是大兴安岭森林-草原地区的鞑袒人穿的是狗皮或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或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的酒是马奶,甜食是一种形状似松的树木结的果实,他们称之为忽速黑,在当地,除这种树木外,其他结果的树不能生长;他生长在一些山上,由于气候极冷,那里找不到别的东西。他们当中大异密的标志是:他的马镫是铁制的,从而人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其他的奢侈品是什么样了[14]。
森林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和文化价值。在走向城镇化、森林民族转型为城市民族的今天,传承森林生态文化,促进城市化发展与建立区域广大的森林自然保护区相结合,是保护森林资源和森林生物多样性,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
[1]南文渊,孙静,关伟,等.北方森林-草原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2]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5.
[3]田继周.明代民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4]孙静.东北满族传统生态文化[M]∥ 南文渊.北方森林-草原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71.
[5]田继周.秦汉民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232.
[6]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M].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52.
[7]何光岳.女真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313-314.
[8]拉施特.史集:第1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02.
[9]路遇,滕泽之.中国分省区历史人口考[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36-37.
[10]韩有峰.黑龙江鄂伦春[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2:100.
[11]尹荣方.神话求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49.
[12]吕大吉,何耀华.哈斯挂讲述资料[M]∥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1.
[13]韩有峰.鄂伦春族风俗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47
[14]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