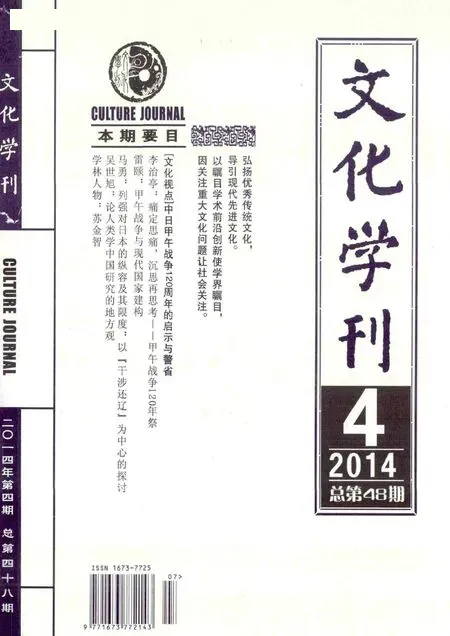刘昌诗《芦浦笔记》之“芦浦”考
——就刘昌诗“来任南监说”与潘杨二先生商榷
万 军
(温州大学图书馆,浙江 温州 325035)
《芦浦笔记》素来以“凡先儒之训传、历代之故实、文字之讹舛、地理之变迁,皆得溯其源而循其流”著称[1],且因其知识广博、治学态度严谨、颇多独到之见,特别是书中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史料和遗文佚事而备受推崇。《钦定四库全书·子部》收录此书。中华书局将此书列入1986年出版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但关于刘昌诗此书的写作地点、书名芦浦究竟何指等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语焉不详。
因为书名“芦浦”二字与苍南之“芦浦”相关,且当地杨氏族谱中存有相关佚文,所以《苍南历史文化》2011年第03期发表了杨乃琦先生的文章 (以下称杨文),文末引用温州市图书馆研究员潘猛补先生的考证结论称:刘昌诗《芦浦笔记》中的芦浦,当在今苍南之芦浦无疑。二者是否真的有联系呢?刘昌诗真的来任天富南监场盐大使吗?本文通过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予以整理考证,也谨以此与潘杨二先生商榷。
一、刘昌诗生平简述
《芦浦笔记》作者刘昌诗,字兴伯,为宋时临江军清江人氏,南宋开禧元年(1205)毛自知榜进士[2]。据《江西省志·行政区划志》[3],宋时清江隶属于临江军 (领清江、新淦、新喻三县,治在清江),即今天江西樟树一带。刘昌诗名列明隆庆《临江府志·选举志》。
根据《芦浦笔记·序》可知,刘昌诗称自己“服役于海陬,自买盐外无他职事”,这是刘昌诗被认为有过盐官任职经历的唯一根据。序文还称撰写此书的初衷是,“久惧遗忘,因并取畴昔所闻见者而笔之册,凡百余事,萃为十卷。”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芦浦笔记》成于宋嘉定癸酉年 (1213)。
在此书既成的第二年,也就是在考中进士之后的第九个年头即1214年,他前往江苏六合县担任县令,这也是他一生中有明确纪年的人生片段。六合县,现为南京市六合区,北接安徽天长市,西邻安徽来安市,东为江苏仪征市,南为长江,有南京市“北大门”之誉。六合还是雨花石的故乡,民歌《茉莉花》的发源地。刘昌诗在任期内有过修建县署、县学以及修造桥梁等举措。光绪《六合县志·官师志》[4]称:“邑人尤称其文教”。
二、评析关于“芦浦”指向的几种说法
学术界基本认定刘昌诗的《芦浦笔记》成形于1213年,而此前的时间,刘昌诗当究竟处于何地过着何样的生活环境呢?学界鲜有述及。“自买盐外无他职事。官居独员,无同僚往来。僻在村疃,无媚学子相扣击。遥睇家山,分不能挈累。兀坐篝火灯,惟翻书以自娱。”这位先人只用不过50个字,就将自己的职业、生活、情感等一段人生经历给浓缩了。位卑职轻,独住僻壤,是导致他1213年以前的人生历程被遗忘的原因吗?夜半兀坐翻书自娱,是他这段经历被忽略的又一重原因吗?一个难解的谜。
下面简要评述一下学界目前对于“芦浦”具体指向的几种说法。
(一)华亭芦沥浦说
《芦浦笔记》撰于何处、书名“芦浦”落在哪里等疑问,长久以来,跟刘昌诗的生平一样,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最早认为“芦浦”是“华亭芦沥浦”的,是钱塘樊榭山民厉鹗于雍正十年十一月所作的考据结论,这也是确定“芦浦”之所在的最初文本说法:刘昌诗乃清江人,开禧元年毛自知榜进士,“芦浦”乃其写作芦浦笔记的处所,即华亭芦沥浦,昌诗盖曾为盐官者…… (据知不足斋本)。此说被《四库全书提要》编者不加考据并附和,“盖其监华亭芦沥浦盐课时作”[5]。
《江西文学史》[6]编者认为《芦浦笔记》创作于刘昌诗在六合县令任期内。从他的生平记载来看,他前往江苏六合县担任县令,是在1214年,更是在此书既成的第二年。此说难以成立。
据同治《清江县志·文苑·刘昌诗》,认为芦浦笔记的写作地点在清江县城江滨的庐州,“昌诗结屋于此,曰庐浦草堂,著书其中……曰《庐浦笔记》”。新编《清江县志》(主编 柳培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版)明显沿用了类似观点。
由张荣铮、秦呈瑞点校的《芦浦笔记》之“点校说明”(中华书局《芦浦笔记·点校说明》撰写于1983年11月)中否定了上述两种观点,认为此说“与刘昌诗的自叙相背的,不可取。”
此外,新编《清江县志》所称的“庐浦草堂”与《芦浦笔记》中的“芦浦”二字相去甚远,更是不可靠。
(二)慈滋芦浦说
清人祝堃并不认同华亭芦沥浦为芦浦之说。事实上,浙江平湖也有“芦沥浦”,因此,“华亭芦沥浦”之说有望文生义之嫌。祝堃以为,“所谓芦浦者,当是宁波边海之区,非今之芦沥浦”(“华亭芦沥浦”),因为“是书 (指《芦浦笔记》)所载地理故迹,多及四明奉化,而无一语及云间 (即上海)”。祝堃的看法虽然有所发展,但也仅限于质疑层面,结论不甚肯定。
由张荣铮、秦呈瑞点校的《芦浦笔记》之“点校说明”中,发展了祝堃的说法,称“在宋人四明志中发现,慈溪县有一驿铺名芦浦铺,靠近海边,而海边又有鸣鹤盐场”,于是认为刘昌诗任盐官的地方就在慈溪芦浦。点校者认为,《芦浦笔记》就在这里所写,时间为刘昌诗登进士第的1205年之后、任六合县令的1214年之前。从上述几处相关地名来看,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如上海“芦沥浦”、慈溪“芦浦铺”,均有与书名“芦浦”相关元素或者近似的地名,这些地点均濒海,也都有相应的盐场。这些元素与刘昌诗“曾任盐官”的经历都可能相吻合,或者说至少能为“刘昌诗任盐官”提供时代背景或是就职空间。特别是《芦浦笔记》中多处言及四明、奉化等地的一些人文历史古迹等,更让人相信与慈溪“芦浦”有着莫大的关系。后人认为,其对某些古迹记载的细致程度,到了非亲历不可为的地步。
对于刘昌诗究竟是否在四明有过盐官的任职,截至目前未见史料可资证明。四明三志 (宋宝庆志、宋开庆志、元至正志)、明天启《慈溪县志》以及其它一些地方文献,均无载刘昌诗在当地的活动踪迹。如果是游学,不载倒也可以理解;如果是任职,这些志书却为何“口径”如此统一,一概不予记载呢?不免令人生疑。
按常理,面对古迹形胜,文人墨客素来指点江山感慨人生,或抒情或言志,这个传统也构成中国古代文学史重要的一个分支——“游记文学”。作为文科进士出身的刘昌诗面对四明的山水名胜、人文风情,他可曾激扬文字?《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四明旧志诗文钞》[7]中,未见有刘诗昌的作品。
《宁波地名诗》[8]是一册当今宁波学人选编的本地古代才人诗集,选编时限上至盛唐下迄当代,收录作者560余、诗作1260余首,作品内容涉及宁波山川关隘、州县乡村、名胜古迹、寺庙道观、亭榭楼阁、街道里巷、风物人情、神话传说等方面。但未见刘昌诗的蛛丝蚂迹,当地一些乡土文化资料里也对刘昌诗“保持沉默”。可见当地学人也并不认同刘昌诗曾在本地活动的说法。
(三)苍南南监 (芦浦)说
新增的苍南南监说,是因为在芦浦(南监)杨姓族谱中保存的宋时佚文,述及刘昌诗及其任职南监的经历,而且还明确提到他所撰写的《芦浦笔记》。于是,温州市图书馆潘猛补先生根据当地文献进行考证而加以认定,认为芦浦笔记中的芦浦二字落在苍南南监,即今天的芦浦。所据文献如下:
1.文献一:《复杨少微广文书》(宋张隽)
张隽在给杨少微的信中称:“昨接《绿云居》大集,盥薇捧诵一通,具见宏词古雅,学有渊源。惟第五十六篇,诋及刘昌诗作盐课司于南监场,撰《芦浦笔记》十卷,谓其考辨疑义,类多闲记轶事,如芦浦本乎回浦,无据,殊非真切。其说甚韪,叹服拜服!庸读竟,鸿便归赵。”此文现收入《浙南谱牒文献汇编·第三辑》[9]一书。
南监杨氏族谱中保存的佚文为《复杨少微广文书》 (题目为后人所置),作者为宋时临安人张隽,嘉定十年 (1217)登吴潜榜进士 (据《宋登科记》、宣统《临安县志》)。南监杨氏先人杨谦度 (字少微),著有《绿云居诗文钞》,入《江南文献录》。这里的江南,指的是昔时温州府平阳县,包括今天的平阳苍南两地辖域。昔日平阳名流方继学曾为该《江南文献录》撰跋,称“是编,于天下之大,虽未敢必其有所裨益,而一方之人文,实于是乎寄,他日考观风俗者,亦可以概见。”遗憾的是,此书已佚。
据杨氏族裔杨乃琦先生称,《绿云居》大集即为《绿云居诗文钞》,其杨氏族谱在张文末注有“四库全书有《芦浦笔记》十卷,附识俟考”字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后人所加。
2.文献二:《临安教授杨谦度墓志铭》(宋·孔景行)[9]
据同族谱另一篇名为《临安教授杨谦度墓志铭》 (宋·孔景行)的文章来观,同好对杨谦度的评价则为:“宜彬彬之英□,振家声于芦浦兮。”据此墓志铭,杨谦度在淳祐初以上舍登特奏名科,任临安“教授”。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在《宋登科记》中见到杨谦度功名记载。
3.文献三:《南监地舆记》(宋·彭仲刚)
《南监地舆记》中称,“温州为静海军,为应道军,为瑞安府,横阳仍平阳旧治。芦浦为天富南监场,仍设大使驻扎,数百年久安长治。”温州市图书馆潘猛补先生综合上述资料考证后撰文认为,“南监盐场属地为芦浦,今尚仍其名,刘昌诗当为南监场盐官,虽志书不载,然《南监东门杨氏宗谱》记载甚明,故我们可得出《芦浦笔记》盖其监天富南监场时作,芦浦乃平阳南监之芦浦镇 (今属苍南)。”
由此,《芦浦笔记》中的芦浦得以确认,刘昌诗《芦浦笔记》的创作地得以揭晓,这似乎解决了一段了历史悬疑。
三、关于南监场盐课司的争议与考辨
(一)南监盐机构建置简述
事实上,上述的这个结论,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另一段史实疑案,那就是天富南监场的建置以及“盐课司”的出现。同样借用上述三个佚文,我们尝试展开解读,寻找些许有关刘昌诗谜一般身世的蛛丝蚂迹。
昔日平阳南监盐场历经宋元明清、民国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盐田随着自然退化而大批被废弃,2004年,芦浦盐场被正式终止其历史使命,成为新苍南建设工程中的临港产业基地。
民国《平阳县志》(符璋刘绍宽等纂修·民国十四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认为,宋时,温州天富南、北监,皆合称一监,其中天富北监在玉环岛上,濮阳李宽知监事,此即盐监官。其监官当设在北监,而平阳为其所统辖。编志者认为,平阳或不再设或另设一场官以佐之,今皆不可考。并称惟《元丰九域志》(光绪八年五月金陵书局刊行)中“乐清下云天富一盐监,平阳下云天富一盐场,此略可见矣”。按宋史有关职官的记述,宋代的监当官,即盐监官、盐监事,掌茶盐酒税、场务及冶铸之事,诸州、军随事置官。光绪《乐清县志》[10]则称:宋时盐监未有盐大使名。
于宋朝始建的“天富南监”,称“南天富场”。据《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南监场》[11]的说法,南监地舆落在今芦浦之地无疑。民国《平阳县志·食货志》:明洪武元年,两浙置都转运盐使司,所辖分司四,有温台分司于温州,置盐仓批验所于天富南盐,场置盐课司大使。明洪武八年……置天富南监场盐课司。“盐课司”这一盐务机构的确切名称首次见载官方史籍。相关称谓,在《皇明一统纪要》中以“天富南场盐课司”相称,在嘉靖《温州府志》中则称“天富南监场盐课司”。也与《读史方舆纪要》[12]“天富场,在平阳县东南三十余里。明初,置天富南监场盐课司于此”相吻合。同样可资佐证的是,平湖芦沥场盐课大使署的设置——“明前无 (平湖)芦沥场盐课大使署,设立芦沥场盐课大使署是从明洪武元年 (1368)开始”。
(二)捉襟见肘的苍南芦浦说
以上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与宋时平阳先贤彭仲刚所撰写的《南监地舆记》等史籍相关记述,则更显左冲右突:
1.“盐课司”被提前记述
《南监地舆记》中称,“温州为静海军,为应道军,为瑞安府,横阳仍平阳旧治。芦浦为天富南监场,仍设大使驻扎,数百年久安长治。”温州为静海军、为应道军、为瑞安府的初始年代,分别在宋朝的978年、1117年、1265年。
乾道二年 (1166)年,平阳县金舟乡人氏彭仲刚中进士第,他曾任金华县主簿。其生卒年为1143年至1194年。温州是在1265年由应道军升瑞安府,这根本就在彭仲刚百年之后的事了。所以《南监地舆记》中出现“为瑞安府”这一史实,值得商榷。这是其一。
既然光绪《乐清县志》言“宋时盐监未有盐大使名”,又何况南监呢?明季始设“盐课司”,而时为南宋的“刘昌诗作盐课司于南监场”的理由又从何而来呢?依据是什么?一个在几十年后或者上百年后才设置的机构、职位,为什么可以被提前表述得如此精确呢?这是其二。
嘉定是南宋皇帝宋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前后续存共计17年 (1208年-1224年)。这是距离彭仲刚仙逝之后10多年的事,彭文所持“仍设大使驻札 (芦浦)”一说恐怕难有服人之理。
2.刘来任无记录
假设嘉定17年间天富南监职官被遗漏了,而这17年间,有可能会是刘昌诗来任吗?从刘昌诗的个人简历来看,游历桂林淮南姑苏等地 (1181-1202)、中进士 (1205)、写就《芦浦笔记》 (1213)、任六合县令 (1214)以及书末自跋所示捐俸刻刊于六峰县的时间“嘉定乙亥(1215)”等。查《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 职 官》[13],歙 县 人、嘉 定 辛 未(1211)进士吕午,“监温州天富北监盐场”,在此职官志中,有宋一朝仅此一人见任北监,更未提及天富南监职官,这应该符合民国《平阳县志》所言“宋时南监盐官几乎无考”一说。
事实上,“监温州天富北监盐场”的进士吕午,是在嘉定辛未 (1211)中第之后赴任。而刘昌诗一生能与苍南芦浦形成交集、有著此书于芦浦的可能年限,只在1205年中举之后至1213年成书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仅有北监官员的出场而无南监,恰恰说明南监无相关职官在任。这与民国《平阳县志》所持观点是吻合的,“平阳或不再设或另设一场官以佐之,今皆不可考。”况且刘昌诗的《芦浦笔记》中,根本没有提及有关芦浦丰富人文资源中的哪怕点滴信息,更可佐证刘此际并未出现在南监。从民国《平阳县志》称“清初仍明旧额,置天富南监场大使一员,驻扎芦浦”一语来看,宋时南监场“未设监当官”的观点是正恰当的。
3.“诋”字背后的信息
给合张隽给杨谦度的函件,我们再来仔细分析。张隽就杨谦度《绿云居》集中“惟第五十六篇,诋及刘昌诗作盐课司于南监场撰《芦浦笔记》十卷”一事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对杨谦度关于刘昌诗《芦浦笔记》“考辨疑义,类多闲记轶事”的作品特点及对“芦浦本乎回浦,无据,殊非真切”说法的点评予以认可,赞赏杨谦度“其说甚韪,叹服拜服!”并在信中回复读罢《绿云居集》后予以寄还。
可见,杨谦度对刘昌诗作盐课司于南监场一事,已有鲜明的立场——一个“诋”字,已经告诉后人早在宋时就已有过关于此书与“芦浦”的争议;一个“诋”字,可见张隽对杨谦度反驳刘作立场的认可。事实上,这段话透露出来的信息已非常明确,刘昌诗及其芦浦笔记,与南监无关!而潘杨二位前辈,仅凭“刘昌诗作盐课司于南监场,撰《芦浦笔记》十卷”来说明此书与南监或者芦浦有关,由此确认刘昌诗生前任职芦浦盐场,或者认定他在此撰写《芦浦笔记》。这种观点与张隽原文意旨明显背道而驰,实乃误矣!
如果凭着三篇有缺陷的文献记载来认定在苍南芦浦,则显然牵强。有清一代大儒阮元,曾撰写《石渠随笔》,其“石渠(里)”也曾是苍南芦浦的旧名,难道也可依此认定此书撰于苍南芦浦吗?
四、“芦浦”或为刘昌诗办公场所的雅称
刘昌诗《芦浦笔记》中的“芦浦”,就他自己所言,“乃廨宇之攸寓云”,即办公场所的一处房子。再看同治《清江县志·文苑·刘昌诗》一文,称江滨有庐州,相传唐庐肇读书处。昌诗结屋于此,曰庐浦草堂,著书其中。如果当地事实上存在过“庐浦草堂”的话,那么由此“庐浦”到“芦浦”的演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也是此志以“庐浦笔记”一名见载的缘由,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芦浦”仅是刘昌诗办公场所或是起居之屋的雅称而已。当然,这也只能存疑,毕竟刘昌诗在当年也仅是一名位卑职轻的小吏,并没有太多的视线投向他的身世,因此也就难以有丰富的史料来证明,至少目前笔者还没有找到更多的依据,尚待以后做进一步的探查。在此,本文仅是以大胆而简单的一点设想抛砖引玉,以求方家的不吝赐教。
最后做一点补记。笔者在查阅刘昌诗的生平经历时,发现了一个有点意思的现象——光绪《六合县志》有刘昌诗小传。列刘传之后,是一位叫陈容的长乐人(字公储,自号所翁,端平二年进士),他任过临江军“通判”(“军治”在清江,即刘的老家),也曾在六合县任过知事。宝祐元年 (1253),他来任平阳县令,颇有作为。在此前的淳祐七年 (1247),是一个叫朱时兴 (或朱宋兴)的平阳人,曾任六合县令。此外,在与刘昌诗同年中毛自知榜的10余位温州籍进士中,有后来升任礼部尚书的吴杜 (乐清人)与官至刑部尚书的赵立夫 (乐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