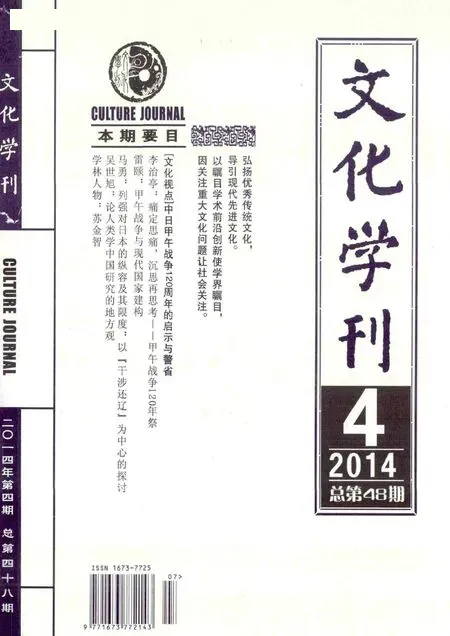论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地方观
吴世旭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中,民族志方法和国家与社会理论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前者以可靠的田野作业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经验素材,后者则以精到的见解丰富了理论探讨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但它们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地方(place)这个基本概念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注,暗含二者之中的不同地方观及其学术建构,是导致这种理论后果的根本原因。现象学家凯西 (Edward Casey)对地方进行的长时段“知识考古”表明,相对于较晚出现的空间 (space)概念而言,地方具有超越历史的先在性,而从鲜活的地方之中抽象出来几何学空间,是在现代性的颂扬下才成为知识生产和社会建构的关键概念的。[1]这个理论见识对于审视上述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并有助于激发新的问题意识和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理论拓展。
一
在诸如村庄这样的小地方中获取据以施展学术想象力的经验素材,很长一段时间都构成了人类学中国研究的不二利器,至今未衰。这种潮流有着复杂的历史与学术渊源,[2]而对民族志方法的运用是其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民族志与生俱来的空间化地方观及其影响,也随之渗入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之中。
小地方与大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特殊问题,它在总体人类学中同样是一个核心主题。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认为,社会人类学的本质在于处理整体,但自从民族志方法发明以来,整体就逐渐以某个地方文化的形式出现,从而构成了一种“人类学的岛屿”。[3]作为现代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民族志方法的形成与马凌诺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有着莫大的关系,正是他首先将其创造性地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之中,并对之做出了全面而细致的阐述,[4]从而确立了其在现代人类学中的基础地位,使田野作业乃是人类学者的“成丁礼”成为一种基本的共识。这种经典民族志方法的本质在于,把意蕴丰厚的地方看作是现实生活的容器,以使致力于从生活中萃取抽象的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家展开实地的田野作业,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把地方等同于进行田野作业的地理空间,体现出了人类学对地方一厢情愿的主观建构,这种建构的思想源头恰恰来自于凯西所言的由地方到空间的现代知识转变。单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将地方加以空间化处理似乎无可厚非,然而,这却对理论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地方自身理论价值的严重忽视。
尽管马凌诺斯基发明的民族志方法后来受到了众多批评,但其将地方空间化的理论倾向,非但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愈加严重。例如,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在强调“深描”之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时指出,以为能够从所谓“典型”村庄中发现社会、文明或宗教本质的观念,显然是一种谬见;他认为,“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他们在村庄里作研究”,人类学家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研究不同的事物,但却不能把地方作为研究对象。[5]又如,阿帕杜莱 (Arjun Appadurai)对经典民族志的批评指出,作为田野作业的地点,地方已经逐渐成为人类学特定理论的隐喻,构成了一个压制“多种声音”的圆形监狱,地方问题因此最终乃是一个关乎权力的问题;[6]他认为民族志的生产应该注重对多种声音的呈现,并在任何一个地方充分挖掘研究主题的多样性。[7]不管是格尔兹的“深描”还是阿帕杜莱的“多种声音”,都试图在小地方与大社会的题域中找到突破马凌诺斯基经典民族志方法的可能途径,但他们所运用的地方概念暗含的仍然是现代知识中空间化的地方观,而正是对“多点民族志”的强调,使这种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同时也于无形之中助长了忽略地方自身理论价值的理论势头。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对地方自身理论价值的漠视,不仅与长时段的观念史息息相关,而且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发展紧密相连。人文地理学家阿格纽 (John Agnew)对地方在社会科学中的“贬值”所进行的学术史考察表明:一方面,由于保守的社会科学把地方和共同体 (community)联系起来,并将从共同体到社会看作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模式,所以导致地方研究胎死腹中,而作为“冷战”中意识形态武器的现代化理论又在地方的棺木上加了一颗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则将商品化的力量绝对化,并认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必然会破坏地方的社会意义,因此看不到地方在现代社会与社会科学中存在的余地。[8]如果说保守的社会科学是在一种怀旧的忧郁中悲叹地方的逝去,从而失去了拯救地方的学术勇气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则是在一种怨愤的激情中欢呼地方的没落,从而剥夺了地方研究的学术生命。虽然人类学更多地是以非西方社会为对象,并主要体现为对和现代社会相对应的共同体加以研究,表面上看似乎完全不同于整体社会科学的理论取向,但是,这种研究本身恰恰是以“共同体-社会”的理论模型为前提,并带着一种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所说的“热带的忧郁”[9]投入到对现代社会的省思之中。正是在这种理论倾向的主导下,民族志方法在人类学的研究中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并沿袭了地方是生活之容器的理论假设。
与整体人类学一样,民族志方法也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与生俱来的空间化地方观同样影响深远。就本土人类学而言,空间化的地方概念最初是潜伏在由community翻译过来的“社区”一词背后,进入本土人类学的研究当中的,并在民族志方法的影响下成为理解社会的基本认识单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学派”的倡导者和领军人物吴文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对社区方法进行的表述中强调,通过特定社区的研究可以了解抽象的社会,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到的”。[10]吴文藻开创的“中国社会学派”希望通过对社区研究的累积与比较来达到对抽象社会的整体认识,暗含其中的同样是“共同体-社会”的理论模型,其背后的主导观念也来自于现代知识,特别是其中空间化的地方观。
尽管在社区方法的指导下,涌现出了诸多中国本土学者撰写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类学著作,但是,对于社区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人类学者却持有各不相同的见解。对社区研究方法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马凌诺斯基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在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所作的序中,他一方面强调中国“有着最悠久的没有断过的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汉学家的历史工作应该“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另一方面又认为费孝通对一个小村落的研究使“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并揭示了“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11]利奇 (Edmund Leach)在评论中国本土学者的四本人类学著作时,也对《江村经济》给予了肯定:“与所有社会人类学的优秀著述一样,其核心内容是关于关系网络如何在一个微型社区中运作的细致研究,”并认为这种研究没有或者不应该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其意义在于它们本身。[12]虽然利奇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费孝通的学术追求,但他显然并不排斥社区方法在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应用。与马凌诺斯基和利奇不同,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明确地提出了对社区方法的质疑,认为它对于研究复杂的文明社会并不适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应该借鉴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探讨社会运作的机制。[13]尽管弗里德曼对人类学中国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但他的忠告并未导致人类学家对民族志方法的放弃,相反,随着人类学研究在香港与台湾地区的展开以及中国大陆的开放,以小地方为单位的研究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而本土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的复兴,则使小地方更多地出现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之中,并产生了大批的“村庄民族志”。在这个过程中,以小地方来反映复杂社会的方法问题进一步得到了深入的讨论,[14]虽然依旧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却大都不再停留于社区方法是否适用的争论上,而是追问如何通过小地方来研究大社会。
不管怎样,社区方法与经典民族志方法对地方的理解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把地方等同于生活的容器,并且将之视为一种人类学的常识。由于二者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和整体人类学一样,这种空间化地方观的负面影响也深深地浸入到了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理论传统之中。
二
“中国社会学派”采用社区研究方法是为了认识中国社会,对社会整体以何种形态存在则似乎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其理论探讨也暗含着不同的可能性,然而,在西方学术话语的支配和影响下,这种弹性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压缩了。当弗里德曼带着人类学家从简单社会中建构的理论成果进入文明中国的研究领域时,国家的存在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冲击力,而他引入的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也深刻地影响了很多人类学家的中国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地方不仅作为生活的容器为人类学家提供了田野作业的地点,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观念隐藏在society即“社会”一词的背后,成为与国家相对的抽象存在。地方相对于国家存在的观念并非人类学家的发明,而是本土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产物。中国社会中心与边缘的政治结构形塑了中央与地方的观念形态,并使之成为中国人认知社会的一种文化常识。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主导下的人类学中国研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历史,并以不同的方式对之加以重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空间的观念成为不同论述的共同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地方自身的理论价值。
弗里德曼通过宗族组织的研究来呈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边陲状态、水利与稻作生产共同促成了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的发达,宗族组织的现实形态可以归纳为从A到Z的一系列理想类型,这些宗族组织不仅相互之间存在争斗,同时也联合秘密会社来对抗作为其共同敌人的国家。[15]在弗里德曼早期的宗族研究中,社会空间意义上的地方隐含在宗族与国家的对立结构之中,并未得到直接的关注,但是,随着宗族研究的深入,他意识到了应该对地方、地区和社会组织的社会地形学如何被纳入到官方地图中保持敏感,并认为行政地图的权限规划与社区及其群体的构造大致甚至完全吻合,而地方民兵系统的出现则把社会地图引入了官方地图。[16]这里所言之地方和地区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中与国家相对应的“基层社会”,而与很多海外汉学家一样,弗里德曼在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中来看待地方的学术倾向,很明显是受到了中国本土文化常识的影响。施坚雅 (William Skinner)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认为“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种空间层次的认识”,并把这种空间结构称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17]施坚雅对中国本土文化常识的学术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暗示着人类学中国研究可以存在不同的理论可能。遗憾的是,他的“区系理论”在强调经济力量对中国社会结构具有根本性支配的同时,认为非正式的市场区系与正式的行政区系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二者并非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在社会空间上相互兼容,这实际上无非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中增加了对经济因素强调,仍然没有摆脱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的根本影响。弗里德曼和施坚雅都是在宏观上来研究中国社会,前者把地方抽象为与国家对立的存在,后者则把地方置于经济区系的网络节点上,其核心观念都是把地方等同于社会空间,从而使地方自身的理论价值埋没在社会结构的宏大理论之中。
尽管弗里德曼和施坚雅之后的人类学家更多地是在小地方做研究,但是,这种微观的社区分析同样大都是以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为根基,并通过小地方的研究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地方自身的理论意义。王铭铭在这些研究中辨识出“行政空间理论”和“宗教与象征理论”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18]行政空间理论强调地方的政治角色,从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角度来思考地方,视国家为一种政治的、全民的、军事化的力量,国家对基层体系的建构,目的在于控制社会,基层社会因此处于消极的、被动的地位。宗教与象征理论则注重当地观念,从基层社会回应国家的角度思考地方,认为,基层社会通过象征自主地建构地方。但是,这种自主建构同样与国家紧密相关,比如,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认为基层社会的自我表述中潜藏着一种“帝国隐喻”的逻辑;[19]桑高仁(Steven Sangren)则认为,一方面,基层社会在通过进香仪式削弱了自身稳固感的同时,也突出了地区权威和王朝权威的功能,[20]另一方面,传统阴阳宇宙观的阶序化使基层体系的阶序化拥有了合法意义,国家因此有足够能力在民众意识中确立支配权。[21]在王铭铭看来,行政空间理论对特定地方的普通民众如何看待地方关注不够,而王斯福和桑高仁则在此处取得了成功,并发展出了可以用于理解民间文化观念的理论模式,但是,在认为民间社会的文化观念乃是模仿了官方关于基层社会阶序化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界定方式的同时,他们仍然没有回答民间社会模仿的究竟是官方行政空间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22]
在关于泉州的“铺境”制度和“东西佛”械斗的经典研究中,王铭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铺境的研究通过把行政空间理论和宗教与象征理论糅合起来,具体考察了行政空间与基层社会的文化认同究竟在何处契合、何处分野,认为铺境既为官方提供了一种社会的空间设计方案,也提供了一种帝国的理想模式,而基层社会不仅通过民间传说和庆典活动来反映和模仿这种理想模式,而且对之加以反馈,从而使帝国模式和民间模式之间在表面的妥协下形成一种矛盾关系,前者服务于帝国的政治目的,强调的是“秩序”,后者则表达了民间社会对在晚期帝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所丧失的自主性的怀旧之情,突出的是基层社会的团结和“社区竞争”。[23]“东西佛”械斗的研究通过政治个体、时间与过程的历史叙述,探讨社会的地形学与官方的地图之间互动的具体方式,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械斗本来是基层社会的一种节庆活动,这种活动以不同的文化意义自主地形塑了基层社会的阶序模式,但是,在政治个体的手中,却成为官方控制社会的策略,并在不同的官方策略中被赋予不同的政治意义。[24]王铭铭的研究同样暗含着一种对本土文化常识加以反思的努力,然而,与施坚雅不同的是,他更强调文化象征与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单纯以政治或经济因素来解释基层社会的不足,同时也使文化与象征建构基层社会的具体方式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尽管如此,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仍然构成了其浓妆重彩之下的底色,而在对历史的重视中也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整体社会科学所秉持的从共同体“发展”到社会的基调。
很难说国家与社会理论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中形成了库恩 (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25]但它确实构成了一条清晰的主线,对诸如宗族与国家、经济区系、行政空间、宗教与象征等理论主题的探讨大都围绕这条主线而展开。尽管这些探讨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理论可能性,但国家与社会理论把地方等同于社会空间的理论倾向,也明显限制了其更具弹性的理论延伸。
三
通过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和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建构,地方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概念意涵。前者把地方等同于容纳社会生活的地理空间,基于人类学常识在方法的层面上强调其作为社会与文化表演场所具有的民族志价值;后者则把地方抽象为相对于国家而存在的社会空间,基于中国本土常识在理论的层面上强调其作为政治与意识形态场域具有的分析价值。或许对于很多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家来说,民族志方法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国家与社会理论也与中国的特征相契合,但是,从更普遍的历史角度来看,地方并非是人类学建构出来的田野作业的地理空间,亦非相对于国家而存在的社会空间,作为人类生活中一种基本范畴,地方自身具有更根本的文化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西的地方研究对于人类学的启发意义,显得弥足珍贵。这种启发首先在于使我们认识到,对地方的空间化处理,并非是人类学家有意为之,而是现代知识的潜移默化所致;而经由人类学的自我反省,进一步的判断在于,从地方到空间的历史转变本身也是社会与文化过程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充满了人类学据以扩展其理论领域的多种可能。
对于凯西的哲学论述,似乎并未得到人类学家足够的重视,例如,王斯福认为,凯西在坚持地方的动态性方面值得肯定,但却不解于他为什么把存在当作哲学沉思的原始对象,同时把身体作为衡量世界的起点,并以澳大利亚土著和汉人的宇宙观为论据,得出了他的研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 (anthropomorphism)缺陷的判断。[26]实际上,凯西关于地方的知识考古和哲学思索,并非是意在探讨地方的“动态性”,而是通过地方与空间的观念史追溯,对二者加以区辨,以此来指出地方超越历史的先在性。地方之所以超越了历史,是因为它并不取决于人的存在与否或以何种方式存在,而正是这种先在性使人对地方的感知成为可能,通过和身体的相互作用,地方便具有了方向性。[27]凯西关于地方的哲学研究并非无懈可击,但他对地方与空间观念做出的区辨及其观念史解析却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斯福对凯西的批评就显得有点南辕北辙了。虽然现象学还原体现出了鲜明的去文化和去社会的特征,但却正是其获得理论洞见的根本依凭。现象学还原看似具有反社会与反文化的倾向,实则是以去社会和去文化的方式“朝向事情本身”,并未否认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存在及其意义;而凯西的研究表明,空间观念不过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它是对人类经验到的地方加以抽象的结果。虽然不同文化中的宇宙观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空间的观念,但同样是地方进入历史的具体表现。王斯福进行学术批评的严肃态度是毋须怀疑的,然而,对现象学的有限排斥却也难掩人类学的些许“傲慢”,以致无法在常识的迷雾中看清地方的全貌,而他把地方营造(place-making)看作是一个中心化的过程,显然受到了汉人社会中心与边缘的政治结构及其造就的中央与地方的文化常识的影响。
尽管如此,但笔者并不认为直接面对现象学意义上的地方应该成为人类学的选择,相反,在充分认识到地方观念史之中必然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展开理论探讨,才应是人类学的分内之事。现象学研究并不在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上关注地方文明化的具体过程,而以往人类学对地方的空间化理解,则通过对地方的无意识拆解,使具有丰盈之态的地方概念转化为干瘪的空间概念,从而无法意识到地方本身的理论价值。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地方概念之所以具有理论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先在性,而是其由先在进入历史的过程。换言之,如果说现象学是经由对社会与文化的去除来还原地方的原初意义,那么,人类学则应将原初意义上的地方回复到历史之中。现象学洞见到了地方超越历史的先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存在于历史之外,相反,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地方不可避免地会进入历史。在进入历史的过程中,地方被披上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外衣,成为人们展开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从而使自己获得了社会生命,并在历史的过程中处于不断的营造之中。这不仅构成了地方在人类学研究中具有合法性的基本资质,而且构成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地方超越历史的先在性是毋庸置疑的,现象学把复数的历史去除掉以朝向事情本身,把丰富的历史还原为人与物,而人类学对社会与文化的倚重却在此处语焉不详,似乎社会与文化是自己生成的;只有认识到地方的先在性并将其重新纳入到历史之中,社会与文化的概念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性,因为是人与物的互动开启了历史,社会与文化的源头在于地方的历史化,二者不过是丰盈地方的一种方式,因此,如果说现象学探究的是“地方为何”的问题,那么,人类学关心的则是“地何以方”的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尽管民族志方法和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它们对地方的空间化处理却在理论上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如果带着地方概念及其问题意识,重新回到人类学中国研究之中,那么,无疑会有助于以往研究的反思和理论领域的拓展。